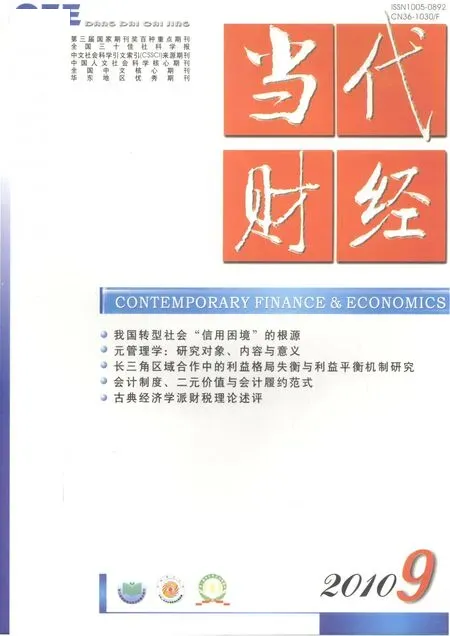我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基于博弈论模型的分析
洪 玫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金融学院,上海 201620)
我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
——基于博弈论模型的分析
洪 玫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金融学院,上海 201620)
以博弈论为基础构建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用缺失问题。通过“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推导,研究发现,实现信用交易守信的途径主要有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在中国由弱流动性社会向强流动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应信用交易的守信保障机制并没有同步建立,这是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之所在。
转型社会;信用困境;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博弈论
一、引言
所谓“信用困境”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失信行为泛滥的现实,这一现实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故称之为“困境”。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演进过程,虽然体制建设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但是一些思想意识转变却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转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还没有在短期内完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失信行为还比较普遍,人们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信用规则行事。
社会的“信用困境”可以说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角债”问题,到后来的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再到近期的资本市场造假丑闻频出、地方政府信用形象不佳。虽然失信行为的阶段特征不同,但是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成立的,那就是我国目前尚未走出社会的“信用困境”。针对上述信用问题,本研究将以博弈论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深入挖掘我国当前“信用困境”的内在根源。
二、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守信问题最为广泛的研究是在产业组织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之间的战略博弈。所不同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与前提假设下,企业之间的博弈结果往往出现巨大差别。例如,古诺模型、波特兰模型等经典产业组织模型在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后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国外有关博弈论模型应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很少将博弈论模型引入较为宏观的信用问题分析,或者说国外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对宏观信用状况分析的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因此,国外的博弈论方法当前多结合信息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运用于机制设计等微观研究领域。
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信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首先,很多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信用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等)强调“信用”本身的重要性(茅于轼,1999;郭红玉,2002;刘拥军,2003)。[1-3]部分文章通过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信息不对称)试图给出信用缺失的一种解释(肖建,2003)。[4]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对于信用问题的分析多处于概念阐述阶段,即使将信用问题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只停留在概念引入阶段,缺乏规范的数理分析。从2006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模型来分析信用问题,尤其是解释当前中国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5-8]这些研究文献存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不拘泥于微观领域,而多侧重于宏观领域,这也许更多是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还都是将比较基础的博弈论模型引入信用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博弈双方既得利益的策略设计过于简单,导致博弈模型推导比较简单,博弈分析的结果也比较模糊,很难将与社会信用机制相关的制度因素作量化分析。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一方面,不仅全面地引入了博弈论的基础模型和多期模型,而且较为详细地定义了社会信用制度的相关变量,使得模型的推导过程更为规范,其结论也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述博弈论模型的时候,将“社会流动性”变化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形态比较的一个线索,通过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结合博弈论模型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信用困境”是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相关信用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产物。本文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不足,那就是博弈论模型仅限于完全信息,对于信息不完全的更为复杂的博弈模型,将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引入,不断充实博弈论模型对社会信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三、“信用困境”的博弈论分析——“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一)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构建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信用这个概念进行适当的阐述。信用的本质是衡量人们对契约(包括正式的有形的合同和非正式的无形的合同)的遵守程度。从单个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是否遵守合同可能与个人的天性和教育背景有关,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对合约的遵守情况则表现出一种规律性趋势,或者可以看成是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如果这种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均衡状态,符合纳什均衡的基本特征,即没有一个参与者在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会有单方面改变战略的激励,那么,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则是整个社会所体现出的共性的制度安排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要深入分析信用问题,我们离不开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在介绍具体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模型的基本假设,这样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深入理解。
假设(1):模型中作出守信或者失信决策的行为主体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该模型中的信用决策主体是利己主义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信用决策主体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假设(2):基于以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需要具体探讨关于不同决策的成本、收益问题。首先,守信的决策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守信的成本会大幅提高。当然,守信同样会带来收益,这种收益相对于守信的成本而言,往往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可以表现为良好的个人信誉、良好的商誉或者是良好的政府公信力等。同时,失信的决策也是有成本的,这种行为模式的成本与失信带来的收益相比也是趋于长期化的。失信带来的这种长期化成本相对于守信的长期化收益而言更加难以消逝,一旦失信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很可能像阴影一样,让人挥之不去,无法摆脱。同样,失信也会带来收益,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这种因失信而产生的收益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也更加趋于短期化。因此,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信用行为决策简单地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守信或者失信的成本收益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守信或者失信的行为决策问题也就成了一个衡量和比较守信、失信的净收益问题,带来更大净收益的行为模式往往更加有可能成为人们最终的信用决策选择。
(二)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1.模型的推导
(1)A表示因为守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这里我们称之为“信用价值”,即我们现实中通常可以观察到的信誉、商誉、公信力的无形价值。这种守信带来收益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
(2)E表示因为失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上文关于模型的基本假设已经谈到,这种失信带来收益在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同时更趋于短期化。
(3)β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即失信行为被惩罚的严厉程度。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通常而言,β>1。从下文的模型结论可以看出,如果β<1,那么失信行为将会成为人们的最优选择。
(4)P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力度,即失信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整体社会管理体制可以有效监管社会全部交易行为的P倍(0<P<1),即如果交易的一方选择了失信行为,那么他(她)有P(0<P<1) 的可能性被社会监管机构发现。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守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失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break faith)=E×(1-P)+(E-β×E)×P=E(1-β×E)
(2)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无法得到失信带来的额外收益,其双方的整体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break faith) =0
(3)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守信的决策,那么守信者因为守信可以带来良好的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收益,同时因为守信也让渡给交易对方失信者E的利益,因此守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keep faith) =A-E+E×β×P
(4)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均做出了守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可以因为赢得并维护了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长期性收益,交易双方的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keep faith)=A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分析模式虽然需要依靠很强的理论假设作支撑,与现实情况相差较远,但是,这种分析模式比较清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图1)。
考察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守信策略能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那么必须要满足条件:


图1 单期信用行为博弈收益矩阵
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

考察这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失信策略也可以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如果博弈满足条件:

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

通过上述守信均衡和失信均衡的条件比较,我们发现实现守信均衡的核心条件在于两个:监管力度βP是否大于1,信用价值A与E(1-βP)的大小比较。
2.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简单变形
为了使得上述模型更能反映现实世界情况,我们这里引入“补偿机制”的概念。假定α代表守信补偿比例,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以一个什么比例转化为交易中守信者的补偿。从对补偿比例α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补偿比例的值域应该介于0到1之间。上面分析的是一种极端情况:α=1,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全部用于补偿守信者的损失。引入守信补偿比例α的概念之后,图1中的博弈模型可以变化为图2。
(1)当α=1(全补偿),即我们上文分析的博弈。
(2)当α=0(无补偿),该博弈的解为:当A>E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 A<E-E×β×P 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失信,失信);
当 E-E×β×P<A<E,上述博弈有 3 个纳什均衡解,其中一个为混合策略均衡,另外两个为纯策略均衡(守信,守信)和(失信,失信)。
(3)当0<α<1(部分补偿),该博弈的解与情况(2) 的解相似:
当βP>1或者0<βP<1且A>E-E×β×P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0<βP<1且 A<E-E×β×P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 (失信,失信);
当 0<βP<1 且 E-E×β×P<A<E-E×β×P,上述博弈有 3 个纳什均衡解,其中一个为混合策略均衡,另外两个为纯策略均衡(守信,守信)和(失信,失信)。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守信补偿比例α基本的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守信者的补偿力度越大,即α的数值越大,信用交易者就越有激励在交易中守信,反映在上述博弈论模型中,即出现(守信,守信)为唯一均衡解所要求的条件越宽松。
3.模型分析小结
从上述简单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保证信用行为博弈出现(守信,守信)的唯一均衡解主要依赖于两类条件:(1)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反映在模型中为βP,即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如果交易的一方选择了失信行为,那么他(她) 有P(0<P<1)的可能性被社会监管机制发现并进行惩罚。(2)市场自发的利益调节机制,即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与失信行为带来的收益E之间的一个综合比较。
以α=1(全补偿)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为例,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足够大,能够满足βP>1的条件,使得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0,那么根据模型的假设,信用交易行为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不能使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0,即0<βP<1,此时依赖市场利益调节机制,模型中的信用交易行为仍然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其条件为:A>E(1-βP)。当0<βP<1,且A<E(1-βP)时,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就只能出现唯一均衡解(失信,失信)的局面。

图2 引入补偿机制的单期信用行为博弈收益矩阵
(三)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侧重于分析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对于信用交易者的行为模式的影响。通过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复博弈(信用交易)的前提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即在单期博弈的守信收益不够大,即A<E(1-βP)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实现(守信,守信)的博弈结果。
在推导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模型的一个关键性假设。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在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中, A被视为守信的长期收益,而且根据现实情况,守信带来的收益一般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一种比较极端同时又比较贴近现实的情况,即每次博弈中如果信用交易者做出守信的行为,那么他(她)将得到一个A的守信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只能在多期博弈的最后一期全部实现。因此,在两期博弈中,即使是博弈双方在第一期均保持守信,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在第一期的收益也均为0。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考察两期博弈的简单情况。
第一期的博弈模型见图3。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守信,守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图4。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失信,失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图5。简单起见,我们在这个两期模型中假设贴现因子为1,即第二期的收益贴现到第一期之后没有贴现损失。为了更加贴近实际情况,我们假设在多期博弈过程中,考虑信用交易者采取如下的带有“报复性”的行为策略。自己在第一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守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失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失信。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可以证明,当A<E-E×β×P,2A>E-E×β×P,两期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都是守信。
首先,我们证明,当信用交易的一方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的另一方的最优策略也是采取上述策略。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者甲也采取上述策略,则甲的总收益为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失信,那么甲知道遵循上述策略的交易者乙会在第二期失信,则甲在第二期的最佳策略应该为失信,因此甲的总收益为E-E×β×P<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守信而在第二期失信,甲的总收益为 E-E×β×P<2A。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交易者乙遵行上述策略的前提下,交易者甲的最佳策略也是遵循上述策略,反之亦然。这说明,上述策略是一个纳什均衡策略,其均衡结果为“双方在两期都守信”。
如果把上述的两期模型推广到N期,根据上面的逻辑,我们不难证明,当A<E-E×β×P,N×A>E-E×β×P 时,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一个纳什均衡结果。这一结论表明,即便守信的单期收益很小(A<E-E×β×P),只要守信的总收益足够大 (N×A>E-E×β×P),在多期博弈模型中,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一样可以实现“守信”的行为均衡。

图3 多期信用行为博弈第一期的收益矩阵

图4 多期信用行为博弈第二期的收益矩阵

图5 多期信用行为博弈第二期的收益矩阵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结论
1.实现信用交易出现守信结果的途
径主要有两条: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
2.第三方监督者通过提高对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使得失信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利益上的吸引力,进而使得失信行为消失。可以说这是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
3.当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不能被满足时,即0<βP<1、E-E×β×P<0时,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也可以让市场信用交易行为出现守信均衡的情况。但是相对于上述第三方监督者的监督惩罚力度的“强条件”而言,这种市场利益保证可以视为一种“弱条件”。
在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只要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足够大,即A>E(1-βP),那么信用行为博弈的结果可以出现(守信,守信)的情况。如果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不够大(A<E(1-βP)),那么信用行为博弈只能以(失信,失信)的失望结局告终。
但是,在多期信用交易(博弈)的情况下,这一条件可以放松,如果单次博弈守信带来的收益不够大(A<E-E×β×P),但是,多期博弈的总收益足够大(N×A>E-E×β×P),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可以说,在多期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要求变得更加宽松,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可能性增大。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应用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应用上文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分析结论,同时引入“社会流动性”这一概念。这一部分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社会形态社会流动性变化和相应信用制度的变化,可以导致不同社会形态满足不同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结论性条件,进而导致不同社会形态出现不同的社会信用状态。通过不同社会信用状态的比较分析,挖掘出当前中国转型社会条件下的“信用困境”的根源。
(一)传统社会的信用制度安排——“儒商秩序”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的儒家信条在整个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商业并不能作为社会的主流产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商业活动中的高级交易活动——信用交易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普遍。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商业行为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传统社会发展到16世纪左右,与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一样,传统社会的这种商业崛起趋势不断明朗化,并积极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儒家传统“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逐渐松动,人们逐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即只要利义一致,牟利也符合道德规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传统社会后期出现了“利以义制”的新儒家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在这个传统社会局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山西商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是宣传新儒家商业思想的理论先导,将自身的行为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合理化,而且切身履行着“利以义制”新儒家商业信条,不仅实现了晋商足迹遍布天下的辉煌,而且实现了“汇通天下”这个传统社会的金融梦想。[9-12]此处以晋商票号为例,详细解读传统社会弱流动性条件下,信用制度安排如何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
虽然晋商票号不仅限于本地经营,还不断追求着“汇通天下”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晋商中的各个商业家族,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弱流动性状态,这种人员的弱流动性状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这种弱流动性状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票号总号的稳定性,(2)票号背后家族关系的稳定性,(3)晋商票号历史传承的稳定性。[13]这种时间和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为传统社会实现稳定且良好信用行为提供了有效的现实保证。首先,基于传统社会下“人治”模式,对于信用交易行为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处于“真空状态”,不仅相关法律接近空白,而且缺乏保证相关法令实施的制度性安排。保证良好社会信用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幸运的是,这种利益机制在“弱流动”社会条件下,通过小范围内重复交易实现了信用信息在局部范围内自然充分扩散和信用交易带有多次博弈属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了传统社会良好信用状况。
而且,传统社会实现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策略能成为博弈双方的均衡结果是一种相对稳态的博弈结果。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就会生发出广泛的“集体惩戒机制”(即人们会排斥不诚实的人,并对发现别人不诚实而不排斥的人进行追究),这使人们不易于打破这种惯例,这就是Maynard Smith所说的“演进稳定性”。[14]它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维护,每个成员都会自觉遵守——无论他出于习惯、模仿还是理性计算的动机。因此,我认为传统社会的信用秩序有着很强的自我维系能力和自我延续能力。
(二)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秩序——以美国为例
这里谈到的现代社会,是针对上文的中国传统社会和当前转型社会的概念而来的。现代社会既是指在农业社会长久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工业社会,也是指转型社会的转型目标。这部分以美国为例,具体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状况,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扩展。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这种“法治”取代“人治”的根本转变填补了传统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监督惩罚能力的缺失,大大提升了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惩处力度。这里所说的信用监管制度包括行业自律的内容,但是主要以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持。美国相继颁布的《个人信用保护法》、《信用平等机会法》、《公正贷款对帐法》、《破产法》、《个人信用限制计划》等法规,规范了信用活动。[15]不仅如此,美国多年的司法成功实践基础使得美国可以有效地执行相关信用法律。总之,有效的法律系统和高效的现代监管体系有效地保证了现代西方社会守信均衡的出现。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在信贷社会可以实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情况下,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体制还可以保证“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均衡“弱条件”的实现。这无疑为保证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增加了一个制度性保险。现代西方社会完善的国家征信体系满足了强流动性社会的信息扩散特点,在关键信用信息的统一搜集和统一发布制度框架下,现代西方社会交易者的交易行为的强流动性伴随着信用信息的强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社会较为普及的信用评级系统为充分流动的信用信息进行了科学的加工,使得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信用信息不仅能够充分流动,而且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现实信息。这样,从“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框架来看,守信带来的收益A将被放大,因为良好的信用信息可以被更多的潜在交易者获知;同时失信带来的收益E则很难实现,因为在潜在交易者比较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带有失信历史的人进行交易。“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E(1-P)) 就很可能被满足。
(三)现代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
结合前文分析不难发现,贯穿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分析主线是“社会流动性”的提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不仅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分析的基本背景,对于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危机根源的分析,社会流动性这个基本背景显得更加具有解释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转型社会。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双重转型”,即同时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双重社会转型;既要完成传统工业化的历史遗留任务,又要追赶信息化的步伐。伴随着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主体形态正在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由个性”的个性转型。这是因为,社会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社会现代化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人的现代化。同时,这种双重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还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化伴随下的双重现代化进程中,在双重现代化推动的人的自由个性现代化进程中,两股力量正在合力推进社会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这种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以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习惯为起点,正在向现代社会靠拢,但是就在这个制度“破”、“立”交替的过程中,一系列制度转型问题凸现出来,直接导致社会信用危机的出现。
具体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原有的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被打破,原来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本背景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契约裁定渠道已经限制了交易扩大的客观需求,但是整个社会建立起如现代社会那样的完善的社会信用系统又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以及财力和物力,更需要大量的时间让人们接受和适应新的全民征信制度。这种背景下,社会一方面不相信原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借助于全民征信系统,无奈之间,社会自发选择了一些带有典型权宜之计意味的预防失信的制度。首先,社会部分地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亲缘商业模式,以家族企业为基本经营模式,试图模仿传统社会依靠家族信任来避免信用缺失问题。不可否认,家族信任作为传统社会维系信用的基本模式,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交易的范围不断向纵深延伸,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漏洞百出、难以为继。其次,传统社会亲缘、地缘信用模式在转型社会的另一个演变就是“熟人经济”或者称“关系经济”,这种模式无非是亲缘、地缘信用模式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现实的一个变体,以关系为纽带,力图在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进而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但是,这种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模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简陋,以至于在现代社会浪潮袭来的时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和不知所措。
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反映在“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社会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和威慑作用不大,守信均衡的“强条件”(E-E×β×P<0)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在缺乏完善的社会征信体制和社会信用评级体制的情况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带有明显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变体特征和“权宜”特征,因此,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E(1-P))也难以满足。可见,依据“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逻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出现信用危机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论
理论上讲,社会出现守信均衡至少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法治让位人治,“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薄弱;但是在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下,基本可以满足“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这一条件,实现弱流动性条件下的局部守信均衡。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虽然社会流动性大大提升,但是其完善的立法体系和高效的司法制度使得“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可以在强流动性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进而保证守信均衡的实现。同时,现代西方社会借助于强大的征信网络和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同样可以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利益调节机制”的作用,使得现代西方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更加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典型的转型期,“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导致“信用困境”问题成为困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顽疾”。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弱流动性状态被打破,强流动性的社会中,保证传统社会的守信均衡的制度安排在转型社会中的功效可谓捉襟见肘,甚至逐步走向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系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任务,目前尚未建立起西方社会那样与强流动性社会相匹配的信用法律制度、征信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社会的守信均衡尚需时日。可以说,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就是造成我国“信用困境”的根源所在。要摆脱当前的“信用困境”就必须要加紧完善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社会信用制度。
[1]茅于轼.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是解决需求不足的良方[J].中国工商,1999,(9):21-26
[2]郭红玉.信用概念的制度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3):25-29.
[3]刘拥军.论产权制度、市场秩序与社会信用的形成[J].当代财经,2003,(1):34-37.
[4]肖 建.诚信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3,(4):32-27.
[5]杨延超.诚信的机制构建与目标追求——以博弈论和效益—成本理论为视角[J].学术研究,2006,(2):56-60.
[6]李广晖.基于博弈论的电子商务信用风险形成探析——买卖双方之间的博弈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7,(10):36-42.
[7]张祖明.诚信生成的经济学分析——基于重复博弈的理论视角[J].经济师,2007,(3):19-23.
[8]叶蜀君.信用风险的博弈分析与度量模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9]张正明,邓 泉.平遥票号商[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10]杨艳红.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J].世界经济文汇,2002,(1):57-63.
[11]孔祥毅.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J].广东社会科学,2005,(1):19-22.
[12]张亚兰,孔祥毅.从山西票号看信任半径、信誉均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J].金融研究,2006,(8):26-32.
[13]周建波.成败晋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14]Maynard,Smith.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5]李依霖,王树恩.基于发达国家经验构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1):46-50.
The Root of “Credit Dilemma”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An Analysis Based on Game Theory Model
HONG Mei(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Shanghai 201620,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credit behavior decision model”based on game theory and takes it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tudy the credit-lacking problem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Through the derivation with the model,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major ways to achieve credit transaction trustworthy,i.e.the third-party monitoring and penalty mechanism and the market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weak mobility to strong mobility,there is no appropriate credit security mechanism established simultaneously for credit transaction;this is the root of“credit dilemma”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credit dilemma;credit behavior decision model;Game Theory
责任编校:沐 梓
F224.32
A
1005-0892(2010)09-0005-09
2010-03-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JL011);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J51703)
洪 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信用管理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