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怀英书法及其篆书艺术之创新
文/王守民
一、党怀英的交友及书法审美观的形成
党怀英(1134-1211年),字世杰,号竹溪,泰安人,宋太尉党进十一世孙。大定十年(1170年)年及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历汝南县尹、翰林侍制、国子祭酒、翰林学士承旨,谥文献。党怀英历经世宗、章宗两朝。他的才华得到金章宗的赏识,使其掌诏告并主修《辽史》。党怀英在金代政坛、文坛都居于重要位置。作为一个文人书家,党怀英的交往圈子十分复杂。他在遗留下来的石刻之中,向我们透漏出他的交往圈的一隅。
刘瞻,字岩老,亳州人。他是党怀英的启蒙老师。《中州集》卷三“承旨党公”小传:“少颖悟,日授千余言,师亳社刘岩老,济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1]刘氏的交往也十分广泛。施宜生、王竞、刘迎等人也与刘瞻相友善。党怀英在刘氏处接受的是宋代汉人教育。
辛弃疾,党怀英与辛弃疾的交往是在刘瞻处。后来二人又都同师蔡松年。《宋史》卷四百零一《辛弃疾传》中写道:“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仕金,辛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2]大定元年(1161年),二十八岁的党怀英与辛弃疾在登上大丘痛饮之后道别,二人从此各事其主,都建立了功业。
王去非,山东平阴人。他是金代中期儒学的代表人物,其门生遍于朝野。党怀英以其为师尊之。党怀英篆额、王去非撰文、王庭筠书丹的《博州重修庙学记》,足以证明了党怀英与王去非的关系非同一般。王去非去世后,党怀英还亲自为他撰《醇德王先生墓表》(《金文最》卷89),足见党氏对他的尊重。
赵沨师从王去非,应该与党怀英很早就认识了。二人的交往是在大定25年(1185年)。因为此时赵沨尚在涿州,党怀英已经在京师翰林院。赵沨来找党怀英主要是要他撰写《王去非墓志》。党怀英在《醇德王先生墓表》中写道:“进士杨好古以泰山李守纯之状,与涿郡军事判官东平赵沨所录遗事来京师,属鄙文以表诸墓。”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赵沨经党怀英、黄久约的推荐,进入翰林院。此后主修《辽史》。在此后的六七年间,赵沨与党怀英同在翰林院,合作撰写书丹的碑刻有《宏法寺碑》、《棣州重修庙学记》、《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济州普照禅寺照公禅师塔铭》。赵沨的书法学习颜鲁公,又能化古而出新意。与党怀英相颉颃。他还被后人成为草圣。他的书法在黄庭坚、苏东坡之间。元好问《中州集》(小传)中写道:“闲闲赵公云‘黄山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超放而又似杨凝式,当处黄鲁直、苏才翁伯仲间’。党承旨篆,阳冰以来一人而已,而以黄山配之,至今人谓之党赵。”[3]赵沨的诗文与王庭筠齐名。党怀英或有不及之处。二人合作的碑刻中,几乎都是赵沨的正书书丹。如《棣州重修庙学记》、《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这说明赵沨在书法方面的地位是超越党氏的。党怀英在赵沨去世后的明昌六年,自己撰文书丹的碑刻较为集中,这一点在党怀英的书刻作品表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是他自己撰文书丹的。其后的如《十方灵岩寺记》、《谷山寺碑》、《袭封衍圣孔公墓表》、《金徂徕山六逸堂碑》等撰文书丹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在当时为皇家御赐碑文的撰文书丹者,都是各方面比较好的才俊。书写者、撰文者也不是轻易可以更换的。所以赵沨去世以后,党怀英的自撰自书的碑刻作品增多亦属常理。二人合作的最后一方碑是《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赵沨撰文在明昌六年(1195年)八月,十月过世。党怀英在承安元年(1196年)年才以隶书书写碑文,可见二人交情甚笃。
黄久约的地位不比党怀英差,至少在文坛上二人是不相上下的。根据黄久约在石刻上的留名,我们可以知道黄氏在国史院编修官赐金鱼袋,同时也是应奉翰林文字同制诰。二人应该是在同一处共事的好友。粗略统计一下,二人合作的碑刻就有:《重修中岳庙碑》(1182年)、《范阳重修文宣庙记》(1186年)、《重修文宣王庙记》(1187年)、《朝散大夫镇西将军节度副使张公神道碑》(1189年)、《重修东岳庙碑》(1189年)。明昌(1190)后,再见不到二人合作的碑刻。党怀英自撰自书的石碑出露端倪,也许是黄久约已经过世了。
党怀英生活在金代初中期的环境之中,其书法审美观的养成,是外在因素与自身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在早年的师从和后来的交友经历,成为促成他书法审美观念形成的主要基础。党怀英在书法上追求复古,注重跨越宋代,自唐以上追求古法。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夯实了他在篆书方面深入探究的基础。从文字学到篆书的取法与创新,都透露了他篆书基本功的扎实和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久的积累与积淀所致。他所交往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日后审美观念形成的促成者,他的审美趣味的养成以致创新思维的萌发,并能在这个氛围中得到很好的成长。
二、党怀英的书刻作品及流传
根据记载,党怀英的书法作品就有34种之多。在这些作品中,篆额25个,书写隶书碑6个,楷书碑刻2个,篆书碑刻1个(见下表)。党怀英书法中以篆书的成就最大。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客观上说,党怀英所处的时代正是宋(南宋)金对峙的时代,而党怀英又接受的是宋代教育。所以接触篆书的机会较多,这为他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学基础。金代书法继承辽代遗绪,在篆书方面不是十分突出。篆书的用途仅仅限于碑刻墓志中的篆额。书写者少之又少。所以党怀英就十分有机会崭露头角。篆书书体很少在碑刻中出现。当时的书刻作品中,唯有《王安石诗刻》是篆书作品,其余都是碑额。可见,篆书的实用性逐渐萎缩,篆书在金代的生存空间不大。其次主观上讲,党怀英在书写碑刻是的常用书体是隶书。赵秉文认为党怀英的隶书、正书是金代数一数二的。元好问在《跋国朝名公书》中说:“党承旨正书、八分,闲闲(赵秉文)以为百年以来无与比者,篆书则李阳冰以后一人。”[4]
党氏主观的选择并不能决定其在历史上的定位。赵秉文对于党怀英的评价还算客观。因为赵氏也是书法家,故而在对于前人的篆书水平的认定上,显然不是盲目的偏见。赵秉文认为唐代韩择木、蔡有邻之辈之所以没有能够有较高的成就,就是应为他们不通字学。反过来讲就是说党怀英对于字学是深有研究的。党氏小楷也写得相当不错。赵秉文在《题南麓书后》中说:“小楷如虞(世南)、褚(遂良),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也。古人名一艺,公独兼之,亦可谓全矣。”[5]党怀英楷书《天封寺记》(1184年)(图1)可以向我们透露一些信息。楷书的取法可以看出颜真卿、柳公权的影子。党怀英楷书未出唐人矩蠖,更多的是受柳公权影响,遒厚则过之。党怀英在楷书方面的创造性尚不能体现出来。《沂州普照寺碑》是集柳公权的字而成(图2),它是在皇统四年(1144年),在山东临沂创作而成的。此时,党怀英十一岁,家住山东泰安,与辛弃疾同学于蔡松年处。可见在金代,中原的书风还是延续宋代风尚,逐渐与南宋的审美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分野。金代崇尚唐楷的风气,说到底还是北宋复古的延续。柳公权楷书集字碑的出现,表明了与金代书法的审美趋向是注重骨力峭拔,气势遒健的意味。
党怀英能够在楷书书写上向唐代靠拢,这是时代的必然。他在楷书中加入了厚重的部分,是当时诸多书家的一贯做法。党氏的楷书确实不能算是金代书家中的突出代表。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写道:“惟党怀英楷法独宗唐人,八分学汉,篆亦在徐(铉)郭(恕先)之上,更为金书之杰。”[6]其实,在金代的大定明昌年间,师法唐代的楷书书家岂止党氏一人。马氏说法自有偏颇之处。党怀英的书法作品在清代《寰宇访碑记》(卷10)中有记载:“篆、八分、正书碑刻共十四方。”篆书作品如果是包括篆额的话,那么根据笔者统计,就不止十四方了,而是三十四方(当然包括有记载已经散佚的碑刻)。可见,在清代孙星衍统计时,由于条件的局限,肯定是是有疏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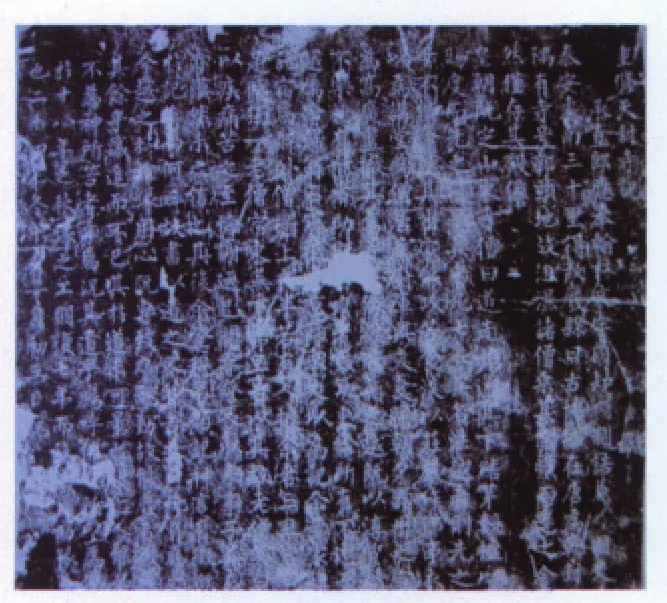
图1 《天封寺碑》

图2 《沂州普照寺碑》

碑刻年代碑刻名称篆额书丹、撰文书体记载文献保存情况大定十三年(1170年)大定十五年(1175年)大定十八年(1178年)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昌元年(1190年)明昌四年(1191年)明昌四年(1191年)明昌六年(1195年)明昌六年(1195年)明昌六年(1195年)明昌六年(1195年)明昌六年(1195年)新泰县环翠亭诗刻 党怀英 党怀英撰 不详 《金石汇目分编》卷10之一 山东新泰县檀特山照寺建释迦殿记 党怀英 党怀英撰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25礼部令史题名记 党怀英撰 行书 《金文最》卷17北京西砖胡同法源寺重修郓国夫人殿碑 党怀英撰 八分 《寰宇访碑录》卷10山东曲阜博州重修庙学碑 党怀英 行书 《山东通志》卷9古迹志 山东东昌县重修中岳庙碑 党怀英 正书 《金石萃编》卷156河南登封鲁两先生祠记 党怀英 八分 《金文最》卷70山东泰安市奉国上将军郭建神道碑 党怀英王去非撰王庭筠书黄久约撰郝史书党怀英撰并书丹任询撰并书 行书 《金石汇目分编》卷10之三 山东青州市重修天封寺碑 党怀英 党怀英撰并书 正书 《寰宇访碑记》 山东泰安市醇德王先生墓表 党怀英 党怀英撰并书 八分 《金文最》卷89山东平阴县大金得胜陀颂 党怀英 赵可撰 正书 《满洲金石志》卷3黑龙江阿城范阳重修文宣庙碑 党怀英 黄久约撰 《授堂金石文字序跋》 河北涿州庆寿寺碑 党怀英 李晏撰 八分 《永乐顺天府志》卷7北京庆寿寺重修文宣王庙记 党怀英 黄久约撰李嗣周书 正书 《金石汇目分编》卷1河北涿州张公神道碑 党怀英 正书 《金文最》卷86山东沂州重修东岳庙碑 党怀英 正书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14泰安岱庙祝圣寿碑 党怀英黄久约撰杨伯仁撰黄久约书党怀英撰并书 八分 《寰宇访碑记》卷10山东济宁张仲伟墓表 党怀英 不详 《陕西金石志》卷24陕西郿县秘书省碑 党怀英 赵沨撰党怀英书 《畿辅金石志》卷1北京大兴棣州重修庙学碑 党怀英 赵沨书、党怀英撰 正书 《山左金石志》 山东惠民时令爱神道碑 党怀英 赵沨书、李晏撰 正书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河北新城王安石诗刻 党怀英书 篆书 《山左金石志》 山东济宁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党怀英 党怀英撰并书丹 八分 《金石萃编》卷157山东曲阜灵岩寺田园记 党怀英 周驰撰 《八琼室金石补正》 山东

碑刻年代碑刻名称篆额书丹、撰文书体记载文献保存情况明昌六年(1195年)承安元年(1196年)承安元年(1196年)承安二年(1197年)承安二年(1197年)承安二年(1197年)承安三年(1198年)泰和元年(1201年)泰和六年(1206年)泰和六年(1206年)泰和六年(1206年)泰和六年(1206年)曲周县重修学记 党怀英 赵元英书、靳子昭撰 行书 《金石汇目分编》卷3广平府曲周县十方灵岩寺记 党怀英 党怀英撰并书 《金文最》卷70山东长清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 赵沨撰、党怀英书 八分 《金文最》卷111山东济宁梁子直墓志 党怀英撰 不详 《天下金石志》 河北献县茶泉铭 党怀英撰 篆书 《天下金石志》 山东曲阜竹溪堂诗 党怀英撰 不详 《天下金石志》 山东济宁孔庙石刻杏坛 党怀英书 篆书 《山左金石志》 山东曲阜谷山寺碑 党怀英 党怀英撰并书 八分 《金文最》卷 山东泰安新补塑释迦佛旧像碑 党怀英 党怀英撰 《金文最》卷70山东泰安袭封衍圣孔公墓表 党怀英 党怀英撰并书 正书 《金石汇目分编》卷12山东曲阜灵王庙碑 党怀英撰 《金石汇目分编》卷10山东新泰《金徂徕山六逸堂碑》 党怀英撰并书 《山左碑目》 山东莱芜
三、党怀英书法及其在篆书创作方面的意义
赵秉文在《竹溪黄山书跋》中说:“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书又次之,皆为本朝第一。”[7]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党怀英的篆书题额是相当多的。他在篆书方面的成就确实比较大,但是否就如前人所讲他是金朝第一呢?其实金朝擅篆书的人不只党氏一人,赵沨、王无竞等均擅篆书,他们为何没有被评为第一?
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党怀英生活在书法的复苏、繁荣期,跨越了天会、大定、明昌、承安、泰和时期。如此长的跨度使得他的书法有了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这是其他书法家所不能具备的条件,故成就自然不能与之相比。其二,党怀英身处翰林,结交俊彦,使得他的影响力大于一般人。黄久约、赵沨、王庭筠、王去非等都是旧交,相互交流切磋提高,是党氏书法提高的重要途径。其三,党氏学习古典,深厚的字学功底足以支撑他的篆书、八分书的创作。篆书隶书创作的并行,更使得篆籀意得到更深地发扬。篆书作为一种书体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其他书体共生的。
党怀英在篆书特点是笔力遒劲。元郝经在《跋党承旨篆字太白琴赞》里写道“太白琴赞二尺余,丞相小篆承旨书。端劲安帖肆雄奇,展尽笔力世所无。”[8]康有为也在《广艺舟双楫》(说分第六)里说:“自少温既作,定为一尊。鼎臣兄弟(徐铉、徐锴)仅能模范,长脚曳尾,体长益甚,吾无取焉。郭忠恕有奇思,未完墙壁。党怀英笔力精绝,能成家具。”[9]党氏的笔力精绝,也是与唐代李阳冰以来的篆书书家相比得来的。我以为,更准确地说是与徐铉、徐锴兄弟相比较而得出的。徐氏兄弟的篆书,确实是力量不及李阳冰。这也是为唐以后的篆书运笔另辟蹊径。欧阳修也曾说二徐笔法颇少力。从宋代的米芾《千字文》篆书、到明代赵宦光、徐渭、王铎、傅山的篆书笔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侧锋的出现,使传统的中锋运笔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宋代的篆书开始在笔法上缺少笔力,因为书写者的积学不够,再加上书写时是带有行书的笔意,结构上又打破了均衡状态。这就使得篆书疏离了最原始的静态而变得动荡起来。

图3 《王安石诗刻》

图4 《京兆府教养碑额》

图5 《赵宦光篆书》
党怀英没有延续北宋篆书之流弊,而是悉心字学,修炼内功,养浩然之气。得强劲笔力于腕底。悬针篆在宋朱长文《墨池篇》有记载:“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到了宋代,关于悬针篆的记述基本都是定位在曹喜身上。僧人梦英有《十八体书》,里面这样记述:“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党怀英除了继承李阳冰正统的小篆以外,在悬针篆方面的造诣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王安石诗刻》(图3)就是一幅悬针篆作品。石在山东济宁。因为悬针篆书写要根据运笔适当改变字形结构,所以它与小篆的结字大同小异。譬如“口”字就写成三角形而不是圆形或半圆形;在转折的地方增加了方折。悬针篆的难度其实比正统的秦篆系统的小篆更大。因为在粗细变化或者是交接之处要做到不露痕迹衔接自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党怀英篆书在金代选择悬针篆,不是偶然的。首先,他的金代文字学研究继承唐代篆书的成就,又能深入古典,跨越古人,钻研新路。这是篆书发展研究的必然。其次,悬针篆的出现,是在宋代书法家如米芾等书法家在篆书方面做的尝试性创作的理性回归。米芾的篆书,带有草书的笔意。可以认为是对传统篆书的颠覆。但是党怀英并没有因循其道路走下去,而是深入字学,钻研古典,在传统的探魅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在泰和三年由咸宁县主薄嘉祥书写的《京兆府学教养碑额》(图4)就是用的悬针篆。其篆书的写法也与小篆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认为是由于女真书本身所带来的。
党怀英的悬针篆的影响还是可以看得见的。清代王澍认为,宋代篆书自唐李阳冰以后很少有继承者,宋代的篆书是断代的。直到元代的赵孟頫才重振旗鼓,“上追(李)斯(曹)喜,下比少温。”金代的篆书成就被忽略了,这是很不符合史实的。尤其是金代在篆书创作方面所做的尝试,对于今天狭隘的篆书生存空间里的艰难蜕变,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四、结论
金代党怀英篆书的创造性对于元明代的篆书书家的启发意义不可磨灭。明人赵宦光的草篆书就是从悬针篆转化而来的(图5)。因为悬针转的运笔出现了粗细变化,这就为书写时的掺杂行书笔意提供了可能。傅山也在赵宦光之后出来了。从创作的渊源上追溯的话,党怀英应该就属于篆书创新这一脉络的源头。
这样看来,王澍的观点是有些偏颇了。金代的篆书在承接唐人篆书的过程中既能从笔法上集成之,又能逾越唐人局限,在字学方面深入因循古人矩蠖,得之于篆籀,以至于金代的书法家也能根据篆书特点金代女真文字,创制出悬针篆书,这使得女真文字也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而不至于走向灭绝。金代党怀英作为金代书法史上的重镇,在金代乃至整个篆书发展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作品的创造性对后世篆书艺术的启发意义不容忽略。
[1](金)元好问.中州集(卷3)[G].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元)脱脱.宋史(卷401)·辛弃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元好问.中州集(小传)[G].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40)[G].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G].北京:中华书局,1991.
[6]马宗霍辑.书林藻鉴 书林纪事[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7]赵秉文.滏水集(卷20)[G].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90册),1983.
[8](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85册),1983.
[9]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