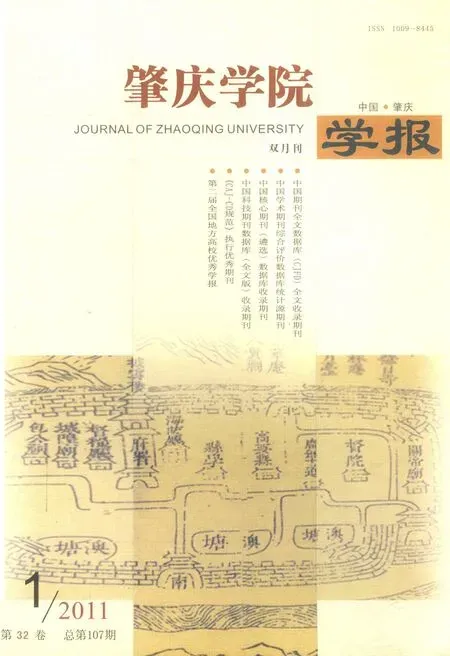论休谟的正义理论
罗伟玲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论休谟的正义理论
罗伟玲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休谟的正义理论体现了理性和情感的张力,他区分了正义规则的建立和正义感的愉悦来源,前者依靠的是理性,后者依靠的是同情。休谟主张正义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但情感是决定力量,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种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结合观没有给理性和情感恰当的定位,因此避免不了道德失范的缺陷。
休谟;正义;理性;情感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先驱。他以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同情原则为基石,创建了一个“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笔者的总结)的道德体系。该体系的核心观点是:道德区分来源于情感,道德评价也决定于情感;理性指示情感的方向,但只是情感的奴隶。正义理论是休谟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内容,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构成了他的整个人性学说的制度性的支撑”。[1]对它的研究是理解休谟整个道德体系的关键。休谟从人性中的自私和同情这两大基本要素出发,在“人学”的基础上建构出他的正义理论。他主要从正义规则的产生以及正义感的德性来源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正义规则产生于人的自私和理性,正义感则来源于对公共利益的同情。本文也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休谟的正义理论,却得出与休谟不同的结论,即:正义规则起源于理性,对正义和非正义行为的道德评价也只能由理性决定。道德来源于情感,但道德评价主要决定于理性,否则就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一、正义规则起源于理性
休谟把德性分为自然之德和人为之德,前者以仁爱为代表,后者以正义为代表。正义不同于仁爱,它不是从人的直接情感产生的,而是人类出于应付生存的环境和需要而采用的人为措施和设计。仁爱由人的天性自然而然发生,并自然地受到人们的赞许;正义是理性的产物,体现的是理性对自私情感的约束和引导。自私和理性是正义规则的根源。休谟从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性的特点这两个方面来探讨正义的起源问题,笔者把休谟的论述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人类必须组成社会才能生存。休谟说:“在栖息于地球上的一切动物之中,初看起来,最被自然所虐待的似乎是无过于人类,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2]525狮子和牛羊这些动物的欲望和自然所赋予满足欲望的条件都是成比例的。相比之下,人类无穷的欲望与薄弱能力间的差距是最大的。单个人孤立的生存不可能调和欲望与能力间的矛盾。只有社会可以为此提供补救方法。人只有组成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超越其他动物。“借着协助,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2]526通过社会的协助、分工和互助,才能摆脱在孤立的自然状态中单个人所可能遭遇的苦难。社会为人类带来力量、能力和安全,使人类生活得更加满意和更加幸福。同时,由人类两性间的自然欲望发展而来的人类两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组成。由单个人向社会的过渡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过程:单个人——两性关系——亲子关系——族群关系——社会。总之,社会的出现不仅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类两性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
第二,人的偏私情感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极大阻碍社会的形成。休谟认为人的天性中自私是最重大的,每个人都想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同时,人性中还包含有限的慷慨。人类除了爱自己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爱护其他事物,尤其是和自己亲近的人和事物。当然,这样的慷慨是有限的,人性中不存在普遍的仁爱。这种人性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与社会相抵触。而且它们一旦与人类生存环境——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相结合,就会成为组成社会的主要障碍。人类有无穷的欲望,不幸的是,自然资源却相对稀少。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必然会产生情感的对立,也就会产生行为的对立,甚至摧毁社会。可见,这种偏私的情感会带给人类毁灭性的冲突,人类必须约束它才可以更好地生存。
第三,人类的知性能力可以修正偏私的情感。休谟指出:“人性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是它的一切活动所必需的,那就是感情和知性;的确,感情的盲目活动,如果没有知性的指导,就会使人类不适于社会的生活”。[2]533-534人类心灵中任何感情都没有充分的力量和适当的方法来抵消贪得的欲望,只有知性能通过改变情感的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类的欲望。当人们意识到社会的纷乱主要来源于对外物占有的不稳定时,就会想方设法稳定人们对财物的占有。人们在经验中意识到:禁止取用他人的所有物,不但不会违背自己的利益或最亲近朋友的利益,恰是对这些利益最好的保护。于是,他们通过缔结协议,稳定财产的占有,使每个人可以安享自己凭幸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正是通过人性中的判断与知性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贪欲和偏私,使他们互不侵犯,甚至保护他人的财产,这才导致了正义规则的产生。
总的来说,“休谟认为正义起源于下述两个事实:主观条件方面是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客观条件方面就是外物的容易转移,以及它们比起人类的需要和欲望来显得稀少”。[3]人们设计出正义规则就是要补救这两个条件结合而产生的不便。一种“共同利益感”促使人们设法稳定财物占有,实现对个人财产和他人财产的保护,于是正义规则就产生了。“共同利益感是致使财产权这样一种人为设计和措施成为可能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休谟——引者)所谓的正义规则的根本基础。”[4]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共同利益感并不是人类自然具有的情感,它是理性对偏私情感约束和引导的产物。没有理性,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更不可能去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正义只是作为一种稳定财物占有,满足自我利益的手段,因此它的德性也就唯一地来源于其社会效用。而只有理性能把正义的社会效用凸现出来。总之,正义规则的出现是理性对情感约束的结果,它不可能来源于人的情感,恰是理性的力量促使其诞生。
二、正义感产生于对公共利益的同情
休谟认为,自私只是正义的原始动机,对公益的同情才是正义获得道德赞许的来源。也就是说尽管正义规则是通过理性建立的,但正义感却是产生于对公益的同情。
休谟认为,尽管人们通过理性能认识到正义规则可以给人类带来利益,但知性的力量仅此而已,我们不能因此就建构出一套正义规则,因为理性对意志和道德行为是无力的。只有当人类“感觉”到这种“共同利益感”,并能把它相互表示出来以及相互了解到时,正义规则才真正出现。这种“共同利益感”是社会全体成员互相表示出来的,并且能诱导他们以某种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当人们在长期的经验中,逐渐‘感觉到’调整自己的行为、尊重他人的财产,对自己是有利的,并且确信他人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时,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5]总之,休谟强调“共同利益感”和人们对此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正义最终只能由情感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共同利益感”不是自然的情感,它要借助理性的力量才能显示出来;同时,休谟所谓的“感觉到”也不可能是单纯的感官感受,更象是理性的直觉。休谟对正义的分析还只停留在经验和观察上,在此基础而言,正义似乎就是建立在情感上的,理性因素只有辅助性功能。但是,当我们一旦揭示出情感背后的理性作用,就会对休谟的这一结论提出异议。我们认为,对正义来说,理性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因素;尽管情感对正义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是情感不是决定力量。
休谟一方面强调正义的人为性,强调它是理性对情感约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它与自然之德等同起来。在他看来,自然之德来源于情感,理性只能指明情感的方向;而正义规则的产生虽然要依靠理性的作用,但是正义规则本身是无力的,它必须与人的情感相结合后,才能影响人的道德行为。所以,赋予正义德性的是情感,情感才是判断正义与否的依据。休谟区分了正义规则的基础和正义德性的依据,前者是理性,后者是情感。也就是说,休谟把我们对遵守正义规则的行为表示道德赞许,对违反正义规则的行为表示道德谴责的主要依据还是归于情感。
休谟认为,尽管人的自私和理性促使了正义规则的产生,但是只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感才是正义感的德性根源。总之,正义之德的道德依据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学”中的第一章“德与恶总论”中着重论证,道德区分的来源不是理性,而是道德感;由德发生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由恶发生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自然之德具有如此性质,人为之德也该如此。按照休谟的观点:人们认识到遵守正义的规则有利于保存社会,有利于保障自己的利益,使自己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他们心中就由此产生愉快的情感,这种情感自然地诱导他们以正义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期别人也遵守这些规则。同时,这种情感也就是我们评价一个行为正义与否的主要依据。这种情感即所谓的“正义感”,它是正义规则和道德感相结合的产物。休谟还说到,正义的自然约束力是利益,而它的道德约束力只能是“是非感”。他认为,正义和非义的这种区别有两个不同的基础,即利益和道德。“利益所以成为这个基础,是因为人们看到,如果不以某些规则约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道德所以成为这个基础,则是因为当人们一旦看出这种利益以后,他们一看到有助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动,就感到快乐,一看到有害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动,就感到不快。”[2]573-574休谟通过同情机制把利益和道德感结合起来。正义规则的起点是个人利益,但它们“具有一种社会利益的倾向,它们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手段”[6]。同情就是沟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桥梁。休谟承认最初使利益成立的是人的理性,因此正义规则是人为的;但这个利益是通过同情原则才得到社会公认的,而对利益的维护需要道德感的约束。故在休谟看来,正义虽然是人为之德,它也只能是情感的产物。“同情是这样一种普遍原则,它是对所有人为之德发出赞许的原因。”[7]
应该肯定的是,休谟把正义规则和情感结合起来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首先,理性在刺激行动方面的确不如情感。我们尽管认识到正义规则对社会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情感的驱动,我们不一定就会按正义规则行事。因为存在“是—应该”之间的鸿沟。但如果我们在这利益的事实中,加入情感的因素,从而把它变成情感的事实,这时“是”和“应该”间的鸿沟便大大缩小了。其次,同情既然可以传递道德感,它对正义感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正义的最初约束力是利益。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他人的利益由于间接影响到我们的利益才受到我们的关注。至于那些与我们相距甚远的正义或非正义行为,对我们利益的影响太少甚至没有,但我们同样为此感到快乐或不快,原因在于同情机制的作用。休谟认为,这种对公共利益的同情不会被个人偏私的情感所蒙蔽,也不会因为相反的诱惑而产生偏见,对公益的同情产生普遍的正义感。所以休谟说:“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2]540所以,对于人为之德同样需要理性和情感共同作用。休谟这种做法再次体现出理性和情感结合的必要性。
但是,休谟站在道德情感论的立场上,将正义德性的依据归于情感,这一观点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不但正义规则起源于理性,对正义和非正义行为的道德评价也只能由理性决定。在休谟看来,单个的正义行为往往是违反公益的,正义的益处不体现在单个行动中,而体现在社会整体或其大部分一致赞同的整个体制或体系中。休谟举例说:“当一个有德的、性情仁厚的人将一大笔财产还给一个守财奴、或作乱的顽固派时,他的行为是公正的和可以夸奖的,不过公众却是真正的受害者”。[2]537再如给乞丐捐赠体现了捐赠者的仁慈,但却助长了乞丐的懒惰,因此是不利于公益的。对于这种单个人的正义行为,我们的情感可能会对此表示愉悦,但我们的理性会指出它的非正义性。可见,就算正义规则已经设计出来了,但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规则,还是要经过理性的分析。判断一行为正义与否的关键是看这一行为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奉行的原则后是否有利于社会全体的利益。这已体现出普遍规则对道德的重要性。这个复杂的利益计算过程不是情感能胜任的,只有理性才能指明公益的方向,而且情感恰恰难于形成普遍规则。所以,正义德性的依据不能是情感而是理性。我们承认正义感不仅是理性的结果,也是情感的结果,但是评价行为正义与否的主要依据只能是理性而不是情感。
三、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评价
总的来说,正义之德一方面以利益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情感为评价依据。这体现了休谟道德理论中功利和情感的交织以及理性和情感的张力。
休谟在探讨正义和财产的起源时清楚地看到它们不可能起源于人的自然情感。人类的自私本性和自爱情感在这种生存资源有限的大环境中,只会引起不断的冲突,甚至毁灭人类社会。值得庆幸的是,上帝给了人类足够的理性。借着理性的力量,人们不断地在生活中总结到这样的经验,即我们必须稳定财产占有、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曲折和间接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为了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这个规则,大家开始签订协议。这个协议是人们理性协商的产物,而不是愉快或不快之情感的产物。“事实上,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是诸签约者们妥协的成果,对于每一个签约者来说都有所得并都有所失,相应地,都有愉快之处也都有不快之处。”[8]既然协议的签订是保障正义规则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那么正义只能来源于人的理性而不是偏私的情感。可是,休谟为了保持其道德情感论的一贯性,他把正义之为德和非义之为恶的道德评价依据归于情感。无论是自然之德还是人为之德,休谟都坚持道德感对它们的决定作用。为此,他甚至在《人性论》一书中断言:“正义感不是建立在理性上的”。[2]536而他这种论说上的前后矛盾却是为了保持其道德情感论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性。无论如何,休谟的正义论比起其道德感理论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在道德评价中理性和情感的张力。理性和情感无论孰轻孰重,它们间那种既互相较量又互相依存的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这成为休谟道德体系的一大亮点。
休谟道德哲学中无论是自然之德还是人为之德,都体现出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令笔者觉得惋惜的是,休谟已经揭示出它们二者的张力,但没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由于他坚持情感主义的立场,过分夸大了情感的作用,没有给理性足够的重视。他那兼顾理性和情感,但却是“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道德评价体系,有其优越之处,但也面临道德失范的难题。情感只是盲目的、主观的因素,以它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就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走出此困境的方法就是坚持道德评价的理性原则。
另外,休谟的正义理论假定人性都是自私的,而理性指导人们通过建立和遵守正义规则来追求大家的共同利益。正义感是对共同利益的关切,是一种“共同利益感”。正义的“有用性”是其道德价值的唯一来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休谟的正义理论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休谟是一位道德情感主义者,但他对“效用”的道德价值的论述的确为边沁点燃了功利主义的火光。边沁也坦言,当他在休谟的著作中读到“一切善德的基础都蕴藏在功利之中”的观点时,“顿时感到眼睛被擦亮了”。[9]同时,休谟在分析正义之初先对善良动机有一番论述,这又体现出动机论的倾向。而他对正义规则的重视又蕴含着道义论的端倪。所以学者张钦评价他是一位“思想丰富、论述跳跃性强,甚至在行文中有时会前后自相矛盾的哲学家”[10]。休谟这种论说上的全面性为后来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义论都准备了思想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休谟的伦理思想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1] 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8.
[2] 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夏纪森.正义与德性:哈耶克与休谟的正义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7.
[4] 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8-129.
[5] 张钦.休谟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73.
[6] CAPALDI N.Hume’s Place in Moral Philosophy[M].New York;Bern;Frankfurt am Main;Paris:Lang,1989:212.
[7] CAPALDI N.Hume’s Place in Moral Philosophy[M].New York;Bern;Frankfurt am Main;Paris:Lang,1989:212.
[8] 罗伟玲,陈晓平.理性与情感的张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1.
[9] 边沁.政府片论[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9.
[10] 张钦.休谟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46.
On Hume’s Justice Theory
LUO Weil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1,China)
David Hume’s justice theory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reason and passion.He separates how rules of justice are established and how we come to approve of them.He argues that the rules of justice are derived from reasons,but the common points of them originate from sympathy.He insists that justice is the combination of reason and passion.Passion takes the decisive role in this combination,while a reason is just the slave of passion.His view of“putting passion over reason” has showed im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son and passion.Therefore,it results in soci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defected moral standards.
Hume;justice;passion;reason
B561.291
A
1009-8445(2011)01-0007-04
(责任编辑:杨 杰)
2010-10-13; 修改日期:2010-11-01
罗伟玲(1983-),女,广东佛山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