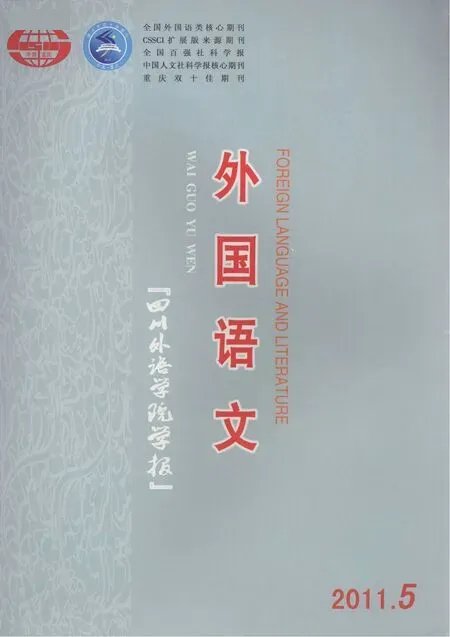用灵魂叙事的人:哈利特·雅各布森《一个奴隶女孩的自述》中的叙事伦理学阐释
焦小婷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引言
叙事伦理学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7,从而激发人们内在的道德情感,促使人们展开对自身的道德反省,进而形成个体的道德自觉。它关心“一个人的生活际遇”,探究“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么样和可能怎么样。”[1]8它重点关注道德的特殊状况,追问心灵的回声而非现实的答案。叙事伦理学把叙事学和道德批判相结合,既走出了单纯的叙事理论自身的局限,又超越了以现实和道德规范和理性意识为标识的伦理批评的界限,更偏重个性、个体、个人化的生命感知。
叙事伦理批评直接指向文学的内部质素,充分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寻和追问隐含在文本叙事要素中的精神价值和伦理取向,判断文本中叙事因素与现代个体价值的关联,追问这些要素是压抑了还是舒展了个人自由”[2]。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伦理批评只注重作者及外部关系而悬置文本的促狭,又拓宽了伦理批评的形式分析。叙事伦理学的先锋人物、哈佛大学教授纽顿(A.Z.Newton)在其《叙事伦理》(1995)一书中说道,“讲述”本身就蕴含了伦理本质,因此“所有叙事都是伦理的”。[3]7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斯更是强调,“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4]151。需要指出的是,叙事伦理批评中的叙事并非单纯地讲故事,即作者遵照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组织成复杂的情节事件。它更像一种个体的言说——对某种社会文化制度背景下个体的生活遭遇和生命感悟的言说。
盛行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奴隶叙事以自传的形式,从社会内部刻记蓄奴制下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讲述主人公从蓄奴制社会走向自由社会的艰辛历程。自我经历和经验是构成这类文本的一条基本线索。它以个体生命的本真构成为基础,是一种生命的自觉。奴隶叙事尽管共享了自传体裁的写作手法,但其厚重、深切的社会、文化意义却使它超越了自传体形式,充斥着由蓄奴制造成的血腥暴力和对白人残暴行为的指证,显现出的是文本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错位和差异,以及个体命运的“偶在性”和不可预测性。奴隶叙事分明呈现出“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活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1]7这一叙事伦理学的特质。它聚焦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张扬的却是灵魂的放飞和自由。
以叙事伦理学批评为切入点对奴隶叙事的观照,不仅契合叙事伦理学的要旨,也契合了奴隶叙事的隐性诉求。因而奴隶叙事中的叙事伦理问题研究,不但应关涉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理性意识,更应结合奴隶叙事的文学性和个体性特质,寻访个体的生命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美国黑人女作家哈利特·雅各布斯(1813~1897)花费五年时间写就的自传《一个奴隶女孩的自述》(1861),通过叙事人琳达·布兰特之口,讲述了作为女奴的她为了自尊如何跟白人奴隶主巧妙周旋,斗智斗勇,最终使自己和孩子获得自由的故事。本自传是首部“公开涉及白人奴隶主对于女奴的性剥削主题的”[5]奴隶叙事,作者曾被誉为“播下当代黑人女权自传和黑人文学传统中女性小说种子的人”[6]。然而国内学界对这一作品却鲜有探讨,仅有的几篇论文大都聚焦于其“控诉、抗争及叙事模式”主题,忽略了隐匿在文本中鲜明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诉求。雅各布森在这部典型的奴隶叙述作品中,没有一味地展现血淋淋的事实,没有一味地经营语言的修辞效果和叙事的技术策略,没有依从对身体细节的写作和不加遮掩的展露,也没有对自传文本中的事实和史实以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以生命对自我生活际遇的理解贯穿于写作的始终,关注的是平凡、感性的个体生存体验,表现的是个体面对社会和现实生存的强大压力所作出的伦理选择。作者也许少有懂得叙事与伦理间活生生的关系,但其伦理观念和伦理思考却深入文本内部。本文将以叙事伦理学批评为切入点,分别从道德评判、道德困境和道德叩问三个方面,探究作者是如何用叙事建构伦理道德问题,述写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而用叙事伦理意识呵护自己脆弱的个体生命。
二、道德评判:白人“十恶不赦”?
叙事伦理批评通过感知和感悟个体生命而趋于道德评价上的悖谬性判断和伦理取向上的尴尬。伦理是对善的一种期待,是向人性、向善的一种规范。善与恶构成了伦理学的出发点。然而世上本无绝对的善与恶。“如果我们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么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有价值的……”[7]从作者在对待白人的叙事态度上,我们看到了她在道德评判上的谬悖性体验和伦理价值取向上的困惑。
众所周知,美国黑人文学叙事从口头讲述开始,无不充斥着对白人的血泪控诉。那些“没长皮肤的人”(白人奴隶主)的罪与恶,从1619年第一批黑奴踏上北美海岸之时起,已被黑人作家撰写进历史的大文本中。黑人作家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沉重的历史褶皱中,一边舔啜、抚慰着自己伤痛的心灵,一边怒斥白人奴隶主的十恶不赦。可在这本自传叙事中,尽管作者认为“善良的白人奴隶主确实有”,但却“就像天使的造访——极少且间隔时间无限”[8]43①见金莉“哈里特·雅各布斯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中的颠覆性叙事策略”《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拙文“一个求索的灵魂——对哈利特·雅各布斯《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经历》自传叙事的思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但事实上,我们在叙事文本中看到的大部分白人都是友善的。外祖母的女主人就是一位善良的白人女性,生前对所有黑人,尤其是外祖母“以礼相待”(p.10)。她的妹妹临死前曾用50美元买回了外祖母的自由,“以一颗博大的心彰显出人性的善良”(p.14);母亲死后,叙述人琳达跟随了母亲的女主人,这位女主人善良、宽厚,“教我读书识字”,“待我像白人孩子一样”(p.11)。然而她临死前却“把我赠给(bequeath)了她5岁的外孙女,我尽管无法理解”,但仍然“心怀感念”(p.12);琳达的舅舅本杰明在出逃时曾经得到了被琳达称之为“圣人”的白人奴隶主的扶助和指点(p.24),连舅舅也赞叹“在这个他十分憎恶的小镇竟深藏着这样一位值得拥有更纯洁背景的极品人物”(p.24);类似的白人还有一路护送琳达到费城的白人船长(p.124);给了琳达无私帮助的费城的邓巴先生(p.126);还有为了帮助她逃离奴隶主的追捕,不惜以自己的孩子做担保的布鲁太太(p.154)……我国学者谢有顺在谈到我国当代文学需要建构叙事伦理时说道,我们应“将生命关怀、灵魂叙事作为写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维度,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与事”[9]。作者有关白人的叙事,正是用“宽广”和“仁慈”对人性善的品质的守望。
善是自传文本中一种潜在的叙事伦理。叙述者琳达在叙事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的发现,让我们领略到了她高贵的灵魂。即使是对于万劫不复的白人奴隶主,她也不放过任何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平日里对自己百般刁难的女主人弗林特太太在琳达的眼里,也不尽然冷酷、无情:“我从来都没有冤枉过她,也不希望冤枉她。她任意一个善意的话语都会让我臣服”(p.29)。弗林特太太得知丈夫对于琳达的侵犯后,审问了她。“或许她对我还有点同情心;因为这次审问结束后,她很温和地和我讲话,并且答应要保护我。”(p.30)尽管弗林特太太真正想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家庭、爱情和婚姻,但琳达对于女主人丈夫不忠的命运和遭遇“深表同情,尽管她不是个善良的人”(p.31)。男主人弗林特在琳达15岁开始就对她进行性骚扰,并发誓永远不会给她自由,且用以后的行为证明了他的决心。然而在作者的笔下他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从来没有惩罚过我,也不允许别人惩罚我。”(p.29)“从不允许别人对我动用鞭子”,包括她的妻子,而这一点“确实帮到了我”。(p.31)在弗林特先生得知琳达怀的不是他的孩子时,“不管是碍于脸面还是出于尊严”,尽管“他恼羞成怒,但还是把举起来的手放了下来”(p.51)。后来弗林特先生开始动手毒打琳达,但事后也会心生忏悔:“我向上帝起誓,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但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p.64)
有关奴隶主弗林特对自己的百般侮辱和性侵犯,叙述者没有像其他奴隶叙事那样给予活生生的事例呈现,而是选用一些含混的词句“他(又)来找我”(p.27)一笔带过。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叙述者对白人、男人的知性存在的勾销,更引发我们思考和想像: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和渴望使她选择藏匿在阁楼里长达七年,眼看着两个孩子的成长却不能亲近?到底是怎样的生存状况迫使她宁愿忍受小阁楼里夏天的蚊虫叮咬、冬天刺骨寒风、春夏季的潮湿霉变也不愿回到主人特意为自己建的屋子?可以想像,如果作者在此放纵自己在种族写作上的经历和经验,其叙事会很容易被淹没在经验的泥潭里。而过度的经验化很可能会冲淡写作中的伦理感觉,使写作表象化而难以企及生命、生存的本真。
因而我们看到,叙事者在控诉、揭露和批判白人奴隶主和蓄奴制的同时,也感念他们给予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善心善意,用叙事竭力呵护着一些脆弱和温暖。这显然超越了现世的伦理,关注的是一种人类性的慈悲和爱。叙事的厚重、伦理意识的凝重感使这本以“控诉”为主题的自传叙事有了一番道德的对话,伦理的交流。作者能够带着自身的伤痛去抱慰别人的良知,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爱的意志比生命的伤痛更有力量。这是一种放逐了恶和绝望的彻底的善,一种能舒缓内心苦与寒的善。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作者的慈悲和大爱与奴隶主的种种恶行和蓄奴制的罪恶渊薮在此形成了极大的伦理道德张力。
三、道德困境:“我”的身体“我”做主?
叙事伦理关注道德的特殊状况,关注个体生命的感性欲望,拒斥用普遍、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理性、甚至科学理性为伦理标杆来衡量个人的道德选择和生命价值。耿占春在《叙事与抒情》中说:“叙事比教义和真理更具有切身的真实性。”[10]在《一个奴隶女孩的自述》中,叙述者冲出传统道德束缚,诉说自己真实的伦理境遇。她的性爱选择就是一个复杂的伦理命题。
雅各布森在自传中,不仅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及他人相助而获得自由的艰难历程,也坦陈为了逃避奴隶主弗林特的性迫害,她主动选择成为白人桑德斯先生的情人,还成了两个孩子的未婚母亲。应该说,这是一种自由且痛苦的伦理选择。其自由表征了她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和掌控,张扬的是个体的生命、尊严和幸福。她在自我身体中找到了自己,确证了自己,欣赏着自己。她选择的是身体,宣泄的是灵魂,而叩问的却是道德伦理。这种选择不正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在权利运用的‘细枝末节’,在黑暗的无意识领域进行的最切实有效的反抗吗?”[11]然而,叙述者面对的现实是,“白人女性的贞洁从少年时就受到庇护,她们有权利选择所爱的人,她们的家庭有法律的保护”。但“黑人妇女不仅无法按照白人社会所要求的妇女保持贞洁的道德标准行事,而且还被迫采用相反的标准”(p.48)。因而她的选择同时也是痛苦的:她想在错综的生活境遇中升扬自己的个性,但却不得不在普遍的、传统的、主流的道德规范和特殊的自我道德伦理情景冲突中挣扎。她体悟到的是苦痛和无奈,述说的是个体道德在悖论中抉择的艰难:“在压力下屈从比把自己主动交出去更堕落。自主选择一个对于你除了好感之外没有其他控制欲的情人也等于某种自由”(p.59)。作者不得不这样进行自我辩护。
文本中关于自己和孩子父亲的情爱关系作者也没有交代,只用了“一种更为温柔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p.47)来表达他对孩子父亲的情感,而把其中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留给了读者去想像、揣测和判断。叙事因而变得复杂而模糊。孩子的父亲桑德尽管一直在暗中帮助她、对她心怀善意,但却在拿钱赎回孩子的自由之后,把女儿送给了一个亲戚的女儿作仆人,且“一直对自己的孩子冷漠无情”(p.146)。作者遮遮掩掩的叙事是想遗忘那段自主选择的生活,还是对自己的情感体验以及道德判断含糊其辞?读者看不到任何的道德评判,但却见识了琳达多次祈求读者的原谅、宽恕和理解:“善良的读者!你们从来不知道身为奴隶意味着什么;完全不受法规的保护;而各种法律迫使你成为奴隶,完全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没有人会比我更加敏感。那痛苦、耻辱的记忆将困扰我至生命终结的一天。然而,平静地回首往事,我觉得不能用判断其他人的标准去判断奴隶妇女。”(p.60)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情窦初开的女子爱上一个未婚的白人男人有什么错?这一选择不正是她所诉求的身体、精神、情感的自由吗?她的道德忏悔是想显现她的无奈,还是欲求人们的理性判断?她是在为自己开拓还是以此为悬镜,让人们反思黑人的爱情究竟要受什么样的限制和禁锢?
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在悬置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是非对错的判断,但实际上却把伦理评判的责任抛给了读者,让读者针对其道德境遇作出见仁见智的客观评价,进而思索自身的伦理道德取向。作者这样做其实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也是对文学的敬重,更是为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理解人、进而尊重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的身体“我”做主,结果自己却陷入了一个五味杂陈。无以言说的道德困境。在这本自传中,我们找不到一种明确的、可以解决人生悖论的道德信念,但却看到一连串的生命疑问。
四、道德叩问:“我”获得了“自由”?
奴隶叙事是19世纪黑人自传的基本形式,大多采用以男性奴隶争取自由的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创作模式,叙事中不乏血腥、暴力和个人英雄气概的展示,且承载着一些沉重的政治使命和历史负担。①典型的男性自传体奴隶叙事中,主要针对男主人公个人英雄主义气概的染色和凸显。《弗雷德利克·道格拉斯生活的叙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但琳达作为女性,渴望的只是温馨和谐的家庭、女性身份和母亲身份,和家庭成员之间、女性朋友之间的互爱互助。这种“小情小爱”正是感性的、平凡的、鲜活而真实的个体生命的体验。自传的结尾超越了传统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模式,在一种无奈、悲凉和失望的情势中作结,而我们所读到的不仅有作者对生活的直接、本真关照,还看到普通而平凡的个人生命及其本真状态。
12岁之前,琳达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一位善良的白人雇主家里,和谐、温馨、爱意浓浓。12岁以后在为自由而抗争的过程中,她从来未曾放弃对爱的祈望——施展母爱、得到父爱、享受情爱。而在自传的最后,作者用充满酸楚的笔触述说了自己“被解放”的事实。“我终于被卖了!在纽约这个自由之城中被卖掉了。”(p.155)十几年心酸的逃亡史,十几年生命的冒险和挑战,此刻却以这样一种不尴不尬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她所渴望的家的温馨何在?她所追求的真爱又在哪里?布斯在强调文本伦理对读者的影响时所说:“一旦一个新的文本被公开,我们便带着生活的事实对文本进行伦理性的阅读时,这一过程将导致两面性:伦理的读者不仅要对文本和作者负责,而且还要对他或她阅读的伦理品质负责。”[4]10读者在此“被担负起”一种伦理批评的责任,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伦理读者,阅读变成了伦理阅读,而这种交互性的伦理回应所升扬的正是文本的伦理意义。
“偶在的个体命运在按照历史进步规律设计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无论在多么美好的社会制度中,生活都是极其伤人的。”[1]227最终落脚在可以买卖人的“自由”之城纽约的叙述者琳达,被生活重重地伤到了:受伤的不单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精神和灵魂,更有她那颗脆弱的、充满期待的心。但不管怎样,既然绝对的自由只是一种虚妄的概念,那么对于琳达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她成为了什么,而在于成为的自由。所以,她写,故她在。面对叙事者悖论性的自由获得的方式,回顾她破碎不堪的生命,这部自传留给我们读者的又是什么样的道德自觉意旨呢?刘小枫说得好:“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1]3
五、结语
叙事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经叙事重述的现实,具有经验与伦理的双重品性,而作者对这种双重性的持守和经营,促成了自传文本中最高的现实。雅各布森通过自己价值观念的生命感悟,在自传叙事中呈现出个人独特的命运轨迹。刘小枫先生说过,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5。我们进入过雅各布森的叙事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根本变化,会否是超越了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艺术大自在呢?既然谋求幸福是伦理的基本主题,那么作者打了折扣的幸福又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伦理意义?这些大概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伦理问题吧。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张军府.现代小说叙事伦理[J].文艺评论,2011(3):8-13.
[3]Newton,A.Z.Narrative Ethic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Booth,W.C.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M].Berkeley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5]Martin,T.J.Harriet A Jacobs(Linda Brent)[C]//D.L.Knight.Nine-t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 Writers:A Bio-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6:264.
[6]Braxton,J.M.Harriet Jacobs’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lave Narrative Genre[J].The Massachusetts Review,1986(27):302.
[7]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52.
[8]Jacobs,H.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文中相关引文皆标明页码)
[9]谢有顺.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建构一种新的文学伦理[N].文汇报,2005-07-31.
[10]耿占春.叙事与抒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4.
[11]李晓林.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