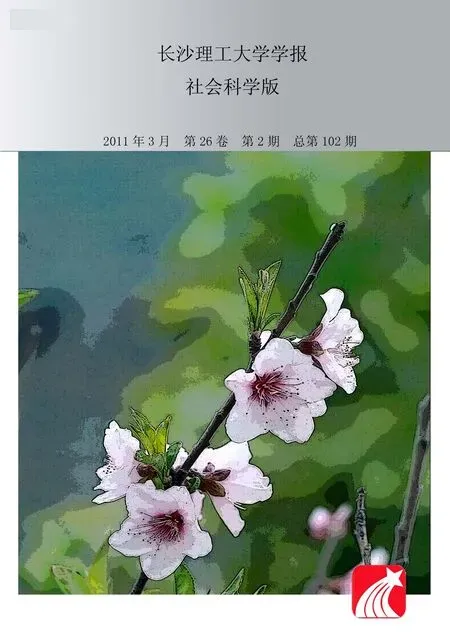技术与控制:一个技术时代难以回避的问题
盛国荣
(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技术与人类同样古老,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现代的技术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了一种新环境,一切社会现象都居于其中。但是,在技术理性张扬的技术社会中,技术似乎具有一种自主的力量,以一种异化的面貌反过来控制人和社会;而且,随着技术的大量应用而导致了目前人类正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等等。“技术问题”正逐步成为技术时代的中心问题;而且,由于现代技术的渗透性影响,几乎迫使20世纪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流派都不得不把技术当作自己的中心议题。[1]因此,德国K·阿佩尔指出,科技文明使所有民族、种族和文化面临共同的伦理学难题……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为其全球规模的行动后果负共同责任的重担。[2]这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抛却技术无政府主义对技术的放纵、技术乐观主义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技术悲观主义对技术的无助,取而代之以一种更加务实而积极的态度——对技术进行控制。换言之,在技术时代,技术与控制需要对照着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一、什么是控制
控制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于人类来说,控制是人们社会实践的关键环节,离开控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实践活动;对于生命系统来说,离开了控制,生命运动也将无法持续;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离开控制,社会也将难以存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将控与制分开来用。控,动词,本义是开弓。《说文》中有“控,引也”的解释。制,动词,本义为裁断,制作。《说文》中有“制,裁也”的解释。在西方,控制(Control)一词来源可追溯到中古英语的controllen,有抑制、限定的意思。
但是,在实际运用控制概念的时候,却出现了如加廷在评价“范式”概念时所说的那样“大多数范式概念的应用却导致了一种无处不在却毫无意义的相关琐碎的类推情况的出现,导致了似乎存在一种‘超级理论’”。[3]因此,首先要明确所谓对技术发展进行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认为美国中断超音速客机的技术开发,或者英国、法国做出促进技术开发的决策都是对技术开发的控制,那就应该把技术发展的控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阻止或延缓某种新技术开发的,可称之为反向控制;二是促进或加速某种技术开发,可称之为正向控制。人们往往对正向控制容易理解,并且确已见到了实效,但是对于反向控制却不以为然。[4]
但是,一般情况下,在人文主义领域,涉及对技术进行控制时,此处的“控制”主要是抑制和限定技术的负面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尽可能减少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即反向控制。也就是说,要对技术的研发、使用及结果的全过程的一种把握,能预测和了解并决定技术的结果,使其符合控制者的意愿,使其能促进人类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发展,尽可能地减少技术的报复效应。
二、为什么要对技术进行控制
对技术进行控制的诉求可以追溯到技能-工具技术时代的古希腊。但由于技能-工具时期的技术多与人自身的体能结合在一起,因此该时期的技术在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活动中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大范围的超越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尽管该时期的技术也存在负面效应问题。所以,该时期的技术负面效应在历史上并不是十分明显,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该时期对技术进行控制的社会意识并不是很强烈。
15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即将踏上工业时代的门槛。到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人瓦特发明的可付诸实用的蒸汽机为标志,人类社会正式开始进入以“机器”为主的工业时代。就18世纪而言,18世纪在实际方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世纪,在技术方面产生了蒸汽机,因而迈进了文明的新世纪。[5]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文明的新世纪”,随着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的逐渐扩散和应用,人们始料未及的各种技术问题也开始逐渐凸现,对技术进行控制的意识也就逐渐开始觉醒。从卢梭(1712-177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控制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技术哲学界,继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后,更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理念——技术控制主义。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烈地对技术加以控制的诉求,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的异化状态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了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对立面。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技术问题,任技术自由发展的技术无政府主义、无视技术问题的技术乐观主义以及面对技术问题而束手无策的技术悲观主义等技术理念逐渐失去了其话语权。这些“技术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类:
首先,技术对人自身的消极影响。尽管在所有的能为人类造福的财富中,再没有什么能比改善人类生活的新技术、新贡献和新发明更加伟大的了;[6]而且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技术就是人类自身的命运。然而,人自从变成有理智的动物的初期,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有毁灭的一面。[7]技术也不例外,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侵蚀着人的道德、人性、自由和精神等等诸多方面,不断消解着人之作为人的本质的东西而迷失在技术世界中,并逐渐物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结果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本性而行动的人,再也看不到他的创造者曾经赋予他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而所看到的只是自以为合理的情欲与处于错乱状态中的智慧的畸形对立。[9]而且,物质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使人失去本真的存在。因此,社会物质文明(技术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来说不是福音,而是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0]
其次,技术对自然的消极影响。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并通过技术而构建成一个暂时适合于人类居住的人工自然环境——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然而,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由技术的应用而带来的自然的问题,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等等,却实实在在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未来。实际上,只要仔细研究人类所有的技术成果为人类带来的实在利益,就会对幸福和痛苦的比例严重失调感到震惊,并且会悲叹人类的轻率行为,而这些苦难正是仁慈的大自然着意要人类避免的;而由于无视大自然给予的教训,人类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11]但是,人类却过于相信自己的技术能力,过于沉迷在自斯多噶学派以来人是宇宙中心的思想中,在培根式的“征服自然”的口号下,无所顾忌地向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大地母亲”进军,辅之以“我们的(幼稚性)剥夺能力已无限增长、却毫无对人类的情绪和愿望的自我控制能力”。[12]可是,任由技术发展到当前的状态,人类仍然无法解答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疑问——技术能征服自然吗?因为人类在通过技术手段“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历史总是印证着恩格斯所告诫的这种情形: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3]由此,2010年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谓“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的断言也许并不是“霍金式的浪漫”。
第三,技术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无论人们想象出的人类社会有多么古老,在这个社会中总是会发现技术的存在:人们可以找到没有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人类社会,但是,不会找到没有技术的人类社会。[14]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技术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技术体现在社会体制之中并且通过人表现出来。[15]然而,现代技术体现了一种特殊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必然地成了人类生活的占有支配地位的逻辑,它颠倒了传统的技术逻辑。技术解决了诸多社会问题,却同时也带来更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如技术社会的分化、技术的社会道德困境、核威胁、民族国家的独立能力弱化、社会的单向度化、社会的非健全化、世界的碎片化以及社会的风险化等等。就当前的信息技术而言,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使人类社会产生出“数字分化”和“数字鸿沟”。就像200年前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一样,今天美国正在成为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领有羊,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繁荣的新时代;而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穷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有可能处在这场数字变革之外。[16]而且,在现代技术文明中,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充满了满足和失望;它有问题地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从而使人类第一次处于通过消费社会的物体系去到处取代自然力量、需要和技术之间的开放互动,这是“技术社会的幼稚病”。[17]
三、技术为什么会呈现失控状态
不可否认,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技术的创造物;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联系,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18]技术的本质即人的本质;而且,人类进化史的基础就是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可见技术之于人的重要性。那么,与人类相伴而出现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之间中介的技术,为什么带来了上述严重的“技术问题”并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技术为什么会走向一种失控的状态?这与技术的属性以及特性不无关系。
技术后果的不可避免性。技术的诞生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只有好的一面,技术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任何技术都同时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正如法国学者让-皮埃尔·范尔南所指出的,人自以为值得庆幸的好事实际却显露出它的恶性;普罗米修斯盗出的火虽然是有益于人类的,但是火本身也同周身渗透着可拍的诱惑力的第一个女人一样,是一件可疑的礼物。[19]只有正效应而不给人类带来不愿意看到的负面结果的技术是不存在的。技术现在成了一种导管,不管人们决定在其中放入什么目标或意图,它都不可避免地会流出特定的产物。[20]只是在手工工具阶段,技术的负面效应没有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技术问题;机器技术出现后,尤其是随着现代技术扩散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技术的后果问题才逐渐凸显并呈现失控状态。
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的后果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往往难以预测,或者说,技术后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相关外延性。实际上,人类的技术行为除了产生它们的目的在取得那种结果即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之外,通常又产生一种或多种附加的、技术主体所不期望出现的结果。如在康德所言,万物一经过人手,即使是目的良好,其终结也都是愚蠢;这就是说,对于它们的目的所使用的恰好是与之相反的手段。[21]这种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人们往往很难在技术后果出现之前对技术采取控制行为,而等技术后果出现后再加以控制往往为时已晚或控制的代价巨大,如治理已经污染了环境。
技术的反自然性。技术相对于自然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它所造就的是一个人工自然,正如日本学者中山秀太郎所指出的:“所谓技术,从其出现的那天起,就是反自然的。技术……只要使自然发生某种变化,就要引起自然的破坏。因此不会有什么绝对安全的技术”。[22]自然在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促逼着的解蔽下,它们变成可估计、可统治的单纯的物质材料,被迫放弃了自己真正的存在,成为物质性和功能性的存在。[23]这种技术的反自然性后果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中,不是减少了,而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表现得越发严重,从而使得当前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等等成了现代人类社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它威胁到人类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但是,这种由于技术而引发的自然的问题往往都是积重难返,问题一旦出现,反过来再对技术进行控制,其难度和效果往往都令人沮丧。
技术的复杂性。随着技术累积发展的加速,技术基础越来越厚实,技术在发展中越来越专门化、综合化和整体化。这种技术的体系化发展成为近代尤其是现代以来技术发展总趋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技术日益专门化的今天,任何技术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要与其他一系列技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结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24]这种技术复杂性的存在,使得在通过技术来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有产生了更多的别的新问题。因此,风险是复杂性的同伴,这种通过技术来解决问题的失效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的增加必然带来风险。[25]而且,在狭隘的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和近视的国家制度的框架中实行的“技术性修补”,无补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并且也是非常危险的。[26]结果,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形,即技术在具体的细节上可以被选择、规划和理性地塑造,但作为整体,技术活动及其结果又是独立于人的、难以控制的历史力量并决定着人类的命运。[27]
当然,除了技术自身的一些属性或特性导致现代技术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外,诸多的社会性因素(如资本主义、工业化、机械化、市场化、价值观念、技术观念、自然观念等等)也是导致技术呈现失控状态的诱因。就“社会性因素”中的社会形态类型而言,当前的世界性技术问题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尤其进入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所出现的财产私有化和金钱万能化等。在私有制社会,“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28]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私有制、还存在片面追求“利润”、利益和享乐的情况下,技术的失控状态似乎也就不难理解。
四、人能控制技术吗
那么,面对日益呈现失控状态的技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技术问题,作为技术主体的人该怎么办?是任其发展还是积极采取行动?而对于所采取的行动中,人能控制技术吗?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一方面,有人认为人不能控制技术。这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有技术万能论(technological omnipotencism)、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技术悲观主义(technological pessimism)、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技术恐惧主义(technophobia)以及技术自主论(autonomous technology)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人无法控制技术的观点,认为技术是一种具有毁灭性发展的力量。随着技术的发展,最终是技术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技术。对此,法国雅克·埃吕尔在《技术的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技术系统》(The Technological System)等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9,30]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人能控制技术。这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有技术行动主义(technological activism)、技术控制主义(technological appropriateness)、技术乐观主义(technophilla)、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Technology,SCOT)、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等等。他们认为技术并没有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强调在技术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并提高人的个体的价值、生态的完整性以及文化的健康性,并注重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对技术进行控制。
应该说,在技术失控的趋势和技术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面前,尽管在个别地区、对特定技术进行控制不成问题,但在整体上能否完全控制技术和技术问题,就目前而言,仍然无法乐观地断言。诚如F·拉普所说:在应付技术问题上,人类已经表现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惊人能力。但是,个人的自我确定和社会结构是否能真正控制变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技术世界,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8](P10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在技术和技术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技术控制主义和技术行动主义等技术理念的新近兴起,就反映人们对技术进行控制的意志。他们主张采取各种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对技术进行控制,如技术的法律控制、技术的伦理规约、技术的社会系统控制(技术的政治控制、经济控制、文化控制)、技术的民主控制、国际范围内的技术控制行动等等;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生态技术、能源替代技术等等,并且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付诸实践。
尽管目前控制技术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是摆脱了技术乐观主义的盲目乐观和技术悲观主义的无助哀叹,而是进行着实际的控制技术的行动。这有助于人们“使机械看到它真正的使命、按照它的能力来为人类服务,使被机械变得更卑躬屈膝的人类能够通过机械的使用而再次站立起来,敢于面向天空”。[31]
当然,在肯定人能控制技术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困境,如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的“控制困境”、[32]技术性修补的困境、能控制而不控制的困境、局部能控制而全球范围内整体性呈现难以控制的困境以及“公有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等等。[33]对此,控制技术的未来出路何在?严重技术依赖的人类的未来何在?康德曾经勾画了一种设想:人类的普遍意志是善的,但其实现却困难重重,因为目的的达到不是由单个人的自由协调,而只有通过存在于世界主义地结合起来的类的系统之中、并走向这个系统的地球公民的进步组织,惟有如此,人类的未来才能够有希望。[34]马克思、恩格斯则设想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解决技术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并实现人类对改造自然的活动的自觉控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5]换言之,当前技术的控制方面尽管存在着暂时的困境,但人类的未来却是充满希望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人而起,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改善人的行为得到解决”。[26](P5)突破技术控制的困境、确保人类的美好未来,这一切都掌控在人类自己的手中。人类主宰了自己过去的命运,同样也能主宰自己当下和未来的命运。
五、结束语
技术是人类自己的宿命。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技术的创造物。人与技术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人类再也无法退回到无技术的生存状态。然而,人类自从获得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与技术的同时,也得到了宙斯的“礼物”——潘多拉以及潘多拉的盒子。当前,人类几乎在所有领域都面对着现代技术都侵袭,面对着它向人类、自然和社会展示的种种人造难题与风险。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力量,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和人类未来的生存。
尽管技术存在着种种风险并已经带来的种种技术问题,但如技术悲观主义那样简单地拒斥技术的态度是不够的和不可取的。盲目地攻击技术世界,这或许是愚蠢的;想把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的勾当,这或许是目光短浅的。我们依赖于技术对象,它们甚至强求我们不断地对技术进行改善。我们以外地牢牢地束缚于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陷入对它们的屈从之中。但是,为了阻止技术危险的波及度,我们不应该把技术置于一旁,而是应该通过完全地揭示构成技术的特征的危险去正视它,“冷静地对待事物”[36]。这种危险的显示绝非是某种否定性的东西,相反,它可能最具解放性和救助性。
因此,面对技术社会中的种种技术问题,并不足以摧毁我们对人的理性、善良意志和控制技术的能力所抱的信心。“只要我们能够考虑到其他的选择,我们就不会被毁灭;只要我们能够考虑到其他的选择,我们就还有希望”。[37]以控制的理念、信仰与实践来对待技术,也许是技术社会中人类未来的一种积极的救世之路。
当然,要完全控制住技术可能是不现实的。虽然控制技术的征程充满困境并且路途遥远,但如英国诗人亚瑟·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所言:“战斗过,却失败,总比从未战斗过好”。[38]
[参考文献]
[1]陈昌曙.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6):29-36.
[2][德]K.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等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259.
[3]Garry Gutting.Paradigms and Revolutions, Appraisals and Applications of Thoma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M].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O:125.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81.
[5][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61.
[6][英]M.戈德斯密斯.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赵红州等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20.
[7][苏]格·沙赫纳扎罗夫.人类向何处去(陈瑞林等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79.
[8]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9]李瑜青.卢梭哲理美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191.
[10]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资料(第五辑)[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5.
[11][法]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9-152.
[12][德]狄特富尔特.哲言集:人与自然(周美琪译)[Z].北京:三联书店,1993.213.
[1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14][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董茂永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6.
[15][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234.
[16]胡延平.第二次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
[17][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51-152.
[18][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译)[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8.
[1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22.
[20]Winner Langdon.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 [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8.278.
[2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94.
[22]肖峰.从技术的人文定位想到的[N].北京:中华读书报,1998-05-13(03).
[23][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3.
[2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36-137.
[25][美]尼古拉斯·雷舍尔.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吴彤译)[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214.
[26][美]欧文·拉格兹.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异端的反思(黄觉等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27]Friedrich Rapp.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New York: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1.134.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8-449.
[29]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4.
[30]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New York:Continuum,1980.
[31][法]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王作虹等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271.
[32]David Collingridge.Critical Decision Making:A New Theory of Social Choice[M].London:Frances Pinter Pub.,1982.
[33]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Vol.162,No.3859,1968.1243-1248.
[34][德]伊曼努尔·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6.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26-927.
[36][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8-199.
[37][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73.
[38][美]罗兰·斯特龙伯格.现代西方思想史(刘北成等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