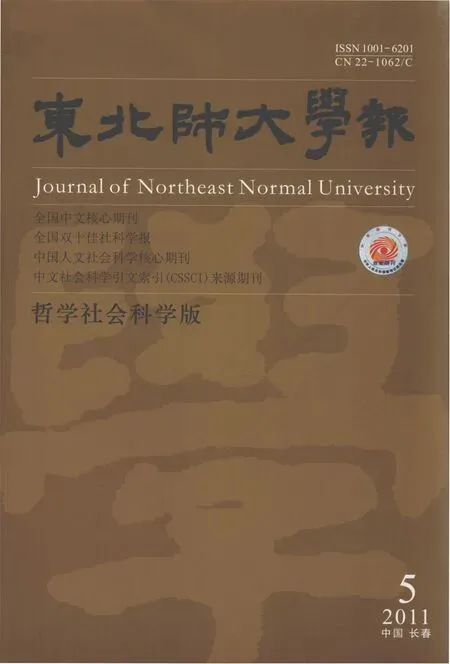不伦之恋,无间地狱
——探析《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救赎之路
宫玉波,郝运慧
不伦之恋,无间地狱
——探析《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救赎之路
宫玉波1,郝运慧2
本文通过不伦之恋&无间地狱这一文学叙事模式来探讨《红字》中罪与救赎这一主题,特别是牧师丁梅斯代尔艰难、痛苦的救赎历程,并探析造成他在救赎路上的延宕之因,即清教思想的体制化和牧师自身的智性化倾向。同时探讨霍桑在清教主义语境下对普遍的救赎之路做出的尝试。
丁梅斯代尔;无间地狱;救赎
不伦之恋&无间地狱式的悲剧爱情是备受欧美作家青睐的一个创作主题,似乎已沉积在其创作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在近现代的欧美文学中,涉及此主题的名作屡见不鲜——《红字》、《喧嚣与骚动》、《无名的裘德》、《洛丽塔》、《荆棘鸟》、《巴黎圣母院》等等。其中描写的教民恋、兄妹恋、婚外恋以及父女恋等一系列为世人所禁忌的爱情和悲剧,无不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诚然,禁果也许异常甘甜,但无一例外都需付出巨大代价。正如《荆棘鸟》中作者题记所言:“这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本文欲通过不伦之恋&无间地狱这一文学叙事模式来探讨《红字》中罪与救赎这一主题,特别是牧师丁梅斯代尔艰难、痛苦的救赎历程,并且探析造成其救赎路上延宕的因素。
一、隐形的红字 分裂的人格
在《红字》这部小说中,那个“熠熠发光的、妙不可言的”[1]34的A字无处不在。在通奸之罪被发现并审判后,女主人公海丝特选择了佩戴着有形的A字,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罪,以一位殉道者的姿态走出了一条平静、光明的救赎之路。而与之通奸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却因虚伪、怯懦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的考虑,选择了背负着无形的A字,在无间地狱中遭受历练,在分裂的人格中自我折磨。从表层意义上说,牧师丁梅斯代尔似乎逃脱了教会与民众的审判;但在内心深处,他却一刻也没得到安宁。上帝的注视、情敌的窥探、良心的拷问使他游离于人生的两极、日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公众面前,他光辉圣洁犹如上帝的天使;面对自我时,他怯懦、虚伪,是骗子、是罪人。在他的生活中,只有“暗影”与“人格面具”的永恒冲突,只有处于人生两极的焦虑与压抑,而没有作为真实自我的缓冲,因此他只能终日在自我分裂中放逐、折磨着自己。
丁梅斯代尔的人格面具是一个正派、善良、博学、雄辩、备受崇敬的牧师;他摒弃一切的世俗、情欲、本能的需求,极力压制心底任何一点的暗影向自我显现,把整个的自我与这种人格面具等同起来。但是,他又无法压制来自“暗影”的赎罪呼唤。“他是被那追逐得他无地自容的悔恨驱赶到这里来的,而这悔恨的胞妹与密友则是怯懦。每当悔恨的冲动逼迫他走到坦白的边缘时,怯懦就一定会用颤抖的双手把他拖回去”[1]99,回到人格面具所容许的世界里。于是他只有靠在密室中禁食、鞭笞自己等一系列的自虐行为来减轻一些心理上的紧张状态。他之所以不肯袒露 “那颗怀有秘密而又负罪感的心”,是因为他此时已被无形中膨胀起来的人格面具所占据和支配,无力恢复本真的自我。这一面具把他推上了荣光的巅峰,得到万千教民顶礼膜拜;也是这一面具把他拉向了压抑痛苦的深渊,忍受长达七年之久的“难言的折磨”。但是,上帝的注视、内心“暗影”的呼唤、齐灵渥斯的无情窥探终于使他的人格面具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他选择了在总督就任的盛大日子,向所有人袒露实情,他走上了那个梦游时曾登上的耻辱台——“牧师站在那里,脸上泛着胜利的红潮,仿佛一个人在极端痛苦的紧要关头获了一次胜利,随即就倒在了刑台之上”[1]178。此时,丁梅斯代尔胜利了,矛盾体对立的双方终于在此达到了和解,完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心灵得以重塑的过程,他的暗影获得了显现的机会,并且与其真正的人格面具合二为一。虽然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但他的人格在人格面具和暗影重合之后获得了新生,走出了无间地狱,实现了救赎。
二、体制化的清教 妥协的囚徒
霍桑把《红字》这部小说的背景置于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当时流亡到此的清教徒怀着“天定命运”的使命感,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欲在这片荒野之中建立一座“上帝之城”。为了在新大陆站稳脚跟、履行上述使命,清教徒们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定严格、专制的教义,整个新英格兰到处充斥着阴郁恐怖的气氛。这一切都可在全书的第一章“狱门”中初见端倪:“新殖民地的创建者们,不管他们原先计划建立的是什么样的人类美德与幸福的乌托邦,一定会在处女地上圈出一块做墓地,另一块修建监狱,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殖民地草创时期不可或缺的东西”[1]39。由此可见这些早期来此的清教徒们抵御一切世俗、情欲以及人的一切自然、本能的需求,践行苦修、戒律、虔诚忏悔,以求洗清身上的罪恶,获得救赎。严苛的清教主义思想作为集体无意识已经渗入到每一个教民的骨髓与细胞,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严酷的清教体制把人的自然的、本能的生命意志不断削减,以谦卑侍奉上帝为最高美德、以自我的张扬为罪恶之首。它就像一座无形的“圆形监狱”,里面的囚徒不仅在行动上受着无所不在的“监视”,而且灵魂也在受“奴隶道德”的“规训”。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惊呼:这种“圆形监狱”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17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体制无意识之中便成了福柯式的“圆形监狱”的翻版,它“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止息的监督”[2]。它就像一个人格面具罩在了所有新英格兰教民的脸上,使其无时无刻不在“上帝”的“监督”之下。久而久之,教民们便形成了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的执行者,他们变得谦卑、怯懦、散尽原始的生命意识和反抗能力。如果说教民们是麻木地将这一人格面具罩上,那么丁梅斯代尔则是有意识地把这一面具罩上,而且越罩越紧。他潜心钻研教义、严于律己、以标本式的虔诚布道来回报上帝的恩宠。作为清教主义的代言人,他的牧师身份以及内心对这种思想的完全认同使他不敢越出这一体制半步,只能终日生活在内心的折磨之中。
虽然备受煎熬与折磨,但是丁梅斯代尔从未想过逃走。清教体制的“规训”已经浸淫到其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抽走了他作为自然人的血性与行事的勇气:“我没有力量出走。像我这样一个不幸的罪人,我已经没有别的想法,只求在上帝给我安排的地方苟延残喘、了此一生。虽然我已失去了我自己的灵魂,但我仍然可以尽我所能为别人的灵魂做些事!虽然我是个不忠于职守的卫兵,凄苦的守卫终了时,所能得到的报偿只是死亡和耻辱,但我仍不能擅离岗位”[1]178。此时的丁梅斯代尔虽然觉得没有救赎的希望,但他仍然甘愿做上帝忠实的奴仆,直到生命消失殆尽。可见,丁梅斯代尔完全自觉地成了清教体制的囚徒,并最终成为这一体制的殉难者。
三、智性化的局限 延长的痛苦
体制化的清教构成了丁梅斯代尔悲剧的内因,但其自身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他的博学多才使他成为万人敬仰的牧师。但同时他的知识与智慧亦赋予了他神经质般的敏感与压抑、哈姆雷特式的忧郁与踌躇、卡夫卡式的迷离与无助。知识把他装扮成光辉圣洁的天使,导引着人性的方向、播撒着天国的慈善与良知;但知识也使他宁愿受刑于无间地狱,而不能战胜怯懦、撕掉虚伪。正如亚当、夏娃因食智慧之果而失去天堂乐园,因此求知的同时便会有开启智性的痛苦,便会开启智性与心灵的冲突,这便成了人间一个永恒的隐喻。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言:“知识就是力量”。几百年来,人们在颂扬知识的力量的同时却极少对知识进行质疑与反思,对知识的悲剧更是关注甚少。知识的力量永远都是建设性的吗?暂且抛开丁梅斯代尔的悲剧不谈,中外有太多的饱学之士皆因智性的灼热而煎熬于心神憔悴,甚至走向自我毁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哈特·克莱恩、海明威,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沃尔夫,俄国诗人叶赛宁、法捷耶夫,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台湾女作家三毛,著名学者王国维、诗人海子…… 这些竞相走向陨落的巨星无不在一个层面上说明这样的道理——知识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无力感,即对生命本原的轻视、行动能力的减弱、痛苦的增长、甚至于信念的丧失。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指出英语中meaning(意义)一词和moaning(悲叹、呻吟)在古英语中是同一个字[3],这似乎也在影射着谁欲探究事物的意义本原将会走向痛苦与无奈。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也曾言:“智慧之灯愈明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才了解我们竟是这样一幅可怜相,而兴起悲哀之念”[4]。德国作家歌德在其巨著《浮士德》中,将知识悲剧冠于五个阶段之首。老浮士德虽已钻研了哲学、法律、医典与神学,最终却悟得:“我一切的欢娱从此远去,再不想,求得什么卓识真知……”[5]。学问、知识就像一场浮华的语言骗局,并未把握住生活的精髓,反而却抑制了本然的生命。
作为新英格兰牧师中学识的典范,丁梅斯代尔自然是这场语言骗局的俘虏。对智性的热衷造就了他多思而忧郁的本性,并进而造成了行动上的延宕。在“牧师夜游”一章中,同样有着智性化特质的齐灵渥斯一语道出了智性化尴尬的局面:“我们读书人,埋头在书本里……我们醒时做梦,睡梦中走路……”[1]139。正是这种现实与梦境的两界游离为丁梅斯代尔增添了太多的假设:“如果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丧尽良心的人——一个本性粗野的恶棍 ― 我也许在很久以前早就找到了平静”[1]172。而正是这种假设延长了其救赎路上的痛苦。正如《旧约·传道书》所言:“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结 语
作为人类心灵幽暗处的探索者,霍桑在自己的被称之为“传奇”的作品之中,以寓言的手法挖掘着“人性的真”,他用自己的艺术揭示着人类命运的困境。在他大多数作品里,中心问题并不是神学上的罪恶问题,而是这种罪恶的信念在早期的殖民者心中所产生的心理后果[6]。对于霍桑内心的罪恶情结,公认的解释莫过于祖辈的所行在其心中留下的“历史重负”。因此,霍桑一方面认同清教的主张,深感人性之堕落、罪恶之普遍。然而,做为惯用讽喻的艺术家,霍桑又是超然的,他站在人道的立场,批判清教的专制与严酷。霍桑的这种“含混”或者“矛盾”其实是他对清教体制下救赎的普遍意义做出的思考。在上帝与罪恶不可调和的清教徒极端主义本体论中,竭力寻找单一的终极意义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漩涡,进而导致自我的分裂;当众忏悔前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好小伙儿布朗便是绝好的例证。霍桑在其创作中一直在尝试探求一条救赎之路,来消解这一绝对二元对立的危机[7]。他塑造出海斯特· 白兰、米丽安等形象,她们先为罪恶所丑化,又为恩典所改造,通过苦修、内省、行善、忏悔等方式达到道德和精神上的升华。牧师丁梅斯代尔虽然生命消殒,但却在临终前勇敢的忏悔中获得了救赎。可见,在肯定上帝的存在、善恶并存的世界中,走向道德、走向人性的复归是霍桑对救赎之路做出的可贵尝试。
[1][美]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姚乃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30.
[3]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54.
[4]叔本华.生存空虚说 [M].陈晓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66.
[5]歌德.浮士德 [M].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1.
[6][美]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汤潮,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8.
[7]张晶.霍桑与救赎 [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6.
I106.4
A
1001-6201(2011)05-0219-03
2011-05-0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09JBZ022)
(作者单位:1.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2.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