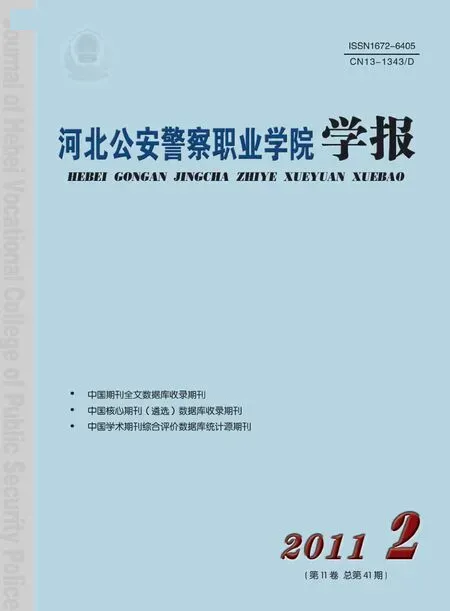关于制约警察使用枪支权力的对策分析
李晓军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关于制约警察使用枪支权力的对策分析
李晓军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当今社会,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必须建立在保护人权的基础上,而每一个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也都要处理好以警察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失控问题,虽然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有助于巩固执政地位,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为此,我们在分析警察“任意”使用枪支原因的基础上,强调要通过修改相应法律、进行司法审查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措施规范和制约警察使用枪支权力。
警察使用枪支;权力制约;司法审查;案例指导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警察权的扩张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如果过分依赖警察权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甚至因此纵容警察权对基本人权的任意侵犯,不仅无助于培养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普通民众和国家公权力的对立,杨佳案后普通民众的反应已说明这一点。不能把警察权当做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而是要当做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这样才不会对本已孱弱的法治环境造成破坏。这就是“不让警察乱开枪”的真正意义。在那些社会秩序良好的国家,警察权无一例外会受到严格约束,人权得以充分保障。对基本人权的敬畏和尊重,理应成为警察权行使的常态。
一、警察“任意”使用枪支的原因分析
(一)体制内部对于警察“任意”使用枪支的纠错能力有限
目前,国家对警察使用枪支并不是没有规制,从政治层面上讲,执政党比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来控制警察用枪。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专门开展了“三项治理”活动,即治理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的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2003年公安部又针对当前公安机关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五条禁令”,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都与严格控制警察使用枪支有关。第一条:“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第二条:“严禁携带枪支饮酒,违者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主张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事件中要坚持“三个慎用”原则,即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考察中国警察因为枪支问题而被追究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的案例,我们发现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如贵州的安顺案件,其特点是直接触犯了刑律。触犯刑律当然也违反了《条例》,但涉案警察是因为触犯刑律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我们极少看到警察仅因为违反《条例》而承担法律责任的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二是因为警察在枪支管理上出的问题。“五条禁令”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因为枪支是危险的,同时又是公权力最醒目的符号,把枪交给警察就要保证枪的绝对安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基层警察不愿带枪巡逻的重要原因)。警察对枪支管理不善,如枪支丢失或被盗抢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寻枪”往往会成为地方警察的主要工作。电影《寻枪》就是一个很接近真实的样本。笔者认为这种体制内的规制所存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规制的范围有盲点。对于公权私用的个人“任意”用枪有规制(以前述案例六为代表),但对警察在执行公务活动表现为武力的过度使用的“任意”保持沉默。至于“三个慎用”原则是专门针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那种)。在这种特定环境下,对个别对象依法开枪的行为往往成为引燃大规模暴乱的火种,基于维稳的考虑,警察甚至在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下,也不应考虑使用枪支,这也是维稳的代价。二是侧重于从管枪、控枪的角度来加强对枪支使用的管理,主要防止“枪支走火”和公权私用。这符合政治对行政的控制的性质,因为不具有分权的特征,所以,仍然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监督”,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强调警察使用枪支要对上负责,要体现人民警察的对党忠诚,这与中国警察的工具性政治法律地位是吻合的。相应的会忽视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在“枪口”下的保护。三是警察使用枪支的报告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根据《条例》第13条: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应当将使用武器的情况如实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也就是警察向领导报告,下级公安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在欠缺外部因素介入的情况下,报告制度只是体制内的信息循环,其对使用枪支的规制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说是不能报有很大希望的。
(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匮乏和失效
体制内部对于警察“任意”使用枪支的纠错能力偏弱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人民警察特殊的政治使命和法律责任,使得警察权的运用在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生活中具有超越其他行政和司法权的作用和影响,以公安机关为代表的警察权的独大问题根深蒂固,具有其自身的系统性和结构。而现行的《人民警察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受到检察院、监察部门或上级警察机关及社会、公民的监督,至于如何监督以及出现问题怎么办,均没有详细的实施细则,使警察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1.依照中国的政权体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具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限制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作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行政机关中的公安机关和安全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具有彼此独立的职权,但在刑事诉讼中又共同担负“惩罚犯罪”的责任,依 《宪法》第135条和 《刑事诉讼法》第7条的规定,在进行刑事诉讼、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使得审判机关难以要求对公安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的合法性进行及时有效的审查,并借此对其权利受到非法、任意限制和剥夺的个人提供有效救济,而且也影响了检察机关现有的对公安机关的有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权力的有效行使。无论是《人民警察法》、 《行政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事诉讼法》等众多法律都赋予了人民警察超乎想象的巨大权力,公安机关不仅具有行政职权而且掌握着司法职权(侦查权)。司法实践中,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权力被人为地交叉使用——运用刑事侦查权进行治安行政管理,将行政性强制手段作为侦查破案、获取嫌疑人口供的方法等,导致出现了法律监督的“盲点”。而一旦将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定性为侦查刑事案件,则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就很难行使法律监督权,因为对于刑事侦查权的监督往往是在案件进入起诉和审判阶段才能进入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规制的“视线”,而在此之前,几乎是公安机关排他性的职权。目前对于在此阶段所发生的职权行为的监督不仅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无有效的具体措施。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不理会对其提出监督的要求,而无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而警察使用枪支后也只是向所属机关报告,并无向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报告的义务。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知情权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也无从监督和制约。“没有知识的渗透,就没有权力的制约”。
2.法律救济途径的阻隔
如果对于警察开枪属于刑事侦查权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则相对人将失去获得法律救济的正常途径。如发生在兰州的讨债人姜云春被击毙案,其家属先后向兰州市政府和甘肃省公安厅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击毙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不当”,均未被受理,其理由相同:“根据 《行政复议法》第17条的规定,该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后其家属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也是兰州警方行为属于刑事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因此不予受理。而如果要申请国家赔偿,依《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应该首先向行为执行部门提出赔偿要求,要求被拒绝后,才能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在本案中,首先应该向执行击毙的兰州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案发至今,姜云春之子姜伟先后在兰州、甘肃以及北京三级公安、法院、检察院奔波,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本案一直未能进入司法程序。姜云春被击毙不久,兰州市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死亡证明,将姜云春定性为“犯罪嫌疑人”,但却没有说明他涉嫌什么罪名。姜伟曾多次要求兰州市公安局公开击毙姜云春前后的录像,均遭到拒绝。他认为,父亲的行为最多只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5款所规定的“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根本够不上刑事犯罪,更不应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击毙。
3.国家赔偿中司法审查的局限性
根据《条例》第14条:人民警察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到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员,由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赔偿。第15条: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无辜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由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而根据 《国家赔偿法》(1994)第9条和第20条的规定,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刑事赔偿都必须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确认,也就是要求“自己承认自己违法”。这在实践中很难想象,导致国家赔偿名存实亡。正因为兰州市公安局至今不予“确认”开枪击毙姜云春的行为违法,姜伟申请赔偿的案件也就一直不能进入司法程序。最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2010)则取消了先行确认的程序,对于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的,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因此,使警察使用枪支的职权行为进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具备了可操作性,对于保护公民权利,控制警察违法使用枪支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2010)第3条第4项和第17条第5项的规定,其所限定的赔偿范围仍然是“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因此,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仍局限于是否合法的问题,无法审查合理性问题,以及具有更强规制性的“任意性”问题。即便是审查合法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的约束,司法审查的效果不容乐观。
4.正当程序的欠缺
正当程序是对公权力使用的过程性控制,但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过程与一般公权力的运用过程不同:从空间上看,是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这样一个对立而又复杂的环境,从时间上看,从作出开枪的决定到将子弹射出,往往在瞬间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正当程序的运作空间十分有限,很难保障相对人的参与。也就是说在作出剥夺相对人的行为能力(甚至是生命)时,本应听取他的意见,让他享有自我“防卫”或“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并且有第三方来“听审”。笔者认为“条件”虽然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依正当程序的精神来理解,警察开枪前的警告和谈判应当视为正当程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方面存在两个明显的的问题:一是警告的内涵不明确,以至于相对人尚未意识到后果的严重程度,有的以鸣枪代替警告,可能导致相对人陷入恐慌而失去正常的辨识能力,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二是把谈判当做事件处置的一种手段和技术,而不是从程序正当的角度发现它的独立价值,因此,也就没有把谈判作为事件处置的前置程序来看。这无疑增加了警察“任意”使用枪支的可能。
警察“任意”使用枪支问题具有系统性,对其产生的原因也要进行系统的梳理,有些因素亦不应回避。如众所周知的警察队伍自身的素质问题(包括谈判专家的缺乏)、警察训练问题、警察内部指挥和管理机制问题等。笔者与一线警察交流时,曾问过他们是否知道警察开枪的法律依据,得到的答案是:开枪的依据是领导的命令,一旦下令,“不怕你把人打死,就怕你打不着”。这是他们从经验出发的、最具实证的免责依据。这固然反应了基层警察法律意识的淡漠,但更多体现的还是警察权的监督和制约问题。所谓“纲举目张”,解决问题还是抓主要矛盾,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就忽视次要矛盾。
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力量,具有强制性和不对等性,当其不受限制地被运用时,必然出现无限扩张的异化倾向。在社会转型期,犯罪诱因增多,犯罪控制手段相对滞后,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如果被暂时的严峻社会治安形势所震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人民警察当做纯粹的“枪杆子”,抛弃或者忽视人权保障,片面强调维护社会秩序,警察权就会成为一柄失去控制的双刃剑,随时可能伤及无辜。因此,法律需要对警察权进行有效而系统的规制,防止警察权力被滥用,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要环节。
二、控制警察“任意”使用枪支的对策分析
(一)相应法律法规的修订
剥夺公民生命权的规则只能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这也是贯彻《立法法》的要求,因此,必须将《条例》升格为法律,以表明国家对生命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承认。建议该法的草案由公安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起草。新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法》应着重体现对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有效“控权”,从源头上防范警察“任意”使用枪支的行为。
1.明确枪支使用的禁止“任意”原则
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绝对必要原则。要求警察只有在必要时,且有说服力的证据相信犯罪嫌疑人将会对警察或者第三人造成导致其死亡或重伤的现实威胁时,警察才可以使用枪支。因此,对于违法和一般的犯罪行为不得使用枪支来制止。此原则可涵盖《条例》的15种可以开枪的情形,比繁琐的列举式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别无选择原则。要求警察为制止上述犯罪,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开枪没有其他选择,亦即警察开枪是唯一选择。警察在开枪前必须做了其他替代方法的尝试和努力,如使用警械和非致命性武器等。三是非致命原则。要求警察开枪尽量避免造成犯罪嫌疑人的伤亡,因此只能瞄准犯罪嫌疑人非致命部位开枪,开枪击毙犯罪嫌疑人只能是例外情况。
2.法律程序的约束
主要应规定以下内容:一是将使用警械(可考虑把非致命性武器归入警械类)作为开枪前的必经程序,把谈判作为对劫持类犯罪处置的前置程序,不使用警械和不谈判就使用枪支只能是例外情况。二是开枪前口头警告的内容应当明确,必须让警告对象明白无误地知晓不听从警察命令的后果是:警察开枪!一般不允许以鸣枪代替口头警告。三是改革警察用枪后的报告制度。《条例》第12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造成犯罪分子或者无辜人员伤亡的,应当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勘验、调查,并及时通知当地人民检察院。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应当将犯罪分子或者无辜人员的伤亡情况,及时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第13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应当将使用武器的情况如实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笔者认为这种自己向自己报告的规则,违反了正当程序的精神,不利于其他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应修改为:警察使用枪支后应立即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如造成犯罪嫌疑人或者无辜人员伤亡的,应立即向所属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报告。当地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参与案发现场的勘验、调查。调查完成后的书面报告由人民警察院向社会公布。
3.法律责任的承担
对警察开枪事件的初步处理主要是根据调查报告的结论。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经调查发现警察使用枪支合法的,就公布调查结果,终结调查;二是确定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违法,给予行政处分;三是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这三种情况均不影响相对人及其家属向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提出赔偿或补偿的权利,也不影响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以上涉及到人民检察院权限变动的内容,应相应地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以保证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
(二)司法审查与救济制度的完善与突破
司法审查的作用和意义就在于通过法院受理相对人的行政起诉,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保障和补救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效规制警察使用枪支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一致的。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解决本文的问题而言,尚有两点不足,需要完善和突破。
1.保障司法审查的中立性和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审查之所以能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滥用情况,与司法权的性质和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要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做出公正裁判,必须由一个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机构来承担这个任务,也只有具备这样“品质”的机构才能胜任这个工作。对因警察权行使而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纠纷的裁判也应由一个独立机构来完成,这也是民主社会基于正当程序的要求,如《英国警察改革法》就明确规定:凡是被投诉的行为造成死亡或重伤的,主管部门必须将投诉提交独立的投诉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因此,人民法院对警察使用枪支的审查也必须保持中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的法制监督不能取代法院的司法审查。为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地位首先应当得到保障。关于中国的司法独立的建构路径问题,学界论述颇丰,笔者不再赘述,当务之急是先从立法上确认法院对警察权的审查范围,笔者认为凡是因警察权的运用导致相对人重伤或死亡的,相对人或者其家属可以针对此行为向法院起诉,而不论行为是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还是刑事侦查过程中,由法院统一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构成犯罪的,移交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立案侦查。
2.扩大司法审查的尺度
“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因此,司法审查是有限度的,以避免违反国家权力分工的原则,导致司法审查制度的异化。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拓展和深化,行政权的扩张愈演愈烈,行政权的滥用已成为公民权利被侵犯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审查仍囿于合法性审查就不合时宜了,因此,有必要考虑扩大司法审查的尺度,以更好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建议把“警察因违法或不当使用武力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的”的情形通过《行政诉讼法》或《国家赔偿法》作为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遗憾的是新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改变对警察使用枪支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规定)。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对警察权的扩大而予以“对抗”和制衡的需要。因为“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法院并非主动扩权,而是因应行政权扩张而予以必要的制衡,并不改变司法的被动性质。二是基于对法律原则适用的限制。笔者认为,司法针对行政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一项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适用与法律规则适用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原则有例外。而能够构成原则的例外事项一定是基于保护某种重大法益的考虑,公民的身体和生命正是这样一种重大的法益。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既然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事项都可以进行合理性审查,更应当对造成公民身体重伤或死亡的事项进行是否合理、是否“任意”的审查。
(三)建立警察使用枪支的案例指导制度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因为情况紧迫,往往很难准确把握特定情境下是否应当开枪的条件,既可能导致对枪支的“任意”使用,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也会导致放纵违法犯罪后果的产生,危害公共安全。因此,有必要借鉴判例法制度,因为“判例法的优点在于其具体性、可比较性、可区别性,因而能有效克服立法规则的抽象,有效地补充法律解释的遗漏。”建立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案例将制定法转变为活的法律,以统一警察使用枪支的条件和尺度,以利于形成警察内部的约束机制和纠错机制。如针对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情况,是否应当开枪并将其击毙,就必须考虑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如2009年10月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4名重刑犯杀死一名狱警后逃跑的案件,在追捕过程中,其中一名逃犯高博在逃跑时突然转身用匕首刺向一名警察,并一连刺了3刀,导致该警察受伤,其中第一刀刺向该警察的颈部,因被手挡住,只划伤颈部,第二刀也被手挡住,手部被划伤,第三刀该警察左腿被捅了一个8厘米深、4厘米宽的刀口。后高博被赶上的另一警察开枪击毙。该案件中,高博在监狱内参与策划和实施越狱和杀害狱警的行为本身就涉嫌暴动越狱罪和故意杀人罪两项重罪,该犯应当很清楚一旦被抓获后的法律后果,在被追捕过程中,又极力反抗,直接追求杀死杀伤追捕警察的后果,足以认定该犯具备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警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条件下,开枪将其击毙是妥当的。试比较另一案例:2010年2月28日发生在上海的赵某劫持女童案,该案中,赵某先闯入一家饭店厨房抢到一把菜刀,出来后见人就砍,在群众报警后,又劫持一名五岁女童,在警方赶到前,将女童颈部割伤,警方赶到现场后,赵某将女童向前方抛出,并在逃跑的路上继续挥刀乱砍,又导致两名过路群众受伤。经警告无效后,警察开枪将其击毙。女童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赵某与一般的劫持人质的情况很不一样,赵某并没有把人质当作筹码要挟他人以达到其追求的目的,也没给警察与其进行谈判的机会,在逃跑过程中继续行凶,表现了一种极端的暴力倾向,也足以确认其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警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条件下,开枪将其击毙也没有问题。通过对案例的归纳,可将人身危险性的要素分解为:所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使用的凶器的危险程度、逃跑过程中是否继续犯罪、是否有袭警和抢夺枪支等武器的行为等。《条例》中的其他“判明”问题,也可通过案例来进一步明确。
目前,中国各地方以公安机关为主,为了实战的需要,也编纂了许多警察使用枪支的案例,但对案例的认识并不统一,甚至出现相反的观点。如前述的讨债人姜云春被击毙案,其家属向兰州市政府和甘肃省公安厅申请行政复议,未被受理;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也未被受理;申请国家赔偿也没有结果。而重庆市公安局在2006年组织编写的《成与败——公安执法实务案例评析》一书中,已将该案件作为反面典型来分析,批评该案件在处置上存在重大过错:一是没有引入谈判解决的方法,二是使用武器不当。笔者建议由公安部组织编纂此类案例,并有明确的结论,每年编纂一次,形成年报,下发地方警察机关学习,作为以后处理类似案件的指导标准。如警察违反案例中的指导标准,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警察机关内部也要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笔者相信该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和完善,最终将形成相对稳定的、妥当的、具有很强指导性的使用枪支的参照系。
[1]孟建柱.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党的忠诚卫士和人民群众的贴心人[J].求是,2008,(21)∶18.
[2]班文战.中国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实施:义务、职责、问题与建议[A].白桂梅.法治视野下的人权问题[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马建文.警械武器使用的原则与法律救济[J].学术论坛,2008,(2)∶109.
[4]刘伯祥主编.外国警察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5]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枪声响一贼亡余落网[N].扬子晚报,2009-10-21.
[8]持刀男劫持女童被击毙[N].现代快报,2010-03-01.
D631
A
1672-6405(2011)02-0028-05
李晓军(1969- ),男,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讲师,主要从事公安法学研究。
2011-05-18
王凤玲]
——献给为战疫而奉献的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