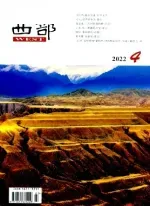爱上施西(下)
文/高寒
爱上施西(下)
文/高寒
“你马上过来,我在马可波罗。”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施西又发飙了。
“我没空,要值班。”
“放屁!我刚查过,今晚不是你值班。”
“我真的没空。”
“反正我身上没钱,咖啡已经喝了。你现在不过来,打烊时你还是要到派出所放人。”说完她挂了电话。
我只好过去,非常不情愿。
“表现不错,这么快。”施西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她这种神态已经消失很久了。她稍加打扮,不再那么邋遢,让人觉得清爽漂亮多了。
我站着正视她:“发什么神经,走吧,我买单了。”
“不,我还没喝够,你就不能坐下?”
我只好在对面坐下,要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
“我没想到你也会骗人,看来这世上唯一诚实的人也死了。”
“我真的有事,一个学生家长要上法院告我嫂子,我必须去跟他们沟通,争取私了。嫂子带了十几个家教,有个男孩是全日制地寄住在他们家。前几天,那孩子忽然在课堂上昏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严重贫血,营养不良。那孩子家长是做生意的,很有钱、没知识,没空带孩子,就一个月给我嫂子一千二。结果这样,那家长心疼得不得了,告我嫂子虐待。”
“变态,你嫂子。”施西鄙夷不屑地说。
“她娘家穷,从小穷怕了,所以现在变本加厉地想赚钱。”
“是不是只有成为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你才不会视而不见,才会有感情?”施西慢慢啜一口咖啡,笑眯眯地问。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我妈说我像沙滩上的石头,硬冷。我只是把一切当事情来做,事情出现了摆在眼前总要应付,就这么简单自然。”
“你父母是怎样的人,怎会养出你这样一个怪胎,真不可思议。”
“我父亲是个渔民,很会打渔。过去我们村那些置了船的人家都争着雇他当船老大,但他家兄弟姐妹多、穷,没人愿意嫁给他。后来,媒婆介绍了我妈,我妈娘家更穷,我妈又不好看,就那么回事了。我妈会理家能吃苦,她上要侍奉公婆,下有五个小叔小姑,还有个老祖母,为此她拼命干活,劳碌一生就是她的命。”
“你父母感情好吗?”
“不知道,我父亲沉默寡言,每天早出晚归,母亲家务乱如麻,他们都很忙,很少讲话。我想母亲对我父亲应该是很敬畏的,她有时受了委屈想向我父亲诉苦,父亲双眼一瞪她就低眉顺眼了。父亲高大英俊、有棱有角,又是家里的主心骨,这是母亲一辈子依顺他的原因。”
“哪一天带我去看看你的故乡。”
我摇摇头,默然失色。
“吝啬,看一眼又不会怎样,又不用你花钱。”
“肉眼看不见了。”
“那该用什么看?”
我指指胸口:“心。”
“为什么?”
“童年的故乡已经在这世上消失了,只留在我的记忆中。现在你看不到金黄的沙滩,甚至看不到一粒金黄的沙子。人们不断向大海扩张,填海建房,一幢幢房子的外面就是大海,海水都打到墙壁上了。海水也不是小时候那种碧蓝碧蓝的,黑乎乎上面浮着一层汽油,近海早已捞不到任何鱼虾,如果不是风吹过来带着咸涩的鱼腥味,根本无法感受到你是在海边。”
施西看着我,神情不可思议,也许她不可思议的不是故乡美景的消失,而是我的表情。我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一个疯疯癫癫、聒聒噪噪的姑娘如今也沉默了,也许我的性格影响了她,使她收敛了。
“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下星期一早上七点,你让汪一洋来局里找我,我帮他找了份工作,小学代课教师,我想他干老本行比较合适。第一天我带他过去熟悉一下。”
施西直直地望着我,接着眼泪滚下来。
“赶快打住,我不相信眼泪。”我把纸巾递到她面前,微笑了一下。
施西拿起我放在桌上的香烟,踌躇之后又放下来,她可能上瘾了。
“走吧。”这种场合这种氛围让我不自在,我不断催促着,但她按兵不动。
“他被我赶走了,我少得可怜的积蓄用光了,现在是负债生活。正如你所说,我确实养不起小白脸。”
“他回了烟台?”
“不知道,应该是吧,或许去了北京,他说他要到北京闯天下干大事,说那种大都市才适合他。奇怪,你为何不笑?我觉得你身上笑的细胞特少,偶尔笑一下也是一闪而过。”
我无奈地扯了一下嘴角,“你是高仓健式冷酷硬朗的男人。”
“居然懂高仓健,厉害!小姐,你不走我可走了,这地方让我郁闷。钱放在这里,足够你喝到打烊。”说完我起身走开,没有拖泥带水。
嫂子对我终于不再那么冷冰,虽然没有笑容,但说话语气好多了。她笑容一直就少,可能小时候吃苦太多,也可能是一个缺少笑细胞的人。
学生事件终于化解,毕竟是家长与老师之间的矛盾,那家长没有强硬到你死我活、置人于死地。在我的道歉和分析之下,家长逐渐平静下来。为避免尴尬,也可能担忧撕破脸后再把孩子放在嫂子班上不会受到照顾,对孩子学习成长不利,最后那家长要求把他的孩子调到其他班去。这事得跟校长商量,起因也就要有所透露,幸好校长从大局出发,又体恤下属,也为了学校声誉,便答应了那家长的要求。事后校长在学校例会上态度明确、措词严厉地申明不准再搞有偿家教,否则出事后果自负。
热火朝天般的家教平息了许多,很多老师悄悄改为地下。虽然校长大会上没有点名批评嫂子,但学校每一个职工都知道这桩学生事件。此事的直接后果是断了很多老师的财路,本来人缘就不太好的嫂子成了众矢之的,她开始被孤立起来,心情更为不好。祸不单行,她的父亲又脑中风瘫在床上了,她哥嫂让她回娘家共同商议两位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哥嫂认为父母是大家的,兄弟姐妹每月都得掏几百块用于老人吃饭吃药雇保姆。嫂子认为内外有别,平分没道理,除非财产也平分。哥嫂可能事先有准备,应付得游刃有余。可他们认为兄妹中嫂子最小,吃苦最少,还让她念了书,这培养的过程谁没出过力,他们要她偿还所有的学费。嫂子据理力争,结局是她哥嫂威胁她如果不履行赡养责任就上法院告她。一时间嫂子内外受敌,受到双重被告威胁,几欲崩溃,整天把锅碗瓢盆弄得噼里啪啦响。其实嫂子对我态度改变有一个关键原因,她知道她们校长跟我是六年的中学同学,关系还挺好。
同事的儿子满周岁那天,请我到他家聚聚。他结婚时买了房,紧接着装修,负债累累,他说没能力操办大场面,就几个要好的哥儿们到他家热闹一下喝两杯。到他家时,客房里的麻将打得正酣,我们便在客厅里喝茶聊天。客人陆续到了,同事让我顶替他老婆打麻将,让他老婆出来招待客人,进去后发现施西正是赌友之一,不由一惊。
“好久不见啊。”施西很随意地打招呼。
我这才想起同事的老婆也是市医院的护士:“没想到施小姐也会打麻将。”
我话音一落,大家便哈哈狂笑起来。
“她是大赌鬼,玩起来最不要命,最长时间坚持了三天两夜,目前本赌场还没人打破这项纪录。每次都是她呼朋唤友,一进入状态就不让停,大家都怕她。”
“娱乐娱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赔上命就乐不了了。”
“还说呢,她快为麻将疯狂了,居然坐到腰椎间盘突出,疼得哇哇叫还蹲着继续打。”其中一位年纪大点的女子说。
我抬头看看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久不见她确实衰老憔悴了很多,人瘦得不成样了,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子。打完几局我就起身了,她们也不勉强,于是散局。
当我把施西等出来时已是凌晨三点。施西没有想到我会站在楼下等她,她看到我时完全呆住了。其他两个女伴无声地先走了,我看到了她们异样的眼光。
施西脸上换了好几种表情,最后她说:“认识三年多了,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找我。说吧,有何贵干?”她故意把“干”字说得清脆响亮。
我无法接受她的野性,便说:“别再打牌了。”
“无聊,我父母都管不着我,你算老几?”她语气很冲很挑衅。
“汪一洋怎样,回来了吗?”
“天哪,那是几辈子前的破事了,我连他长啥样都想不起来了,你还记得他的名字,你真是一个大情种!”施西狂笑起来,笑声很恐怖很刺耳。
我木讷地站着,又想不到其他话题,她也不再说话。
“好好治下病,去你们医院骨科做个牵引。”我说完走向自己的摩托车。
“告诉你个好消息。”她忽然大笑着喊起来。
我回过头来,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还不知道她的荒诞。
“我终于见到我的初恋情人了,真正的初恋情人,他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我们像干柴遇到烈火,一点燃就着,就偷偷跑去开房,结果你猜怎样了?哈哈哈……第三次时被他老婆逮了个正着。现在可热闹了,他老婆每晚让他跪在床头忏悔,一会儿吵着要离婚,一会儿威胁要自杀,那可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家庭。”
我不知如何是好,空空麻麻地站了很久,最后说:“回去吧。”然后走了。
施西的母亲在婚变后改嫁给了施西的干爹,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原来最要好的朋友互换了丈夫,这事曾一时传得沸沸扬扬。再婚后,施西的母亲更痛苦,她意气用事的目的是为了报复背叛自己的好友。但她很快发现自己的好友并无痛苦的迹象,她仍然有滋有味地生活着,安逸、满足,而她自己却陷入了无边的痛苦、耻辱与悔恨中。她终于明白自己还非常爱自己原来的丈夫,于是痛上加痛,几次自杀未遂之后便疯了,经常间歇性发作,发作起来就毁灭家具。精神崩溃后,她的第二任丈夫也不要她了,把她遣送回原来的家,她变成了寄人篱下的累赘,施西的父亲雇了一个佣人照顾看管她。
这事是那位刚为儿子办完周岁酒的同事告诉我的,他曾追问我是否与施西有过风流韵事,我想一定是那两个打麻将的女人传达给他老婆的。
我感到无可奈何:“认识一个人就一定有戏?”
他说没有最好,这是一个烂货,千万别招惹。
我当场给他一拳:“嘴巴干净点,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权评判他人。”
同事有点狐疑,过后也不再过问。
一天大哥又哭丧着脸跑到我家,看到他我很郁闷,虽是手足,但我是越来越厌烦看到他。
“学校要撤我的职。”
“撤就撤吧,又不是什么大官,清静。”我有点不耐烦。
“你是知道的,在中国如果没有犯错误是不会丢官的,人家会怎样看我?人要脸树要皮,无缘无故被撤职,我还有啥脸面在学校混,我们祖宗脸上也无光啊。”他的苦瓜脸更皱了。
“别扯那么远,祖宗可能都转世投胎了。你倒说说他们干嘛要撤你的破官?”我边泡茶边问。
“还不是校长搞鬼,他左右看我不顺眼,现在他在提拔自己的亲信扩大自己的势力,就对我下手了。”
“如何撤你的?”
“他搞民意测试,让老师们进行民主选举。”
“有没有当场唱票?老师们都选对方?”我递过茶,自己抽起了烟。
“当场唱票,对方得了三十六票,我只有七票。”他说话的底气不足了。
“可见失败的原因还是在你本人身上,一方面是你工作能力有限,工作不出色;另一方面你没有搞好人际关系,校长总不至于给每个老师都做思想工作,为对方拉选票吧?”
“你怎么说话的?我是你哥,你居然教训我,还偏袒对方。”我哥霍地站起来大声喊。
“但我也是人,做人有原则,我也要辨别是非。你要懂得自我反省,否则即使再爬上去,也会再跌下来。”
“你教训我?你今天有没有吃错药?这事你要不要管?”
“这是民选的,我怎么管?我又没有通天本事。”我叹气,对他无可奈何。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局里,学校会把申请材料送上去,局里批不批是另一回事,主动权捏在上面手里。”
“算了吧,这样争来也不光彩,以后你也难开展工作。再说学校工作就政教这摊子最难弄,你何不轻轻松松去上班,上完课回家忙家务。政教主任的补贴今后你每个月准时到我这领,包你领到退休。”
“看来我今晚求错人了。”大哥气呼呼地站起来摔门而去。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特没劲,换了运动服拿起球离开家。
清寒的月光照在坚硬的水泥场地上,我非常专注地投球,篮球“嘭嘭嘭”地响在地板上,和着我的心跳,而我却觉得心没着落。
小时候父母总是宠着大哥,有年春节母亲为大哥买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而给我的却是二十块一条的冒牌货。初三早上我趁大哥还在睡觉,偷偷穿上他的苹果牌牛仔裤去参加同学聚会,晚上回家被母亲逮住,结果被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打屁股。后来大哥到外地念书,只要周末他不回家,我就要负责为他送钱送物。
我用力打球,特别卖劲。当我气喘吁吁停下来时,才发现施西不知何时已坐在石凳上。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开始抽烟,这是我们经常不自觉中保持的相处状态。我曾问施西为何总跑来看我打球,她说无聊,走投无路,也想静一静,但在完全安静的状态里人是静不下来的,单调的打球声能让人心静如水。
“还好吗?”她沉默,我只好先开口。
“什么?哪方面?”她转过脸来研究我的表情,眼睛在夜幕下闪着光。
“你的身体,具体地说,是你的腰。”
“有好转,还要继续牵引。”她淡淡的。
“配合吃点消炎药,效果会更好。”
“我知道,再怎样不学无术,我也在那鬼地方混了几年。”
“好好生活,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没有理由这样不负责任地混日子。”
“负责任?现在这世界谁还会对谁负责任?”她眯眼看我,她的魅力就在于她有一双勾人魂魄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却时常发出与之很不般配的冷峻之光。
“至少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你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怎么了?我们是垮掉的一代,自甘堕落自我毁灭,是吧?”
“应该说是迷惘的一代。”
“你客气了,你舍不得用严重的词伤害我。你们那一代呢?”
“不知道,我不能代表一个群体,我只是一个生命个体。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个哥哥,比我大六岁。如果我是小混蛋,他就是大流氓。他说他要玩遍所有他能玩到的女人,他不结婚不生子,要让施辉煌断子绝孙。我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他了。”
“去哪了?”
“不知道,在外面混。”
我不禁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她居然面带微笑,我看出了那微笑中的残酷和辛酸。抬头望四周,高大的楼房密密地刺向天空,把天空切割成狭小的碎片。
“爱唱歌吗?有空听听音乐。”
“不听。”
我拿眼睛询问她,心底更加忧郁沉重,没有音乐滋润的心灵该多么寂寥。
“热闹喜气轻快的歌,听了没劲,与心境不合,抒情缠绵忧伤的歌一听就伤心。”在我注视下,她认真做了解释。
“找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投入地认真地去做。”
“想不出来。”
“你最向往去哪里?”
“天堂。”
“你最想做的事呢?”
“折磨他们报复他们,让他们生不如死,我恨不得用最疯狂的方法把他们统统逼疯。”施西咬牙切齿地说。因为激动,她两条柴棍似的手臂在微微发抖。那两条细长雪白的手臂,本来让人产生的应是“清辉玉臂寒”的美妙联想,然而它们却让我不忍细瞧。
“放弃仇恨吧,你年纪轻轻,没必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幸福。”
“幸福?我还有幸福可言?别用这种字眼刺激我了。我早已坠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烂透了,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条贱命。”
“你这样会让关心你的人心碎。”
“扯淡!放屁!鬼才相信!我连心都没了,管他们碎不碎。谁还有多余的心为别人心碎?”施西非常激动,她的眼神闪着一种近似疯狂的毁灭的光芒。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成为天使还是魔鬼,有时只在一念之间,放弃恨,你才会活得轻松快乐,你才会可爱。”
“我选择做魔鬼,我喜欢魔鬼,我就是一个女魔鬼。”她用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做着张牙舞爪的动作。
我笑不出来,抬头仰望星空,天上没有星星,只有化不开的墨黑,一种铺天盖地的惆怅和绝望让我呼吸困难,我忽然觉得揪心地疼痛,抽烟的手轻微颤抖:“小时候的夏天晚上,我们总是躺在庭院的竹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比谁的眼睛亮,看到的星星多。大人们告诫我们不能数,数是不吉利的,会招来麻烦。天上繁星闪烁,让我们的心也闪烁起来。小孩不懂不吉利有什么直接的可怕后果,数累了星星,我们就比赛唱歌,一首接一首,变声变调地唱,笑声伴着歌声飘向四面八方。”
施西听着我低沉缓慢的诉说,安安静静,不再疯狂了,其实她完全可以成为天使般的姑娘,她文静的时候美得让人心动。
我吐着烟圈,不厌其烦地看着它们升腾、散开、淡去。
“施西!”
“别说话,此刻沉默是金。”
我望着她,惊叹于她的聪明,也无奈于她的冷淡。我移开视线,天幕上有两颗微弱的星星,相距遥远,孤独地闪着寒光,它们温暖不了对方,也温暖不了自己,当然也温暖不了深情凝望它们的地上的人。
侄女打来电话,她简明扼要:“我爸让你马上过来。”说完,不等我反应就干净利索地挂了电话。没有称呼,命令式的冷冰冰的语气。我一阵冷颤,但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任务,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一场激战,客厅里还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嫂子冷着一张脸,看见我不打招呼就走进了卧室。侄女头也不抬,安之若素地做她的作业,我过去敲敲她的脑袋,她抬头看看我,没有言语,一脸的平静冷漠。
“她整天找碴耍脾气,硬是闹着要离婚。”大哥的态度中显然有怪罪之意。
“局里批下来了?”我问。
“还没有,所以她硬逼我去走关系。她说只要还没批下来就还有希望,还有回旋的余地,不能坐以待毙。”
“干嘛非当这个政教主任,这官值得这样在乎?”
“她说无缘无故被撤职就是一大政治污点,这世道弱肉强食,我如果任人宰割,以后还怎样混?她还说她们学校的女老师不是丈夫当官就是公公当官,一个比一个威风,我被撤职自然会连累她,她在学校会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所以不如趁早离了。”
“那你去试试,找找朋友同学,你的我的都行,人情以后有机会再还。”
大哥仍是一张不满的脸孔,他无语。我抽完身上的香烟,闷坐了一会儿,起身把带在身上的银联卡放在他面前:“里面有万把块,你都可以取走,自个儿去活动吧。局里安排我去北京培训三个月,明天就走。”
离开他们家,我忽然很迷茫,不知走向哪里。我刚刚把全部家当押在那张污迹斑斑的茶几上了,我再次沦落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这种遭遇我常常经历,早已应对自如。晚上十点,我回到黑乎乎、冷冰冰、脏兮兮的家,感到无比疲倦无比孤独。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便听贝多芬的《月光》,这是陪伴过我无数寂寞时光的钢琴曲。我默默抽着烟,一个念头跳跃上来强烈地占据了我的意识,主宰了我所有的情感,我踌躇又踌躇,终于拨打了施西的手机,占线,对方正在使用中。一根香烟后我拨了第二次,再抽完一根拨了第三次,总是没有接上,我知道她用手机在上网聊天。三次之后我的热情与勇气就丧失了,虽然没有联系上,但我仿佛完成一项重大使命,顿时轻松了许多,于是打开房间所有的灯,在刺眼的光芒下准备行李。
施西回电话已是第二天黄昏,她没有解释迟回的原因,在她凡事不需要理由,那时我早已飞到了祖国的心脏。
“什么事?”她直截了当,省略了所有的枝节。
“没有,打错了。”
“不可能,哪有打错三次的,实话实说。”
“想和你告别。”
“告别?你也想自杀?”她惊叫起来。我不禁大笑起来,这就是她独特的思维方式。
“你在哪里?”
“北京。”
“很遗憾,错过了绝佳的机会,那可是发生一夜情的最好理由。”
“你就不能淑女一点稳重一点。”
“假正经,过过口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不起,忘了你是天底下最后一个钟情、纯情的男人,我才不会玩你呢,没劲。”
我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出现了难堪的沉默,还好看不到对方的尴尬。
“最近忙什么?”我只好选择其它话题,其实这是我非常关心的。
“炒股票,全国人民都当股民、基民,我不凑热闹可能吗?”
“战绩如何?”
“战绩辉煌,振奋人心,日子充实,前途光明。”
“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能耐。”
“我拜了一个免费的指导老师,他可是专家级人物,所向披靡,棒极了,简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下了多少本钱?”
“二十万。”
“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理智冷静……”
“打住打住,你真不识时务,我现在的状态让我理智冷静,这不是废话?”
“据说中国股市已进入完全失控的状态,非常危险,前景不容乐观……”
“乌鸦嘴,你太令人讨厌了。我这边热火朝天,你却冷言冷语。我们真的是没有共同语言。告诉你,即使血本无归也无所谓,反正是他的钱,不用白不用。花钱买心跳,刺激!”
施西又进入到另一疯狂状态中,我束手无策,施西总是用一个又一个的疯狂来填补生活的缝隙。她不敢闲下来,只有疯狂才能暂时麻醉她的神经。我和她道了声“再见”,也许她在手机另一端感到了我最后的冷漠,她也不再打电话给我,我也知道疯狂之中的她是不会给我留下一点空隙的,便没再联系她。但从那天开始我居然关注起股市来,每天都会了解一下红绿颜色、波线起伏、正负数。
培训的生活非常单纯,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轨迹,也远离了熟悉的人。我经常独自手拿一张北京地图,一站接一站地在祖国的心脏里猎奇。在这远离故乡的土地上,我常常出发,为出发而出发,不是为了风景,而是为了静下来,在风景中坐下来吐烟圈。团团烟雾中,我一次次拷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又将归于何处?”
培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我大哥家,我带回几只北京烤鸭给他们。他家的寄读生是有增无减,我不知把屁股放到哪里,大哥干脆对我说:“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坐坐吧。”
坐下后我第一件是问他工作上的事。
“没事了,虚惊一场。其实校长想撤掉的是总务主任,他是原先那校长提拔的,但这总务主任有靠山,他动用了上面的人,结果闹大了,局里不想麻烦,批示是维持现状。校长不仅用不上自己的人,还搞得两边不是人。我就这样不花一分钱保住了位子,哈哈哈……”
“嫂子带这么多学生不会有问题?风声不紧了?”我忽然问到这问题。
“又不是她强迫学生来晚修,是学生家长求上门的,这些家长都表示一旦查下来,他们都愿意证明是无偿辅导,学校能拿她怎样?”
望着洋洋得意的大哥,我说不出话来。只要他日子过得如意,我就省心了。我想到了离开前留给他的银行卡,便向他要,他掏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当时把钱取出来打算去走动关系,后来用不着,准备给你存回去,但最近太忙……”
“算了,你留在身边当私房钱吧,千万别让嫂子知道,朋友一块儿出去也买回单,别总蹭别人的,让人瞧不起。平时身上也放一两张大票子,阔绰一下才不委屈自己。”
大哥红了脸,我也感慨万千。
三个月不住人的家,简直狗窝不如了。我万分沮丧疲惫地站着环视了许久,不知是将就一宿还是找个地方寄宿一夜。我放了贝多芬的《田园》,拉开窗帘一看,今夜无月。音乐声中,我随意地坐在地板上抽烟,孤独得害怕。抽完香烟我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打扫房间,哪怕干到天亮。世界之大,容我之地太小,我必须善待自己,给自己一个立足之地。打扫中,我疯狂地把身外之物当成垃圾,装了一袋又一袋,大有和过去再次决裂的决心。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我已入睡,刺耳的铃声突兀地响起,我迷迷糊糊地问:“谁?说话。”
“人死后有灵魂吗?”
我一激灵,马上清醒过来,坐直起来环顾四周,冷静了一下才清晰地说:“有。据科学家研究,人的灵魂只有五克重,这是科学家在实验中得出来的精确数字,他们把一个快死的人放在磅上称,人刚断气的那一刹那轻了五克。”
“五克的灵魂哪儿去了?”
“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有的四处飘荡。”
“我只有四处飘荡了,我没有资格上天堂,也坏不到下地狱。”
“今晚怎想起这么深刻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母亲会去哪里,很困惑。”
“你母亲怎么了?”
“上周一晚上跳楼了,永远解脱了。”
我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怀疑是他杀,她神智不清,哪会自杀?一定是他们想图个清静甩掉包袱,把她推下了阳台。”
“别胡思乱想了,谁都知道杀人会受到法律制裁的,你母亲构不成威胁,他们不可能为此丧失理智,轻率地把已拥有的幸福弄丢。”
“那是天底下罪恶深重的幸福,下地狱去吧,我永生诅咒他们。”
“你在哪,能出来吗?”我不知是情不自禁,还是被她的疯狂吓着了。
“你回来了?”她懒洋洋的语气没有一丝惊喜成分,像一盆冷水劈头盖脸泼向我,我忽然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
“上周。”
“算了,我觉得没劲,懒得出去了。”
“那就早点休息。”放下手机我再也无法入眠,我的头脑全都被她占据了,不断更换的是瘦骨嶙峋的她深夜到处游逛的身影。倘若真有灵魂,施西就是一具寄存在空壳里的灵魂,她就是幽灵。
我又恢复了夜晚打球的习惯,施西一直没再出现。我去过电话,她那边都是正在使用中,过后也不回。凭我的直觉她又陷入另一场网恋了,对方很有可能是教她炒股的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位股神。
施西怎么样了?想起她时我有时感到很苦很累,苦到感觉自己已不再爱她,累到感觉自己已没有能力爱她。她在我生活中也像幽灵,总是晚上出现,而且神出鬼没,来去无影。我把一直没有表白的感情深藏起来,慢慢地,人也不再觉得刀割肉般疼痛了,所谓“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样吧。
大哥家终于闹得人仰马翻,起因很蹊跷,且是毁灭性的——居然有别有用心的人写匿名信告诉我大哥,说他女儿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大哥觉得那一刻天塌下来了,他存着一丝侥幸问我嫂,没想到嫂子居然平静地承认了,还面不改色地回答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大哥来我家时已喝得醉醺醺,又哭又闹,完全失控了。我把他安顿好,他闹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沉沉地睡去,我却一宿无眠,黑暗中,我痛痛快快地流着泪,千万次地向父母的亡灵忏悔。
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大哥学校帮他请了一天假。我们关在家里做了一次长谈。大哥离开时很平静,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就只能屈服于现在,他心灰意冷地说:“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人生不过如此,什么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但他再三叮嘱我,“咱可不能让村里人背地里骂秦家断子绝孙啊,传宗接代的任务由你完成吧,否则到了阴间,妈准饶不了你。”
一周后一个晚上,施西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篮球场。我忽然想起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对她的意识也苏醒过来,我发觉自己其实并没有忘记她,只是把她藏得更深。
我们像过去那样坐着,四周沉静。早春二月,春寒料峭,让我们不胜寒意。一股浓重的惆怅随之袭卷而来,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力控制了我。
“我要走了,去上海,结婚也好同居也好,反正让他养活了,混一辈子。”
“教你炒股的那个人?”
“你怎么知道?”
“猜的。这边工作不要了?”
“我妈过世后我就没有去上班,自动辞职了。”
“他能养活你?”
“可以,他工资很高,一年收入超过十万。他说我们一起炒股,向浦东进军。”
对话在平静平淡中进行,我想不出其它话题,只好沉默。记得母亲曾说我三锤打不出一个响屁,我这点是遗传父亲的。母亲痛恨我这德行,是因为父亲的这种德行折磨了她一辈子,让她终生都没走近他。
“抽根烟吧。”她忽然以轻松的语气提议道。
“好。”我们一根接一根,很快就把一包烟抽完了。抽完烟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有点遗憾,又如释重负。我们静静地对望了一会儿,接着她转身走开。我目送她远去,她的身影单薄、寂寥,我看着看着,内心的孤独和惆怅击溃了我,我情不自禁地跑过去冲到她面前,她望着我,仍是波澜不惊的冷漠。
我鼓起勇气对她说:“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成熟,也等待机会。”
“你太严肃太深奥,看不懂,让我害怕。”
“有的书可以看一辈子,人也一样。”
“其实人生,怎样都是一辈子。”
“保持联系好吗?把下一个机会留给我。”
施西平静冷漠地看了看我,不置可否,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如释重负,为自己终于把握机会对她说出了一个沉重的秘密。
三个月后,我收拾简单的行李也离开了这座城市,飞赴新加坡。前妻告诉我,她把女儿独自一人送到了新加坡一所贵族学校念书。听了这事,我送了她一顿痛快淋漓的国骂,然后开始办理去新加坡做劳务的申请手续。
离开前一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到篮球场打球,休息的时候我抽着烟,我在烟雾缭绕之中仰望星空,身边没有一个人。
在异国他乡,我曾打手机联系过施西,已是空号。不久,中国股市从九千多点的高峰开始狂跌,一蹶不振。次年,世界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很多国家经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