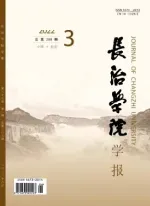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外语学习动机演化研究
竹旭锋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外语学习动机演化研究
竹旭锋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学习动机是影响外语学习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多维性、社会性和动态性的特征。本研究以两名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长达两年多的历时跟踪调查,采用学习自传和访谈结合的方法搜集大量语料,通过分析发现社会环境、学校政策、教师因素、家庭因素和同伴竞争等社会因素都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演化产生了影响。
外语学习动机;动机演化;社会因素
一、引言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外语学习动机作为语言学习者个体因素中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之一受到了众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学习动机能够激发、维持和引导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始于 Gardner和 Lambert(1959)[1]。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对动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从而产生了众多的动机理论,如Dörnyei的学习动机三层面说(Three-Level Theory),期望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目标理论(Goal Theory),自我实现理论(Self-actualization Theory)等等。另外Deci&Ryan(1985)将动机划分为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2]。近50年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研究涉及学习动机的定义、分类,建立动机模型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动机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周璇,饶振辉2007)[3]。
二、国内外语动机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以引入、介绍和翻译国外理论和研究著作为主,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对学习者个人因素和学习过程的重视增加,在动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王初明,1991;华惠芳;1998;李梅,1999;石永珍,2000;吴丁娥,2000;周福芹、邵国卿,2001;武和平,2001;刘东楼,2002;文秋芳,1995;1996;2000;2001;高一虹、赵媛等,2002;高一虹、程英等,2003;转引自王晓旻,张文忠 2005)[4]。
虽然我国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着些许的遗憾。大致有以下几点:1)在研究内容上,内部分类研究多,但对外部社会对动机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在研究维度上,静态共时研究多,动态历时研究少。3)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多,定性研究少。4)在数据收集手段上,调查问卷多,访谈个案少。最近20年来的有关实证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调查表的帮助,来推断被试者的学习动机,但是问卷测试本身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是问卷设计得是否合理、科学;其次,被试者所提供的答卷是否真的客观公正;第三,所提供的数据是否充分可靠有说服力。奥勒等人指出,调查表的使用有三个严重不足:赞同动机、自我奉承和反应定势(王初明 1991:102)[5]。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通过对两位非英语专业学生长达两年多时间的跟踪调查,采用回忆性自传、访谈和观察等多种手段收集数据,通过分析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的演化过程,试图寻找出影响他们外语学习动机变化的社会因素。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跟踪调查的对象为两名某省属重点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其中Z学习者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学习主动性强,英语学习成绩较为优秀,口语突出,并分别在大学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一次性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另外由于专业特点,对英语能力要求相对比较重视,课程计划中除了常规的大学英语课程之外,也有一些专业方面如外贸函电、国际贸易理论等双语课程。另一位C学习者为应用化学专业学生,英语底子相对薄弱,多次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均未通过,由于其理工科专业背景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英语学习上受挫感比较明显,但是学习比较努力。
(三)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有:学习者自传和开放式访谈记录。数据收集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大一开学初),要求学习者写一篇关于自己英语学习历程的回忆性“自传”,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与感受;第二阶段(第一次四级考试后,即大一结束后):对Z和C分别进行开放式访谈;第三阶段(第二次四级/六级考试后,即大二第二学期结束后):对Z和C分别进行开放式访谈;第四阶段(第二学年结束后):对Z和C分别进行开放式访谈。
四、学习者的动机演化过程分析
由于动机为内在的心理因素,其变化无法直接观察到,也无法直接像自然科学一样有直接测量的指标和工具。因此本研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长期接触中搜集到的质性数据,进一步加以解析和阐释,力图重现其学习动机演化的重要阶段和主要特征。同时动机具有的多维性特点,与外在的自信心、焦虑和自主性等有着紧密的联系;Dörnyei(1996)也曾提到语言自信心,包括语言焦虑感,都是个人动机的核心构成[6]。因此在分析语料时,对这些要素加以了特别的关注。以下分别为两位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演化过程做初步分析。
(一)Z学习者
对于初学英语的情景Z学习者在回忆性的学习自传中描述得非常具体,如“7岁时,在我溜冰的地方来了一个外国的大哥哥,我学着电视里说道‘Hello!’,那时起,我开始接触英语了,但只是口语和听力”。由此可见,此时虽然Z并没有开始接受学校设置的正规的语言课程,但是在社会媒体(一些专门的英语教学电视节目和外国电影等)的影响下,已经初步开始对语言学习有了概念。
接着,Z学习者描述在她小学时的情况:“上小学四年级起,我们有了真正的英语课,为了会读,为了背出,我开始在下面标注白字……到了五年级,我‘竟然’不需要白字的帮助了……”随着国家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和社会的需求,英语课程的设置也出现了低龄化的现象,80年代之前基本上都只在初一开始设置英语课,而近些年在一些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已经普遍开始在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主要以基本的口语交际教学为主,甚至有些学校为了追求特色,自行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英语课。
“进入初中、高中,在老师和外教的训练下,我觉得自己的口语有很大的长进,可是笔试常一般,觉得词汇积累少,又乱,在学习中,我只好狂背单词表中的词,狂背很多,也不见得有所长进。然后是阅读,看到不认识的词我一定要查,不查我就心里难受,不打算看下去,也从来好像做不到快速阅读。”对于中学英语的学习,Z对学习的描述反映出了一个普遍的现实,即学生的语言学习动机受到了考试的限制,应试教学导致了学生的应试动机或狭隘的工具动机。学生对语言学习的概念也局限于与考试相关的词汇、阅读等,学习者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评价也来自于考试中的成绩。
大学阶段,Z学习者依然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很努力,也顺利通过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然而之后突然出现一种迷茫的状态,如在一次访谈中,Z表示“接下去我不想把英语丢掉,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此时,由于学校英语课程的结束,所有要求的英语水平考试也都通过了,长期处于考试和课程目标驱动下的学习者突然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出现暂时性的迷惘状态。
另一次访谈中,Z讲述了妈妈学英语的故事。“父母对我的英语学习很重视,甚至妈妈要求我能教她学习英语。”Z表示“有些句子我能看懂,自己明白什么意思,但当我妈妈要我讲意思,我讲不出来……有些语法,原本以为自己懂,但真正教别人的时候,却怎么也说不清楚。”家庭氛围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如Z学习者的父母通过自己学习语言的要求来暗示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并促使她保持学习的动机。
(二)C学习者
C学习者在小学时并没有接触英语,而是从初一才开始接受正式的英语学习。他对英语学习的初始阶段具体情境描述得也相对简单,大部分的语言都透露着考试成绩不好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到现在已有八个年头之久,但感觉成绩不是很好。”显然C学习者将考试成绩的好坏作为衡量自身英语水平的高低的标准,这与目前大多数中学教育始终以应试教育为主,在课程教学中传递给学生考试成绩重要性的信号,并不断强化有关。此时,C学习者对自身的学习反思也与考试的题型直接挂钩,如“每当我背单词的时候,背了很长时间之后,单词记住了,但过一会儿发现自己又忘光了。做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时,常常看不清文章的内容而导致不知道改如何下手。在英语听力中,常常是根本听不懂。每当我对英语越努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自己对英语原来是这样一无所知,我时常对四级感到极度的恐慌。”
从初一到大学阶段,C始终将考试作为衡量自己学习结果和水平的工具,在这种应试型动机驱动下,考试受挫给C的心理上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之开始怀疑努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大学一年级结束时,C曾向英语老师询问关于期末开始的改卷情况,表示“感觉自己只得了65分,有点少。听力也只有70分,上个学期的综合英语也只有70来分,听力60分。”此时,成绩的影响还是在继续困扰着C,也一直将六级考试作为学习努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同伴的比较差距也给他带了一定的压力。
在大二学年,对C的一次访谈中,C谈到自己的综合学习成绩排名从班里10名到了第1名,于是对于自己的评价开始有些“贪婪”,想要继续保持。“上个学习成绩有80几分,感觉对自己的排名很有影响,比之前要好多了,至少不会拉分。如果四级能通过,还可以加能力分3分。”此时考试成绩的好转,让C开始有了学习的自信和更大的学习动力。另外,与考试相关联的排名和奖学金评比也在影响着C的英语学习动机,开始关注并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投入更大的努力。
此阶段C的学习动机明显增强,具体表现在学习热情增加,自信心的提升,能主动与老师交流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恰当的自我评价与定位。
按照学校的课程设置,从大三开始不开设英语课程,一次C主动找到英语老师,咨询关于GRE考试的相关事宜。原因是暑假期间C有一个亲戚从美国回来,提到考GRE的事,说只要他能考到550分,其它大学申请的事情由他来帮助办理。C说道“自己感觉这对考研也有帮助。另外自己也辞去了学生会干部职务,专心学习英语,毕业前能够考几次。”在没有常规考试后,C的英语学习动机从先前的等级考试开始转化成对自己专业的进一步发展(考研)的帮助。与此同时,家人等因素也对C设定学习目标产生了影响,由此内化为学习动机的强化。
五、影响动机演化的社会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对两名学习者Z和C的学习自传和访谈结果的初步分析,我们不但可以体会到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演化的,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外语学习动机的演化受到了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动机的社会性。这些影响因素既有宏观上的,也有微观上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社会环境(政府层面、民众层面)
在全球化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国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其重要性被越来越多人认可,由此带来了全国范围的英语热,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语与计算机等一起被国人认为21世纪人才必不可少的技能,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将外语能力作为招聘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
国家也对外语教学非常重视并出台了相关语言政策,除了要求在高校内开设英语专业培养专门的外语人才,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也必须修习一定学分的外语课程之外,也设置或引进了多种英语水平测试,如大学四六级考试、公共外语考试、商务英语证书考试,开放了雅思和托福等国外考试系统。在中小学层面上,英语更是作为高考和中考的重要科目,成为升学的必要条件,更有甚者,一些中小学为了吸引生源直接冠上了外国语学校的头衔,幼儿园挂上双语幼儿园的牌子。这些教育领域内的变化迅速延及到了社会上,如今在各大中小城市,外语培训学校林立,培训对象从幼儿一直到了成人,尤其是家长不惜重金,只求孩子的外语能力有所进步。这些宏观因素也直接对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产生了影响,学习者或出于融合性动机(如出国留学,移民等),或出于工具性动机(如考试,就业等)的驱动来学习外语。
(二)学校政策
学校设定的基本氛围和实施的政策(Maehr&Midgley,1991)[7],具体表现为学校的课程设置、评价标准和管理体系等,也都对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有直接的影响。大部分中小学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应试教育特点比较明显,然而有部分学校有所变革,重视学生的外语能力综合发展,如聘请外教开设口语课,培养学生的实际外语交际能力,这对学生的外语学习动机影响很大。在大学阶段,目前大部分大学都要求非英语的大学本科学生必须修习1.5-2年的英语课程,并获得相应的学分,有些专业也开设了一些双语专业选修课。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基本上出于无奈和“生存”的压力,学习的热情可想而知。华惠芳(1998)将这种动机类型定义为中国特有的“证书动机”[8]。
(三)教师因素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影响是多面的,涵盖了从性格到社会交际能力,Dörnyei(1994)将其归纳为三种:亲和力(affiliativemotive)、权威(authority)和直接社会化(direct socialisation)[9]。首先,教师的个人性格特点或者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即亲和力)也会影响到学生外语学习的动机。而假如有些英语老师担任班主任的话,和学生的接触相对较多,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也会相应增强。另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心理学上称之为皮革马利翁效应,即教师的信任、鼓励和高期望会被学生直接感知,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其次,教师的权威主要在课堂教学和管理中体现,如教师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很容易被学习者接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相反教师如采用带有一定强迫性的教学手段,往往会使一部分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与动机,产生恐惧感,回避或者讨厌学习外语。外语教师往往是学生学习英语动机直接社会化的引发者,教师对外语学习的意义、目的、概念、方法等描述或体现能直接影响学生。
(四)家长等家庭因素
人们很容易忽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动机也受那些并不直接出现在学校中的人的影响,尤其是家长们。教育心理学家一直以来认为家庭特征和行为与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有关联,而其中最重要的纽带便是动机(Gottfried et.al 1994,转引自 Dörnyei 2005)。Eccles等(1998,转引自 Dörnyei 2005)总结了影响学生学习动机的四大因素:持续适时的成功要求或压力;对自己孩子的高度自信;一个宽容和支持性的家庭情感氛围;积极的榜样示范[10]。如此次研究中,Z学习者的家长表现出来的重视与关切程度,以及“妈妈要学英语”这样的榜样示范作用无疑对Z的英语学习动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同伴竞争
学生的学习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始终处在一个群体当中,因此学习动机也势必受到学习同伴竞争的影响。在中小学阶段的考试排名行为(虽然教育部门已经在着力取消这种排名行为)和大学阶段奖学金的竞争(如本研究中的C学习者)等都和英语课程有很大的关联。学校或教师的出发点是希望学生在对比和竞争中找到进步的动力,然而副作用之一便是强化了学生外语学习的应试动机,反而不利于学生学习动机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
六、结束语
本次研究所坚持的观点有三个:第一,动机的多维性和不可观察性。动机虽然不可直接观察和测量,但往往通过学习者的学习态度、信心,焦虑和自主性表现出来。第二,动机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动态演化的。因此研究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必须从历时的角度来进行,单一时刻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所揭示出来的结果往往十分有限。第三,影响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的社会因素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因此在研究学习动机演化时必须结合这两种视角综合考虑。在已有的大量的动机研究成果背景下,本研究坚持这三个观点,从历时的角度跟踪研究两名学习者长达两年之久,采用学习自传和访谈结合的方法搜集大量语料,发现在外语学习者动机演化过程产生了影响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社会环境、学校政策、教师因素、家庭因素和同伴竞争等。
[1]Gardner R C&Lambert W E.Motivational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study [J].Canadian Journalof Psychology,1959,(3):24-44.
[2]Deci E L&Ryan R M.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 ination in Human Behaviour[M].New York,NY:Plenum Press,1985.
[3]周璇,饶振辉.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的方向问题[J].外语界,2007,(2):39-44.
[4]王晓旻,张文忠.国内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现状分析[J].外语界,2005,(4):58-65.
[5]王初明.应用语言学——外语学习心理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94-106.
[6]Dörnyei Z.Moving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to a larger platform for theory and practice[A].In Oxford R L(ed).Language Learning M otivation:Pathways to the New Century[C],Honolulu: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89-101.
[7]Maehr M L&M idgley C.Enhancing student motivation:A schoolw ide approach[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1991,26(3/4):399-427.
[8]华惠芳.试论英语学习动机与策略的研究[J].外语界,1998,(3):44-47.
[9]Dörnyei Z.M otivation and motivat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The M 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4,(78):273-284.
[10]Dörnyei Z.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Motivatio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H319
A
1673-2014(2011)03-0057-04
2011—01—25
本文系2008年度浙江师范大学校级青年基金项目(SKQN200865)成果之一。
竹旭锋(1983— ),男,浙江绍兴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语教学语用学研究。
(责任编辑 晋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