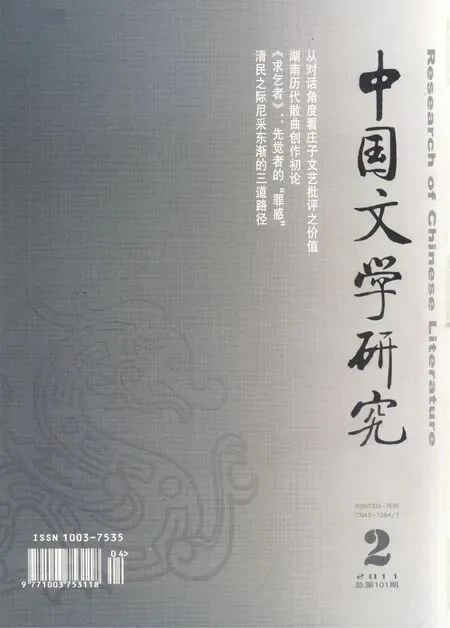南朝文论中的文质观及其意义
周 悦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在中国文论史上,南朝论文风气浓厚,文论发达。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作为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论专著在此时出现成为主要标志。它一方面是对既有的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同时又深深地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实践和审美价值取向。而在南朝文论中,“文”与“质”成为广泛论述的核心概念,刘勰,钟嵘,沈约,裴子野,萧统,萧纲,萧绎,都有关于或崇文或尚质的文质论,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很多篇章文质对举,文质并重是他所标榜的核心文学理念。可以说,文质兼备成为诸多南朝文论的关注焦点,进而言之,它也是南北文风融合的取法标准,而且昭示了汉唐文学发展的正确走向。
一
“文”和“质”作为相反的概念对举,其实并不始于文论领域,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被用来描述不同的对象,使用于非文论的其他领域。
以文质评人,文质关乎个体品性。《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即一个人如果仅有淳素质朴之态而少外在的文饰,则犹如乡野之人;如果外在的文饰妨碍了内质的体现,则如书史,有虚华无实之嫌。“质”可理解为质朴,质实,“文”是指文华,文饰。这里“文”“质”概念是用来描述个体人格的培养与规范,“文质彬彬”是形容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和修养礼仪,认为只有这样方可成为“君子”。
以文质述政,文质则关乎王道政治。“文”“质”概念亦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如《礼记·表记》中记载,孔子曾说:“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以文质的互变来指称朝代变更,亦以文质的升降暗示人类淳素之渐失与伪饰之渐滋。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则以质文代变来概括政治风尚变更,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刘向的《说苑·修文》及班固的《白虎通德论·三正》中都作过质文互变的论说。大体上“质”指质朴淳厚,为政简易,不太讲究礼法;而“文”则指礼乐刑赏,设立人为的礼法制度。总之,汉儒是以质文互变来解说王朝变迁,以“尚质”和“尚文”来评判为政之道。
王夫之曰:“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则体要立矣。”〔1〕他则上升到哲学高度从文质一体相互依存的性质,文质不同的功用特点论述文质。
二
“文”“质”概念广泛的出现于南朝文论中,成为南朝文论关注的焦点。
它在南朝文论中的具体所指,有的认为是指作品的形式和内容,〔2〕有的认为在“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3〕应该说这些认定各有依据,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刘勰在这里用“质”比喻情性,“文”比喻文辞,情性是内容,文辞是形式,“质”“文”当然理解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在同一篇中,又曰:“《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这是说君子居丧期间的谈吐不需要文采,而平时说话则不必质朴。老子痛恨虚伪才说漂亮的言辞不真实,《道德经》洋洋五千精妙之言,并不弃绝文华。研究体会《孝经》《老子》则知道语言的华美质朴是依附于人们的性情的。显然,这里的“文”“质”是指语言的文华和质朴。通观《文心雕龙》各篇,的确更多用“文”“质”指语言的文华和质朴。因为文学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汉语言文字的经典精美的组合,自汉代以来,扬雄等就是首先从语言开始认识文学的特质。而事实上,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质论相比南朝其他文论中的文质对举之说,贯穿全篇尤其系统而富于创见,其文质兼备的文学观念,关乎总体文学风貌;关乎具体作家风格,亦关乎不同的文体特征。
《文心雕龙·征圣》篇云:“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指出圣人的经书是既雅且丽,文华质实兼备。当然是文学作品师法的对象。在《辨骚》篇中,指出诗赋为主的文学作品要依照《诗经》,驾驭楚辞,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也就是说既要酌取楚辞的奇丽文采,又不丧失《诗经》的雅正质实。在《通变》篇中,更是以质文变化来概括文学史的流变:“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他认为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质趋文。其中商周时代的文章“丽而雅”,“丽”就是华美有文采,“雅”则是典雅,可以理解为“质”中的褒义,与“质”中的贬义“俗”和“野”是相对的。“丽而雅”其实就是文质参半文质彬彬的意思,当然最为理想。商周之前的文章偏于质,商周之后的文章则偏于文。从楚辞汉赋夸饰艳丽,到魏晋文章平易而华美,在由质趋文的发展进程中,刘宋文章竟至于讹而新,这个“讹”即“穿凿”“诡巧”,“新”即是尖新。遣词造句求讹追新,实际上是以颠倒文句,生造词语等手段达到怪奇尖新的效果。可见刘勰对于近代文学往“文”的方向走得太远已经颇有微词,言语间已经带有贬抑的感情色彩了。
的确,就纵向的文学发展而言,自楚汉直至南朝是文胜于质,到齐梁时期讲究语言之文采臻于极端,这种过分追求文采的努力,结果导致文胜质衰。那么如何来纠正这种弊端呢?首先,刘勰在《宗经》中明确提出了为文之宗旨:“风清而不杂”“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即风格清新不混杂,体制精炼不繁冗,文辞美丽不浮靡。《通变》中则指出了实现的具体途径:“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即通过学习经书雅丽而质朴的篇章去做到文质相兼,雅俗相济。同时,刘勰倡导风骨,因为风骨和质实关联。六朝时期风骨本用来品评人物,如《世说新语·赏誉》:“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其注中引《晋安帝纪》说:“羲之风骨清举也。”具有质实品格之士往往颇有风骨。文如其人,“风骨”运用于文论领域,刘勰提出“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其目的正在于以质救文。故他所谓风骨,是指明朗刚健的文风,“风清骨峻”“文明以健”都是强调质朴刚健的一面。他批评晋宋以来的文章“风昧气衰”,〔4〕(P272)也就是风骨不振缺乏质朴刚健。认为在风骨和文采之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4〕(P266)因而明确标榜理想的文风则是风骨与文采的结合,也就是质与文的结合,最终达到文质兼备。
涉及到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刘勰也用文质兼备的标准。如他认为在文质之间,曹植王粲“兼善”,左思刘桢“偏美”。〔4〕(P62)“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淮南泛采而文丽”〔4〕(P161)“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4〕(P213)他称道:“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4〕(P423)评价司马相如“洞入夸艳,致名辞宗,”“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4〕(P424)认为司马相如文辞夸张艳丽,成为辞赋领袖,但是文胜于质,因此认同杨雄对他的文丽用寡的批评。
针对各类不同文体,他也作出了具体分析,如《明诗》中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称道建安诗歌在抒情述理遣词描写方面,文辞不求纤巧繁密只求显著鲜明。能够在文质间调适至于恰到好处。而“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指出晋宋诗歌流于轻浮绮丽,文辞繁富竞至于要求全篇对偶,造句奇突,遣辞尖新,已经有文胜于质的明显趋向了。他认为不同的文体在文质之间各有偏重,如《颂赞》中云:“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刘勰认为赋与颂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虽然都需要有所铺叙,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4〕(P82)不妨极丽靡之辞,而颂则要求典雅,不应该过分华艳夸张。按照这样的文体要求,他批评马融的《广成》和《上林》类似于赋,竟至于文采过盛而丧失颂要求语言朴质这一文体特点。《书记》中在罗列属于书记类的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之后云:“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认为以上二十四类文体有些可以用语质朴,有些可以杂以文采,但都以精炼简要为贵。
纵观《文心雕龙》各篇,不管是在文学总论,还是文体论和创作论,乃至文学评论各个部分都贯彻了文质兼备的审美理想,它成为刘勰《文心雕龙》的核心文学理念。
刘知几《史通·自序》:“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的确,中国古代文学历经漫漫征程,尤其是经过汉魏晋宋这一时段发展,到了齐梁时期,既往的文学作品需要理性的甄别评述,当下的文学创作也需要理论的引领指导,文学的理论与创作需要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核心文学理念和价值取向,《文心雕龙》的应运而生成为时代的必然产物。与此同时,在时空交汇的历史坐标上,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刘勰身上移开,瞩目一下他周围的文论环境,与他相比,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同时代的其他文论是如何论述文质之道的呢?
首先要拿来作为参照的是钟嵘的《诗品》。《文心雕龙》据学者考证是诞生在南齐末年,《诗品》出现的时间较之稍晚,在梁代初期。后世多将两者相提并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曰:“《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他们论文都特别注重历史源流,只不过一以文体为纲,一以作者为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小序所云:“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期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钟嵘以品第的方式论五言诗作家,也是围绕着“文”与“质”展开,同样贯彻了文质兼备的评判标准。在《诗品序》中纵论各代五言诗作,至于汉代,认为:“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5〕(P1)明显否定班固的咏史诗质木无文,然后历数建安各家,称赞建安诗歌“彬彬之盛,大备于时。”〔5〕(P1)即是肯定其文质兼备。他主张作诗应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5〕(P2)要求风骨和文采结合,也就是要文质兼备。具体品评各代诗人时,也体现出文质兼备的评价标准。如他特别推崇曹植,评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5〕(P20)认为他深得文质兼备之美。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5〕(P21)认为他风骨极高但是文采不够,质胜于文。评王粲则是:“文秀而质羸”,〔5〕(P22)文采秀美但风骨柔弱,文胜于质。虽然他们同属于上品,但以文质兼备的标准而言,皆不及曹植完美。至于班固《咏史 》诗,“质木无文 ”,〔5〕(P1)曹操诗“古直”,〔5〕(P56)明显偏向于质者,置于下品。魏文帝诗“洋洋清绮”〔5〕(P32)但“率皆鄙质如偶语”,〔5〕(P31)置于中品。评陶渊明诗:“世叹其质直,”“风华清靡”,〔5〕(P41)置于中品。张华诗“其体华艳,兴讬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5〕(P33)明显偏向于文者,置于中品。
如果说刘勰和钟嵘皆专以文论著称于世,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齐梁时期还有引领时代风气的文坛重要人物,他们的文质观也是必须关注的。
沈约历事宋齐梁三朝,齐梁之世已经是位高权重名扬文坛的显赫人物了。当位卑人微的刘勰自得于《文心雕龙》的创获,又苦于默默无闻时,是略施小计而终于博得当世文宗沈约的称誉。沈约的文论散见于史论,书信以及一些品题奖掖的言论中。最重要的当属《宋书·谢灵运传论》。因为《宋书》不列文苑传,故《谢灵运传论》就取代了文苑传论的作用。《南齐书·陆厥传》中载有沈约的《答陆厥书》谈论声律问题也算是他的文论。沈约永明中已贵为文坛领袖,受其身份地位与心态的影响,就文学史观而言,明显厚今薄古,他对当代文学推崇备至。就其文质观而言,尤可注意的是他在叙述刘宋以前的文学发展时,论到建安文学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6〕(P1778)指出其重抒情重文采两个特点,“以情纬文”,是说根据作者感情来组织文辞,“以文被质”,是说运用华美的辞藻行文。明确指出陈思王曹植无疑是建安文学中的佼佼者。这与刘勰和钟嵘的评价无异。
而与刘勰和钟嵘力图以文质兼备的标准去客观地评判作家创作不同的是,沈约的文论中,更为自得于当世作家在创作中的探究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其旨趣明显偏重于文华藻饰。他评屈原、宋玉、贾谊、相如是“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6〕(P1778)王褒、刘向,扬,班,崔,蔡是“清辞丽句,时发乎篇 ”,〔6〕(P1778)“平子艳发 ”,〔6〕(P1778)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6〕(P1778)评潘岳陆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6〕(P1778)这些评述多关乎文藻无疑。尤其是评价宋代文学:“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6〕(P1779)认为宋代文学的代表颜谢足可以与前代杰出作家并驾齐驱,也为后世作家提供经典示范。
这显然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对宋代文学“讹而新”的贬抑有别。而他对于齐代文学的评论,尤为自得于声律学说的发明,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永明诗人“妙达此旨,”〔6〕(P1779)而这是“自骚人以来,此秘未暏”〔6〕(P1779)的。可以说,沈约这种厚今薄古文论,已经推崇当代文学的贡献达到极致了,而且,这种推崇是与他尤为崇尚文华的审美取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声律论以及他所倡导的“三易”主张,都是在“文”这一方面不断地孜孜探求获得的成果。由于沈约在齐梁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同道及追随者众多,更进一步推动了永明以后齐梁文学重文轻质乃至于崇文弃质的时代风气,此后这种崇文弃质的风气甚嚣尘上引领潮流。
裴子野尚质轻文的文论却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堪为另类的一种声音。裴子野作为尚质派的代表人物,其实在梁代文坛有过较大的影响,也许因为他曾撰《宋略》二十卷,后人多以史家名之,反而文名不著。《梁书·裴子野传》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说他不尚丽靡之词正可见他的创作实际与其尚质文论一致。他的文论主要是《雕虫论》,联系裴子野的生平经历可知,他的尚质文论与他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作风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其儒学伦理观和俭朴人生观的渗透下,裴子野纯然立足于文学的社会政教作用论文,他认为文学理应“劝美惩恶”,以王化为本。因而斥责宋齐作者追求“繁华蕴藻”是舍本逐末。文中严厉斥责崇尚文华的文风曰:“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雕虫论》作于齐末,主要是针对刘宋时期的文风立论,兼及齐代文风。〔7〕在他周围有着一个主张相近的文人圈子,《梁书·裴子野传》曰:“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这些人士皆学识渊博,裴子野文人集团可谓是博学尚质派。
在刘勰沈约钟嵘及后来三萧文论巨大的影响力掩盖下,后世学者似乎对尚质的裴子野一派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裴子野盛年后在梁武帝的赞赏与支持下在当世享有盛名,《梁书》本传载“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可见影响力在当世不可低估。萧纲的《与湘东王书》中将他与谢灵运相提并论,曰:“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他成为后起的萧纲萧绎求新竞丽一派的对立面,与他们针锋相对。
刘勰沈约裴子野文论出现在齐末,钟嵘文论出现在梁初。到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沈约去世。萧统编撰《文选》选录的作品也基本上止于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的作家。沈约之死标志永明文学时段的结束,而此后梁代三萧的文论进入我们的视野。
后世习惯将梁武帝的三个儿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并称为“三萧”,乃因皆文才卓异,也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创作与文论上的切磋与交流,还因为志趣相投和仕宦遇合分别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不同的文学集团先后立于梁代文坛。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是风格彰显特征鲜明的创作实践和理性自觉的文质论主张。概而言之,其文质观异中有同,同中见异。
萧统的文论主要体现在《文选序》和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及《答晋安王书》与《陶渊明集序》中。
后世学者多目他为折中派,其实他是主张在新变中追求文质兼备。《文选序》曰:“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至于在文质之间如何调适与平衡,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 〈诗苑英华 〉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这段话表明萧统的文质观:典而不野,丽而不浮,文质彬彬。这是萧统所向往的为文最高境界。
萧统身边还有与他志趣相投的诸多文士。《梁书·刘孝绰传》:“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梁书·王筠传》:“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这些文士都是追随昭明太子久有时日,自然声气相投。萧统集合这些文士编撰《文选》,有利于这种观念渗透到文集的具体编辑过程中。萧统对刘孝绰特别敬重,刘孝绰奉命纂录《昭明太子集》序言中也提出了与萧统一致的审美取向:“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善众美,斯文在斯。”标举典而不野,丽而不淫。
萧统这种取向亦与刘勰的理念互相呼应,《梁书·刘勰传》:“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萧统礼遇刘勰,刘勰后来亦成为萧统文学集团成员。
萧统的规矩折中与他特殊的身份地位及受到的教育和个人性情有关。作为太子,萧统拥有最优质文化资源与纯净的生活环境:卷帙浩繁的图书典籍与学问渊博的精英文士。加上个人性情不喜女乐声色,爱自然山水,好文士雅集。因而他崇尚的是典而丽这种最理性完美的选文标准。
事实上,萧梁时期文质兼备已经成为评判作家的标准,如范云称道何逊,《梁书·何逊传》:“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古今,见之何生矣。’”萧统赞美萧纲:萧纲曾作《玄圃园讲颂》赞颂萧统在玄圃园与学士名僧讲经,论说佛法和儒道的融合,萧统则作《答玄圃园讲颂启令》回赠说:“得书并所制讲颂,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雅。岂直斐然有意,可谓卓尔不群。”这里“典”与“艳”相对,“典”即是“质”中的褒义,可见萧统正是以文质兼备的标准来称道萧纲的作品。
萧纲则不同,身边的文人崇尚丽靡对他深有影响,武帝对他藩王而非太子的期望与定位也影响到其性情趣味。
作为新变派的代表人物,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新变主张,他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古今文学各异:“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厚今薄古乃至是今非古的主张表露无遗。
而他所谓“变”,主要就是在文质之间追求文华藻饰,鄙弃质朴无华,将文学的丽靡特质张扬到极致。因而他对前辈裴子野崇尚质朴的创作与理论颇不以为然,态度鲜明地斥责其“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
萧纲身边也聚集了不少声气相投的文士,他们是徐摛父子,庾肩吾父子,陆杲,刘遵,刘孝仪,刘孝威等人。《梁书·庾於陵(附弟肩吾)传》:“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周书·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可见在永明新变文风影响下,为文崇尚丽靡,追求绮艳已经成为萧纲文学集团成员的共同特征。
一般学者对萧统为折中派萧纲为新变派不存分歧,萧绎则介乎其间。他与萧纲为同父异母兄弟,自小两人关系友善,甚为“相得”。梁大同二年(536年),太子置文德省学士,庾信,徐陵,张长公,傅弘,鲍至等人入选。这时萧绎更有意趋附萧纲,在频繁论文切磋中两人的主张逐渐趋于一致:主张新变,偏重于追求绮艳华靡。他在《金楼子·立言》中曰:“至于文者,惟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认为文学作品需要文采繁富,音韵谐美,情感激荡。因而《隋书·文学传序》将他们相提并论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
其实,萧绎也主张在文质间兼顾。《内典碑铭集林序》中即提出了文质兼备的观点:“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予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这种“艳而不华”“质而不野”的取向则似乎更接近乃兄萧统的主张。
总之,萧纲一派崇文弃质追求新变,倡导绮艳丽靡文风,与萧统典丽相济的文质观,与裴子野崇尚质朴的文质观迥然有异,是沈约崇尚文华文质观的延续,更能代表梁中后期文风的潮流和时尚。尤其他们在语言上的趋新求变,标志着对于文学语言技巧的追求达到非常精深的程度。
三
南朝文质兼备理念的确立,成为南北朝后期南北文风融合的取法标准,也昭示出汉唐文学发展的正确走向。
自东晋立国江东,南北政权对峙导致文学传统的分化和文化环境的改变,文学传统和文化环境的南北差异形成,导致南北文学地域差异彰显,姑且不论文学创作的局面差异与成就高下,仅就取向而言,南方尚文,北方尚质。与此同时南北文学也经历分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考察齐梁以后南北文学融合的具体情形,可以发现,文学风貌固然南北各异,文学的繁荣落后南北差异明显,但审美理念却趋向一致,文质兼备被普遍认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确立的文质兼备的文学理念遂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受到当世文风影响与刺激,但事实上是《文心雕龙》中所确立的文质兼备的文学理念确实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成为南北朝后期文学创作中南北作家共同师法的创作目标,也是南北文风融合的取法标准。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由南入北和由北入南的作家创作实践所证明。
比如萧梁后期,随着绮艳丽靡文风的代表人物徐陵和庾信的入北,徐陵出使东魏,庾信入西魏北周,加速推进南风北渐,南方尚文的风气迅速影响到北方尚质文风的改变。可以说,恰恰是萧纲一派这种过分崇尚文华的取向,更能突显出南方文学特色,与北方一直以来形成的质朴文风形成极大的反差。反差越大则融合反而越是明显,这颇类似于水的流动,落差越大流速越快。一方面,北方本土文人接受南风北渐的熏陶,在重质少文的基础上学习南方精美圆熟的语言技巧,增加文华藻饰,比如卢思道之清刚实则体现了文质的调和;另一方面,入北文人接受北方文化环境和北方文风的影响,也在他们固有的华美文风基础上融入刚健质朴的风骨。比如由南入北的庾信就是将南方的绮丽华美与北方的苍凉雄壮结合最为完美的典型。它是一种双向互动,这种相当长时间中的互动,他们反向的变化却显示出共同的趋向,其变化的核心乃在于在文质各有偏善的基础上的文质调剂,互相改观。在动态中追求文质之间的调适和平衡,南北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呈现出一种臻于文质兼备,文质彬彬之至美的动态发展趋势。
正是立足于南朝文质论的基础上,联系南北文风融合的创作成果,唐代人以统括南北的视野进一步推进了有关文质的论述。《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它最早明确地把南北与文质关联起来,将南北文风的融合阐释为文质的调适与平衡,对南北文学的差异和融合的成果作出总结。由此反观,南朝文论中文质兼备的文学理念,其实昭示出了自汉至唐文学发展的正确走向。如果以南朝作为基点上溯下延,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自汉至唐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质文互变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在质文间求平衡,作调剂,最终走向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而唐代文学高峰正是在经历了纵向的文质互变和横向的文质调适后显示出来的辉煌成果。
〔1〕王夫之.尚书引义〔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2.
〔2〕宋晓红.论刘勰的文质观〔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3).
〔3〕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J〕.文学遗产,2002(5).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沈约.宋书(卷 67)〔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日)林田慎之助.裴子野《雕虫论》考证〔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