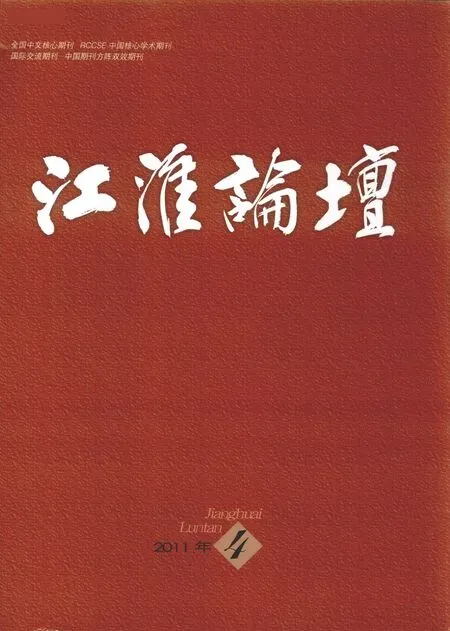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
张新广 李明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
张新广 李明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危害人类罪已经成为强行法中的罪行。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一战后对德国责任人的惩治失败了,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二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较为成功,但也促使国际社会反思这种惩治模式的不足并加以改进。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是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最新模式,特别是国际刑事法院,它代表了惩治这种罪行的最先进的模式。在惩治危害人类罪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事后立法和法庭本身合法性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但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使得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国际法机制更加完善。
国际法;危害人类罪;惩治
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是国际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核心罪行之一,在近现代国际社会历次重大刑事审判中,危害人类罪都是被惩治的重要对象。今年,在利比亚冲突中,因为卡扎菲涉嫌危害人类罪,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970号决议,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卡扎菲,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签发针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逮捕令。这就引发我们的思考:国际法如何惩治危害人类罪?国际法在惩治危害人类罪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通过惩治危害人类罪,我们以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国际法治?本文结合国际法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历史和现实,总结国际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希望获得必要的经验和教训。
一、危害人类罪已经成为强行法中的罪行
强行法原本是国内法中的概念,后来被借鉴到国际法之中。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一次在国际法文件中正式使用了这个措辞,公约第五十三条规定:“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 (绝对法)抵触之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从此,强行法这个措辞就不仅是学理上的称呼,而且成为正式的国际法术语。
强行法进入国际法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罪行要求严厉禁止和惩治的一种决心,这些严重罪行当然包括危害人类罪。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即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是最早体现国际社会惩治危害人类罪决心的国际法文件之一,其序言规定:“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马尔顿条款,在这里,“人道主义法规”是从英语“the laws of humanity”翻译过来的。我们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虽然条款并没有白纸黑字的使用今天的“危害人类罪”这个措辞,但其隐含的意图与今天惩治危害人类罪没有本质区别。
强行法和对世义务联系在一起,违反了强行法,就是违反了对一切人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危害人类罪就是强行法上的罪行,因为危害人类罪违反了对整个人类的义务。
在纽伦堡审判中,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注意到从1939年战争开始起轴心国人员大规模地犯了战争罪,它们也是危害人类罪,而战争罪是传统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国际罪行。法庭的这个说法告诉人们,纽伦堡宪章中包含与战争罪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是合理的,具有习惯法的性质。[1]此外,对德管制委员会第十号法令、远东法庭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对纽伦堡原则的确认,更加强化了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这种强行法罪行的肯定。
二战后,对世义务和强行法理论都得到了发展,这也推动着国际社会对危害人类罪的研究和实践。
对世义务和强行法往往被看作是同一只硬币的两面。学术界一般认为,来源于强行法的义务是对世的,主张即“强行法”必然的产生“对一切的”义务。
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就对世义务发表过经典的评论,它说:在一个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和那些出自外交保护领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义务之间,必须做出实质性区别。考虑到所涉及权利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可以看作是在对于它们的保护中具有法律利益;它们是对世义务。
在这里,国际法院对“对世义务”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标准,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明显就是为了实施危害人类罪,那么它会因为违反强行法而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具体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员也应为自己的危害人类罪行为而承担个人责任。
二、国际法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方式
(一)一战后对德国责任人的失败惩治
一战后,协约国试图惩治挑起一战的德国皇帝及其手下一些官员。为此,协约国准备组建一个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且荷兰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理由拒绝交出威廉二世,所以这个尝试失败了,不过仍有积极意义,这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了运用国际法庭这种方式惩治责任人的重要性。
协约国和德国妥协的结果是由德国自己的莱比锡法院审判被告人。这次审判几乎是个形式,德国本国法院中立性大打折扣,但是,这次审判的积极意义仍是存在的,它确立了个人在战争期间的罪行在战后应当得到惩治这样一个理念。
(二)惩治二战责任人的方式
根据美国陆军部长史丁生及其下属莫里·柏奈斯制定的方案,盟国决定通过国际审判的方式惩治轴心国危害人类罪等罪行的责任人,1945年8月8日,同盟国在伦敦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决定成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国还制定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作为协定的附件。
法庭于1945年10月开始工作,总检察官委员会对纳粹德国的24名领导人及其所属的组织提起控诉,这些被告人当中,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腾布龙纳、罗森堡、弗兰克、弗里克、施特赖歇尔、冯克、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施佩尔、牛赖特、博尔曼、席拉赫、弗里切这18个人被指控犯下危害人类罪。[2]375-376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判决结果是:除了赫斯与弗里切两个人被宣告没有犯下危害人类罪之外,其他16个被指控犯下该罪行的被告人都在判决中被宣布犯有此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设立,设立的法律和理论依据与欧洲法庭基本相同,它对危害人类罪进行了类似的惩治。法庭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因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被判处死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2名战犯被判有期徒刑。
两个国际军事法庭惩治危害人类罪的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惩治犯罪,儆戒未来。两个法庭对危害人类罪这种极其严重的罪行进行了惩治,但惩治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威慑、警告那些潜在的危害人类罪行。纽伦堡法庭检察官杰克逊说:“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如何忠实的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3]其次,重新认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主权至高无上”曾是许多人的主张。纽伦堡审判破除了这种过于绝对的主张,向全世界表明,主权并非不受限制,主权必须尊重人权。在那些最为严重的国际罪行面前,受害者的人权应当得到国际法的保护,加害者则要承担连主权国家也无法为其开脱的国际法责任。[2]336第三,它们为以后的国际社会惩治危害人类罪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还出现了其他对危害人类罪进行审判的事件,如根据对德管制委员会第十号法令在德国各个占领区内由占领国进行的审判、1990年代出现的联合国两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塞拉利昂和柬埔寨法庭的审判、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等,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影响,它们惩治危害人类罪的经验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不过,审判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它们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首先,设立法庭的主体特殊。两个法庭虽然名义上是“国际”军事法庭,但是出面成立法庭的只是二战中的战胜国。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战中对德日作战的国家在战后组建法庭审判昔日的对手,有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的嫌疑。其次,审判对象特殊。两个法庭审判的对象仅限于德国和日本的战犯,可是,在同盟国一方,也出现过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没有受到审判,战后有人称这两个审判是“选择性的正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次,法庭的管辖有限。两个法庭是临时设立的,只是为了惩办二战中违反国际法的轴心国人员,一旦审判任务完成,马上就解散了。它的成立比较仓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瑕疵。比如,它们不允许被告人上诉,同时,还有个问题,法庭惩治被告人所依据的法律(即纽伦堡宪章和东京宪章)是在战后才制定的,而惩治的对象却是在此之前所发生的行为,法律似乎有溯及力,这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最后,法庭惩治不彻底。这里指的主要是东京法庭。
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的四大占领国即美苏英法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根据对德管制委员会第十号法令也设立法庭对危害人类罪进行惩治。纽伦堡法庭审判的是最重要的战犯,而根据第十号法令审判的是那些相比较而言不那么重要的战犯,但这些审判同样意义重大:惩治危害人类罪,发展危害人类罪的相关理论。
(三)联合国两个国际刑事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
1993年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1994年成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和卢旺达冲突中出现的危害人类罪(以及其他严重的国际法罪行),这是在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出现的对危害人类罪的大规模审判和惩治。
这两个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有其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首先,设立的主体具有公正性。设立两个法庭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是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它代表的是全世界、全人类。因此,惩治“危害人类罪”也就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气。其次,法庭的审理程序更加严密。法庭设立了上诉庭,允许被告人上诉,增加了稳妥和保险系数。再次,大大发展了危害人类罪的理论。在审判过程中,两个法庭对一些案例进行阐述,澄清了危害人类罪中的一些争议,如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的关联性问题,危害人类罪所要求的“广泛或有系统的对平民进行攻击”中的“广泛”如何理解?“有系统的”是什么意思?“平民”的内涵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在两个法庭在审判中解决的。
不过,法庭的管辖也具有局限性。两个法庭管辖的地域仅限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管辖的犯罪仅限于前南斯拉夫地区1991年以来发生的罪行,以及卢旺达境内1994年发生的罪行。两个法庭的审判任务一旦完成,马上解散。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是打了折扣的,对于两个地区之外以及规约规定的时间之外发生的危害人类罪,它们是无法惩治的。
(四)国际和国内混合法庭
1.混合法庭的典型例子
混合法庭是由东道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共同组建的法庭,其典型例子是东帝汶混合法庭、塞拉利昂混合法庭、柬埔寨混合法庭等,它们致力于审判和惩治的危害人类罪行为主要是:发生在1999年东帝汶暴乱期间的罪行,发生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的罪行,以及红色高棉统治期间的罪行。这些混合法庭具有国内法庭和国际法庭的双重特征,比如,东帝汶法庭每个分庭由2名国际法官和1名当地法官组成,特别法庭还设立一个调查股,在东帝汶总检察长领导下调查严重的犯罪,调查员多数是国际职员。上诉案件向帝力法院提出,其多数法官也是国际法官。[4]136塞拉利昂法庭和柬埔寨法庭也有类似的做法。
2.对混合型法庭惩治危害人类罪的评价
混合型法庭惩治危害人类罪考虑到了国内正义和国际正义两方面需求。
从国内正义来说,这些冲突虽然可能也有涉外因素,但基本上是国内冲突,在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时候,其本国司法机构起重要力量。而且,由本国法官参与,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司法资源,吸收当地法官参与审理,有利于调查案情。同时,可以避免审判由国外力量操纵的嫌疑。
从国际正义来说,国际社会有必要介入一国的危害人类罪惩治之中。危害人类罪即便是在一国内部发生的,也是对全人类尊严的侵犯,国际社会参与惩治,不仅是为了犯罪发生地的民众,也是为了全人类。在一国内发生的危害人类罪,是对该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一个威胁和破坏,国际社会参与惩治,也是为了防止事态蔓延。
(五)国际刑事法院
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大会在罗马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2002年7月1日,规约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法院管辖的核心罪行之一就是危害人类罪(其他核心罪行是:灭种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国际刑事法院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方式比较稳妥。
首先,设立法院的主体是整个国际社会,它的权威性是很强的,可以说是代表全人类,它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具有非常强的合法性,甚至超出安理会,因为安理会是个政治机构,一个政治机构设立国际司法机构(比如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并且这个国际司法机构还附属于这个政治机构,那么这个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就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它是常设性的机构。二战后两个军事法庭、联合国两个刑事法庭以及混合型的司法机构都是临时性的,一旦完成审判任务就立即解散,而国际刑事法院在理论上是讲是永久性的,这种永远存在的特征,可以极大的威慑潜在的危害人类罪行为人,把一些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再次,它适用的法律比较规范。国际刑事法院有专门的规约,其中详细规定了它管辖犯罪的构成以及审判所涉及的程序性事项,在规约之外,还有犯罪要件,其中更加详细的规定了危害人类罪各个罪行的犯罪构成,这便于法院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惩治危害人类罪。因为规定的非常详细,就大大减少了出现争议的可能性。特别是,国际社会在惩治之前进行了立法,可以避免过去出现的关于事后立法的争议。
最后,在地域上的管辖具有全球性。国际刑事法院地域管辖范围比之前的国际军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庭要广阔,它不仅可以管辖缔约国国民的危害人类罪和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的罪行,甚至可以管辖非缔约国国民和非缔约国领土上发生的危害人类罪。这就大大加强了打击这种罪行的力度,等于是严厉警告了全球的独裁者和其他潜在的犯罪人。[5]
三、国际法惩治危害人类罪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
在国际法惩治危害人类罪过程中,曾出现过被告人对国际司法机构惩治这种罪行的合法性问题的质疑,归纳一下有两种:第一,对危害人类罪的事后立法问题;第二,国际司法机构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一)事后立法问题
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时候,一些被告人提出这个质疑。表面上看,这样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之前,没有哪个国际法文件明确的禁止“危害人类罪”,在国内法中也找不到这个罪名,而两个法庭宪章却在意图打击的行为发生之后,才规定惩治这些行为的,这不是事后立法吗?事后立法问题不仅出现在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中,在冷战后的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中实际上也出现了。
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法庭花了比较大的力气来解决被告人提出的这个质疑。不过,纽伦堡法庭的一些法官和当时一些学者对于事后立法的解释却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不敢苟同的解释主要有:(1)法庭被自己法律所拘束因为不能调查自己的合法性或其法律的合法性;(2)危害人类罪是战争罪的延伸,因此纽伦堡宪章这样规定就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3)宪章宣布了国际法,并且国际法禁止那样的行为。[6]这些解释无助于驳斥被告方的质疑,因为这些解释要么是同义反复(比如第一种和第三种),要么是难以说服严格的实证主义者(比如第二种观点)。
其实,要解释“事后立法”所带来的困惑也不难,我们可以找到几点理由:
第一,国际法的渊源不仅有条约,还有习惯。在纽伦堡宪章之前已经出现了禁止危害人类罪的观念、原则,尽管这种禁止并不像后来的宪章那样白纸黑字的明确。从这个角度来说,纽伦堡法庭把危害人类罪作为习惯国际法上的罪行加以惩治,是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第二,对危害人类罪等最严重罪行进行惩治才是法庭的目的,也才是国际正义的要求,这要求实现实质上的正义,事后立法这个瑕疵,不足以掩饰实现实质国际正义的光辉。如果我们机械的、僵化的理解罪刑法定,那么对历史上最残暴罪行的惩治就会落空。
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已经不会出现事后立法这个争议。
(二)法庭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国际法在惩治危害人类罪过程中,除了遇到事后立法这个质疑之外,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法庭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这里我们主要以联合国刑事法庭惩治危害人类罪过程中法庭的合法性为切入点。
塔迪奇(Tadic)在前南法庭被指控犯下危害人类罪和其他严重罪行,其辩护人提出,《联合国宪章》没有关于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来建立一个司法机构的明确规定,更不用说安理会拥有设立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刑事法庭的权力。[4]168
现在问题的核心是:安理会到底有没有权力建立前南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等罪行进行审判?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是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的联合国机关,第七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这里,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是“武力以外之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从字面上看,第四十一条也没有明确规定安理会就可以设立国际刑事法庭。
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是军事行动。安理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行为不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措施,虽然在法庭下令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会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但设立法庭这个行为还不是。
可是,我们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字面上,第四十一条没有明确提到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不等于它不允许这样做,它所列举的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等等,只是举例子而已,宪章并没有说可以采取的措施就必须局限于这些,特别是“得包括”一词意味着这些例子供安理会参考,安理会还可以其他措施。基于这样的分析,前南法庭上诉庭得出结论认为,安理会有权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因此前南法庭的合法性不是问题。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在惩治危害人类罪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本身的合法性遇到的挑战比较少,因为它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成立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四、结语
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最初的时候,国际法对这种罪行的惩治方式是比较简单、粗糙,也是 分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审判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虽然后来失败了,却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躲在主权的屏障后面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二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是比较成功的,但仍存在不小的瑕疵,特别是在罪刑法定和法庭自身合法性等方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两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实践推动了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思考,这些有益的思考最终也推动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在笔者看来,由国际刑事法院对危害人类罪进行惩治,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惩治危害人类罪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事后立法和法庭本身合法性这两方面的质疑,虽然这些问题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但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使得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国际法机制更加完善。从总体上看,国际法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方式越来越成熟,这是国际法机制走向健全的一个标志。
[1]杜启新.国际刑法中的危害人类罪[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74.
[2]何勤华等.纽伦堡审判[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3]P.A.施泰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
[4]朱文奇.国际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朱文奇.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J].政治与法律,2003(1).
[6]M.Cherif Bassiouni.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International law[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149.
(责任编辑 吴兴国)
D99
:A
:1001-862X(2011)03-0122-006
张新广(1970-),男,河南西平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法研究。李明奇(1979-),男,河南焦作市人,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