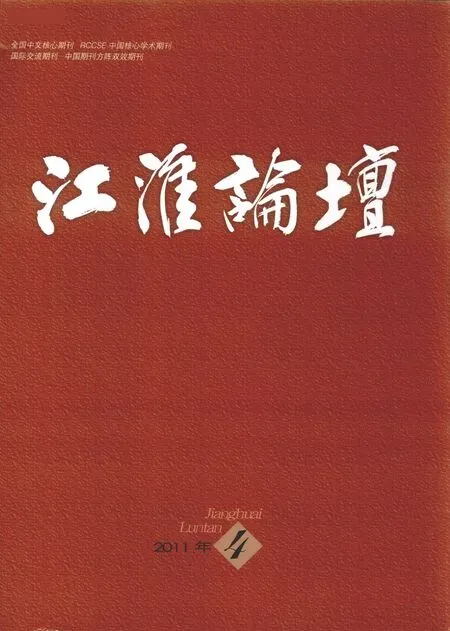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
——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
高超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 041004;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
——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
高超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 041004;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进入了形象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宇文所安通过对唐诗的翻译与阐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唐代文学文化世界,而孕育其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更是富有创造性特质。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探究宇文所安文论中所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生成方式以及形象建构的意义。
形象学;唐代诗人形象;宇文所安;文论;《初唐诗》;《盛唐诗》
在比较文学的语境下,形象学是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分支而存在,以研究异国形象为主要内容。传统形象学研究文本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游记和文学作品:一是研究 “游记这些原始材料”,但主要还是研究“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直接描绘异国,或涉及到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一个异国的总体认识”。[1]
步入当代形象学以后,形象学研究逐步拓展了它的疆域:研究文本的范围开始由文学文本扩展到非文学文本的文化领域,因为 “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这种研究方向要求比较学者重视文学作品,重视其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同样也要研究一切文化材料,我们是用这些材料来写作、生活、思维的,或许也是用它来幻想的。”[2]154-155
首先,法国学者巴柔把一些非文学文本引入形象学研究领域,并拿它们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做对照,他指出,“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学文本,而是看看在其它领域(报刊,私人信件,半理论化文本——序言、申明、论文、教材,这些对复制描述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中,那些原先孤立地存在于虚构文学中的形象是怎样重复和变化的”。[3]129其次,有着“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美誉的德国学者狄泽林克发现了研究形象学的一个新视角,“即形象存在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编撰和文学研究中”,他认为,“翻阅一下文学史专著,便能较快地获得关于形象问题的相应印象。这些书籍几乎见之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外语课所采用的读本,其中甚至包括对他国“本质”和他民族“特性”的极其惊人的浮泛之论,且不加批判地传递给读者。”[4]此外,翻译《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的方维规先生把狄泽林克先后有关形象学研究的论说作了一个很好的勾勒:“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4]由此可见,形象学研究的边界逐步得到拓展——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进入了形象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
在当代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中,宇文所安不仅凭借着丰硕的文学著述给西方读者带去鲜活、灵动的中国“文学文化”(1),而且其新颖、富有创见的文学思想也正以最迅猛的速度反向传播到中国本土。宇文所安通过对唐诗的翻译与阐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唐代文学文化世界,而孕育其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更是富有创造性特质。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探究宇文所安文论中所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生成方式以及形象建构的意义——借用巴柔所引用乔治·杜毕和费尔南·布洛代尔常说的一句话来表述,就是“精神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在物质层面上产生出反响? ”[3]130
一、宇文所安文论中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
宇文所安文论中的唐代诗人形象,主要是指宇文所安在对唐诗的阐释中所建构的唐代诗人形象。宇文所安对唐诗进行了比较系统化的翻译、评析,其相关著述颇丰。单就其专著而言,从他最初的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歌》,到他的成名作《初唐诗》,再到《盛唐诗》、《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追忆》、《迷楼》、《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他山的石头记》和《晚唐诗:九世纪中叶的诗歌》,就有十部之多,实可谓硕果累累。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视域里的中国唐诗无疑属于西方文化的“他者”。宇文所安对唐诗这一“他者”的审视必定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视角,这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质所决定的。宇文所安曾经十分诚恳、谦逊地说:“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5]1这里的 “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显然是指他所处的中国学术传统之外的西方文化学术背景,因此,所产生的“不同的角度”是必然的,由此而生成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学术效应也是十分正常的。下面我们主要以《初唐诗》和《盛唐诗》为例,探究宇文所安在阐释唐诗、建构唐代诗人形象时有哪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以凸显其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独特性。
其一,唐诗史研究新线索的发现。宇文所安发现唐诗在由初唐向盛唐的历史演进中存在着一条重要线索,即“宫廷诗”与“京城诗”的线索。宫廷诗,是宇文所安创建的、易于理解而又方便使用的术语:“‘宫廷诗’这一术语,贴切地说明了诗歌的写作场合;我们这里运用这一术语松散地指一种时代风格,即五世纪后期、六世纪及七世纪宫廷成为中国诗歌活动中心的时代风格。现存的诗歌集子中,大部分或作于宫廷,或表现出鲜明的、演变中的宫廷风格。‘宫廷诗’必须明确地与‘宫体诗’区别开来”。[5]5宫廷诗在内容上多是歌功颂德、娱乐消遣一类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矫饰的感情。宫廷诗在形式上虽有矫揉造作之嫌,却代表着当时流行的雅致、华彩的宫廷趣味。比较常见的宫廷诗有宫廷宴会诗、宫廷咏物诗、科举考场中的应试诗、朝臣之间的酬赠诗以及包括朝臣“奉和”皇帝、公事送别等涉及各种礼仪活动而制作的应制诗。宇文所安认为,在初唐诗歌的演进史中,初唐的宫廷诗源于南朝的宫廷诗,它与其对立面——具有复古观念的“对立诗论”相伴而发展;但初唐宫廷诗的标准和惯例又为后来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超越的对象:“盛唐的律诗源于初唐宫廷诗;盛唐的古风直接出自初唐诗人陈子昂和七世纪的对立诗论;盛唐的七言歌行保留了许多武后朝流行的七言歌行的主题、类型联系及修辞惯例”。[6]4而且“宫廷诗在应试诗中被制度化,而终唐一世它一直是干谒诗的合适体式。 ”[5]11因此,宇文所安把“宫廷诗”作为一个视角,一条主线来安排《初唐诗》的结构与叙事。《初唐诗》共分为五个部分——“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脱离宫廷诗”、“陈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张说及过渡到盛唐”。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宫廷诗”这条叙事主线。“陈子昂”也是被宇文所安作为高度个性化的诗人而归入“宫廷诗”的对立面——作为“宫廷诗”的否定者出现的,而张说更像初唐宫廷诗的“收尾者”,及至到了张说的门生张九龄已是一脚迈进了 “盛唐”——此时宫廷诗人与外部诗人的界限已被打破了。
“京城诗”这个术语,也是宇文所安的“专利品”。宇文所安主要用它来概括盛唐时代诗歌的主流趋向,“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 ‘京城诗’的现象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诗涉及京城上流社会所创作和欣赏的社交诗和应景诗的各种准则……与宫廷诗一样,京城诗很少被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是主要被当作一种社交实践……”[6]4如同“宫廷诗”是《初唐诗》的叙述主线一样,“京城诗”成了《盛唐诗》叙述的一条主线。《盛唐诗》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盛唐的开始和第一代诗人”有九章内容,第二部分“‘后生’:盛唐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有十六章内容。它是按照“京城诗”的线索来安排篇章结构的:在一些主要篇章的题目中,作者采用比较明显的“京城诗”的字眼(像“开元时期的京城诗”、“京城诗的新趣味”、“八世纪后期的京城诗传统”等),其它单列篇章的重要诗人不是京城诗人就是作为京城诗人的对立面——非京城诗人而出现的。《初唐诗》与《盛唐诗》属于文学史写作的范畴,“宫廷诗”与“京城诗”作为其叙述线索,是不同于中国学者的新视角、新发现,既合乎唐诗发展的实际,也契合于唐诗演进的规律。
其二,宫廷诗人与非宫廷诗人。宫廷诗是《初唐诗》的叙述线索。它既然是“大部分或作于宫廷,或表现出鲜明的、演变中的宫廷风格”的诗,那么宫廷诗人的指称范围就异常广泛了。其实,不写宫廷诗的非宫廷诗人是不多见的。更多的初唐诗人是介乎于宫廷诗人和非宫廷诗人之间的诗人,既写“宫廷诗”,又写极具个性化色彩的“个人诗”。宇文所安聚焦“宫廷诗”的目的在于更清楚地探究“宫廷诗”以及偏离“宫廷诗”倾向的诗作(包括与“宫廷诗”截然对立的“对立诗论”的诗)的历史演进轨迹。宇文所安概括出了宫廷诗的三种程式化的“标准和惯例”——一是“题目和词汇的雅致”,一是“对隐晦词语、曲折用法、含蓄语义及形象化语言的普遍偏爱”,一是其 “三部式——主题、描写式展开和反应的结构惯例”。[5]7-8宇文所安依照这种宫廷诗的“标准和惯例”对重要的初唐诗人展开了细致的文本细读。从宇文所安对诗作特点的大量分析中,我们发现了诗人的性情,发现了诗人的自我形象特点。
“宫廷诗人”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那些明显具有“宫廷诗”风格的诗人。比如,来自昔日南朝文化和宫廷诗中心的太宗朝诗人虞世南、褚亮、许敬宗和陈叔达都是宫廷诗的“能工巧匠”;被赋予“上官体”荣誉称号的上官仪,犹如戴上了一顶“宫廷诗人”的“桂冠”,却免不了陷入宫廷利益的争斗而不得善终;严守宫廷诗的成规,却集咏物诗作之大成的初唐诗人李峤以120首咏物诗辑录成诗集《杂咏》,受到盛唐作家张庭芳的高度赞誉;与李峤同为“文章四友”的杜审言不仅以优美率真的诗句彰显了宫廷诗中的个性因素,促进了律诗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中国诗坛上伟大的“后来者”——他的孙子杜甫;中宗朝最重要的两位诗人沈佺期与宋之问,对宫廷诗的改造与律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却因依附武后、投身武后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而遭贬逐……一类是那些既写“宫廷诗”,又写“个人诗”的诗人。宇文所安认为宫廷诗基本上反映一种无个性差别的活动,所以他对背离宫廷诗风格、注重表现诗人个人生活和内心情感的诗以“个人诗”冠之。这些既写“宫廷诗”、又写“个人诗”的诗人在初唐诗坛上也不乏其人。比如,被一些宫廷诗的“巧匠们”包围着的唐太宗就是这样的人,他怀抱着中庸之道——“既鼓励儒家的教化,也提倡宫廷诗的雅致”[5]42;从隋朝入唐而来的具有“对立诗论”风格的魏征和李百药却走向了“对立诗论”的反面:魏征转向了枯燥乏味的说教诗,而李百药则趋奉太宗的宫廷诗倾向;[5]22“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初唐四杰”以真实直率的朴素美逐渐溢出了“宫廷诗”的那份“雅致”;从初唐步入盛唐的诗人张九龄以大量带有复古思想的宫廷诗,开始打破了宫廷诗与外部诗人的界限……
“非宫廷诗人”是那些与宫廷风格背道而驰的诗人。这种在初唐诗坛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非宫廷诗人非王绩与陈子昂两位莫属。王绩是一个“既抛开柔软的宫廷风格,也脱离对立诗论枯燥诗歌”、具有“陶潜的精神”的“怪诞的醉汉、固执的隐士及自足的农夫”[5]48-56——一个“不愿写、也不会写宫廷诗”[5]264、高洁而朴实无华的隐士诗人形象;曾在京城里追逐功名、胸怀天下之志兼有宇宙意识的“蜀子陈子昂”却高扬着复古的大旗解构了“宫廷诗”的娇媚和柔弱……
其三,“京城诗人”与“非京城诗人”。宇文所安打破了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和边塞派诗人的界限,以“京城诗人”与“非京城诗人”为视角,重新审视八世纪的中国诗坛。宇文所安认为,在盛唐时代诗歌是“京城名流广泛实践和欣赏的一种活动”,而“京城诗人”则是“其中最著名、最引人注目、最有诗歌才能者”——“虽然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诗歌趣味和美学标准,他们并没有共同推尊某一位大师或某一种诗歌理论,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他们的诗法中的共同成分,从属于他们的友谊和在京城社会的地位。”[6]63-64显然,宇文所安主要是从诗人活动的地域、诗歌中共同的旨趣以及诗人之间的友谊和地位来裁定“京城诗人”的。因此,在宇文所安的视域里,盛唐诗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京城诗人”、“非京城诗人”。
首先,“京城诗人”主要指居住在京城、以诗歌作纽带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他们是在与外地诗人对照中形成的——“与那些相对独立地形成诗歌风格的同时代诗人的对照”[6]72。宇文所安把处在开元时期(713-741)的京城诗人视为第一代京城诗人,他们的核心人物是王维、王昌龄、储光羲、卢象及崔颢。大诗人王维是京城诗人中善写寂静和隐逸主题的最杰出代表。他把八世纪京城诗人的精致技巧与对陶潜诗中的“随意简朴”风格的模仿相结合起来,使得这两种对立的诗风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完美的地步。王昌龄创作的边塞诗,作为京城诗的 “变体”——“虽然保留了京城诗的社交范围,却尝试了新的题材和模式”,[6]64开创了京城诗的新趣味。 储光羲“在陶潜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质朴田园诗。 ”[6]72崔颢广交京城诗人,放荡不羁,“与他作为浪子的典型角色相一致,他偏爱的是乐府和七言歌行”,[6]73一首七言律诗《黄鹤楼》赋予他在唐诗史上不朽的地位。作为京城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是八世纪中、晚期的一群沿袭京城诗传统的“追随者”。
其次,“非京城诗人”又被宇文所安称作“真正的外地诗人”——因为他们 “缺少京城诗人的共同联结——他们的文学修养及为适应京城名流的需求而经常进行的艺术实践”[6]64。他们大都是地方诗人和外地来京城的诗人,往往形成了与“京城诗人”迥异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诗风。除了大诗人王维是典型的京城诗人之外,盛唐其它大诗人诸如孟浩然、高适、王昌龄、李白、岑参、杜甫、韦应物等都是“非京城诗人”著名的代表,其中“李白和杜甫占据了读者的想象中心”。[6]导言这些“真正的外地诗人”,虽然“有些诗人向往京城诗,有些诗人反对京城诗,但正是在京城诗背景的衬托下,他们成了真正具有个人风格的诗人”。[6]导言比如,孟浩然对隐逸和风景题材的偏好与京城诗人趋向一致,但其诗歌的背后却隐藏着独特的气质——一种散漫随意、洒脱快乐的自由,超越了京城诗的典雅。宇文所安认为京城诗代表着盛唐诗坛的主流趋向,京城诗人普遍享有广泛的社会声誉和影响,但真正创作出盛唐时代最伟大诗歌的当属“非京城诗人”。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宫廷诗”还是“京城诗”都不是定义明晰、准确严谨的科学术语,仅仅只是宇文所安写作唐诗史时的一条叙述线索,一个观察视角。恰恰是因为这条线索的明晰性和这个视角的独特性,宇文所安才得以凭借诗人的传记资料,建构丰富、合理的历史想象力,清楚地为读者展现了大唐时代诗人们生活的广阔背景。而这种趋于真实的历史语境的建构正是宇文所安解读唐诗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宇文所安通过细读诗歌文本为我们展现了唐代诗人的风貌。单以《盛唐诗》的写作而言,宇文所安抛开了自南宋严羽以来所谓“盛唐气象”的观察视角,以具象化的历史语境再现了诗人们作诗论文的背景。李白和杜甫已不再是仅仅代表着“盛唐气象”的李白和杜甫;宇文所安没有用他们来界定盛唐时代,而是借助盛唐时代诗歌的实际标准来理解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据此,我们重新认识了处于变化中的唐诗风格以及变化中的唐代诗人形象。
二、宇文所安文论中唐代诗人形象的生成方式
如前所述,以《初唐诗》与《盛唐诗》为例,我们发现了宇文所安以“宫廷诗人与非宫廷诗人”、“京城诗人与非宫廷诗人”的分类方式,以是否居于时代诗坛主流为标杆,重新审视了七、八两个世纪的唐代诗坛的历史风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唐代诗人形象。下面我们将结合宇文所安的其它相关文论,对宇文所安文论中的唐代诗人形象的生成方式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宇文所安非常注重诗作者的生平与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喜欢在历史语境中把握一首诗的思想内涵以及诗中的诗人形象。他认为,“从文学经验的角度看,作者的生平及特定的创作背景是首要关注的对象:诗歌被十分突出地作为历史表现的特殊形式,而不是普遍真理的陈述。”[6]113比如,在《盛唐诗》第六章中,宇文所安评析诗人孟浩然的诗作时,即是把孟浩然的生平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其诗作的分析与阐释过程。他叙述孟浩然的生平事略依据的是加拿大汉学家白瑞德(Daniel Bryant)的《盛唐诗人孟浩然:传记和版本史研究》和中国学者陈贻焮的《孟浩然事迹考辨》。细读孟浩然的诗句:“家世重儒风,……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松泉多清响,苔壁饶古意。”“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邻清。”宇文所安从中发现了诗人在作品中所呈现的自我形象:一位失败的求仕者,一位热情的旅行家,一位喜欢欢宴的朋友及一位闲适的乡村绅士。把诗人的生平与其诗作结合起来,宇文所安发现作品中的孟浩然形象就是诗人自己真实面目的一部分。[6]86-90诗人孟浩然的形象是诗歌文本中的诗人自我形象与历史传记文本中的诗人形象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形象。它既有写诗人孟浩然所创造出的形象成分,同时又有作为读者的宇文所安主观想象而构建出来的形象成分。
宇文所安这种注重诗歌文本与作者及时代相关联的批评方法,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以及“以意逆志”的方法如出一辙。“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这两种方法最初是由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孟子在《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就是把作品、作家同时代联系起来。为了知人论世,古代文学批评中遂有“纪事”、“年谱”等类著作。纵观宇文所安的《初唐诗》与《盛唐诗》,我们可以看出,宇文所安非常注重对诗人的生平传记的考释。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逆志”是指以说诗者之意去推度诗作者之志,注重的是说诗者主观的作用。宇文所安深谙中国抒情诗“诗言志”的传统。在《盛唐诗》中,他还对“志”作了一番解释,“‘志’集中于、产生于对外界特定事件或体验的内心反应……‘志’是由实际心理和特定的外界体验决定的,中国诗人作品中的各种复杂多样反应,都可归因于‘志’的激发。”[6]88无疑,他在阐释唐诗、建构唐代诗人形象时采用了“以意逆志”这种方法。宇文所安如此熟练地运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唐诗,表明他十分透彻地了解中国传统诗歌的内涵,也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
其次,宇文所安自身的西方文化学术背景身份,又常常使他站在中国学术传统之外看问题。他对于唐诗的阐释与唐代诗人形象的建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在《苦吟的诗学》[7]159-175一文中,宇文所安对那些殚精竭虑苦苦吟诗的诗人作了一番经济学的分析。文章开头是清代诗人黎简(1748-1799)的一首五律《苦吟》:巷庐都逼仄,云日代晴阴。雨过青春暝,庭凉绿意深。病从衣带眼,老迫著书心。灯火篱花影,玲珑照苦吟。宇文所安借这首诗追溯历史上的苦吟诗人,并探寻苦吟的意义与价值。宇文所安的提问方式非常直接:“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写一首诗?”[7]162他很快在贾岛的一首绝句中寻到了答案: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们看到了某种好似经济宣言的文字,诗人对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予以精确的计算”,苦吟诗人苦吟诗作是在寻找 “知音”:“如果我们把经济的比喻延伸到美学的领域,价值非常需要一个‘买主’——一个赏识的人”[7]164很明显,宇文所安发现了中国诗人的商人气质。为了证明他的发现,宇文所安列举了许多诗人有关苦吟的诗句作为例证。其中,他又引了贾岛的一首诗《戏赠友人》: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由此,宇文所安成功地建构了唐代诗人中的“商人”形象。
但是,针对同样一首《戏赠友人》,日本学者、唐诗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贾岛的这首诗体现了唐代诗人普遍存在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位专写‘苦辛词’的诗人他也感到,像他那样,把自己的生命清白地维持下去,有一种值得自豪的愉快,这是不能称作消极厌世诗的。 ”[8]
吉川幸次郎与宇文所安对同一首唐诗的解读如此大相径庭,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他们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吉川幸次郎还是宇文所安,他们都视中国文化为“他者”。法国学者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2]155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唐代苦吟诗人形象,对于吉川幸次郎与宇文所安而言,都是“他者”形象,而这个“他者”形象的建构却充塞着吉川幸次郎与宇文所安“自我”的想象。 巴柔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2]157我们不难看出,宇文所安视域里的苦吟诗人形象——一个有着极强功利色彩的“商人”形象,必定带有身处西方发达商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宇文所安“自我”想象,正如巴柔所言,“这个‘我’想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2]157。而吉川幸次郎眼中的苦吟诗人,却是一群视苦吟为人生乐趣、积极向上的中国文人形象。由于吉川先生身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并不太大,所以他建构的苦吟诗人形象比较接近历史语境中的苦吟诗人。
宇文所安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构筑在对唐诗文本以及相关历史文本阐释、评析的基础之上,它不可能是唐代现实生活中诗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只能是诗的写作者和兼有读者与作者身份的评论家宇文所安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形象,正如法国学者莫哈所言:“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作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这些都是主观性向往相异性所特有的”[1]。因此,宇文所安文论中建构的唐代诗人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宇文所安自我想象的因素:有的形象较接近于历史语境中的唐代诗人,有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想象。
三、宇文所安文论中建构的唐代诗人形象的意义
如上文巴柔所言,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之间的互动,而且“他者”形象投射出了形象制作者自身的影子,因此,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更注重形象制作者一方的研究。中国学者孟华教授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的革新与继承,她说:“如果说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注重对主体的研究、注重文本内部研究以对传统的革新为主,那么重视总体研究则以对传统的继承为主”。[9]上文对宇文所安文论中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与生成方式的探讨,即是着眼于文本内部的研究——文本中的“异国形象是怎样的”以及注重对形象创作主体“我”的研究。被孟华教授视为对传统继承的“总体研究”,指的是“要从文本中走出来,要注重对创造了一个形象的文化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研究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9]由此看来,探讨宇文所安文论中建构的唐代诗人形象的意义,还应更多地着眼于他者形象抑或异国形象的制作者宇文所安以及其所在的注视者文化本身。
注视者宇文所安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宇文所安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对中国文化由衷的喜爱之情,他说,“十四岁那年,……我偶然读到一本英文的中国诗选,感到非常新鲜,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中国诗歌。后来到耶鲁大学读书,我主要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大学毕业后,很自然地考进耶鲁的研究院,学习中国古代文学。 ”[10]“中国古代文学最吸引我的,是其中充满着那种可以被整个人类接受的对人的关注和尊重。我所喜欢的诗人,不是那种带有神性的高高在上者,而是一个能和其它人进行平等对话的人的形象。”[11]相对于西方的现代诗而言,宇文所安更喜欢中国古典诗,他曾说过,“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12]
作为西方学者文化身份的宇文所安,除了对中国文化表示极大的尊重与喜爱之情之外,还表现了一个作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批评者的极大热忱——这种热忱主要体现在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利用关系。美国学者史景迁说过,“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利用是极其复杂的,它不仅体现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两个不同民族间思想和意愿的微妙的交流中。”[13]宇文所安视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他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将成为全球共同拥有的遗产,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物”[10]。基于这样的理念,“为我所用”的思想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指出“其实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主要为了美国的文化建设,而不完全是为了对中国文化发言……我认为,在中国文学中,深刻地体现了生活和写作的完美结合,我希望美国文化中也能够融入这种精神。”[11]
由此可见,当“本土”的西方文化与“异域”的中国文化相遇时,作为注视者“我”的宇文所安,对于“他者”文化更多地传递了一种平等与友善的理念。巴柔曾指出,支配对他者言说的某一个作家或集团的态度有三种,其中之一是:“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视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的。这种相互的尊重,这种为双方所认可的正面增值有一个名称:‘友善’。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3]142因此,宇文所安文论中建构的唐代诗人形象,构筑在中西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的大语境下,对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民族间相互认知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他者”形象所促成的国际间文学、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姻缘”有力地证明了形象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合理性。
注释:
(1)宇文所安常用“文学文化”这个词指称“关于文学出现的整个文化世界”,参见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 “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0,(9):67。
[1][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J].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5,(1).
[2][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德]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J].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3).
[5][美]宇文所安.初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6][美]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7][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03.
[9]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
[10]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0,(9).
[11]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J].文学遗产,1998,(1).
[12]李宗陶,宇文所安﹒中国古诗里有人与人的交流[J].南方人物周刊,2007,(30).
[13][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3.
(责任编辑 文 心)
雅雅的骂詈,倒背离了他们的个性。所以他们的骂辞中,命令、诅咒、威胁、揭隐,应有皆有,特别是骂娘,还比率偏高。
由此可见,文学创作,形象塑造,手段方法多种多样,而骂詈的描写,特别是骂辞的信息范畴的选择,是有效方法之一。骂辞的信息范畴选择,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教养和生存环境,一句话,要符合人物个性,要服务于形象塑造。在这方面,以上三位文学大师以他们的成功创作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
注释:
(1)[南梁]肖统《文选》卷44李善注引《魏志》。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133.
[2]何兆熊主编.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0.
[3]李炳泽.咒与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98.
[4]鲁迅.漫骂[A].花边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0.
(责任编辑 文 心)
I207.22
A
1001-862X(2011)03-0181-007
山西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YS08016)
高超(1969-),男,安徽淮南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文学关系研究、欧美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