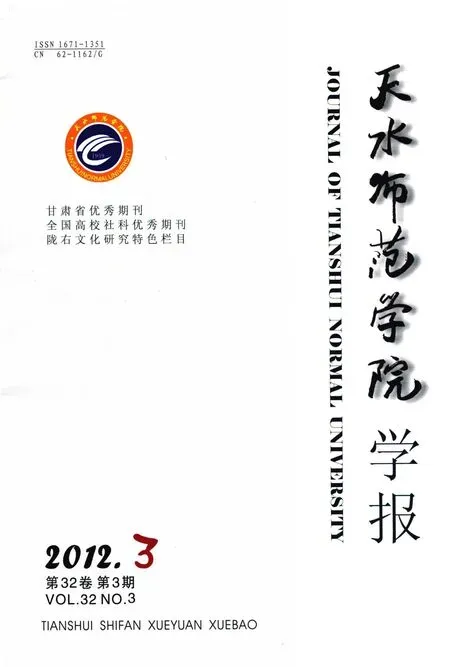论秦文化的尚武精神
蔡智忠,马明达,聂 晶,毛海燕
(天水师范学院 体育科学研究所,甘肃 天水 741001)
论秦文化的尚武精神
蔡智忠,马明达,聂 晶,毛海燕
(天水师范学院 体育科学研究所,甘肃 天水 741001)
大秦帝国在建国立基前经历了十三代几百年的创业奋斗历程,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军事、经济底蕴与实力。以武立基、武力建国是秦人成功的一条不二道路,秦人长期生存在西北戎、狄等少数野蛮民族之中,艰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给秦人太多生存的障碍和展示勇武的机会,悍勇尚武,隆兵重伐,是这一时期秦人唯一的选择。历史选择了骨子里透着霸气的“赳赳老秦”岁月锻造出了有“虎狼之帮”称谓的秦人“锐士”,凭借军事、文化上的强势,挺进中原,完成了“扫六合,成一统”的历史伟业。
尚武精神;秦人;文化;霸气
一、秦人、秦族及秦文化
秦人的远祖出于何方?这在史学界一直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秦人可能出于东夷系统,起源地在山东或东北。也有人认为应出自西北的西戎系统。两说各有所据,迄今并无定论。[1]但其崛起之地是在甘肃的秦地,这是学界普遍认同并被大量考古资料所证明了的。所谓“秦地”,即今天甘肃天水市境内的清水、张家川一带。近年来,秦的先公先王和贵族大臣的墓葬之地在今陇南礼县的大堡子山一带被盗掘,一个规模宏大而陪葬丰富的王者之墓,被认为很可能是秦国立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秦襄公之墓。[2]此外,在天水的张家川、清水、甘谷等县和天水市北道区等地也先后发现有早期秦墓。
秦人的来源是还需要继续探讨的疑难问题,很难遽作定论。根据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考证论述:“秦人起于西北,在陇西的秦谷滋生繁衍,故名秦人。”“从《毛诗》的诗篇《秦风》与《史记·秦本纪》中可窥寻秦人生息发展的脉络。”(文怀沙著《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秦文化明显受到西北羌戎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周文化的浸润。正由于秦人长时间与羌戎杂处,甚而会有民族融会关系,故秦人有慷慨激越、尚勇敢战之风。王遽常先生说:“秦起西垂,多戎患,故其民朴实坚悍,尚气慨,先勇力。读《小戎》、《驷铁》、《无衣》诸诗,其风声气俗盖由来久矣。商君资之更法,以强兵力农,卒立秦大一统之基。”[3]卷29《三力传》180
王先生所言无疑是准确的。秦国的确是一个尚武的国家,纵观从秦襄公正式立国,经过商鞅变法,到最终由秦始皇灭亡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全过程,这一特点贯彻始终,成为秦的文化优势,也是最引人瞩目的特点。《诗经·国风·秦风》存秦诗十首,多首与战争和行猎有关,上面王遽常先生提到的《无衣》一首,可作为代表之作。关于此诗,高亨先生说:“这是秦国劳动人民的参军歌。”袁梅先生认为:“反映了古代人民以爱国精神参加正义的卫国战争的思想情感。”[4]古典注家说:“秦人强悍好斗,其平居相谓如此。”但也有学者认为它表达的是“上下相一体之意”,即既有“王于兴师”时,“民皆自修其戈矛而与之同仇”的情形,也有表达老百姓互相引为“同袍”而同仇敌忾的精神。[5]卷11《无衣》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关于《无衣》,《毛诗序》说是“刺用兵也。秦人剌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也。”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则云:“山西天水、安定、北地地势迫于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兵,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6]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在我们看来,显然班固之说是诸家解说中最可取的,班固博学多识,去古未远,他的解说必定有所依据。要之,《无衣》是武土们奉命出征时的壮行诗,是勇者的沉吟,是战友间的激励!修戈矛、修矛戟、修甲兵的战前准备是何等壮怀激烈;与子同仇、偕作、偕行的互勉与激奋,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和团结精神!这在以战争为题材的古代诗歌中的确是不多见的,真正是鼙皷催人的金声玉振之音,所以千古以来成为此类作品中最具代表的佳作。
关于秦的尚武传统,不少学者已有所探讨,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我们再通过以下几点来叙述我们的拾遗补缺之见,以备大家参考。
二、孟贲、乌获——勇士的象征
秦人尚勇,这首先表现在秦的历史上出了许多有名的勇士,这些勇士名重天下,成为秦人武勇精神的标志,也成为天下人心目中勇士的象征。明人高弘图认为,秦人的雄桀之气出于天性,他以孟贲、乌获为例,说:“始皇帝燔上世之书,自为制诏碑颂,其雄霸桀鷔之气,前无古昔。然资禀甚异,譬如孟贲、乌获,虽不由师授,而拳勇过人,其文熄而能创。”见于史籍,最早具有奇才异能的勇士应是秦的先祖、嬴姓贵族中的费仲、恶来两人。这两个人名声不大好,但他们的多力善走成为他们留名千古的主要原因,亦见秦人对他们仍然心存崇拜之念。
殷纣王当政时,秦的祖先有蜚廉、恶来二人,《史记·秦本纪》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纣。”《晏子春秋·内谏篇上第一》载:“殷之衰也,有费仲(即蜚廉)、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7]卷1《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二人以材武受到纣王重用,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纣本人也是“材力过人,手格猛虎”的勇士。彼此有惺惺相惜之情。[8]卷3《殷本纪》然而,蜚廉、恶来但都是贪利轻义的小人,对殷政的败坏负有一定责任。武王灭商后,杀死恶来以平民愤。蜚廉因为善走而正在外面为纣王办事,侥幸逃脱杀身之祸。[1]51
秦史上真正受人尊崇的勇士是秦悼武王和他宠爱的任鄙、孟贲、乌获三位大力士。
秦武王是著名的勇士,秦国因为他“以身率,尚武之风益盛。”[8]卷71《樗里子传》武王在位时(约前310~307),在他的引领召唤之下,列国的勇士纷纷入秦,其中有夏育、任鄙、乌获、孟贲(或称孟说)
四人,都是力量超绝的大勇士,受到武王喜爱,得以出任大官。夏育,卫国人,能“力举千钧”。任鄙多力,与秦之名臣樗里侯齐名,“一以智,一以力”,曾长期担任汉中守。秦国人有谚语说:“力则任鄙,智则樗里。”[8]卷5《秦本纪》乌获能举千钧之重,曾经随从秦武王到洛阳,“举周鼎,两目血出”。[8]卷71《樗里子传》最突出的是孟贲。孟贲原本是卫国人,能生拔牛角。如汉刘向《说苑》说:“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于天。”然,他一旦听到军令则惧,足见是个严守秦国法令的勇士,故能位列显贵,成为秦国的名臣。他的遭遇是不幸的。《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尚力,本人与孟贲进行举鼎——“龙文赤鼎”——的比赛,竟至于“绝膑”——胫骨折断而死,[8]卷70《张仪列传》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死于举重竞技的帝王。比赛导致武王绝膑而死,孟贲遭到“族诛”的刑罚。但,毕竟他是无与伦比的大力士,所以一直受到秦人和天下的崇敬。秦国直到秦始皇时,“犹象而祀之”。[8]卷71《樗里子传》实际上自秦武王以后,乌获、孟贲就成了勇士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大量传说,多不胜计。总之,孟贲、乌获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是秦人崇尚武勇的标志,也成为中国古代勇士的标志。
三、锐士——秦军主力
秦国第一次显露军事实力,是在西周幽王灭于犬戎,秦襄公率领军队出援周室,与卫武公、晋文侯、郑世子率各国军队收复遭到严重破坏的镐京。此次战役史家称“镐京战役”,秦国的军队担当了重要任务,但具体情况不详。对之,《史记·秦本纪》只有几个字的记述:“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后来襄公又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周平王乃封秦襄公为诸侯,秦国正式建国,与诸侯间有了正常的通使关系。
秦人长时间与羌戎打交道,在与羌戎的战争中拓展了疆土,也逐步发展了自已的武力,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特色。到秦穆公(前659~621)时,秦的兵力已相当强大,能够与齐、晋、楚等大国争雄,进入所谓“春秋五霸”行列。有人统计,秦穆公以大兵护送晋公子重耳(晋文公)返国,有战车五百乘、骑兵两千、步兵五万,这是一支强大的车步骑联合军队,在当时的诸侯里也是强势之国。战国时,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以农战奖惩制度为核心,拥有了一支近于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战国的游说之士张仪曾在秦国为臣,了解秦的实力和特点。他向韩王讲述秦的军事实力,虽不无夸大,但大体上是可信的。他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8]卷70《张仪列传》
由此可以看到,首先,秦国拥有十分庞大的兵力,除了带甲之士百万,还有大量戎兵作为预备。而且这些戎兵很可能主要是骑兵,因为秦国有大量良马。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山东各国办不到的。其次,秦人勇悍敢战,战士们不戴头盔
(“科头”),袒露着身体(“捐甲徒裼”)冲向敌人,也就是以不惜以巨大的伤亡代价换取胜利,这种战法有悖常规,但会给敌方造成严重的心理冲击。为了计功(秦以首级计功授爵),他们“左挈人头,右挟生虏”,个个都是孟贲、乌获那样的勇士,相比之下,敌国士兵如同怯夫,如同儿童!总的相比,山东之兵“被甲蒙胄以会战”,打的还是老套的对阵战;秦兵则“捐甲徒裼以趋敌”,以迅猛的主动突击为主要战术,二者的不同显而易见。
《荀子·议兵篇》对战国几个军事强国的特点曾有所评议。他说,齐国人“隆技击”——注重个人武勇之技,而其军队敌不住魏国的“武卒”,因为“武卒”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选拔出来的军队。但“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荀子没有说明“锐士”在军事技能上的特点,我们则由此得知秦军有叫“锐士”的兵种,实际就是以重利鼓励下的勇士,唐颜师古概括为两个字“利勇”,其实是很形象的。[6]《刑法志》锐士之所以战胜攻取,无往不胜,就是因为秦有一套严格的奖惩法规,核心是对战功的重赏,奋勇杀敌成了老百姓发家致富的唯一渠道,借此把秦人勇悍好战的民风发扬到极致,故而秦在六国心目中被视为“虎狼之邦”。《荀子·议兵篇》曰:“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9]卷10《议兵篇》273
应该说这是政治因素,是制度保障,是严峻的法令加上高额奖赏引发的效应。然而作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保障的,没有技术,没有具体的训练状态和战术教例,仅凭勇敢,是不可能常胜不衰的,更不要说保持“四世有胜”的记录。正因如此,荀子才认为“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显然“节制”是一种更具优势的治军制度,其中包括训练水平。[9]卷10《议兵篇》274可惜的是,史书中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秦兵训练和武艺特长的记载,故我们对“锐士”只能望文生义,在字面上进行揣测。
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使这一情况有了一定的改观。借助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等文章,[10]我们对秦的军队状况有了比以前详实得多的了解。概括言之,秦的军队由车、骑、步三个兵种构成,这一点与战国各国的情况并无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第一,二号坑出土了大量骑兵俑,四马一组,十二马一列,九列组成一个长方型的骑兵阵,共108骑构成一个战斗单位,约相当于现代的一个“骑兵连”。马一律配有鞍仗,但没有马镫。骑兵俑作提弓状,装束与步兵不同,上衣和铠甲都是比较短,上衣袖口也比较窄,这些明显都是为施射方便。这些骑兵的着装,有明显的羌戎因素。地接羌戎而多产良马的秦国,可能拥有战国时最多最好的骑兵,从而形成巨大的军事优势,这是骑兵俑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第二,这些步兵俑出土数量最大,以一号坑为例,绝大部分士卒束发免胄,身不着甲,也不持盾,只是手提弓弩。他们的装束与其他坑中所见到的身着铠甲的俑大不相同。显然轻装免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向敌方发动冲击,古代或称为“旋锋”,这批俑的装束符合上引《荀子》所说的“跿跔、科头”,由此联想到他们就是秦军的“虎贲之士”,是向敌方发起决死冲击的“特种兵”,乃是真正的“锐士”。这应该是周武王克商之战中太公吕望亲自指挥的“虎贲”的遗制,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秦的军事文化还有周的痕迹,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四、秦兵器一瞥
兵器是反映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技艺水平的重要的标志,是研究一个王朝军旅武艺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可惜我们的学术工作在这方面非常薄弱,迄今尚未形成具有专门属性和领域的古兵器学科。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由于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取,新的资料源源不断,秦的兵器研究已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可以说是秦汉以前各代中成果最多的。
秦有巨大的官办的兵器制作产业,有细密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体制,以其有效的工作为战争提供了武器保障。从传世文物和考古发现的器物看,秦国兵器很多都有铭文,有的是兵器执用者的名爵,如“秦子戈”、“秦子矛”之类,有的是监造机构或具体制造者的名字或职务,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对制造过程的监控和责任。秦兵马俑坑一共出土箭镞4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为三翼和三棱镞,而且三棱镞式样、规格和份量都基本一致,大有“标准化”制作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秦朝的铜镞接受了春秋战国时期秦的因素,但在用于作战方面有了自己的模式,它舍弃了一些不足,只选取了其中威力最猛,杀伤力最直接的型式。[11]秦的兵器种类繁复,难以尽言,我们只选择几种与后世武术关系较为密切者,稍事论说。
(一)短兵之首——剑
青铜剑崛起于春秋后期的吴越,铁剑则出现于春秋晚期的楚国,这是以往兵器史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认识。楚国铁剑最重要的物证是“长扬六十五号墓”出土的铁剑,此剑残长38.4厘米,是一把经过反复锻打制作的退火中炭钢剑。[12]而现在新的考古发现已经突破了此说。1978年,在甘肃灵台县的景家庄1号墓出土了一把铜柄铁剑,剑身残长约9厘米。挖掘简报说,“依形制看,原长当超过20厘米”,而且“铁剑叶焊接于铜格上”。李学勤先生说,此类短剑在西安等地也有发现,剑的国别无疑属于秦国,时期应属于春秋早期。灵台秦墓铁剑的发现,不仅在中国冶铁史具有重要意义。[13]我们更注重它在兵器史——具体说是剑的发展史上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它实际牵涉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景家庄1号墓的秦国铁剑是秦国自产还是引进的?这还需要深入研究,至少目前仅凭这个孤证无法证明秦国在铁剑制作上领先于楚。马明达先生认为秦在兵器上善于引进它国技术,犹如它在人才上善于引进一样,这是秦以一个西土羌戎为根基的国家能逐步崛起,最终吞并山东六国的重要原因。马明达在《短剑与长剑》一文中曾论及秦国长剑发展的脉络:“楚国的长剑是楚国兵力的象征,必定引起列国注意,而最为注意的是与楚国并立为强国的‘虎狼之邦’秦国。善于引进人才并积极学习六国之长,是秦国最终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著名的相剑家薛烛曾活动在吴、越地区,专门为吴、越国君鉴定宝剑。这位薛烛就是秦人。说明早在春秋末期,秦人就通过民间交往熟悉了吴越宝剑的优长,并且产生宝剑鉴定专家。”
剑的引进并不是特别艰难的事,难的是剑技的普及和提高。秦简公的两条命令,目的就是在秦国营造一个适宜剑发展的环境,借以提高秦国剑的综合水平,终极目的是要军队掌握这种当时最先进的兵器及其击刺技术,以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以吴、越和楚国为例,那里是剑的勃兴之地,不仅铸剑水平天下最高,而且击剑水平也是最好的。春秋战国以后数百年,一直到了汉代,吴地人民还保持着“尚勇轻死”的风俗,荆楚故地多“奇材剑客”。这是因为吴、越和楚国有喜好击剑的传统。所以,要提高一种兵器的总体实用水平,这需要时间和环境,需要培植基础,需要造就一支技术队伍并形成传统。绝不是一旦有了这种兵器便可以运用自如,绝非如此,因为这不符合冷兵器的实用技术特点。
马明达先生认为,“长剑的出现及普及,使短剑黯然失色,但这并不意味着短剑就此消亡了。长剑有其优势,这是事实,而短剑也因为有它的特定技术而继续存在下去。长、短剑同时存在,剑技内容更丰富了”。[14]说明秦对楚国长剑从器物到技术都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进,以至连秦始皇都佩带着长剑,能以长剑自卫,击伤荆轲,免于被刺。所以我们不排除甘肃灵台景家庄1号墓铁剑原本是楚地产品或引进楚地工匠所造的可能性。秦在春秋早期是否已具有制作铜柄铁剑的能力,这需要有别的证据。但景家庄1号墓铁剑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说明秦人在使用钢铁兵器方面是走在列国前面的,也将秦人对剑的重视提早到了春秋前期,时间上比战国时的秦昭王(前306~250)要早得多。
(二)长兵之矛、铍和殳
矛是秦国兵器中最常见的兵器之一,考古发现数量不少。过去大家都注意到秦国一种叫“厹矛”的矛,见《诗经·秦风·小戎》:“俴驷孔群,厹矛鋈錞。”《毛传》:“厹,三隅矛也,錞鐏也。”“厹”音“求”,但什么是“三隅矛”呢?其实很难说得明白。宋林之竒《尚书全解》卷37引唐孔颖达曰:“三隅矛……古今兵器名异体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之也。”这话是有道理的。
根据对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各式兵器的分析研究,白建纲先生提出秦的军队主要有射击手和长矛手两类构成,前者主要指弓、弩手而言,后者指持矛、戟、戈、铍、殳等兵器者,核心当然是长矛。这种装备情况,“具有非常强烈的古代东方特色和较高的组合水平。”[15]
秦俑坑出土的矛、戟、铍,大部分柄杆
(“柲”)已经残断,依据发掘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白建纲先生做了一个统计表,矛、铍类兵器刃柄残存通长大致在350~430厘米之间,个别残柄保存较完整者,长度有超过600厘米以上的。戟的长度相对要短一些,大致残存在120~285之间。从整个长度看,秦兵所执矛、戟、铍长度,平均约在400厘米以上,比明清一般步战用枪要长,比民间武术家的大杆子之类也要长。白建纲先生认为,秦的“长矛手”可能分为重、中、轻三种,其中“重长矛手”是相对远距离剌杀敌人的兵种,由于矛柄很长,必须双手去持,可杀敌于六七米之外。但当敌人钻到矛杆之下,冲到五米之内与他们格斗,他们便处于被动。由此,重长矛手在作战中要排成密集队形,前后左右照应,才能发挥他们的优势。
白建纲先生认为,“中长矛手”主要是指持用有柄长铍的战士,铍全长约359~382厘米,杀伤方式与矛类似,但杀伤半径小于“重长矛手”。“轻长矛手”主要指殳,三号坑的指挥部出土了30件殳,“其中第三单元,除领队二人外,有20名卫士,放置了20件殳,证明全部装备殳,是执殳队。殳的柄部残长皆为一米。这部分按武器编队组成的队伍,就其性质属于短柄格斗武器,可列为特别的‘长矛手’,属于轻型长矛手,执行队伍的警卫作战任务。”[15]
白文所做的分析是有启发性的,“长矛手”的密集队列也有一定道理,但“中矛手”、“轻矛手”之说缺乏必要的文献引证,不免失之臆想。
关于“铍”这种兵器,过去虽见于《左传》等史籍,但缺乏实物参证,对它的式样功用没有人能说得明白。近年来古发掘中多有发现,于是才见到了真正的实物。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多功用的兵器,可长可短,其柄并无定制。汉《方言》卷9记载:“锬谓之铍,今江东呼大矛为铍。音彼。”就其形制来看,除了矛的剌的功用外,另一个矛所不具备的功能是砍杀,属于可击可剌的兵器。《说文》云:“铍,大针也,从金皮声。一说剑而刀装者。”《急就篇》卷3云:“铍,大刀也,刃端可以披决,因取名云。黄氏曰:铍,剑如刀装者。”据之,铍应当看作是大刀的前型,是剑、刀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兵器,所以它的长度有较大的灵活性,始皇陵俑坑的长柄铍只是一种而已,并非定制。汉以后铍就基本上消失了,因为有了越来越成熟的环首大刀和各式长柄大刀,铍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将铍也归之“长矛手”,似乎并不合适。
至于“殳”,它是一种击打兵器,所以柄杆不会太长,太长了就失去击打的威力。三号坑出土的30件殳,殳的柄部残长皆为一米,这是恰当的长度。将功能与长度都显然不相类的殳,也归之“长矛手”系列,虽然白文加上了“特别的”三字以示区别,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可知,秦人崛起于陇右,受周边诸羌、戎和周文化影响,以武立国是确凿事实。
五、结 语
大秦帝国的形成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其在短暂的控御时间里,对人类文化、文明的贡献之杰出,影响之深远,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仅见的。与正史、野稗及地上地下文化实物相互印证,我们可以认为,有秦一代最值得今天追念的,莫过于秦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一个遭亡国失姓之辱,苟延性命,谪居“蛮荒异域”的弱小族姓,凭借民族自强、尚武精神和骨子里刚健有为的生命基因,化腐朽为神奇,变柔弱为刚强,由附庸而大夫而诸侯,一步步走向了复兴(崛起)之路,实现了一朝帝国之大梦。在大秦的各种文化基因中、最有生命力、最为振奋撼人的,就是透射着坚刚之气,雄宏壮阔的尚武精神。
[1]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早期嬴秦探微[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
[2]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J].文物,2000,(5).
[3]王遽常.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0.
[4]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3.
[5]严虞惇.读诗质疑[M].咸丰江南书局刊本.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71.
[7]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
[8]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集[C].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100.
[11]石岩.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189-190.
[12]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挖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J].文物,1978,(10).
[1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03.
[14]马明达.说剑丛稿[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20.
[15]白建纲.论秦俑军队“长矛手”及其战术[J].文博,1994,(4).
K207
A
1671-1351(2012)03-0012-05
2011-12-21
蔡智忠(1957-),男,甘肃秦安人,天水师范学院体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国家社科项目“西北武术文化历史与开发”(07xty00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艾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