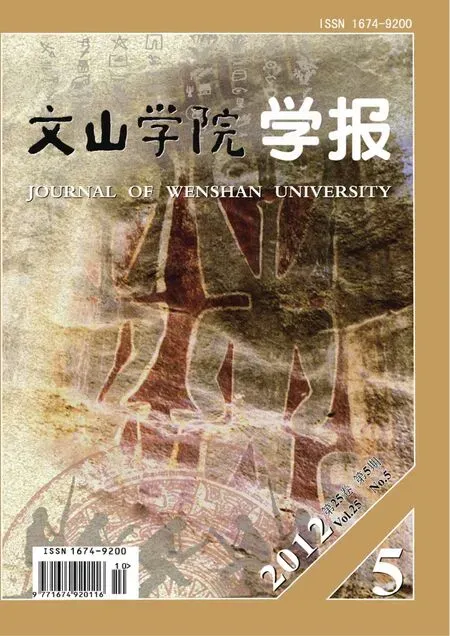试论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
洪 涵
(云南行政学院 法学教研部,云南 昆明 650111)
广义地说,“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云南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种对超自然存在物、超自然力的信仰及仪式,以功能主义视角观之,它们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设置,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承担着社会控制的功能。
一、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种类
人们一般将具有严格的组织、教义、仪式、活动场所、神职人员的信仰形式称为制度性宗教或人为宗教,而将与之相对的,教义、组织人员、活动场所、仪式活动都比较松散的信仰形式称为原始宗教。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云南各民族形成了多种对超自然存在物、超自然力的信仰:
(一)自然崇拜
在先民的生活里,强大的自然力带来的旦夕福祸,常使他们敬畏不已。在不能将之制服之际,只有寄希望与之修好,于是山、地、雷、电、火等自然物质、现象逐渐被人类视为“神”或“鬼”而受到膜拜。例如传统上,云南佤族祭奉的最大神就是山神鹿埃姆和鹿埃松。
(二)动植物崇拜
动植物既是人类的生产资料、生活同伴,也可能伤害人类,各民族于是也将各种想象加在动植物身上。如云南藏族、摩梭人、普米族都有松树崇拜,布朗族则有专门的祭竹鼠仪式。
(三)图腾崇拜
“图腾”本是美洲印第安人鄂吉布瓦语“totem”的音译,意为“他的亲族”, “图腾”崇拜一般与族群划分相联。在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纳西族、怒族均有崇拜虎的现象,以虎来命族名,认为虎是祖先、狩猎不猎虎,举行大事时要择“虎”日等等。
(四)祖先、灵魂、鬼魂崇拜
对梦、昏、死亡、疾病等现象的困惑,对先人、英雄的崇拜追思,促使先民产生了灵魂观念,同时还基于血缘感情并加以功利主义的想象,认为祖先的灵魂一般是善的,能够保佑生者。而陌生人的鬼魂则可能作祟为恶,应该敬而远之。如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云南某些地区居民的瓮棺葬中就有专门为不死的灵魂提供出入的小孔,表明当时的这些居民已有了复杂的灵魂不死观念。[1](P18)
(五)巫术
人们企图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通过一定的仪式对预期目标施加影响或者加以控制的活动一般被称为巫术。[2](P364)如怒江傈僳族相信有一种能致人死亡的“杀魂”巫术,如果路遇某人后生病,就是被该人“杀”了“魂”。[3](P216)
(六)禁忌
很多民族都有为避免招致不好的后果或惩罚,而规定、遵守一些行为规则,禁止同“神圣”或“不洁”的事物接近的禁忌。如云南哈尼族就禁忌牲畜上房屋、母鸡学公鸡叫。
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种类多样、关系复杂,不过总结来看,它们都是通过一系列“仪式”得以表达,通过一系列“神话”得到诠释的,其中,“对超自然存在以至于宇宙存在的信念假设部分”,就是信仰;“表达甚而实践这些信念的行动”,就是仪式。[4](P219)一方面,人们口耳相传了种种言说与神话,替各种信仰找出解释的理由,构成一个满足人类求知愿望的系统,另一方面人们还普遍采用祭祀、祈祷、舞蹈、歌唱等形式来表达这些信仰。
二、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
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视角,主张研究、揭示社会有机体中各种社会设置、文化因子的“功能”。以功能主义视角观之,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如下社会控制功能:
(一)稳定社会主体
原始宗教信仰可以安抚个体心灵,使个人确定性地归属于某个集体:
1.安定、抚慰个体心灵
信仰一般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调适,它帮助人们将现实中的种种不确定神秘化,使各种社会存在在人的主观意识中“有序”而不“动荡”。如面对生老病死,许多民族都相信死者灵魂不灭,常由巫师手持刀、矛或木棍开路,为死者举行“送魂”仪式,让其与祖先欢聚。通过此类仪式,安抚了生者的内心,使个人得到了关于生死、意外的解释,通过稳定社会个体,进而实现社会有序。
2.划分社会群体,促进族群认同
在初民社会,地域分割性明显、群体依赖性强,对生产、生活资源的争夺往往以群体为单位,所以划分群体,在群体内进行合作,群体外或竞争或合作,稳定社会成员的分布,使个人归属于某个集体,是社会控制的基础。云南民族传统社会经常借用原始宗教的途径来划分群体及其“势力”范围,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通过图腾、借助神话。如云南怒江白族《氏族来源的传说》解释了白族熊、虎、蛇、鼠四个氏族的来源,并分配了他们的居住地——兰坪、怒江、泸水①。这种基于动物图腾所作的群体划分,既强调了几个支系的同源及团结,又对他们各自的地域范围、自然资源进行了确认、分配。
(2)通过设立并祭祀寨门、寨心、寨桩的形式。寨门、寨心、寨桩是承担着群体划分功能的建筑文化,如云南爱尼人的传统寨门分坑玛(前门、大门)、坑止(后门)、坑丈(侧门)三种,每年三四月份,全村成年男子要在祭司“追玛”的指挥下举行祭寨门仪式。[5](P179-185)又如傣族、布朗族、阿昌族、拉祜族的寨子也有以某些建筑物或设施为标志的“寨心”,以强化“寨子”的存在。
(3)通过崇拜守护神。如傣族把有共同血缘和历史关系的许多村寨组成的片区称为“勐”,每个勐有勐神一至几名,他们一般是建勐时的英雄或首领,用专门的祭祀勐神的仪式,祭祀期间全勐要停止生产活动二至三天。祭祀时还要统一服装,通往其它村寨的路口要插上树枝“封路”。[3](P323)
(二)形成公共执事组织,集中行使公共权力
没有公共决策、管理组织及首领,社会秩序会发生紊乱,云南傣族《咋雷蛇曼蛇勐》、哈尼族《三种能人》等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一道理②。各民族还基于原始信仰,形成社区的首领、公共执事组织,管理公共事务:
1.用神裁或神裁与原始民主相结合的方式
如布朗族的“召曼”(村社头人)是通过在神庙里抽签产生的,他们认为这是本寨寨神“再曼”选择的头人。[6](P71-72)又如基诺族认为,祭司、铁匠的产生是“鬼女”看上了人间的某个人,而来挑逗,被选中的人会得到种种预兆,见到预兆后要去求卜,若被卜证实,就要与鬼女结婚,然后担任祭司或铁匠。[7](P800)
2.直接以神的名义宣布
一些首领、执事人员的产生直接被以神的名义指定。如历史上云南傣族过“开门节”时,最高头人要按程序分封或加封各头人,并对百姓说:“当着佛的面,把你们喜欢的人,拥护的人加封了,你们要好好听他的话,要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被封的人面对佛像念读任职誓词,念毕,将其烧为灰放入杯内,当众一饮而尽,以表示对封建领主和佛主的无限忠诚。[8](P135)
3.神职人员转变为世俗首领
弗雷泽曾在其著作《金枝》中分析了一些民族所共有的由“祭司”发展到兼行首领、祭司权力的“首领”,再到“祭司”、“首领”分离的历史过程。[9](P48-49)云南民族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彝族毕摩就是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祭司和酋长,直至唐、宋时期,祭司仍由酋长兼任,到忽必烈平大理国,将原有酋长/祭司任命为土司、土官后,一种叫“奚婆”的祭司才从奴隶主、封建主集团中分裂出来,清朝改土归流后,进一步发展为专司宗教职事的毕摩。[1](P214-215)
首领及公共执事组织产生后,各民族往往还通过各种禁忌、神话来强化首领、公共组织的权威。如爱尼人推选“龙巴头”,要求其家中“清净”,“清净”指的是家中没有六指、双胞胎,家人健在、没有未婚先孕,办事公道等。又如昆明彝族撒尼人祭天选举会长、祭司、执事人员时,凡行为不端、重婚纳妾、当年家中有产妇及丧事者均不得当选。
(三)形成行为规范,调整社会关系
许多民族传统信仰,在观念上是唯心的,但在行为上,却是唯物的,信仰,把神与人类生产生活秩序联系在了一起。
在生产秩序方面,云南许多农耕民族在砍地、烧地、播种、收获、装仓时都有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安排了生产秩序,灌输了生产常识。如哈尼族每当阳春三月,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第一次听到布谷鸟叫,都要报一声“我听见了”,并要在多数人都听到布谷鸟叫声后,约定一个属羊的日子,向布谷鸟献祭,以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3](P328)
在生活秩序方面,云南各族在诞生、成年、婚姻、丧葬等方面都有一些超自然信仰及仪式。如瑶族男子“度戒”,要经翻云台、上刀梯、踩火砖等考验,还要由度师传授宗教仪礼,背诵宗教经典和本民族、家族历史。度过戒后才能正式成为“盘王”的子孙,列入家谱名册,同时说明男子已进入成人阶段,有了参加村社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力和婚恋的资格。[10](P101-119)
(四)惩罚越轨行为,解决纠纷,救济权利
在生产生活中,基于信仰,人们自觉维护“规范”,社会得以有序。倘若出现违反规范的越轨行为,源自信仰的强制力会对之进行制裁:
1.直接提出以超自然制裁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
“超自然也经常(虽然并不是一直)严密地监视着活人的道德行为。而且人们也常常把习惯规则和程序附会成天神的旨意,使其更具约束力而带有终极、绝对与神圣之名。”[11](P368)如纳西东巴经典中常提到“犊姆”一词,意为做事的规矩、程式。“犊”为可以做的事,公众认可的事宜,“莫犊”则为不可以为之事。再如哈尼族的《神和人的家谱》,也谈到最大的天神俄玛在创造儿孙时,觉得应该先造“规矩”和“礼节”,没有他们,神殿都会被“闹翻掉”,所以首先生了“玛白”和“烟似”这两个“规矩” 姑娘和“礼节”姑娘。[12](P65)
2.纠纷解决及权利救济制度
(1)神判。在云南许多民族历史上都曾有过捞油汤、占卜等神判方式。如阿昌族发生是非之争难分泾渭时,就约定地点,找来公证人,由当事者同时点燃大小、长短相同的两支烛,以谁的烛燃烧时间长为有理。[6](P83-84)
(2)通过祭祀、巫术。许多民族在驱鬼仪式中都要驱逐“口舌鬼”。如景颇族在木脑纵歌中要由三个“董萨”念“木宋鬼”(即“口舌鬼”),据说这类鬼有30多个,它们会使人们生病惹祸、吵架斗殴,必须杀牛祭献。[13](P85)兰坪维西的那马人用“活人鬼”来称呼活着的某些女人的魂魄,每个村子中的几个嘴快、心丑的女人都可能被视为“活人鬼”,在祭鬼时,要念她们的名字。[14](P416)
三、原始宗教信仰承担社会控制功能的特点
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承担着社会控制的功能,其特点有:
(一)自发性、内化性
传统信仰的产生,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们源于人类的情感和心理活动,也源于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这些信仰通过仪式、神话的反复强调,形成一种固定化模式,每一个新的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着它们的模塑。
(二)神、人、自然秩序的合一性
原始宗教信仰,以鬼、神的逻辑来解释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将神、人、自然秩序合为一体。世俗公共执事组织的活动、人们的行为规范都以神的名义来进行、来发布,社会控制通过这种“合一性”得以实现。
(三)微观、宏观调控相结合
从微观来看,原始信仰虽然提供了一些行为规范,但这些规范还是有些杂乱、混沌、含糊不清。原始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主要还是体现在调适社会主体心理、划分社会群体、加强社会团结这些宏观层面上。
(四)调控结果的超验性
原始信仰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的“后果”,往往是非理性的、超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了了之
当事人可能基于神秘的信仰,安慰自己“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还可以通过诅咒、发誓等形式,给自己愤愤不平的心态予缓冲。虽然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可能只是放空炮,非正义方得不到现实的制裁,但却可以缓解矛盾,为社会减压。并且当一个人在菜园中咒骂、对着竹篱笆念念有词,以求蔬菜等不被偷盗之际,周围的观众,将再一次感受、重温共同行为规范。
2.让当事人如“惊弓之鸟”
“是鬼魂、幻影、幽灵造成的虽无根据但有益处的恐惧,它使得冷酷无情的恶棍和亡命暴徒胆战心惊。”[15](P109)神秘的信仰凭借着神灵的诡异,使当事者可能基于对超自然力制裁的恐惧而出来承担责任,甚至因被吓而曲打成招。如云南怒江傈僳族就有过因畏惧捞开水而自杀的事件。[6](P4)
3.基于概率得到某种不一定符合实质正义的“后果”
传统社会有限的物质技术条件,难以确保实体正义的真正实现,神秘信仰之下的种种定分止争的期望,可能会基于概率得到某种“说法”。如捞油锅的结果可能单方受伤也可能双方受伤或双方都不受伤,出现前种情况,则纠纷可以得到解释,后两种情况则需要其它解释,如可以解释为此次主持者的咒语无效,也可以解释为双方都是无辜的等等。虽然“神的旨意”不客观、不科学,但事实上却有助于冷却矛盾。
4.将偶然性事件视为“应验”的表现
将偶然性事件视为“应验”的表现,既可能是认识上的错误,也可能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必然”而得出的“推定”。例如傈僳族的“杀魂”之说,之所以会将路上偶遇的“某人”确认为“嫌疑人”,多是基于生活经验。就如普里查德分析阿赞德人请示毒药神谕一样,他们总是从平时有过矛盾的人当中一一列出“嫌疑人”的候选名单。[16](P123)
社会有序离不开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方式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在血缘、地缘、族缘密切联系的小型社会中形成和存在,这种小型社会有同质的文化背景,容易形成集体意识,便于实现社会控制。在传统简单社会向现代复杂社会变迁过程中,原有的社会控制方式也将逐步发生变迁。现代社会应该根据复杂社会的特质及现实需要,构建、完善适宜的社会控制方式,维护社会稳定。
注释:
① 故事说的是,一场洪水灾难后,剩下的两兄妹得到神的旨意成亲,他们先后生下五个女儿,大姑娘嫁给熊,发展成一个大氏族,住在兰坪一带,叫熊氏族;二姑娘和老虎成亲,后代叫虎氏族,居住在怒江地区,即勒墨人;三姑娘嫁给青蛇,生两兄弟,两兄弟又生子,有的说怒族话,有的说傈僳话,他们是蛇氏族;四姑娘嫁给老鼠,他们带着孩子在泸水居住,后代为鼠氏族;五姑娘和毛毛虫结婚,婚后被毛毛虫吓死,没有后代,所以也就没有毛虫氏族。参见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白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页。
② 傣族《咋雷蛇曼蛇勐》说的是“盘巴”时代、“赖盘赖乃”时代,首领沙罗、桑木底分别认为人类社会要有序都得有“头”。哈尼族《三种能人》讲的是官人、祭司、匠人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参见王松、王思宁:《傣族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3页;李少军:《诗性的智慧——哈尼族传统哲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27页。
[1]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郭恩九.云南文化艺术词典[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4]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6]夏之乾.神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7]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基诺族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8]王松,王思宁.傣族佛教与傣族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9][英]J.G.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刘魁立审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10]赵廷光.瑶族祖先崇拜与瑶族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11][美]基辛.文化人类学[M].张恭启,于嘉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12]李少军.诗性的智慧——哈尼族传统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3]刘稚,秦榕.宗教与民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14]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白族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5][英]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M].阎云翔,龚小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6][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