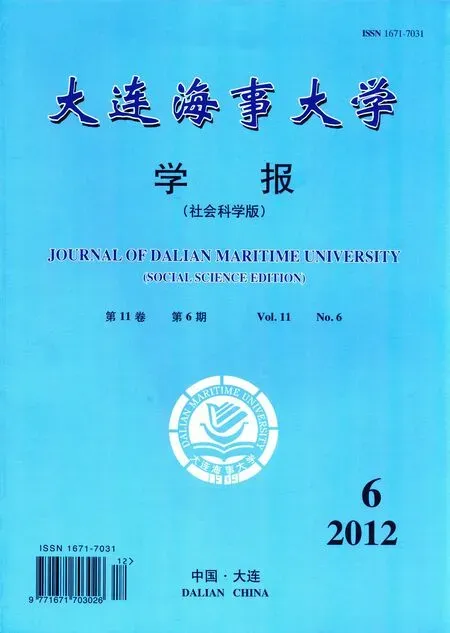论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与属性
李天生
(1.大连海事大学 a.法学院;b.法学博士后流动站,辽宁 大连 116026;2.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博士后工作站,辽宁 大连 116026)
随着中国海商法实践和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海商法》制定生效近20年来,海商法学研究与教学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海商法、海事法概念的歧义,《海商法》适用和理论观点中,关于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法律属性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如何正确理解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属性,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基础问题。
一、海商法的概念
海商法,英文对应的名称有“maritime law”和“admiralty”、“law of admiralty”。“maritime”一词的词根来源于拉丁语“mare”与“maritima”,意为“大海”;“admiralty”一词的词根来源于阿拉伯语“amir”,意为“指挥官、司令官”,经常后缀“al”(在……中)和“ma”(水)、“bahr”(湖、河或海)使用,这一词根加上前缀“ad”组成的“admiralty”,最早大约1205年出现在英语中,大概是从西班牙语或法语传入英语的。[1]从词源可以看出,“maritime”的范围泛指海上的一般相关事项,“admiralty”更偏向存在航行指挥关系的海上或水上活动,“maritime law”的范围比“admiralty”范围更广。随着海洋利用范围的急速扩大,“maritime law”含义随之扩大到所有与海洋资源使用、海上商业和航海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的概念,但“maritime law”与“admiralty”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也日益复杂。①有观点认为,“admiralty”范围既比“maritime law”的范围窄,又比“maritime law”的范围宽:说更窄是因为“admiralty”仅指与航海和运输相关的私法,说更宽是因为“admiralty”的适用范围既包括海上,又包括内陆水域。参见文献[2]。
在中国语境下,一般认为,“maritime law”通常翻译为“海商法”,“admiralty”则为“海事法”。[3]但从实用的意义上说,二者已没有区别。美国的Robert Force教授就直接使用“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的用法,并强调“admiralty”、“maritime law”和“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三个概念具有同等含义。[4]吉尔摩教授等认为,就实体法而言,admiralty和maritime law在美国事实上是同义词。[5]加拿大的台特雷教授认为,“如今在maritime law和admiralty law之间已经根本不可能明确划分清楚其区别和界限了。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分别在世界各国不同的时代里进化和发展了”[6]。中文“海商”(即 maritime commerce)一词,来源于亚洲对中世纪商航一体时代的运输的称呼,[7]1即贸易航运为同一主体的情况。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欧完成了工业革命,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事业蓬勃发展,商航一体时代开始解体,海上运输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现代海商法专注调整海上运输及直接相关活动,已不再调整关于贸易的商业性活动,所以有观点认为,海商法的名称也应该正名为“海事法”。[8]2还有学者认为,在中文环境下,狭义的海商与海事是有区别的,前者指海上商事活动,如海上运输、船舶租赁等,后者侧重于海上发生的事故,如船舶碰撞、海上污染等,广义上的海商与海事则是同义词。[3]
由于“海商法”一词自1929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公布我国首部《海商法》后,一直沿用至今,已成为一种习称,①我国清末修律时叫《商船法》,至民国元年完成,未公布,后民国十五年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暂采用《商船法草案》,民国十六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开始编订《海商法》,民国十八年我国首部《海商法》公布。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了多部海商法著作,如民国二十四年王孝通的《海商法》、民国十九年王效文的《中国海商法论》、民国三十六年耿光的《海商法》、国立武汉大学印刘经旺的《海商法》(出版时间不详)、民国三十六年刘笃的《海商法论》、民国二十二年魏文翰的《海运法》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海商法一直在起草之中,出版了1964年魏文翰的《海商法讲座》,1984年魏文达的《海商法》、张暨义的《海商法概论》等著作。可见,我国现行《海商法》立法以前,多数著作均以“海商法”命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称呼。因此笔者认为,基于海商法、海事法概念在我国使用的复杂的客观现实,可以参考美国海商法学者的做法,不再区分“海商法”与“海事法”的概念,可以在不同语境下根据不同需要灵活使用。并且对于海商法这样一个不是我国历史上固有的、从西方法律体系移植而来的名词,随着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其内容也日益丰富,范畴日益扩大,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海商法的概念。
二、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法的调整对象是指某一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是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调整就是对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行为在法律上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8]3自我国《海商法》1993年7月1日生效实施以来,人们对我国海商法应以哪些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一直存在争议,对此问题不加以明确和界定,也导致在实践中对发生的特定案件是否适用《海商法》存在争议。在我国修改《海商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个问题亟须解决。笔者认为基于海商法的含义不同,其调整对象应有所不同。目前,在我国,狭义的海商法一般特指1993年《海商法》,在性质上认为其属于民商法的特别法;而广义的海商法是指作为法学学科下的一个分支,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将海商法作为二级学科国际法学的一个分支。但海商法学者认为广义海商法应作为法学下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随着我国航运业的迅速发展和海事立法的不断完善,海商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在国际上,海商法在一些航运发达国家是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存在的。[8]5
(一)狭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我国《海商法》第1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本条既是本法立法宗旨的体现,也是其调整对象的反映。据此,通常认为我国《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分为两大类: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
1.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不同观点
(1)海上运输关系。我国《海商法》第2条对“海上运输”的界定,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之间的直达运输”。但《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沿海、内河运输而仅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关于“海上运输关系”的具体内容,第一种观点认为,仅包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海上拖航合同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指的是海上运输中发生的债权关系,具体包括:①有关海上运输的合同关系,例如以提单为书面表现形式的班轮运输合同、旅客运输合同、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光船租船合同、海上拖航合同、海上保险合同等;②海上侵权关系,如船舶碰撞、船舶污染时产生的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③海上特殊风险产生的社会关系,如海难救助、共同海损、责任限制、船舶优先权等。
(2)船舶关系。从《海商法》的规定看,该法第3条关于船舶的定义,在碰撞和救助两章中被扩大到20总吨以下的海船和内河船,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一章中又被缩小到国际航行的300总吨以上的海船,各部分关于适用船舶的范围是明确的,但关于“船舶关系”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有观点认为包括与船舶经营有关的所有关系,如船舶、船舶租用合同、船舶碰撞、船舶拖航等;也有观点认为,仅指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等船舶物权关系。
2.对《海商法》定义及学者观点的评析
对我国《海商法》的调整对象,仅从法条规定看上述不同理解都有一定道理,这说明法条本身并不科学,并不周延。
首先,不是一切与海上运输和船舶经营有关的社会关系都为海商法所调整,例如,海上运输的税费由税法调整,海关对船舶和货物的监管关系或者卫生部门对船舶和货物的卫生检疫关系,由海关法和卫生检疫法所调整。其次,“船舶关系”用词不当,法律的调整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以物的名词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命名,容易令人误解和迷惑(如书本关系、茶叶关系),把船舶关系仅理解为船舶物权关系,就和这个“船舶关系”的用词有关。再有,《海商法》不同章节涉及的社会关系通常既涉及船舶,也涉及海上运输,如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第七章海上拖航合同,既是运输合同关系,又是与船舶有关的合同关系,因为船舶是海上运输的基本载体。又如第九章海难救助、第十章共同海损、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既涉及海上运输关系,又属于与船舶有关的债权关系。所以,《海商法》第1条把“船舶关系”与“海上运输关系”并列为调整对象,在逻辑上是不准确的。[9]
关于海商法调整对象的定义,有观点提出“海商法是调整特定的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和与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8]3。这个定义将海商法调整对象限定为“特定”的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从外延上看做了更明确的界定。但该定义同样使用“船舶”这一名词作为社会关系的分类。而且,从逻辑上看,“特定的海上运输关系”也属于“与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因此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还有观点提出“海商法调整海上运输关系以及其他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9]。这个定义存在两个问题:将所有的“海上运输关系”都作为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外延明显过大;“其他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虽然解决了与“海上运输关系”并列的问题,但同样外延不当,例如造船合同和船舶买卖合同,多数海商法典就并不适用。
3.本文的观点
笔者认为,比较科学的海商法调整对象的定义是“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和“与船舶有关的其他特定社会关系”。这一定义与我国《海商法》的制度内容相符,且克服了上述两种调整对象并列的逻辑缺陷和外延过大问题。
“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种合同关系,例如以提单为证明的班轮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货物保险合同等,有时也体现为侵权关系,如收货人对实际承运人提起侵权之诉时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与船舶有关的其他特定社会关系”指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船舶物权当事人之间、船舶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海上侵权行为所涉及的当事人之间以船舶作为客体形成的法律关系。
(二)广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广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包括狭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此外,无论是客货运输、海难救助,还是拖航、打捞、捕鱼、采油,都必须有船舶参与,使用船舶是各种海上活动最基本的特征。[10]4船舶登记、船舶安全和船舶对海洋的污染等都要受到行政部门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发生与船舶有关的当事人和行政部门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例如,各沿海国或者港口,出于对港口、沿海水域的管制,制定了各种法律、法令、规章和制度,即以规范船舶安全为中心的各种行政法规;船舶在海上航行必须悬挂一国的国旗,必须取得一国的国籍;船舶必须配备合格的船长和船员;为保障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船舶必须经过严格检验,取得合格的安全航行证书等。为此,必须制定船舶登记,船舶检验,船员考试、发证和值班,船员配备,船长职责等规定或者船员法、海上交通安全法、船舶丈量、海上避碰规则、防止船舶油污等法规。这些以保障海上安全航行及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有关法规都属于行政法规,其调整是纵向的,体现的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7]3这些都属于广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另外,海运市场中的无船承运人的资格、从事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资格等市场准入制度,班轮运输运价备案、垄断豁免等市场行为规制制度,航运产业振兴和产业促进的有关规定,都可以属于广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还有,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与海运服务有关的一系列文件已经基本确立了WTO海运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中国加入WTO的正式文件中,也对海运服务及其辅助服务市场的开放作出了承诺。关于WTO和我国其他法律中调整海运服务市场开放的有关法律机制,以及日益严峻的与运输、船舶相关的海事犯罪问题,也亟须研究和完善。把这些法律领域纳入广义海商法中进行统筹研究,对解决海事实践问题、促进我国贸易与航运业的发展、繁荣海商法学理论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说狭义的海商法或我国《海商法》法典调整或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民事关系,不调整或主要不调整纵向的行政关系,对于广义海商法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分支,其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相对较广,既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海商法律关系、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关系,又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海事行政关系和海上刑事法律关系等。
三、海商法的属性
海商法的属性,也就是海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位置。从法理上说,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综合。[11]海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决定海商法的性质,即法律属性。[12]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1.海商法在法律体系中地位、属性的不同观点
(1)海商法是商法的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海商法多作为一编被列入商法典之中,如德国海商法列在商法典第4编、法国海商法列在商法典第2编、日本海商法列在商法典第5编。因此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法学理论认为海商法属于商法的一部分。
(2)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在民商合一的国家,这种观点较为普遍。因为这些国家无独立的商法典,而是以民法作为基本法来调整广泛的市场经济活动,同时,制定相应的特别法予以补充。其中,因海上运输市场具有自身的特点,就由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适用于该经济领域的关系。即首先用海商法来调整海上运输市场,而海商法未规定的,则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13]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来看,我国是民商合一的国家,海商法应属于民商法的法律部门,是民法的特别法。[8]6
(3)海商法属于经济法或国际经济法的范畴。1984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海商法是“国内经济法兼有国际经济法性质的法律”。①参见文献[14]。该书2006年修订版已删除了海商法属于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原国家教委所做的至今仍然实行的学科分类中,海商法也是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一个分支。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海商法所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海上运输活动实行专门组织管理的意志。在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海上运输已经与一般的商事活动相分离,构成特定的生产经营行业。各国均对海上运输及其以船舶为中心的各种经济关系实施专门的组织管理。这一国家管理职能决定了海上运输不能为民法所调整,而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13]
(4)海商法是海法的一个部门法。“海商法者,为海法之一部。”[15]所谓海法,是指调整与海洋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6]海法的划分是基于与海洋有关的社会关系有区别于陆上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在海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下,国际上有一种观点,把纵向行业行政管理法谓之“公海商法”(public maritime law),而将调整横向民事法律关系的海商法称做“私海商法”(private maritime law)。“欧洲海商法组织”(EMLO)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公海商法的民间组织。而“国际海事委员会”(CMI)则是一个专门研究私海商法的民间组织。[10]5-6
(5)海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观点主张,如果继续把海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或者商法的特别法,恐怕与现代海商法的发展不符,因为海商法已自成体系,成为一门融行政管理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于一体的独立的法律部门。[8]5,[10]6
2.本文的观点
上述观点均从某个层面或角度揭示了海商法的属性,或者说海商法的特定内容具有上述各种法律部门的属性,即从广义和实质意义海商法的角度来说,海商法包含各种法律属性,尽管所包含各种属性的比例有所差异。因此,研究海商法的不同内容,要以该特定内容的相应法律属性为出发点。例如,船货利益平衡问题既体现在横向的平等法律关系之中,也体现在纵向的不平等法律关系之中,如贸易航运政策、管理等关系;既体现出商法的效率原则,又体现出民法的公平原则;既体现在市场自由之中,又体现在国家干预之中;既受海上特殊风险的影响从而具有海事活动本身的特征,又受经济规律和法律原理的制约从而具有一般产业活动的共性;既体现在国际商航传统、惯例之中,又处处包含着主权国家的利益。因此,结合上文所述的广义海商法理论和实质意义海商法理论,从某些研究角度和需要看,本文倾向于将海商法划分为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而不是局限于任何一个归属的法律体系地位或法律属性。当然这个法律部门的基础和核心还是民商法(狭义海商法)。从研究路径来说,应在民商事法律理论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出发,运用所涉及的每一个法律部门、属性的理论进行研究。
四、梳理海商法概念、调整对象与属性的意义
海商法的概念,由于海商法的国际性,在不同的语言下存在词源和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人们理解上的混乱。比如,在大连海事大学将海商法学自主设置为二级法学学科的过程中,校内外的专家对到底叫“海商法学”还是“海事法学”就存在不同看法。事实上,海商法并非我国历史上固有的名词,其概念和词源来自于中国近代对西方法律体系的引进过程之中,并且“海商法”的名称和概念从我国第一部《海商法》立法开始就由来已久,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现代不再是“商航一体”,但对一个外来词源和概念,只要意义明确,并无区分和改变的必要;另一方面,“海事法”的概念也长期使用,并且常常特指海商法典或海商法学中船舶碰撞、油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难救助、共同海损等特定部分或领域,虽然从语义上看,脱离了“商航一体”后可以将海商法正名为海事法(我国的专门法院就命名为海事法院),但这又与海事法常用的这些特指并不相符。因此,在不同语境中根据需要使用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只是,我们需要梳理清楚,以解释这些特殊名词、概念给人们带来的困惑。
关于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正确的界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的不少争议。案例一:某船舶触碰码头,码头方多次发函要求船东赔偿损失,船东不予理会,码头方在船舶触碰码头之日起2年后向船方提起诉讼。船方辩称,双方因船舶触碰码头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海商法》第1条规定的“船舶关系”,根据《海商法》第267条的规定,只有提起诉讼或仲裁、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以及扣船这三类行为才能构成时效中断,单方发函要求赔偿不能导致时效中断,因此码头方的索赔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码头方则认为本案应适用民法规定,即发函主张权利可以构成时效中断。案例二,某船受雇为航道疏浚单位在海上倾倒疏浚物,但倾倒在非法定倾倒区,造成海洋环境与养殖物污染,受害人向船舶所有人提出索赔。船舶所有人提出其倾倒船是海船,属于《海商法》第1条规定的“船舶关系”,同时也是运输疏浚物,他可以按照该法第十一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受害人则认为其不能限制赔偿责任。
根据本文关于海商法调整对象的定义,上述两个案件的争议就比较容易解决。案例一中,首先应当明确,不是所有涉及船舶的社会关系都由《海商法》调整。船舶与码头的“触碰”,不属于《海商法》调整的“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和“与船舶有关的其他特定社会关系”范围:“触碰”首先不是运输关系,虽然与船舶有关,但不在“其他特定”的与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范围之内,《海商法》调整的碰撞关系主要在船舶之间发生,因此不能适用《海商法》的时效中断规定。案例二中,海上倾倒侵权涉及船舶,但此船舶不是从事《海商法》规定的海上运输和海上商业拖带业务,且《海商法》调整的污染环境侵权也只限于“特定”的货物运输或船舶本身所致的污染,因此“倾倒关系”不属于“海上运输”和“其他与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自然不能适用作为《海商法》特殊制度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关于海商法的属性,也处于海商法概念同样的境况。在大陆法系概念体系中,一般的法律都有明确的归属,各个法律部门之间泾渭比较分明。海商法在航运贸易中具有日益明显的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在狭义海商法民商事法律属性的基础上,也逐渐随着法律的发展具有不同法律部门的属性,相应扩展成为广义的海商法,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把海商法学理解为一个独立的二级法学学科,把海商法界定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意义的。因为,正确理解海商法的多部门属性或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不但可以解释不同环境下海商法的定位和相关法律的适用,而且适度开放性的海商法属性也有助于适应航运贸易的发展要求,拓展深化海商法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1]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SCHOENBAUM T J.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M].4th ed.St Paul:West,2004:1.
[3]张湘兰.海商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
[4]FORCE R.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M].Washington:Federal Judicial Center,2004:ix of preface.
[5]吉尔摩,布莱克.海商法[M].杨召南,毛俊纯,王军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
[6]台特雷.国际海商法[M].张永坚,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序言.
[7]吴焕宁.海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8]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9]赵德铭.国际海事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
[10]於世成,杨召南,汪淮江.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8-100.
[12]张湘兰,邓瑞平,姚冲天.海商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
[13]贾林青.海商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14]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260.
[15]王孝通.海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6]司玉琢,胡正良,曹 冲.试论海法独立学科体系[J].航海教育研究,1997(1):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