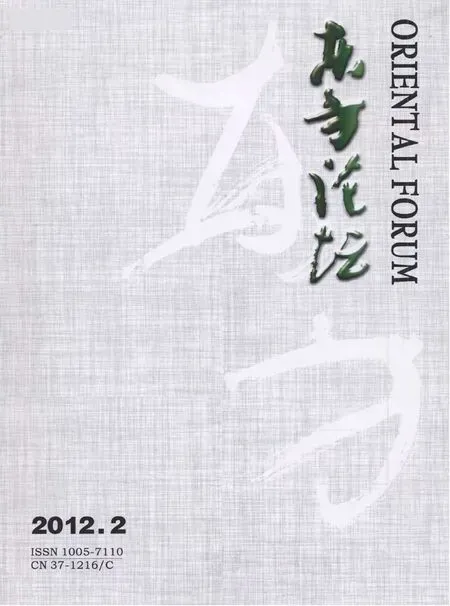论史铁生小说的全息人物
论史铁生小说的全息人物
张 细 珍
(江西财经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史铁生小说中的人物既是自成一界的特定符号,是性格人、命运人,存在人、意象人,是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接通寄予着作者关于命运与存在的思考;也是自由无界泛化的“X”,是显现“我”之“印象”的印象人,能于“我”之印象中悉见世界,是携带生命消息、息息相通的生命全息体。从而,一方面促成主题的复调,文本的敞开、叙事的解放;另一方面,全息也只是“我”的印象,是浩渺消息之一种,体现了作者认知的深刻与悖论。而其“反中心人物”的符号手法也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确定,缺少心理细节与动作情节的细织密缀,而显得意念化静态化。人物是特定的符号?还是无限填充作者意念的X?或是“符号+X”的有机体?这或许是任何一种先锋写作都应思考的界限问题。
史铁生; 人物; 符号化; 全息性
当代作家史铁生一直依着“心魂”的引导,向“那无边无垠的陌生之域的存在”,寻求“新的思想与语言”。艺术语言是其心魂探路的触角,而在语言的界限之处,心魂又继续为其开路。在他那里,心魂的深入探险与艺术形式的开放创新是相生相长的两位一体。心魂与形式的此种共舞,作者自称为“写作的零度”,我则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坛最本源又最先锋的写作,本源因其直抵存在的本体、本相,先锋因其所惑所问之深、之透、之超前。此种本源性、先锋性在其小说的全息性符号人物身上多有体现。
一、由实体而符号
西方理论界对“人物”(character)的理解差异较大,其中有两类观点较典型:一、“心理性”①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1-60页。人物。即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个体“人”。简言之,是性格人,是一个血肉骨架俱全的生命。二、“功能性”人物。即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亚里士多德说,可能有无性格的故事,却不可能有无故事的性格。若以此为标准来概括史铁生笔下的人物,那他们是兼有心理与功能的符号人。
史铁生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尚有姓名,如《爱情的命运》中的小秀儿,《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破老汉、留小儿等。至《山顶上的传说》、《命若琴弦》,开始隐去人物姓名而代以泛称,如小伙子、老瞎子、小瞎子等。从《钟声》开始,则以字母代替人物,人物抽象化为一个个符号代码,如B。至《务虚笔记》,人物几乎全部符号化,如画家Z、诗人L、少年WR等。这些人物具有符号化与全息性特征,故可称为全息性符号人物。近作《我的丁一之旅》,人物又恢复了名号。但是,人物名称只是有限肉身的代码,真正的主角是无限自由的“行魂”。
史铁生小说人物指称更迭的背后是作者创作理念的变化,由初期对生活与人物的写实性描摹,走向对生命与存在的象征性隐喻。人物的符号化与其内省、冥思型的写作风格有关。残疾境遇使他感知世界的肉身触角内敛,代之以精神触角的张扬。小说多以冥思、玄想、独语、回忆、梦幻、超时空或时空倒错的意识流、潜意识心理等不确定叙述,探讨生命与存在等本源性的“务虚”主题。
基督教中,语言的原罪在于,人类建巴别塔的妄想导致了语言的隔离;史铁生笔下,人物的具体姓名,如同有限的语言与肉身,会带来精神的隔离,而虚化、抽象的符号则引领精神走向自由与相通。随着生命探索的推进,史铁生笔下的人物也由现实的实体走向精神化的符号,进而全息化,于全息中携带存在的诸多可能。
二、全息性符号
人物符号化体现了史铁生小说的先锋性、实验性,这也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传统小说讲究人无名不立,名不正便言不顺。现代小说则消解人名,“甚至人物的姓名——这是写人物必不可少的——对现代小说家来讲也成了一种束缚。”[1](P653)人物符号化在西方现代派小说中早有实践,如卡夫卡笔下的“K”,乔伊斯小说中的H.C.E,还有纪德、罗伯-格里耶等小说中的符号人物。法国新小说的干将罗伯-格里耶是史铁生喜欢的作家。新小说的人物观便是“物就是物,人只不过是人”,反对传统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使物从属于人。小说主要任务不是描写人物,而是呈现“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探索“潜在的真实”人物只是没有姓名符号化的“临时道具”[2](P79-80)。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派作家余华等人的笔下也较集中地出现了符号化的人物。不同于许多先锋小说符号人物的非人格化,史铁生小说的符号人物既是性格人,命运人;又是存在人,意象人;还是消息人,印象人。简言之,是全息性的生命体。
全息论,源于物理学。大卫·玻姆是现代全息理论之父。核心观念是,宇宙是一个由各部分组成,彼此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机体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携带着整体的信息,即部分是整体的缩影。如柳条携带柳树的基因信息,能成长为一颗大树。史铁生小说中的人物既是自成一界的特定符号,是性格人、命运人,存在人、意象人,是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接通寄予着作者关于命运与存在的思考;也是自由无界的泛化的“X”,是显现“我”之“印象”的印象人,能于“我”之印象中悉见世界,是携带生命消息、息息相通的生命全息体。
(一)自成一界的符号
史铁生小说人物首先是特定的符号,是一花一世界、自成一界的性格人,命运人。每个符号人物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心史灵谱、性格特征、命运轨迹、欲望梦想、思想悖论。《务虚笔记》中,每个符号人物遭遇不同的“生日”,进入各自不同命运之门,陷入各自的身份境遇,也都可以贴上明显的性格标签,如诗人L,智者F医生,高贵者O,弱的天才Z,强者WR,庸者F夫人与O前夫等;有着各自的性格缺陷,如诗人L的泛爱主义、残疾人C的自卑意识、画家Z的自卑情结与等级观念、WR的权力欲望等。正是这些性格特点与缺陷决定着他们各自的命运轨迹。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性格人,命运人。
史铁生创造符号人物的重点不单在于塑造生动丰富的人物性格典型,更是把人物当作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其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务虚笔记》可谓一部“研究存在”的小说,每个符号人物都显示着不同的存在之相,作者与笔下的人物是“存在的勘探者”[3](P42-43)。因而,这些符号人物又是寓意的符号,是存在人,意象人。他们接通寄予着作者关于命运与存在的思考,作为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每个人物符号因其强化凸显的性格特征,而被类型化为一种人性代码与存在符号,赋予象征意味。
这些人物是存在人,各自代表人生百态、存在本相之一种,有着自己的深渊与梦想,他们作为自成一界的个体都携带着整部小说的主题信息,都可从各自的角度对存在作独立的阐释,也即每个人物符号都隐含着一个自足的主题。具体而言,F医生代表一种理性主义的存在观,是智者;诗人L则终其一生在写爱情的诗,是泛爱主义的梦想家(后来成为《我的丁一之旅》的主角),是“诚实的化身”;画家Z则沉溺于等级化的价值深渊,“他的全部愿望,就是要在这人间注定的差别中居于强端”,是弱的天才;还有残疾人C的残缺世界;强者WR的权力世界;高贵者女教师O的爱的终极追问与悖论;葵林里的女人在为爱献祭与叛徒原罪间纠结;庸者F夫人与O前夫那被忽略的世界等等。
除了表意,符号人物还具有结构整部小说的功能。正如“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说:‘人物是各种母题的有生命的载体,介绍人物是把它们集中和联系起来而常用的一种手法。’‘人物起一种导线的作用,它可以指引搜集母题的方向;人物还起一种辅助手段的作用,用来把具体的母题加以分类和排列顺序。’(《主题》)”[4](P251)《务虚笔记》就是在“写作之夜”的统摄下,由众多符号人物组构起来的自成一界又开放复调、众声喧哗的存在世界。
(二)自由无界的X
作为“符号+X”的混合体、开放体,人物不仅是一花一世界、自成一界的符号,又复调开放、自由无界的X,是全息敞开、息息相通的消息人、印象人。在“写作之夜,空间和时间中的真实是不重要的”,“他们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时间里”,重点不在于人物是什么,每个人是游走在人世宇宙间的生生不已的生命消息;“重要的是印象”,是人物做什么,是他们生命体验与存在境遇的同调与复调,并能于我一印象中,悉见诸世界。
人物的全息开放性,常常表现为叙述的不确定性。小说人物身份充满不确定性、流变性,人物与人物间经常相互叠加、重组、分化。作者很少将一个人物的生命流程连贯地叙述到底,总是节外生枝、枝外又生节。在中断叙述的过程中,经常插入其他人物经历乃至将二者甚至三者混合融并在一起,从而使一个人物符号上面叠加着两三个人物的身影,“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小说中诸如此类的语言随处可见:“如果”、“似乎”、“可能”、“或者”等等。诸如此类的叙述话语随处可见:“WR和Z,在他们早年的形象中,呈混淆状态。”“模糊的少女T,在诗人L初次失恋的夏天重新分裂为N和O。”“谁都可能是C。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淆。”人物间的此种洗牌游戏般的分合叠化、自由替换暗示了人类命运的神秘性、共通性,如画家Z 、WR 、“我”可能都在童年碰见过一个“可怕的孩子”,可能都在黄昏走进各自的命运之门,领有各自的“生日”,然后分化离散,走向各自的生命轨道。在《务虚笔记》中,每个人物都是携带存在消息,又息息相通的全息体,能于一人身上看见全人类。
人物交叉叠化同时,又携带着各自独特的生命消息进行着多声调的对话。其实,整个小说人物便是多组对比性互文性的设置:医生F与诗人L、少年Z与WR、画家Z与“写作之夜”的“我”、女教师O与“写作之夜”的“我”、医生F与“我”、“我”与WR等等。人物的声音在文本中经常被作者自由地超时空地放在一起,或交锋、或对话、或叠合。如小说中会出现这样的话:
“以上对话的双方,有三种可能:
(一)F医生与诗人L。
(二)F医生与F医生自己。
(三)F医生与残疾人C。”
人物的自由开放、交叉叠化,人物间超文本超时空的对话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物符号化(非实体化)的同时还是一个独立而又整体的生命全息体(话语主体)。他们是游走在人世宇宙间的,“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时间里”的生生不已、息息相通的生命消息。这使得对话不显零乱、破碎,反而具有内在的整一性。此种人物符号的全息性生成多视点叙事。多视点叙事带来的是存在的悖论性、叙述的不确定性、主题的歧义性,从而使得《务虚笔记》的文本世界呈现为一个复调多声的“狂欢时空体”①此概念引自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参见《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在这时空体里,人物的全息实则生命、宇宙的全息,隐含着作者俯瞰众生的大生命意识、悲悯情怀。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写作之夜”“我”的“印象的一部分”,我途经这些人物,借人物的视点,进入世界。同时,“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人物全息性的同时最终又“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所谓全息也只是浩渺消息之一种,从而体现了史铁生认知的深刻与悖论。
三、符号与X
符号人物,用符号指称人物。人物向符号的转换生成过程中,还有个变量X的问题。这个X是作者的意念思绪投影于人物时的想象,也可以是读者的意念思绪投影于人物时的回味。
在史铁生笔下,人物有限的名称如同肉身,会带来精神的隔离,而抽象的符号则引领精神走向自由与相通。人物是特定的符号的同时也是无限的X,其符号人物是“符号+X”自成一界又自由无界的全息体。其人物多重“神”而轻形,只抓住并凸显每个人物的精魂,拒绝传统人物典型塑造过程中的精雕细刻,而代之以寥寥几笔的写意与白描;拒绝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平铺扩展,尽量省略对人物具体生命历程的细致展现,而代之以自由跳跃的跨时空叙述、元小说等写法,从而促成人物、主题的复调,文本的敞开,叙事的解放。
人物的符号化全息性是由作者将人物视为存在的镜像这一创作意旨决定的。拖着沉重的肉身,走过短暂一生的史铁生将他的一生咀嚼、反刍、然后炼成文字,借助笔下的人物走过多种人生,探究的存在的可能性,由此而获得永生。这是史铁生创造的符号人物的独特意义所在。读史铁生,应在作品里找个适合自己的角落,坐下,借助人物的眼睛,从里往外看。读者能从小说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看完之后,再从外往里看。看人物的升沉起伏,人间的爱恨情仇,人世的沧桑变幻,人生的百般况味。看人物,也看自己。
人物的符号化全息性在获得主题的丰富性、文本的启示性的同时,此种少性格血肉,少心理动作,多思想理念,没中心、没定向的“反中心人物”[5](P212)倾向也容易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随意的跨时空组合、替换与更迭,则使他们缺少心理细节、性格逻辑、动作情节的细织密缀。因而,在获得象征性的同时,失却了人物所应有的丰富性、生动性、流变性,显得静态化、抽象化、概念化。甚至,有时因过于强化人物的某一性格特征,在叙述上显得有些牵强失真。如作者将画家Z的命运全部归结为一个细节:童年的一个冬日黄昏,他在一所美丽的楼房里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她怎么把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使其生命“就在九岁那一年的回声中碰到了一个方向”,由此产生了影响一生的“自卑情结”。在以后关于画家Z的叙述中,作者反反复复地渲染着他的这个冬日情境,从而使Z这个人物在极致化的同时又显单一化、静态化,性格自始至终没有生长。除此以外,由于人物频繁的分化组合,使其人物刻画无法集中笔力,从而个体上丰富性不足。可以说,读完《务虚笔记》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物形象,而是由众多人物连缀而成的群体。另外,由于人物的此种变化又会影响读者阅读思维的连贯性、统一性,造成阅读印象的模糊甚至混乱。这也是《务虚笔记》“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人物是特定的符号?还是无限填充作者意念的X?或是“符号+X”的有机体?这可能是任何一种先锋实验都应思考的界限问题吧!
[1] 崔道怡等.“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
[2] 智量,熊玉鹏.外国现代派文学辞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 鲍昌.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Holographic Characters in Shi Tiesheng’s Novels
ZHANG Xi-zhe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The characters in Shi Tiesheng’s novels are designated symbols for character, fate, existence and image, conveying the writer’s puzzlement and reflections about existence. They are also an open “X” and holographic life, manifesting my impressions of the world and carrying information of life. The holographic characters bring about polyphonic theme, open text and free nar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holographic characters are just one part of my impressions and one kind of information in the world, which reflects the writer’s paradox. The symbolic writing of anti-central character caused indefinite character’s identity as a result of lacking psychological details, exquisite actions and abundant plots. Is the character a designated symbol, open”X” or combination of symbol and “X”? It is a question of limitation that every vanguard writer should think about.
Shi Tiesheng; character; symbolization; holographic
I207
A
1005-7110(2012)02-0066-04
2011-12-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大转型期北京作家群的形成、选择与困惑》(06BZW060)的阶段性成果。
张细珍(1981-),女,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