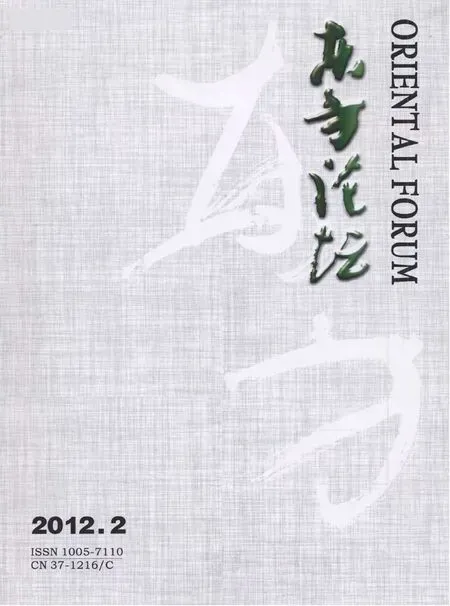论史铁生对生命之路的探寻
论史铁生对生命之路的探寻
戚 国 华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510640)
“路”在史铁生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由于双腿瘫痪,他无法走路;将近四十年,他不断地探寻人的生命困境的缘由与终极希望之出路。从荒诞的命运谜路走向“爱命运”的审美与艺术之路,他经历了漫长的求索之路;至终他坦然认同并走在仰望与奉献的爱愿之路上,完成了他的“过程即目的”的人生突围之路。
史铁生;生命;命运;荒诞;爱愿;审美;过程
史铁生在他21岁时因病双腿瘫痪,后他选择写作,将写作视为“为心魂寻一条活路”。他曾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写作动机:先是为了谋生,然后看见价值、虚荣和荒唐。他以笔为腿,终生探索摆脱人间困境的道路,慢慢地“一颗世间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他的后期写作不再过多的描述人生外在生活的真实,更主要的是揭示自身内在真实的心路历程,他一生都在寻找超越困境的道路。
一、“人间戏剧”——走出偶然与荒诞命运的精神之路
在对人生的原生态进行了种种抽丝剥茧的分析后,史铁生在代表作《病隙碎笔》中得出了人类的命运是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并由上帝设置了精彩纷呈的情节,并且每个人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因此,具有“粒子样位置”的人就有了“波样的命定之路”,并由“生日”这天被固定为个人永远的命运。他认为这种“偶存性”的荒诞与神秘却要看重并善待它,因为“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1](P9)他在《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中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
他的作品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谁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呢?我们真的已无路可走了吗?在对人类难解之谜的追问与求解的过程中史铁生走过了十多年痛苦的心路历程,终于明白了: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他早期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常常充满着命运的偶然性与荒诞性,并流露出愤激的情绪。如《山顶上的传说》那个小伙子因为到一间八面漏风的潮湿的小屋睡觉而终生残疾;《来到人间》一对健康的夫妻生下一个先天性的侏儒,纯粹出于偶然;《边缘》中老头冻死在自以为床的石头上。《原罪·宿命》最具代表性,前途光明的青年莫非即将出国留学,却忽然“因一秒钟的变故”被汽车撞断了腰椎而好运告罄,而悲剧的原因寻根问底竟是一声很响但是发闷的“狗屁”!中期作品《务虚笔记》中,为了展现命运的偶然与荒诞,他更是将同样的事情让不同的人都经历,并将我一分为“我”与“史铁生”两个人,时空界限也被打乱。MR因为不可选择的出身问题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多年的奋斗化为泡影;画家Z由于自小家境贫困,受到歧视,而终生走不出屈辱的阴影。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他竟让灵魂陪同肉身“丁一”一同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将“我”拆成三个人:“我”、史铁生、丁一,他们同时或交叉出现于作品之中,他一生的思考都浓缩在迷宫般的文体中,读者若没有足够的耐心很难读完全篇。仿佛冥冥之中有命定,一个偶然的非选择性的原因,就决定一种生命形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生充满了荒诞和虚无。他肯定命运是“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黑夜”,而陷入谜团之中。他甚至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苦难,从根本上说就是荒诞的(曾被誉为“中国的加缪”)。“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是人类的局限、痛苦与深刻的绝望。经过迷茫、挣扎、困惑后他找到了“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内向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2](P97)“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3](P308)史铁生终于说服了自己,把对苦难命运无法理性解释的强烈生命意识转化为精神信念。于是,他由对个人无定命运的拒绝与愤怒转变为坦然与平和的接受,并升华为整个人类生存本相的担当,还原了人生的悲剧性并具备了崇高的悲剧意识,使中国当代文学有了自己的空灵、美丽而又诗意的灵魂之舞,就像史铁生在作品中一再写到的那只悠然飞翔的白色大鸟,纯洁、高贵、美丽。他的写作也因着涉及了一个独特而纵深的领域——人的精神和形而上的生命而得到提升,在中国作家少涉足的区域开出了“一朵朵艺术奇葩”。在此意义上史铁生也超越了自己“沉重的肉身”而开始走上独吟“精神”之路,找到了一条超越人性普遍困境的救赎之路,成为他实践人生的第一条突围之路!为人与为文融为一体,他的人生及写作历程在与人类困境与个人宿命较量的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缺少内在精神信仰和心魂建设的时代,史铁生的独特写作引发了我们对人生意义更深层次的注视。
二、“爱命运”——仰望与奉献的爱愿之路
史铁生的人生态度在创作后期杂文集《扶轮问路》里得到了高度的总结与概括。开篇他就说:要爱命运,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爱命运,既是爱上帝——上帝创造了无限种命运,要是你碰上的这种不可心,你就恨他吗?爱命运,也是爱众生——假设那一种不可心的命运轮到别人身上,你就会松一口气怎的吗?在他看来,人置身苦难命运中,有两种基本心态:一是怨恨,一是爱愿。怨恨使人走向孤苦、争竞和虚荣,爱愿使人走向信仰、尊严和献身。在《放下与执着》中写道:由衷感到,尼采那一句“爱命运”,真是对人生态度之最英明的指引。不仅爱好的命运,对一切命运都要持爱的态度,爱是人类唯一的救助。爱命运就是与上帝和好,接纳上帝给予的一切。爱命运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敢于承担非他意志所能支配的一切,是一个强者正面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人生选择。“尼采说,伟大的人是爱命运的。是呀,既不屈从它,也不怨恨它,把一条冷漠的宿命之途走得激情澎湃、妙趣横生,人才可能不是玩偶。那是什么?又如尼采所说:既是艺术品,又是能够创造并欣赏艺术品的艺术家。”[4](P66)“拯救,即在有限向着无限的询问中、人向着神秘之音的谛听中;而大道不言,大道以其不言惊醒了人间的智慧——唔,那原是一条无休无止地铺向圆满与善美的神性之路!从而你接受宿命又不囿于宿命,从一个被动的玩偶转变成自由的艺术家,尊重原著又确信它提供了无限可能。圣灵即于此刻降临。所以,拯救必定是‘道成肉身’。”[4](P67)而《欲在》更是一首爱的赞歌:爱是对他者的渴望,对意义的构筑。爱是拯救,既拯救了当下又成就着永恒;爱是受命于上帝的一份责任,爱是主旋律;不管什么样的生命你都要以爱的态度来对待,这不单是受造者对创造者的承诺,更是上帝拯救人于魔掌的根本方略。爱命运,不等于喜欢命运。喜欢意味着占有;爱,则是愿付出。在生命的戏剧中并没有纯粹的观众。所以,上帝并非是让你喜欢存在,而是要你热爱存在。(创世主)在人四顾迷茫而不见归途之际,他以其爱愿,温暖了这宇宙无边的冷漠。真正的神恩,恰是那冷漠的物界为生命开启的善美之门,是那无限时空为精神铺就的一条永不衰减的热情之路。在《理想的危险》中总结为:“人类的一切精神向往,无不始于一个爱字”。在《门外有路》指出人生的意义“是要把一条困顿频仍的人生之真路,转变为一条爱愿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条无尽无休、颇具荒诞的人生之实路,转变为雄关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4](P95)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灵的完善”。到了生命的晚期,史铁生仰望“神启”,做到了豁达与甘愿。他生前多次表达过想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的愿望,当他的呼吸一停止,肝脏就被摘取给急需的患者。史铁生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实践完全同构在了一起。确实,他的腿虽不能站起来,却比我们有腿的人看得更高更远;他不能用脚走路,却比很多走遍世界的人拥有更开阔的心,他比我们许多人都健康!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他都具有着非凡的地位与高度。他设计并实践的人生突围的第二条路——爱愿之路,将鼓舞更多的人加入爱与奉献的路。
三、“永恒回归”——永远在过程中的艺术与审美之路
史铁生在《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一文中说:“永恒回归”又译为“永恒再现”或“永恒复返”,意思是:“一切事物一遍又一遍地发生”[4](P51),“像你现在正生活着的或已经生活过的生活,你将不得不再生活一次,再生活无数次。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新的”,[4](P51)生命的前赴后继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的内容,或生命中的事件,无论怎样繁杂多变也是有限的。有限对峙于无限,致使回归(复返、再现)必定发生。那是出于人的根本处境,或生命中不可消灭的疑难。“永恒回归”指的是生命的主旋律,精神的大曲线,根本的路途、困境与期盼是不变的;根本的喜悦、哀伤和思索也不变。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永恒回归”是无穷路,只能是无穷地与困苦相伴的路;没头,都得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做无限的行走。“永恒回归完全发生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另一个世界,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天堂),也没有一个更坏的世界(地狱)。这个世界就是全部”。[4](P51)人间的智慧——尼采、玻尔、老子、爱因斯坦、歌德……他们既知虚无之苦,又懂得怎样应对一条永无终止的路。
人生中的过程与目的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史铁生在多篇散文中谈到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他说: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唯有过程可以变得十分精彩、美好,值得体验和享受。因此“过程就是目的”。他说到:向美向善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再怎样走,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不可及。只有过程才是“人类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寄托”。史铁生由开始写作关注目的转向了后期写作的体验过程,他似乎看开了自己的命运,认为也许“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他思想的转变为人类困境又寻找到了第三种出路。因为“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把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崩溃了,它必然溃败。你立足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3](P294)他也多次说过: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才是存在的根本,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人生百般奋斗不断超越的意义不在于去实现一个具体现实的功利“目的”,而在于不懈追求的“过程”本身之中,过程就是目的。西西弗斯就是在滚动巨石的过程中战胜了绝望,成为壮美的生命过程的象征。
《命若琴弦》、《对话四则》是他的过程哲学的最形象诠释:人生一世其实活得都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人生的目的是虚幻的、自造的。只有那过程中满怀希望弹断的琴弦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拥有的快乐,弹出最优美的旋律就会给人带来欢乐,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了。即使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是0 : 0,但球迷们自始至终保持狂热的兴致。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球迷们欣赏到了球员的生命的矫健、坚强、智慧和优美,在输赢难定的过程中享受了激情、惊险、渴望和着迷。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就是美,这就是生活的目的。人生难道不是上帝安排的一场球赛?所有的人都在场上摸爬滚打,企望射中目标。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有好运,每次都能达到目的,如果只注重目的的实现,人永远也不能得到满足,一生处在无涯的痛苦之中。所以,人只有把关注的重心放在过程之上,在上帝设置的困境之中不断超越,人的生活才会充满激情,人生才会获得快乐。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艺术正如爱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无尽头,比如‘诗意的栖居’可不是独享逍遥,而是永远的寻觅与投奔,并且总在黑夜中。”[2](P116)
从思想渊源看,史铁生的命运观与永恒回归思想都深受尼采影响,而尼采又受古希腊悲剧命运观与佛教轮回的强烈影响。“说他与存在主义相通,根本原因在于他对苦难,对困境的理解和感悟,正是这些把他引向‘存在的意味’。”[5]作为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命运观,“爱命运”思想是希腊悲剧命运、英雄行为和主体意识的高度升华和综合。尼采认为最高的善是源于创造的善,谁要创造,谁就要爱命运,爱生命的过程,而不去追究它的实质和归宿,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性中获得艺术快感和审美陶醉。人类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就算人生是个梦,要有滋有味地做,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趣;就算人生是幕悲剧,也要有声有色地演,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美。这种审美的人生不计较任何功利目的得失,而只注重过程的精彩,不再管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幸运还是不幸,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人便在审美的意义上获得了超越。史铁生以自身和整个人类的生命状态为审美对象,以哲思和写作为自己的审美方式,以博爱为自己的审美追求,孤独而又执著地建立起自己的审美世界,他所开出的人生困境突围的第三条路——审美的艺术之路真的能救赎人类永恒的困境吗?
综上所述,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史铁生人生突围之路的三条路——前两条即精神与爱愿之路虽具有一定的超越意味,但还是缺乏神圣的根基,他所言的精神最终并非承载苦难而还是解释了苦难,走向了自我超脱;他所认为的爱愿的生发即信仰的过程,因缺乏具体的信仰对象而有悬空之感,连他自己也承认是证明了神性而否认了神。他以爱愿取代了信仰,以精神取代了上帝,信仰精神既深刻又虚妄。第三条审美之路更使其走了后退的路而回到了原点,因为这实际是一条没有盼望、没有终点的封闭式的无效徒劳之路。正如他在《叩与问》中所说:“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对于永远的游魂,危难并不在于旅途的崎岖坎坷,而在于归心昭昭然而却归路昏昏!‘日暮乡关何处是?’”[6](135)所以在史铁生的哲学思索中,尽管存在着一些形而上的追求,但人本主义还是占了主导地位,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寻找的每条路还是理性、自明之路,他穷其一生所艰难探索出的心灵跋涉之路依然是一条人间的路——没有确据的路——沉浸在人性幽暗的深渊里发出绝望的呼告和祷愿的路,他是在封闭系统内的突围,其实是走向了死胡同,没有找到活泼的有盼望的开放系统的活路。正如齐宏伟所说:他在写作中把苦难转化为一种信念,没有强大的信仰支撑单单依靠自我设置、自我生发的神性能否支撑着语言成为存在的家园?信念毕竟不过是信念,还没有凝铸成完整而有生命活力的信仰,还没有超越理性推演和批判反思层面,还没有展示出真正有原创力和超越力的精神资源,也还没有解决自我信仰与信仰自我等等这些最为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这致使史铁生的写作显得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解释过多而聆听过少。也正如史铁生自己所言:“确实,人一直是在解释的路上,且无尽头。事实上,未必是我们在走路,而是路在走我们。”[7](P97-198)其实在命运面前,重要的是承载而不是解释。
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是古今中外拥有“人间智慧”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们都无法突破的致命瓶颈。哲学的尽头正是神的起头。生命的困境,只能靠超生命的神去解套。史铁生虽也多次谈到神,但是“说神,道主,怕又要惹人疑忌。其实呢,‘名可名,非常名’,姑且名之罢了。你叫它‘大爆炸’也行,谓之‘太初有道’或‘第一推动’也可;名者,不过为着言说之变。”[4](P86)“其作者无论叫‘上帝’,还是叫‘大爆炸’,一样都是永不可及的谜。”[4](P136)虽然他信有神,但不是人格的神,也不是自己的救主。他由残疾走向爱情,没有由苦难走向信仰,正如罗丹的雕塑《行走的人》:无头,无臂,只剩下结实的躯干和跨开的大步,很盲目地走向前方。他失去了大地,但也没得到完全的天空,他只是个朝圣者,“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4](P10)
[1] 史铁生.写作之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2] 史铁生.病隙碎笔[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
[3] 史铁生.别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4] 史铁生.扶轮问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 胡山林.苦难把你引向存在的意味[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4).
[6] 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 史铁生.活着的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Shi Tiesheng’s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Life
QI Guo-hua
(Faculty of Arts,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Road” had a very special meaning in Shi Tiesheng’s life experience. Paralyzed, he was confined to a wheelchair. The helplessness and pain forced him to take up writing, which was his way of living and where his value lay. During some forty years of “road quest on the wheelchair", he kept on seeking the reasons for the trapped life and the ultimate way out for himself as an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s. It took him a long time to shift from the puzzlement of absurd fate to the aesthetic and artistic road of “loving his fate”. Finally, he was reconciled to his fate and was happy on his road of faith and dedication, thus completing his breakthroughs in life with the theory that “process is purpose”.
road;fate; absurd;desire for love;aesthetic appreciation;process
I207
A
1005-7110(2012)02-0070-04
2011-11-27
戚国华(1962-),女,山东黄县人,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