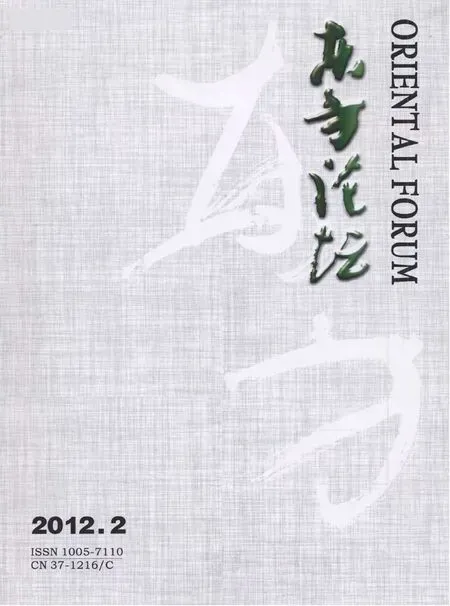论唐代骈文文体观的变化
论唐代骈文文体观的变化
翟景运 牟艳红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虽然唐代骈文在作者和作品数量上远超古文,但传统的文体正宗地位逐渐颠覆,走上向专门性应用文体转变的道路。在唐代骈文、古文盛衰消长的表象之下,骈偶文体的地位客观上在一路走低。如果说唐代骈文在创作上呈现时高时低的波浪线,而骈文文体在唐人心目中的总体价值则大致呈现为一种单纯的下滑线。
唐代;骈文;古文;文体
伴随着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高涨与衰落,骈文声势也相应地有所反复:大抵中唐古文创作繁荣而骈文风头稍减,晚唐古文式微而骈文复盛,两者关系大致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但在骈文、古文盛衰消长的表象之下,骈文的社会价值相对于古文来说,实际上是在一路走低。在唐代,骈文传统的文体正宗地位逐渐颠覆,从而走上向专门性应用文体转变的道路。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并未因为晚唐五代骈文创作的复兴而受到影响。骈文创作的盛衰与文人对骈文社会地位、艺术价值的估价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把唐代文人对骈文看法的变化作一梳理,对于理解这一段文章格局演变的大势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一、初盛唐:以骈偶为正宗的六朝遗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文章骈俪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另一方面,几乎各种体裁均开始使用骈体,骈文写作的体裁成为正宗体裁,极少数仍用散体写作的体裁则边缘化而不受重视。散文与骈文并行的作品,《文选》编者只选其中的骈文部分,比如史传,不选传记本身而只选录论、赞部分。一般史书之外,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山水地记,即使富有文采,也被排斥在“文章”之外,列于史志目录中的史部。散体文在骈文的排挤下明显边缘化了。《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自然当中对称现象十分普遍,文章亦自当效法自然,讲究对偶。推尊骈体为文章正宗,刘勰的这段话是最直接、最明确的理论表述。若在今天看来,文章未必一定要对偶,散笔单行也是文章,可刘勰力主为文必须骈偶,这是当时通行的文章观。
在隋和唐代初年,关于文学审美特质的探讨仍然在继续进行。如对声律、对偶等诗文形式美的探讨和总结,对诗歌情景关系的思考,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文学审美特质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骈文的发展也有其自然过程,不会在历史的某一个点上戛然而止。骈俪体制在中古时期扩展延伸到绝大多数文章体裁;进入唐代以后,特别是古文运动兴起之前,骈文的影响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受到太大影响,仍然具有雄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实际上就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以及文学传统的自然延续。
从骈体文逐步得以定型和确立的南朝,到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对于骈文的批评始终未曾中断。不过批评的性质却不尽相同,有针对文风者,有针对文体者,大抵除了唐代古文家之外,以针对文风的批评为多。典型者如梁代裴子野、北齐颜之推、隋初的李谔、唐太宗时代的史臣、初唐四杰、陈子昂以及史学家刘知几等等,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的浮艳文风有所抨击,但他们反对的不过是内容空洞或修饰太甚,而绝非骈偶文体,实际上他们针砭文章弊病的论著也都是骈体。
再如唐代科举制度体系当中,曾有不少有识之士对严格讲究骈偶和声韵规则的诗、赋等考试内容表示不满。早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就有诏书说:“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1](卷六三九)所谓“进士以声韵为学”,所针对的就是诗赋试。安史之乱以后,部分士人痛定思痛,寻找祸乱的根源,推及到科举制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弊病提出尖锐批评,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试就是主要对象。赵匡、杨绾、贾至等人屡屡指出:诗赋考试只重视文辞华丽、技巧纯熟,全不在乎彰显孔孟之道,这种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必然导致学风、士风的浇薄,他们还认为这种舍本逐末的考试方法造成“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是安史之乱的诱导因素之一,因此他们都主张废除明经和进士科。
以往有些学者常常把这些言论同唐代古文运动反对骈文的论调等同起来,略加分析便知此论欠妥。改革呼声的焦点集中在考试内容、录取标准与现实的需要不能衔接,或者说按照诗赋标准所录取的人才与治国经邦的吏干之间存在着距离;主张取消诗赋试,并不代表否定诗赋本身,而是诗赋不适合作为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因此无论改革的主张无论能否付诸实施,并不会从根本上触及骈体文的生存权。杨绾的《条奏贡举疏》和赵匡的《举选议》都是骈文;权德舆在文学理论上主张“尚气、尚理、有简、有通”,他与陆贽、高郢一班人在主持贡举期间重经义、轻文辞的措施在精神上与古文家们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对古文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否定或主张取消骈体文。《权载之文集》卷四〇有《明经诸经策问七道》,这是权德舆在贞元十七年至十九年知贡举时所出的试题,都是用工整的骈体文写出。因此,有必要把反对进士科试诗赋同否定骈文这两种主张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的实际意义截然不同。文风改良的策略首先表明在根本上认同骈偶文体;而且文风改良的客观效果必然是增强骈文的适应性,扩大其影响和流行范围。
六朝时代,人们已经注意到骈体和散体的区别,当时分别称之为“今体”、“古体”。《梁书·裴子野传》说他“其制作多法古,与今体异”;《周书·柳虬传》载:“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在骈体独尊的时代,“法古”者显然属于十分罕见的特例,在人们将“文必对偶”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氛围里,他们既没有有意识地对两种文体作出什么价值评判,也没有明确表达对骈偶文体的质疑和反对。如果不是唐代古文运动明确提倡“明道”之文,标举同“时文”、“今体”异趣的全新创作理念,并最终建立与之全面对抗的“古文”,对偶甚至不会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体特征。
二、中唐:“当对”与“不当对”的对峙和较量
到了中唐时代,南朝以来文必偶对、以骈体为正宗的文体观仍然影响巨大。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对属》云:
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匹配而成。……比事属辞,不可违异。故言于上,必会于下;居于后,须应于前。使句字恰同,事义殷合,犹夫影响之相逐,辅车之相须也。[2](P1675)
又云:
在于文章,皆须对属,其不对者,止得一处二处有之。若以不对为常,则非复文章。(自注云:若常不对,则与俗之言无异)……故援笔措辞,必先知对,比物各从其类,拟人必于其伦。此之不明,未可以论文矣。[2](P1686)
强调对偶是“文章”、“文笔”的基本条件,与前述《文心雕龙·丽辞》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可谓桴鼓相应,一脉相承。遍照金刚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七月随遣唐使来到中国,在中国留学约三年,于唐宪宗元和元年(日本大同元年,806)八月回国。之后于日本弘仁十一年(820)撰写《文笔眼心抄》,其自序称:“余乘禅观余暇,勘诸家诸格式等,撰《文镜秘府论》六卷,虽要而又玄,而披诵稍难记。今更抄其要,含口上者,为一轴拴镜,可谓文之眼,笔之心,即以‘文笔眼心’为名”。[2](P1934)然则《文镜秘府论》当作于宪宗元和元年与元和十五年之间,其中见解正可反映当时中土文坛上的一般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唐宪宗元和(806-820)时期,恰好处在古文运动的高潮阶段。元和十四年(819)、穆宗长庆四年(824)柳宗元、韩愈先后病逝,古文运动遂迅即转入低潮。韩、柳不仅是古文运动的中坚,也是最早自觉张扬古文、反对骈文的人。《旧唐书·韩愈传》说:“常以为自魏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激烈批评骈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却无补于世用的弊病;韩愈《毛颖传》因文体而遭受攻击的时候,柳宗元则在数千里之外撰文为韩愈辩护,热情赞扬韩愈在文体上的开拓和创新。与《文镜秘府论》力主骈体为正宗的论调综合起来看,中唐文坛显然较之六朝和初盛唐出现了一个绝大的变化:自觉挑战骈文文体正宗地位调子正式出现了,骈文的地位受到了质疑甚至否定。骈文、散文究竟谁是正统?六朝到中唐之前,答案是一元的,此时则变成了二元的了。深受韩愈影响的作家李翱,在其《答朱载言书》中对当时文坛上的这种“二元”格局有一非常精确的总结,他说:“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3](卷六三五)对偶还是不对偶,正是骈文和古文在文体层面上的基本区别。所谓“时”,时尚、时俗之谓,“溺于时者”代表了六朝以来的旧传统,和“病于时者”则是传统的对立面。很明显,时代风气的主流仍然是主张文章应当对偶。李翱说自己致力于创作古文乃是“不协于时”的举动,流露出中唐古文家普遍具有的孤独感。韩愈就在《与冯宿论文书》中描述当时古文创作的遭遇说:
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4](P196)
由此可见当时凡“应事”即须作“俗下文字”,即骈体文,古文的市场逼仄狭小。社会上对文章的需求,无论就实用还是审美的角度而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古文家的理想相反。古文家皇甫湜(约777-约835)评价韩愈古文说:“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3](卷六八七)一方面对其造诣表现出高度的推崇,另一方面也承认其缺乏市场和实用性。明人胡应麟说:“昌黎一代斗山,而文字殊不为庙堂重。生平纪述时政,惟《平淮西碑》及《顺宗实录》,而《淮西碑》以愬妻肤受,改命段文昌,《顺宗录》亦以记载失实,更命史官再撰……二事绝类,皆文字之不遇也。”[5](P200)指出韩愈“文字殊不为庙堂重”是符合事实的。刘禹锡曾说:“窃观今之人,于文章无不慕古,甚者或失于野。”[3](卷六〇四)约略透出在中唐时一般作者的心目中,文章复古容易导致质实朴野、缺乏文采的倾向。不过像韩愈这样最杰出的古文家,其实相当重视语言的修饰锤炼,在今天看来,他的不少古文作品文采斐然,颇具形式之美,只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尚未被一般人所认识。日本山田钝曾在《文笔眼心抄释文序》中对遍照金刚绝口不提韩愈古文一事给予专门解释,他说:“大师(遍照金刚)入唐也,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此编所论,专为四六骈俪,其言不及杜少陵、韩昌黎,何也?盖虽少陵变诗格,昌黎唱古文,久而后行,当时言之者少,……大师入唐,气运未开,故其言不及杜韩耳。”[2](P1935)
的确,从魏晋到中唐,骈文的绝对优势已经维持了五百多年,形式上逐渐趋于精密完备。特别是在唐代,骈文成为选举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文人们代相沿习,浸淫钻研,久而久之便逐渐习惯了这种特殊的思维、写作方式,所要表达者自然而然地要出之以骈偶俪对,骈文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除了各别特具才力和识见的杰出作家之外,无论是文章的基本语言结构,还是构思和布局,一般文人很难完全摆脱骈体的影响,古文要压倒骈文的优势,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如此,上引李翱《答朱载言书》中的一点言外之意还是应当给予特别强调:“文章必当对”的观念虽然还是主流,但已经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信条,它已经遭到“病于时”者的质疑,而且与之截然对立的、主张“文章不当对”的声音已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对以往的正宗文体观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三、晚唐:骈文向专门性应用文体的转变
在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之间,晚唐五代出现了骈文创作的又一个高潮。古文运动鼎盛时期,从骈文中夺过来若干体裁,原本使用骈体来写作,改由古文来写;随着古文运动声势的消退,被古文夺走的若干体裁又在一定范围之内还原为骈体。仅以墓志而言,它在韩愈的古文创作中数量最多,三十二卷之中占到十二卷,总计78篇;韩愈的碑志之作在古文运动中的艺术成就突出、影响也最大,是推广古文的一面旗帜。然而据《全唐文》统计,元和、长庆以后至唐末,散体在墓志中所占的比例呈现递减之势:卷731~760骈体墓志只有4篇,而散体者30篇,骈体占11.8%;卷761~790骈体5篇,散体24篇,骈体占17.2%;卷791~840骈体17篇,散体3篇,此时骈体占到了85%。骈体的增长在会昌、大中以后最为明显。但骈文创作量的增长并不代表这种文体地位的回升,晚唐骈文呈现出复盛态势的同时,已经表现出从普遍的文章形态向专门性应用文体过渡的趋势。骈文在此时的形势,颇类似于《红楼梦》里冷子兴所说的一句话——“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首先,晚唐时代骈文回潮,并没有造成六朝后期那样一统文坛的绝对优势。六朝骈文之盛,“上自帝王诏令,下至赠答笺启,无不刻意美化,适会声韵之学,自西徂东,益助文章之唱叹……几不复知世有散行文字矣。”[6](P88)当时写信用骈文,记事用骈文,吊祭碑传用骈文,乃至著书立说也用骈文,朝廷发号施令的典重文字,更无不用骈文。与六朝不同,除了行政公文和科举文体等应用性文章以外,其他各种体裁在晚唐始终存在用古文写作的情形。虽然骈体比例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却也只是造成了文坛上骈、散两种基本文体分裂、对峙的局面。骈文维持了五百年左右的一统文坛的地位终于被打破,骈文已经不再是垄断性的文体,这是唐代古文运动即古文与骈文的第一次较量之后的结果。
其次,“四六”名称的出现,是骈文向应用文领域退守的标志。李商隐首次用“四六”命名其幕府公文文集,此后迅速成为此类专门文体的代名词,唐末文献中所出现的当时的“四六”全部都是指以藩镇幕府为中心的骈体公文。《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有田霖《四六》(《直斋书录解题》云田霖为南唐人);《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有崔致远《四六》一卷;李巨川《四六集》两卷;《崇文总目》卷五有樊景《四六集》五卷(樊景,《通志》卷七〇注云“唐人”);郑准《四六集》一卷(唐荆南从事);《白岩四六》五卷(白岩,《通志》卷七〇注云“后唐人”)。经过北宋古文运动一直到清末,公私应用文成为骈文最后的领地,因此宋代以后的人又习惯以“四六”指代所有骈文。《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条云:“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同晚唐“四六”出现之前的一般骈文相比,“四六”更强调应用性,更倾向于格式化,谢伋《四六谈麈序》所谓“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而知。”其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格式、程序极为固定的机械操作。
第三,中唐时代一般只有古文家抵制骈文,但晚唐最杰出的骈文作家也贬低骈文、抬高古文。李商隐的骈文,数量、质量均称翘楚,近人黄侃称其“上承六代,而声律弥谐,下开宋体,而风骨独峻,流弊极少,轨辙易遵,”[7](P37)可谓允当。他虽然爱好骈文、擅长骈文,却并不看重它,甚至屡屡加以贬低,或者将其视作与童蒙或博弈近似的“小道”(《樊南甲集序》),或者说它只是职业需要,谓之“非平生所尊尚,应求备卒,不足以为名”(《樊南乙集序》);他虽然对自己骈文写作的艺术水准颇为自得,却也感慨“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漫成五章》)——骈文写得再精美,也不过是寻章摘句,片面追求声韵和谐、对偶工稳的雕虫小技。一代骈文圣手却对骈文如此轻蔑,实在值得玩味,然而这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晚唐首屈一指的律赋作家黄滔,被清代赋论家称之为“小赋第一手”,[8](卷上)李调元将其与王棨并称律赋作者中“一时之(周)瑜、(诸葛)亮”,[9](卷二)不过黄滔却推重古文,反而把律赋等骈俪之文贬得很低。他在《与王雄书》中说:
夫俪偶之辞,文家之戏也,焉可赍其戏于作者乎!……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尝聆作者论近日场中,或尚辞而鲜质。多阁下能揭元次山、韩退之之风。[3](卷八二三)
李商隐、黄滔视骈文为小道、“文家之戏”,绝非自谦之词,这是骈文文体地位降低的鲜明标志。如果说这种趋势在晚唐还只是端倪初开,北宋古文运动之后就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比如洪迈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宋四六话》记载当时人说“四六近俳”,俳者优也,即文字游戏,都是此意。
综上所论,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描述晚唐文坛的情形:古文创作虽然衰落,但影响已深入人心,生命不绝如缕;骈文创作复兴,却难免为人轻视,客观上地位已经降低。如果说唐代骈文在创作上呈现时高时低的波浪线,而骈文文体在唐人心目中的总体价值则大致呈现为一种单纯的下滑线。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北宋古文运动的冲击,古文彻底压倒骈文就是势所必然的结果了。
[1]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张仁青.骈文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7] 程千帆.量守庐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6.
[8] 浦铣.复小斋赋话[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9] 李调元.赋话[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Evolvement of the Stylistic View about Parallel Prose of the Tang Dynasty
ZHAI Jing-yun MU Yan-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In spite of the larger number of authors and works, the parallel prose gradually lost its dominant status in the Tang Dynasty. Furthermore, it bega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riginal dominant literal style to a special pragmatic style in late Tang. The renaissance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parallel prose caused little change on the all-time low trends of its social status.
Tang Dynasty; parallel prose; folk prose; literal style
I207
A
1005-7110(2012)02-0086-04
2011-12-20
翟景运(1978-),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牟艳红(1978-),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学士,青岛大学党委办公室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