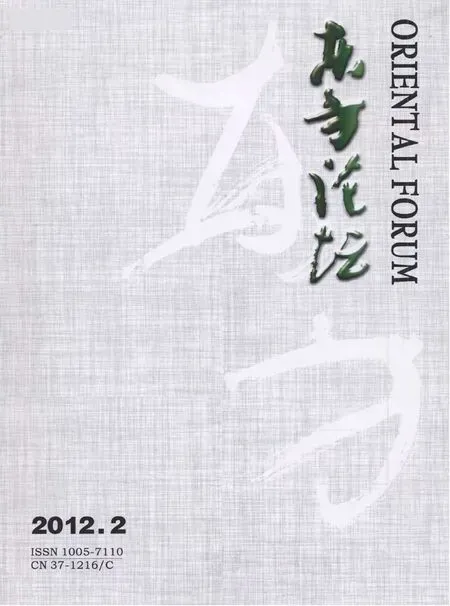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规范思想初探
马克思恩格斯规范思想初探
刘 苏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规范哲学思想。科学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规范思想得以产生的理论基础。马恩认为规范不仅要反映客观世界的各种规律,还要充分展示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度自觉性。规范以自由为基础,是对自由的体现和确认,但同时又规定自由的限度。规范体现了客观性真理尺度与目的性价值尺度的统一。
规范;马克思;恩格斯;自由
自由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然而,自由有两种,一种与规律相对,是对自然和社会客观必然性限制的克服;另一种则与规范相对,是对行为规范的约束的摆脱。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也一直关注着自由与必然,自觉与强制,正义、平等与利益的实现,政治实践和价值信念等“应然性”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为规范下一个教条性的定义,虽然他们谈到的规范大多局限于道德和法律规范,而没有涵盖规范的所有具体类型,虽然其规范思想总是散见在道德、法律、政治理想的思想之中,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规范理论体系,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形成关于规范的基本观点。从规范的角度重构马克思恩格斯解决相关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仅会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哲学寻找到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而且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所进行的具体的社会规范的研究、制订和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规范与自由的关系、规范思想确立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则三个方面来剖析马克思恩格斯的规范观。
一、规范与自由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规范观是在讨论自由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1](P454)因此规范与自由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规范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
马克思认为,自由有其特有的存在和表现方式。“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2](P176)所以,自由就体现并存在于法律规范之中。同时自由又是有界限的。它既要摆脱限制,又离不开限制。对自由的限制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它是自由得以体现和实现的保证;一种是消极的,它是自由的桎梏。不存在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绝对自由。在马克思看来,普鲁士“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3](P655),是一种对自由进行消极限制的规范。虽然在任何制度完善的国家中,自由都是受法律规范严格限制的,但真正的法律规范不但不会压制自由,反而体现自由,是自由实现的保证。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出版法就是这样的规范,是真正的法律。他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2](P176)因此,真正的法律规范应该具有“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的特征,即肯定人民的自由权利,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成为行为的普遍准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些特征使得真正的法律规范体现自由,并且这种在真正的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的自由是“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它不仅仅是个人的、个别的自由,而且是多数人合法权利得以保证的自由,是以固定的形式表达和表现出来的自由,是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的自由。因此可以说,真正的法律规范是以自由为基础的,是对自由的体现和确认。规范以自由为基础,但规范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确定自由的限度。因此“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4](P183)
正是规范与自由的这种关系,使得我们制定规范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反映和确认人的自由本性,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马克思提出,“英明的立法者预防罪行是为了避免被迫惩罚罪行,但是他预防的办法不是限制权利的范围,而是给权利以肯定的活动范围,这样来消除每一个权利要求中的否定方面。”[2](P254)因此,立法的合理目的仅仅在于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本性而“肯定权利的活动范围”,“消除每一个权利要求中的否定方面”,使人民具有“运用自己权利的现实可能性”。规范不论是规定何为合法,何为犯罪还是规定如何实施惩罚,都是对自由的承认。
那么判断已制定的规范合理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它是否体现了“肯定的自由”。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当它完全没有被采用的时候,例如在北美,它也必须存在,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农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2](P176)而“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的差别就是任性和自由的差别。”[2](P179)“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2](P175)因此他说:“对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5](P67)只有体现了“肯定的自由”规范才是合理的好的规范。这里肯定的自由指的其实就是客观规律和人民的普遍意志的统一,只有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反映公民的“普遍权利”而非少数者的“特权”的规范才是真正合理的。所以马克思指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2](P176)
二、规范思想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论述:“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6](P92)他们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P32)“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7](P38)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和法律观念和规范时,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规范的研究和分析上,而总是坚持寻找它们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力图从现实的社会道德关系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物出发来考察和分析法律现象和问题。因此在他们看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作用于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科学的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规范观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首先,规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6](P72)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规范的起源和产生过程,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P211)正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分工、分配和交换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基本因素的出现,规范的产生才有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规范产生、存在和得以发展的理由和根据只有回到经济生活条件之中才能真正找到。具体到法律和道德规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8](P291-292)“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P434)正是因为规范总是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保持一致,所以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之下的规范才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因此马克思才指出“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的良心”,因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8](P152)因此也只有从分析现实存在的“物质活动”、“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和阶级地位入手,我们才能找到法律和道德基本观念、原则和主要规范的真正来源。正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才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如何制订相应的规范来解决个人、集体、阶级、社会中的利益矛盾。我们的道德和法律观念、指导行为的道德和法律准则,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所以,社会经济结构才是规范的基础。
其次,规范会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历史的、具体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道德就是伴随人们的物质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恩格斯认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P433-434)马克思则指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1](P114)可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同样地行为或事件的善恶评价结果也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规范的发展往往与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随着一个统治阶级的腐败,往往出现社会伦理道德的严重失范和恶化,这种伦理道德的恶化又成为社会进一步腐败没落的助推器,从而促进社会阶级状况的变革,促进新的统治阶级以及与之利益相一致的新规范的诞生。因此,规范产生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规范本身也有存、废、立、改的历史发展过程,规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表现出其具体性。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然形式。”所以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工作是“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并意识到“这种对立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而自行消失”。[9](P104)很明显这是一种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唯物史观的课题内容。
三、规范思想的基本原则——客观性真理尺度与目的性价值尺度的统一
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规范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的规范思想遵循着一个必然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规范不是主观的、随意的产物,它有着客观的现实基础,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表述,规范的形成要符合客观性的真理尺度。马克思把规范的制订者与自然科学家相比较,在《论离婚法草案》的文章中,他明确指出:“立法者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2](P347)因此可以说“对于与人的行为相关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必然的把握,不仅是技术规范,也是社会规范得以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10](P22)规范的制订要以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为前提,规范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
但同时,规范是以人为目的而产生和制订的,只有它从“无意识”的规律状态发展为“有意识”的状态时,才真正具有了规范的形式和实质。因此马克思指出法律规范既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又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2](P176)这就是说,人的行为所遵循的规范不仅要反映客观世界的各种规律,而且还要充分展示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度自觉性。规范通过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同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什么应该去做,怎么做才是合法的、正确的;什么不应该去做,怎么做是非法的、错误的,从而使人们的行为既合乎客观规律,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既定的目标,实现社会生活一定阶段的历史使命,体现人的自由和价值。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真正的规范看成是对人的限制和束缚,如前所述,在他们看来,规范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自由的保障,因为规范是目的性尺度的体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自律的体现。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1](P96)“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5](P15)所以当规范是人本身自由意志的体现,人们自觉遵守规范时,规范的强制力就没有意义。只有当人们不愿意遵守规范或违反规范时,规范的强制力才会显现出来。就像马克思所比喻的:“作为落体定律,只要我违反它而打算在空中飞舞,那它就要我的命。”“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这种表现为国家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规律才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2](P176)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缩的。”[2](P176)可见,规范是由人制订的,只有当规范没有体现自然或社会规律,或没有反映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取向,或制订规范的人或制度是不合理的时候,规范才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规范不仅仅是客观性真理尺度的体现,还是目的性的价值尺度的体现。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不自由的现象作了解剖,指出人的不自由状况包括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分工或私有制、普遍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压抑、偶性对个性的压抑、城乡对立、阶级对个人的束缚、观念崇拜等,而共产主义就是要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和制订规范的权威的方式,使得规范建立在真正的人类的普遍意志之上,用自由自觉的活动代替自发强制的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由此而制订的规范就是自律的,而非他律,是自由实现的保证而不是障碍。
由于规范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具体到阶级社会中,规范的本质就体现为其阶级性,规范正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存在的体现。大部分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都是为维护阶级利益,调整阶级矛盾而确立起来的,规范是阶级利益的体现,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实现革命变革的时代,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统治阶级的更替也会通过打破原有规范体系,建立新的规范体系的方式变现出来。因此,这种阶级性也正是规范合目的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恩格斯认为,“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P435)因此,阶级利益关系决定着人们对个人、社会集体关系的理解和调整,也决定着阶级社会中规范的内容和形式。在原始社会,个人利益从属于氏族部落利益,这时的道德以风俗习惯的形式自发地维护氏族的整体利益。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中,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规范逐步被废除,维护劳苦大众利益的规范体系得以建立,这也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对立被消灭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公正合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人成为了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主人,成为真正自由、自主、自律的人,社会、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有了得以实现的条件,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使得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等规范的实现成为可能。可见,规范是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的体现,是以实现阶级利益为目的的。
同时也正是因为规范具有阶级性,会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并不存在永恒的、终极的、不变的规范,而只存在某一历史阶段人类共有的具有相对普适性的规范。不同的阶级只有处在几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利益上具有或多或少的相同之处,具有相对普适性的规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自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1](P434)因为“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1](P434-435)所以,规范总是具有相对的普适性。
规范具有阶级性,也并不代表只要体现了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的规范,其存在就是合理的。因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规范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合理的规范还需要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而不能成为个人任性的表现。“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2](P349)可见,一定历史阶段之下的具有相对普适性的规范是存在的,共同规范是共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共同利益的体现。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人民的事业始终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因而人民的意志最能和客观规律的要求相符合,只有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规范才能同时体现客观性真理尺度和合理的目的性价值尺度,是两者的真正统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 徐梦秋.规范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郭泮溪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Marx and Engels’ Normative Thoughts
LIU S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 China)
Marx and Engels’ ethics,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tain rich normative thoughts. We try to reinterpret Marx and Engel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from a normative perspective,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It not onl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on specific social norms. Scientif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rx and Engels’ normative thoughts. They think that norms not only reflect all kinds of law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but also fully display the high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humans in the social life. Norms are based on freedom, express and confirm freedom, but at the same time norms provide the limits of freedom. Norms reflect the unity of objective measure of truth and purposive measure of value.
norms;Marx;Engels;freedom
B17
A
1005-7110(2012)02-0095-05
2012-01-14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研究”(JBS09322)阶段性成果。
刘苏(1981-),女,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