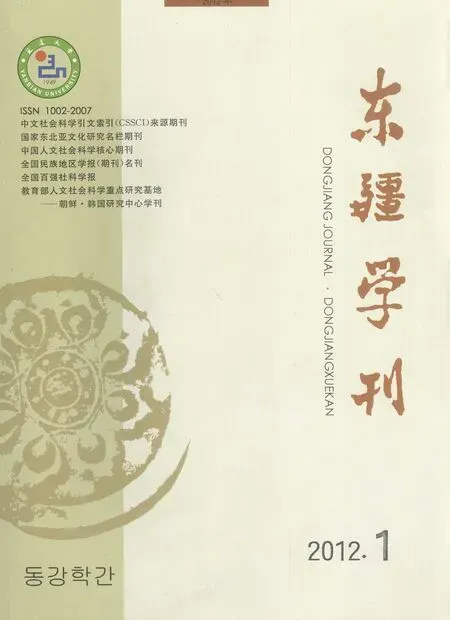犯罪客体之反思与新界
梅 锦
犯罪客体之反思与新界
梅 锦
刑法理论界所持有的对犯罪客体进行完善或废除的观点囿于通说理论,对犯罪客体进行了不合理的认定。犯罪客体要件是发动犯罪评价的前提,也是整个犯罪构成体系能否进行深入评价的首要条件,对于认定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具备。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工具,所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应当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借助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内在统一关系,犯罪客体的内涵应当界定为: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
犯罪客体;认定工具;完善论;犯罪对象
近年来,随着主张引入“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呼声增高,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再次成为刑法学界的热点。笔者认为,不论是“全盘引进”、“重新构建”还是“加以完善”,首先要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个正确的理解。而犯罪客体无疑是我国犯罪论体系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争议的焦点之一是犯罪客体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一、犯罪客体存废之争
(一)现有学说对犯罪客体的理解
对于犯罪客体,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1](55)对于犯罪客体之存废,学界有三种基本观点:“维持论”、“完善论”和“废止论”。
1.维持论
“维持论”的观点,由我国老一辈的刑法学者所提出并倡导,现行的法学教材也多采用此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中也处于通说的地位。“维持论”学者对犯罪客体的认识稍有差异,但本质上一致,即将犯罪客体界定为某种“社会关系”。如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2](106)另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关系。”[3](113)
主张“维持论”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犯罪客体概念是可行的、合理的。犯罪客体可以揭示犯罪的危害本质,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认定犯罪的性质,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犯罪客体影响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影响到量刑等等。反之,如果去掉犯罪客体,则会引起我国犯罪构成的功能缺陷,从而影响到定罪量刑,如“在盗窃罪中,‘占有说’与‘所有权说’的差别,直接影响对盗窃本人被司法机关扣押财物行为的定罪”。[4](112)
2.完善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犯罪客体存在不足,但不应当加以废除,而应在保留犯罪客体的前提下对其内涵加以重新界定。持完善论的学者较多,但各个学者之间的观点却多有不同,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社会利益说”、“法益说”、“社会关系+法益说”、“法律关系说”和“对象说”等。“社会利益说”认为,刑法不仅应当保护社会关系,同时也应当保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利益这个范畴与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密切的联系,故而“犯罪客体是犯罪主体的犯罪活动侵害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利益”[5](286)。“法益说”认为:“将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的上位概念,在具体犯罪构成及具体事案的分析中显得难得要领……‘法益’这一概念既有极强烈的针对性,也有非常宽泛的涵盖力,可兼容‘社会关系’、‘制度’、‘权利’、‘秩序’等犯罪所侵犯的不同内容;既能包容各种犯罪场合对客体之不同表述,又使分析思想始终盯注某种具体实在的生活现象。”[6]持“社会关系+法益说”的学者则认为:法益和社会关系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不应用一者取代另一者。刑法中的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等,尽管也受法律所保护,但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法益相等同。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利和利益存在。正确地认定刑法中的客体,应当同时采用社会关系和法益的概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侵犯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集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权益。这里讲的‘权益’,即法益。”[7](6)持“法律关系说”的学者不赞同其他学说将犯罪客体认定是一种事实,而认为犯罪客体是一个动态的评价机制,即“作为犯罪成立与否的评价标准,犯罪客体的内容应该是评价性的而不是对某一事实的表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犯罪客体是对行为的判断或评价,评价实质上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作为一种评价机制,犯罪客体应该有自己的表达范式,这个表达范式应当具有三个要素: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以及由此构成的评价本身。”[8](52)“对象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为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具体目标,主要是指具体的人、行为、物、精神财富以及权益等。”[9](58)我国刑法学界持“对象说”的学者较多。这类学者认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语言学中的客体与对象,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客体就是对象,对象就是客体……在中国内地,目前除了刑法理论之外,我国的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等实体法学理论,在术语运用上,都只有客体,没有对象。”[9](58)
3.废止论
“废止论”在我国刑法学界也是一种比较有力的学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一个政治产物,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且在刑法结构中没有其恰当的容身之处,故而应当废除犯罪客体。如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要件,它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对该要件的抨击由来已久……犯罪客体应从犯罪成立条件中去除,这是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是犯罪客体的去魅过程。”[10](101)杨兴培教授认为:“犯罪客体本身是政治需要而非法律的产物。刑法作为一种规范表现不应有犯罪客体存在的空间,刑法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可以体现在刑事立法的原则性规定中,一旦刑事立法确定后,犯罪客体不应再具有独立的评价功能。”[11](119)张明楷教授则明确提出犯罪客体不属于构成要件,因为“犯罪客体实际上是保护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它属于犯罪概念的内容。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法益,但要确定某种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了什么法益,并不是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犯罪客体与其他三个构成要件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去除犯罪客体不会给认定犯罪带来困难。外国刑法将法益视为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没有任何人认为刑法保护的法益是构成要件”[12](134)。
(二)对现有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不论是“维持论”、“完善论”还是“废止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国现有的刑法框架中,都存有一定的不足。对此,笔者对上述观点试作简要的评析。
“维持论”肯定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之一在体系上的地位和认定犯罪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该观点对犯罪客体内涵的认定导致的问题更多,概括而言,总要包括以下几点缺陷:首先,犯罪客体概念政治色彩浓厚。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引自于前苏联,而前苏联的刑法学者们之所以想创造这一全新的刑法理论现象,与苏联在特定时期刑事法律政治化的倾向是不可分的,“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得以建立之初,同样年轻的苏维埃刑法学者们真诚地认为,无产阶级的法律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形式方面都应当是崭新的。再加上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最初颁布的一大批法令中,缺少对犯罪行为精确要件的规定,有时没有指出具体的法定刑,这就使得某些法学家产生误解了,以为这恰恰是无产阶级刑法的特点。”[13](14)正因为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研究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成分,使得犯罪客体成了没有独立品格、纯粹是政治在刑法理论上的畸形品。其次,现行的犯罪客体概念与其自身的价值定位相矛盾。在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之一,它应当与其他三个要件一道共同发挥着认定犯罪成立与否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功能,即其价值定位是犯罪评价的工具。作为评价工具,其自身就应当是清晰的、易于掌握的。但是,通说的犯罪客体却被归结为某种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人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14](1578)这种关系又具体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内容抽象而又空泛的概念,由于它并不直接表现在外,既不可触及又不能加以目视,所以对其认知较为困难。实际上,它只是对出现的某种行为从社会整体意义上进行的分析与评价,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批评的,我国现行的“犯罪客体的价值在于说明犯罪行为为什么要被规定为犯罪,而不在于说明犯罪是如何构成”[15](179)。再者,犯罪客体的涵义违背了认知规律。在认知过程中,人们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过程。关于犯罪的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所以作为判断工具的犯罪构成各要件的判断就应当是事实判断,否则犯罪的认定就无法进行。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犯罪客体作为“某种社会关系”却是一种价值判断,且该“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否受到侵犯,只有等该行为性质最终确定后才能知晓。因而,不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的排列顺序如何,其违背人类的认知规律是无疑的。最后,对某些学者提出的对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采用“占有说”还是“所有权说”,将直接影响对盗窃罪的认定。其实,对盗窃罪究竟应采用何种学说才更合理,只能从刑法条文中去加以理解,这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而与犯罪客体没有直接的联系。
对于“取代论”而言,其注意到了用“社会关系”来界定犯罪客体所导致的犯罪客体不易把握、飘渺不定以及违背认知规律的缺陷,因此主张在保留犯罪客体的前提下,对犯罪客体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取代论”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代论”的诸多观点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对于倡导“社会利益说”、“法益说”、“社会关系+法益说”的学者而言,其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关系的概念较为狭隘,不能完全涵盖刑法所保护的范围,同时社会关系过于泛化,不易把握。实际上,这是对“社会关系”与“利益”两个概念的误解。刑法最终是对利益的保护,因此,用“社会利益”或“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来界定犯罪客体在范围上是可以的。但是无论何种利益,归结到底都体现为一种关系,利益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因此,用“社会关系说”来界定犯罪客体,其缺陷不在于其不能有效涵盖刑法所保护的范围,而主要在于其过于泛化。“社会利益说”、“法益说”在批评“社会关系说”的同时,自身又同样陷入过于泛化的尴尬境地。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从论证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寻求政治正确性。可以说,除了概念的变动之外,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10](100)“社会关系+法益说”认为,单独用“社会关系”或“法益”都不能对犯罪客体加以有效涵盖。这种观点除了对“社会关系”和“法益”的认定有误之外,同样面临着通说观点所存在的过于宽泛的缺陷。相对于社会关系与利益而言,法律关系的内涵显然更加规范与清晰,但是正如“法律关系说”的倡导者所认为的:“犯罪客体是对行为的判断或评价,评价实质上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8](52)故而,在“法律关系说”中,犯罪客体的判断仍然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其结果同样不是直观可见的,尽管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评价过程。在任何犯罪中,犯罪所具体指向的对象总是具体的,因此用犯罪对象来代替社会关系的“对象说”在事实认定方面无疑是可行的,但是该观点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一方面,该种观点认为由于在其他法律中,客体与对象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在刑法中也同样适用。但刑法与其他法律不同之处在于:刑法调整的是个人与整体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的论证)。在某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中,犯罪指向的对象是特定的人或物,但刑法惩罚的目的不在于此行为对该人或物造成了侵害,而是因该行为对人或物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制度造成了侵害。可见,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并不属于一个层次,也不可相互替代。另一方面,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合理的。每一个犯罪的成立,都表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制度受到侵害,亦即客体要件应当具备。如果用“对象说”来界定犯罪客体的话,则每一个犯罪对象也要遭到损害。但现实情况是,在许多犯罪行为发生时,犯罪对象并不必然受到损害,有时甚至犯罪对象的价值会增加。如在某盗窃案中,甲窃得乙家中的名画一幅,将其装裱后珍藏。此时用“对象说”的观点就不好解释。因此,无论是从刑法理论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对象说”都是有缺陷的。
对于“废止论”而言,持该观点的学者看到了犯罪客体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不能发挥应有功能的缺陷,故而主张将犯罪客体加以废除。这种观点确实指出了问题之所在,但是如果将犯罪客体加以废除,则产生的问题会更大。一方面,缺少了犯罪客体则缺少了实施刑罚的根据。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成立理论是一致的,没有了犯罪所指向的具体目标,就没有理由再进行后面三个构成要件的评价。犯罪客体对于评价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构成多少犯罪都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另一方面,历史的教训也表明,犯罪客体是不可缺少的要件。犯罪客体的存在——即某种具体侵害事实的出现,是进行构成要件评价的前提,否则必将导致司法的恣意和人权的被侵犯,而这已经为现实所证明。历史上,民族英雄岳飞父子就是被奸臣以“莫须有”的罪名所陷害;前几年震惊全国的湖北“佘祥林”案以及刚刚出现的河南“赵作海”案等都清晰地表明缺少了犯罪客体,司法权就会被滥用,人权就很容易受到侵犯。所以,对“废止论”的观点,笔者实不能赞同。
综上而言,笔者认为“维持论”的观点过于陈旧,它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使其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构成要件之一应有的功能。而“废止论”的观点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实践中侵犯人权的可能。所以“维持论”和“废止论”的观点都不可取,笔者在整体方向上赞同“完善论”。鉴于现有“完善论”观点的瑕疵,应在保留犯罪客体的同时对其内涵作出新的界定。
二、犯罪客体内涵之界定
根据唯物辩证法可知,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象中包含着本质,而本质则通过现象体现出来。事物的本质属于不可以直接感知的一面,而现象则属于可以直接感知的一面。具体到犯罪,“刑法的调整对象不像民法或婚姻法那样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或者像行政法那样仅是公民与国家的某种职能之间的关系,而是公民个人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16](119)。因为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公民个人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以犯罪侵犯的就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这种侵害,由犯罪人通过作用于一定的人或物而体现,被作用的人或物就是犯罪对象。被犯罪行为作用之后的犯罪对象,尽管其本身可能不会有所改变,但其所处的状态却一定发生变化。犯罪对象状态的变化就体现了社会整体法律秩序的被侵犯,此时已形成犯罪客体。可见,犯罪客体通过犯罪对象来体现。这种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哲学中现象与本质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因此,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客体非犯罪对象本身,而是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亦即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一定人或物的存在状态。只有以此来认定犯罪客体,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使犯罪认定得以顺利进行。
根据唯物辩证法可知,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物加以认知的过程。认定的最终结果既是一个价值判断,又是深层次的、抽象的、理性的判断。更由于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性措施,其以剥夺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为手段,因此对其适用更应加以谨慎对待,而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在意大利,“当一种制裁或措施直接或潜在地涉及到剥夺人身自由时,立法者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只有在最适当,即‘完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者才有权规定刑事制裁。因为,宪法中有关‘刑罚’、‘刑事责任’以及有关保护人身自由的规定,不论对立法时规定刑罚,或是对实践中适用刑罚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7](6)。所以为了谨慎起见,对犯罪的判断就需要以犯罪构成作为辅助中介。从符合认知规律的角度来看,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就应当是表层的、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在任何一个犯罪中,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人或物的状态都是清晰的、容易判断的,因而将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行为作用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就满足了构成要件作为判断工具所应当具备的简洁、可操作的要求,符合事物的认知规律。
其次,与犯罪对象相统一,有助于对犯罪对象的正确认识。
在现行的刑法理论中,有观点认为:“有些犯罪没有犯罪对象”、“犯罪对象不是每个犯罪的必备要件”[1](62)。其实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在上文中所阐述的:犯罪是对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的侵犯。而社会的法律秩序是抽象的,在现实中必然要通过犯罪对象来体现。犯罪对象状态的变化表明了社会的法律秩序受到了侵犯,也显示了犯罪客体要件的具备。缺少了犯罪对象,就不可能具有犯罪对象状态的改变,但是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整体法律秩序又如何得到体现呢?不少学者认为,“没有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的人或物,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犯罪都会对一定的人和物发生影响,都要以一定的人或物的一定特征为自己的对象。”[16](254)“脱逃罪”和“偷越国边境罪”常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没有犯罪对象的典型例证,笔者现试对此二罪的犯罪对象作简要分析。所谓“脱逃”,是指处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犯罪分子用非法手段摆脱司法机关控制的行为,其结果是处于司法机关控制的人变成不受司法机关控制的人,亦即犯罪分子的人身状态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体现了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侵害,因此,“脱逃罪”的犯罪对象正是犯罪分子自身。同样的道理,在“偷越国边境罪”中,犯罪分子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就使其从处于本国的状态变成处于他国(或地区)的状态,从而对国家的国边境管理制度造成了侵害,故而该罪的犯罪对象也是犯罪分子本身。
再者,有利于正确适用刑法条文,发挥犯罪构成的应有作用。
采用通说对犯罪客体的理解,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犯罪客体都存在争议。如对于受贿罪而言,其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廉洁义务、国家的廉洁制度,还是财产所有权?理论界对此颇有分歧。而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起着决定犯罪成立与否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作用。如此一来,由于受贿罪的客体要件存在分歧,在具体认定犯罪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实际上,如果认识到犯罪客体就是“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财物的状态从他人所有转变为该国家工作人员所有,且这种状态的改变是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所造成的,该国家工作人员就构成受贿罪,而根本不需要去认定到底侵犯了何种社会关系。以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作为认定犯罪客体的标准,并将其运用到受贿罪或者其他任何犯罪中,犯罪的认定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操作,分歧也会减少,而这与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否则,犯罪客体的抽象性将导致犯罪认定的不明确性,刑法的确定性就会受到破坏。正如有学者论及传统理论在认定贪污罪的犯罪客体时所批评的:“原刑法中贪污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人认为贪污罪的同类客体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当新刑法将贪污罪与贿赂罪合并组成独立的一类犯罪后,很多人又开始认为贪污罪的同类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今天的贪污罪依然是昨天贪污罪的继续,只是刑法在规定的排列上稍作一下变化,在犯罪客体上就立即出现法变亦变的情况,丝毫不能体现自己的独立品格。”[18](11)
最后,有利于犯罪论体系的完整,发挥保障人权的功能。
在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尽管对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观方面三个构成要件的内涵存有一定的争议,但此三个要件存在的合理性则得到普遍认同。保留犯罪客体这一要件,使犯罪客体对应于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对应于犯罪主观方面,在体系上具有合理性和完整性,使传统“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所具有的对称性美感得以保留。同时,将犯罪客体的内涵界定为“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使其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可操作的层面,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保障人权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进行犯罪侦查的前提是:存在犯罪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而作为侦查犯罪前提的犯罪事实,必然要通过一定人或物状态的变化体现出来,如一具尸体的出现或者某人的财物丢失。否则,仅仅具有某人的口述就不能进入到犯罪的侦查环节,也不应当进行犯罪的认定工作。在此,可以发现,犯罪客体的成立是犯罪构成中其他三个要件,也是具体犯罪认定的必备前提。否则,在犯罪客体尚未具备的前提下,仅仅凭借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和一些伪造的物证就可以定罪的现象就不会杜绝,司法中刑讯逼供的现象也不会杜绝,类似于湖北“佘祥林案”的悲剧就仍然会发生。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之一,同时赋予其新的内涵之后,新的犯罪构成将不光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同时也将成为全体公民的大宪章。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
[3]马克昌主编:《刑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4]薛瑞麟:《犯罪客体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5]何秉松:《刑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6]冯亚东:《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性分析》,《现代法学》,2009年第四期。
[7]江礼华:《再论犯罪客体的概念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二期。
[8]童伟华:《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9]王仲兴:《反思与重构:犯罪客体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二期。
[10]陈兴良:《犯罪客体的去魅——一个学术史的考察》,《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十二期。
[11]杨兴培:《“犯罪客体”非法治成分批评》,《政法论坛》,2009年第九期。
[12]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13][苏]皮昂特科夫斯基,等:《苏联刑法科学史》,曹子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年。
[14]《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15]朱建华:《论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三期。
[16]陈忠林:《刑法散得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17][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18]杨兴培:《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缺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一期。
D915.12
A
1002-2007(2012)01-0094-06
2011-09-1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CDJXS11081133。
梅锦,男,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理论研究。(重庆400045)
[责任编辑 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