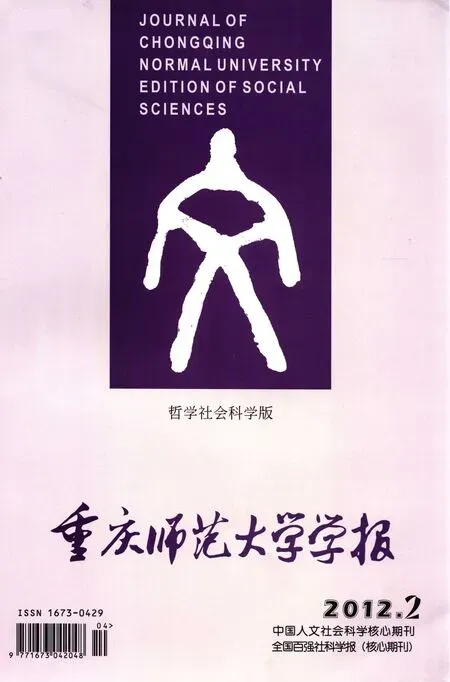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高蔚 徐径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
——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高蔚 徐径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美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白话”新诗;审美意识;文化焦虑
在语言学意义上,“白话”只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而在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的生命链条上,“白话”早已成为汉语诗歌写作的一个理论命题,它拥有自己的话语逻辑和美学旨趣。同时,在新诗自我建设中生成的诸多审美意识里,“白话”与时代、政治、文化的关系,较之与艺术内部诸多因素的关系,也比其它任何一种美学思虑都更为密切。在这个意义上,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美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完全合乎“范式”理论对“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的相关作用、形态、价值进行考察的科学假设。
毫无疑问,早期白话新诗写作的理论预期和艺术实践,曾一度对中国新诗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美学认知,具有示范工具的意义。尽管这其中“言文合一”的写作构想,将情感重心投注在了言说内容和范围上,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模式,对新文化建设的考虑也远远多于对新诗艺术形式的考虑,但“白话”新诗写作的话语方式,由于是历史情感与历史内容的见证,无论它始终伴生的“摆脱”文化母语的焦虑,还是美学旨趣中的文化再造意绪,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新诗范式研究,都富有多种考察意义。
一、“言文合一”写作构想里的“文化母语”转变焦虑
“白话”新诗写作的话语方式,由于摒除“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尚典雅”的传统桎梏,“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1](215),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偏重语言和艺术形式的考究。但事实上,在汉语诗歌艺术渐变的历史事实里,胡适等人热衷提倡“白话”和坚持淘汰“文言”的关节点,在于诗歌能否恰当充分地表达现实欲求。
在近代文化先贤的切身感受中,汉语诗歌的拟古之风已令人不堪忍受,才有黄遵宪的严厉批评:“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2](486)这些所谓的诗歌,“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重形式而去精神”,“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其中实无物可言”[3](117-118)。胡适总结当时的现状说:“尝谓今日文学已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龛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4](15)
然而,这些诗坛遗风无论在黄遵宪眼里,还是对龚自珍、魏源来说,都绝不仅仅是艺术问题,而是中国文化思想界严重缺乏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表现。龚自珍较早突破书斋束缚,将“侠骨幽情箫与剑”的诗歌风格引入个体写作,基本实现了汰除复古拟古的时病,但他“本无一字是吾师”的独创精神与“夫诗必有原焉”[5](553)艺术思想之间的矛盾,还是透露了文化母语转变中的内心龃龉。其实,魏源不惜冒“复古”之嫌,力图恢复和重建“诗以言志”的儒家理想,重构“志”与“道”的关系,也是一种文化焦虑的表征。
在掀起变革第一次较大波澜的“诗界革命”里,梁启超的一系列宣言(1889年):“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歌伦布玛赛郎然后可”、“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歌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6](188)等内容,其核心意旨事实上也都并非汉语诗歌的写作形式本身。尽管梁启超对“诗界革命”抱有诸多期许,在他的思想观念中,汉诗已走到生死攸关的渡口,必有起改革之刀,方才有生存之途,但“求新又恋旧”的心理惯性让他的“革命”主张更多停留在一种改变“文化母语”的审美意识启蒙上,他始终未能超越的格律乃“诗之本能”的局限,其实意味着他的“诗界革命”在更为深层的潜意识里,倾向于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而非诗歌艺术中“言”与“文”关系所纠结的言说方式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黄遵宪的锐气令人注目却也不无遗憾。黄遵宪早在1868年就认识到“言”与“文”脱离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带来的严重滞碍,他的“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7](815),甚至触及“言”、“文”不一致所危及的文学生态与社会生态问题。然而,尽管他与龚、魏革新理念有着本质差别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写作口号,因意欲在古典诗歌的传统体式中用俗语作诗,而被胡适誉为“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8](98)。但这种用“流俗语”等生活常态用语冲淡旧体诗中习焉不察的一切陈腐套路的诗歌变革理念,深化的依然是将诗歌内容从故纸堆拉回现实世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往,其具体的艺术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外来词语和底层俗语的参与,固然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诗歌的言语方式,也对“言”、“文”脱钩的现状略有改变,但已盖不如古的现代人群思想和情感状态,并不能在依然完好的格律体式中得到充分表达,这也曾一度让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实绩感到惶惑与迷茫。
在此基础上,胡适认定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钞袭;其完全钞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9](118)则更具开拓性。那么,何以创造出“自然的真诗”?胡适的想法,不仅要纳白话入“诗”,还要打破平仄格律,“言文合一”[10](13),即“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1](69)。显然,胡适的目标是不再苑囿于对传统形式的小修小补。在他眼里,“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12](133)胡适虽从语言形式入手,但目标却是“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10](13)。毫无疑问,这绝不仅仅是汉语诗歌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大胆叛离。
事实上,在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的生成史上,传统诗歌表达方式暴露的弊端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朱经农致胡适的信所说:“文言”和“白话”,“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字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兼收而不偏废”,“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13](33)“言文合一”的“白话”新诗虽代表了汉语诗歌一种崭新的表达形式,但在“五四”新文化历史语境里,却有着多重内容的文化母语转变的焦虑与裂痕。然而,无论这转变的焦虑与裂痕里粘合了多少重塑民族精神的文化实践,汉语诗歌所意欲尝试的新的抒写构想,毕竟促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审美意识的生成。
二、“作诗如作文”美学旨趣的文化再造意绪
“作诗如作文”在胡适“诗国革命”的具体实施方案里,实际上是欲彻底改变汉语诗歌的文言言说方式和思维模式。胡适对这种艺术理论的阐发是渐进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胡适“革命”理念表述的转变和演进,二是胡适“革命”思想理论根据的深化。
关于胡适“革命”理念表述的转变和演进,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摆在我们面前,即被胡适作为重要改良纲领提出的“八事”理论,在多次被表达时,其所关涉的指向不尽一致。在1916年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胡适最早提出的“八事”是:“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律)。四曰,不必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革命也。”继而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引用的“八事”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必俗字俗语。”到了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上,“八事”的内容又变为:“一曰,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曰,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曰,不用典。须讲求文法。四曰,不用套语烂调。五曰,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曰,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曰,不摹仿古人。八曰,不必俗字俗语。”
这里,胡适虽一再强调了新的汉语诗歌的重要尺度:废律、不用典、讲求文法、口语入诗等问题,但这三次表达之间的明显变化在于,在1916年首次提出的“八事”中,“须言之有物”排在最后一个;1917年的“八事”,“须言之有物”升为首要一条;到了1918年,“须言之有物”的首要地位被再次确定。表面上,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渐渐认识到文学变革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物”,因为在胡适看来,“文学的美感”在于“说得越具体越好,说得越抽象越不好”[14](104),那些空洞的模仿古人之作完全是“以文胜质”。但就深层而言,胡适“言之有物”的着眼点是在诗的言说方式中,摒弃那些“只认风花雪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3](118)堆砌起来的内容,让诗回到自我心性的抒写上来,而并不是如何使用韵律、典故、文法、口语等内容本身。这也说明胡适关注的基点是民族文化转型的现实语境下,文化母语的割裂与重造问题。胡适主张用“白话”的理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做“白话”新诗的首要目的同样并不在“通俗,使妇女童子都能了解”,而是“要使中国有新文学”,“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15](86)
就“革命”思想理论根据的深化而言,胡适受杜威“实证主义”思想影响颇重,习染自由主义理念也日久,早在美国留学时期,他就有“革命”思想的阐发和论述。1917年,他回到本土卷入“新文化运动”的激烈论辩时,“实证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理念都发挥了作用。他极尽引经据典之能事,爬梳古典文学嬗变的例子,构建出一套“白话文学演变史”逻辑,来验证“白话”是否能成为诗的骨肉和文学改良的标志。他认为,“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律,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16](8)所以,白话入诗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得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种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3](127)。在这些思考里,我们依然发现,胡适当时的目光聚焦,更多偏向文化一隅,对艺术精神和价值的审视排在其后。其实,胡适内心始终纠结一个问题,即诗体的“解放”并不等同于“改良”,“改良”的着眼点在艺术自身,这是需要渐变的,而“解放”的关注重心在文化,文化的转型或改造则强调裂变。
因此,在胡适这里,诗体“解放”所要求的绝不仅仅是抛却格律这么单一。由于格律诗体和“缠足”、“八股”、“君主专制体制”[17](82)一样,散发着令现代人厌恶的封建气味,被视为“死语言”的文言和在梁启超看来还是“诗之本能”的平仄格律被要求一并废除,自然透露的是文化再造之用心。事实上可以这样理解:与其说胡适准备大刀阔斧地进行诗歌改革,不如说这是他社会变革的“文化想象”,因为,他并不确定“白话”能否在诗中终结硕果,直到1922年他还对此存疑:“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18](13)然而,即便如此,也无碍胡适以“作诗如作文”的汉语诗歌“策略”,觊觎他的文化革新,因为他奉信“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他也确实为此准备了一系列自以为足以支撑的“求证”步骤。应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颠覆性话语系统里,胡适的这种想象也颇为合理。正如我们并不确定民主制度能否贯彻中华大地,却并不妨碍我们去推动和破除各种千年沿袭封建桎梏的道理一样。
时代推动了胡适艺术“革命”理想的大胆施展,但“传统”并非那么容易被这种以“作诗如作文”展开的诗歌“策略”所动摇。胡适“革命”理念的“合理性”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诘难。任永书就极为担心“作诗如作文”的后果,他说:“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19](11)这种诘难代表了大多数反对者的意见。胡先骕甚至认为胡适“所主张之摒弃一切法度,视之为枷锁自由之枷锁镣铐,则为盲人说烛矣”[20](311)。显然,他们并未看透,胡适的“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培养新的“陶谢李杜”,而是期待一种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是从汉语诗歌出发来打造新“文化母语”的战略。
应该说,胡适“革命”理念表述的转变和演进与“革命”思想理论根据的深化,是“逼上梁山”的产物,是在反对者的相互博弈中渐变的产物。“学衡”诸学者以及一切反对者的否定,终究未能阻止它在激进的“革命风暴”裹挟中,成就一种刷新“文化母语”的可能。然而它又提醒我们,作为胡适“革命”话语逻辑起点的“作诗如作文”,其美学旨趣所潜藏的对传承千年的“文化母语”的反叛和背离,不仅已成为一种历史知识,它所关涉的对文学语言系统和思维模式的重构,对民族精神形态的重塑,均为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超越艺术形式本身的尝试经验。
其实,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是极为丰富的,一篇小文不可能言尽它作为“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新诗审美意识生成史上所担当的所有角色。这里仅仅梳理了它众多价值形态之一种,其艺术内部诸问题,当另有专章予以探讨。
[1] 康白情.新诗之我见[A].康白情新诗全编[Z].花城出版社,1990.
[2] 黄遵宪.杂感[A].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Z].上海书店,1991.
[3] 胡适.尝试集·自序[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 胡适.致陈独秀[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 龚自珍.送徐铁孙序[A].龚自珍全集[M].上海书店,1994.
[6]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饮冰室合集第七卷·专集之二十二[M].中华书局,1989.
[7] 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论争集上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胡适论争集上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C].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2] 胡适.谈新诗[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3] 朱经农.致胡适的信[A].胡适论争集上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 胡适.答张效敏并追答李李安镗[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5]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6]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53.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0.
[17] 胡适.答任叔永[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8] 胡适.答任叔永书[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9] 胡适.与任叔永书[A].胡适文集第三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0] 胡先骕.评尝试集[A].胡适论争集上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One Kind of Speech of Breaking Away From Cultural Mother Tongue—on New Vernacular Poems
Gao Wei Xu Jing
(College of Art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541004,China)
As the aesthetic category,“vernacular”was conducted into the historical visual threshold of its generating and developing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the Chinese new poems.And its“signifier”embodying in both aspects,“spoken-written in one”as an idea of writing early poems in“vernacular”,it is not only a change of words,but also a running-away from logical system of our mother tongue.Based on it,a socalled“project”of writing was produced called“like poem,like article”.Obviously,its aesthetic interests didn’t appeared,as the logical starting of Hu Shi’s“revolutionary”words,focusing on the arts’forms of poem itself,but on the whole transforming of the cultural patterns.On the other hand,for the way of words formed by“vernacular”in the Chinese new poems,it was very rich abounding in its“significant”space itself.There were kinds of valued patterns of arts making up of its main content inside.Both of these two aspects have provided us with the arts’experienc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poem writing in the coming every period of history.And here are some views on the first aspect.
new vernacular poems;aesthetic consciousness;anxiety of culture
206.6
A
1673-0429(2012)02-0096-05
2011-12-30
高蔚(1963—),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徐径(1988—),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西教育厅2010年度科研项目“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12MS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