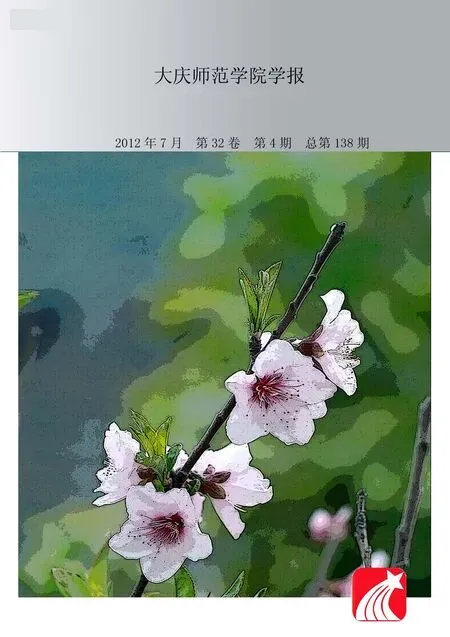论甘阳对列奥·施特劳斯古今之争问题的三种表述
余宜斌
(华南师范大学 南海校区,广东 佛山 528225)
古今之争问题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围绕着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研究,因而成为他的代表作。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前言部分,甘阳写了一篇长达八十余页的文章,题目是《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该文对施特劳斯的生平、基本思想以及施特劳斯学派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然而,在对施特劳斯最关切的古今之争问题的解读过程中,甘阳这篇文章却先后给出三种不同的表述,其中第一种与另外两种几乎完全对立。本文的目标就是对这三种不同的表述加以分析,弄清甘阳的表述是如何严重背离了施特劳斯的基本思想的,以此进一步澄清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问题。
一、第一种表述
甘阳的第一个表述是这样的: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是否存在着任何独立于一切流变的好坏标准、对错标准、善恶标准、是非标准、正义与否的标准”,[1]10是不是“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都是随 ‘历史’而变化从而反复无常?”[1]10在这个问题上,古代政治哲人与现代政治哲人的回答是完全对立的。古人认为存在,现代人认为不存在。
甘阳教授的这个表述对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问题的把握是准确无误的。在列奥·施特劳斯的著作当中,古今之争问题就是古典政治哲人与现代政治哲人之间的争论的焦点问题,这个焦点问题就是:我们“能否获得有关什么才内在地就是善或者真正的知识”[2]5。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回答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政体,判断好的生活与好的政体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标准等问题。对于上述几个问题, 古代政治哲人与现代政治哲人的答案完全相反。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哲人有意识地背离古典政治哲人,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3]32。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西方人乃至西方学术界不相信有什么客观的善恶标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现代学术界流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以历史名义来否定存在永恒不变的思想观念,否认存在永恒不变的善恶标准。历史主义的最基本的主张就是所有的思想观念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历史性,因而对于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2]13历史主义的这个主张的基本依据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善恶标准,一切有关善恶的标准都是随着历史而变、反复无常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善恶标准。这种历史观念导致人类不再相信任何永恒的善恶是非标准。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学术界中流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提出并倡导的价值中立,它主张科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应当遵循客观事实,而撇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立场,回避自己的价值。施特劳斯认为,“韦伯坚持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道德中立性的真实原因,并不是他相信‘是’与‘应该’之间的根本对立,而是他坚信对于‘应该’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知识”[2]43,在施特劳斯看来,韦伯的这种完全否认对于善恶这样的观念是存在什么真正的知识或真理的思想导致的结果与历史主义是一样的,即虚无主义。“韦伯的命题必定会导致虚无主义或者是这样的观点:每一种取舍,无论其如何地邪恶、卑下或无辜,都会在理性的祭坛前被判决为与任何别的取舍一样合理。”[2]44
正是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现代西方学术界放弃了对好坏标准、对错标准、善恶标准、是非标准、正义与否的标准的捍卫与信奉。甘阳指出,施特劳斯站在古代政治哲学的立场上展开对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目的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同时是对现代政治哲学与现代学术界的批判,认为现代学术思想抛弃善恶标准是误入歧途。施特劳斯所创立的政治哲学学派也因此几乎与所有的当代西方学术界格格不入,成为最孤立、最边缘、最受排斥的学派。
二、第二种表述
甘阳关于古今之争问题的第二种表述:“如果说罗尔斯现在的中心论点是‘权利优先于善’,那么施特劳斯的基本立场正是‘善优先于权利’,更确切地说,施特劳斯所谓‘ 古今之争’的问题之一就是检讨从古典政治哲学的‘善先于权利’如何转变到近代西方霍布斯以来‘权利优先于善’的问题。”[1]47
甘阳对于上面的表述做了进一步阐释。罗尔斯所谓的‘权利优先于善’,实际上就是主张所有宗教、文化的善观念都必须得到公平的对待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必须把任何宗教道德的‘好’的标准打入私人领域,最高的善或至善就是把所有的善的标准都放到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1]50。自由主义说这是最高的善、最高的道德,因为它能公平对待所有的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理性的人都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主体有能力摆脱任何特定的善观念的支配,亦即一个自由人的标志首先就在于他不受任何特定族群、宗教的善观念的支配,所以是自由的。”[1]51甘阳认为, “康德、罗尔斯那样把所有人都提升到‘绝对自由’和状态,这等于把所有人都连根拔起”[1]56,即必须以虚无主义才能奠定政治社会根基,结果只可能是彻底动摇政治社会的根基。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最大危险所在。所以,甘阳认为,施特劳斯的主张与罗尔斯相反,是“善优先于权利” ,即主张回到政治社会当中去,各种宗教与文化都坚持捍卫各自的善观念。
甘阳认为施特劳斯的主张回到政治社会当中去,完全背离了施特劳斯的观点。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等著述当中,施特劳斯绝不是主张各种宗教与文化都坚持捍卫各自的善观念,这正是施特劳斯所要反对的。施特劳斯把这种主张各种宗教与文化都坚持捍卫各自的善观念的思想叫作习俗主义。所谓习俗主义,就是主张“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正义观念”[2]11。习俗主义的错误在于,从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正义观念、善观念这个前提出发,得出所谓永恒不变的为所有人所能接受的正确的正义观念或善观念是不存在的结论。习俗主义的这个主张是与古典政治哲学的主张相对立的。古典政治哲学认为,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正义观念、善观念,并不能说明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正义观念或善观念。“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正义观念或正义原则。犹如人们变化万端的宇宙观念并不就证明宇宙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对宇宙有真实的描述,或者人们永远也不能达到关于宇宙的真确的最终的知识一样,人们变化不定的正义观也并不就证明,不存在自然权利,或者自然权利是不可知的。”[2]98并且,形形色色的善观念恰恰表明存在着一种唯一真正的善观念:“形形色色为数众多的对于正确和错误的观念的知识,并非与自然权利的观念毫不相容,这种知识乃是产生自然权利(正确)观念的根本前提”[2]11,正是各种关于权利(正确)的观念的知识,激发了人们去寻求自然权利(正确)。古典政治哲人的工作正是从这些多种多样的正义观念或善观念出发去寻求真正的正义或善。
由此可知,施特劳斯站在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上,主张从形形色色的善观念出发,探求一种真正的善观念,而不是如甘阳所说的回到政治社会中,停留在形形色色的善观念上。在形形色色的善观念上止步不前的是习俗主义,这正是施特劳斯所要超越的。在古典政治哲学当中,形形色色的善观念都是关于善的意见,而不是关于善的知识,古典政治哲人的使命就是从诸多的关于善的意见上升到善的知识的过程。“哲学就在于由意见上升到知识或真理,就在于可以说是由意见指引着的一场升华。当苏格拉底把哲学称作‘辩证法’时,他心目中主要想到的就是这一升华。”[2]125而甘阳的第二个表述却错误地将施特劳斯的立场描述为习俗主义者的立场,而不是古典政治哲人的立场。
进一步分析表明,甘阳也误解了罗尔斯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对立。罗尔斯等现代政治哲人从形形色色的关于善的意见出发,所要寻求的是对这诸多的善的宽容,即诸种善的意见都必须得到公平的对待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这里所说的善是较低层次的,是形形色色的关于善的意见,而不是较高层次的关于善的知识。罗尔斯的中心论点是从关于善的意见出发得出一种权利理论,而不是去寻求一种作为知识的善,这在施特劳斯看来其结果必然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第一章当中,施特劳斯就指出,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基本主张主要是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宽容每一种善观念,“宽宏大量的自由派们……似乎认定,既然我们无从获得有关什么才内在地就是善的或对的真正的知识,这就使得我们被迫容忍各种关于善或者对的意见,把一切的偏好和一切的‘文明’都视作是旗鼓相当。唯有漫无限制的宽容才是与理性相吻合的”[2]5,而漫无节制的宽容的后果就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与罗尔斯不同的是,施特劳斯的中心论点是从关于善的意见出发得出一种善的知识。施特劳斯的这个论点可以概括为:作为知识的善优先于作为意见的善,而不是甘阳所说的“善优先于权利”。罗尔斯与施特劳斯之间确实是对立的,罗尔斯从关于善的意见出发得出一种权利理论,而施特劳斯是从关于善的意见出发得出一种善的知识。罗尔斯放弃了对善的知识的追求,不相信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善恶标准,而这正是施特劳斯所批判的现代政治哲人的共同信仰。
三、第三种表述
甘阳关于古今之争问题的第三个表述是:“在施特劳斯看来,所谓古今之争的全部问题实际即在于现代‘哲人’拒绝古代政治哲人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这一深刻认识,亦即现代‘哲人们’日益坚定地相信,可以用哲学的‘知识’取代政治社会的‘意见’。”[1]63-64甘阳认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具有癫狂性,这是因为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必须要求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必须要求不受任何道德习俗所制约……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1]61。并且, “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任何一种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社会‘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1] 62。 所以,“哲学作为纯粹的知性活动是非道德、非宗教和尼采所谓超载善与恶的,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则离不开善恶标准即道德,这种道德在西方又以宗教为保证,因此哲学与政治(道德、宗教)从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1]63。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主张就是要重新把人从所谓的真理与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与偏见的世界,引回到现实的政治世界。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试图首先从第二洞穴(科学化的以‘真人’为预设的普世大同世界)返回第一洞穴(前科学的以‘常人’为预设的特殊政治世界)。施特劳斯的工作就是“把人从这所谓的真理与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1]66。
这个表述与施特劳斯的基本立场的背离最为明显。在施特劳斯那里,相信可以用哲学的“知识”取代政治社会的“意见”的并不是如甘阳所认为的现代哲人,而是古代哲人。现代哲人恰恰是放弃了这一立场。甘阳错误地将施特劳斯的思想认定为要重新把人从真理与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与偏见的世界,引回到现实的政治世界,而事实上,施特劳斯的基本思想恰恰相反,是要遵循古典政治哲人的教导,把人从意见与偏见的世界引回到真理与光明世界。而这正是甘阳第一个表述的意思,古代哲人要从诸多关于善恶的观念中寻求永恒的善恶标准。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等著作中表明,古典政治哲人的全部工作是“从洞穴中上升到光天化日也即真理之下。洞穴乃是与知识相对的意见的世界”[2]13-14,并且, “对古典派而言,哲学化就是要走出洞穴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同代人来说,所有的哲学化本质上都属于某一‘历史世界’、某一‘文化’、 ‘文明’或‘世界观’——那也正是柏拉图所称之为洞穴的”[2]13-14。苏格拉底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来了解它们的本性的。……无视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就等于抛弃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重要的真理的足迹。……因此,哲学就在于由意见升华到知识或真理,就在于可以说是由意见所指引着的一场升华”[2]125。这一过程正是追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过程。然而,任何政治社会都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所以,从意见升华到知识的过程有可能造成对政治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的颠覆,进而引来对哲学家的迫害。古典政治哲人是否就放弃了哲学的使命呢?是否就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呢?是否就滞留在意见的世界呢?依据甘阳的解释,古典政治哲人主张哲学的活动不能破坏现实政治社会的主流价值,所以他们要把人从真理与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但是,施特劳斯笔下的古典政治哲人并非如此。古典政治哲人并没有放弃哲学的任务,哲学就在于由意见升华到知识或真理,就在于可以说是由意见所指引着的一场升华。他们用隐微写作的方式来实现隐讳教导的目的,即让真理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既危害社会又危害自身,从而得以完成哲学的使命,使真理长存于世。古典政治哲人的隐微写作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中最著名的发现。所谓隐微写作,就是同一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一种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即所谓“俗白教导”;另一种是政治上有忌讳而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即所谓“隐微教导”。正如刘小枫所言:“隐微的说辞是哲人并不与现世状态妥协的体现。”[4]215
现代哲人不再沉思何为好人,也不再沉思何为好的政治制度,不再否定现存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不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于是,他们与现政权也就不会构成潜在的政治冲突,与现代社会之间也就不会出现冲突或紧张关系。首先明确放弃古代哲人立场的是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将古典政治哲学,从而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传统视作徒劳无益的而加以排斥:古典政治哲学以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为己任,而回答何为社会正当秩序的问题的正确方式,是要探讨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2]181-182。”马基雅弗利之后的启蒙运动继续展开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这个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的基本思想是,“善根本而言等同于快乐[2]172。”霍布斯的这个思想完全背离了古典政治哲人的主张,即“善的事物本质上有别于使人快乐的事物,善的事物比使人快乐的事物更为根本[2]127。” 究竟什么是善?古典政治哲人认为:“善的生活简单地说来,就是人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满足的生活,就是人最大程度地保持头脑清醒的生活,就是人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虚掷的生活,善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完美化。”[2]128施特劳斯还指出:“洛克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所谓的好与坏,不过就是快乐与痛苦。”[2]254按洛克的看法,通过释放人的具有生产效力的贪欲,人们实际上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个人也从先于同意或协约而存在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那种贪欲必定是(即使偶尔才是)有益的,并且从而是有可能成为最强有力的社会束缚[2]254。 现代政治人确实是要把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引开,但是他们绝不是要把人引到哲学世界,而是要引到享乐主义的世界。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甘阳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一文对施特劳斯著名的古今之争问题给出三种不同的表述。第一种表述是,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是否存在着任何独立于一切流变的好坏标准、对错标准、善恶标准、是非标准、正义与否的标准,这个表述对施特劳斯的把握是准确的;第二种表述是,古今之争就是检讨从古典政治哲学的“善先于权利”如何转变到近代西方霍布斯以来“权利优先于善”的问题,甘阳在这种表述的阐述中把施特劳斯描述成了一个习俗主义者,一个放弃了善恶标准的人,这恰恰是施特劳斯所要反对的。第三种表述是,古今之争问题在于现代哲人相信,可以用哲学的知识取代政治社会的意见,而古代哲人的主张正好相反。这个表述把现代政治哲人与古典政治哲人的基本思想完全颠倒过来了。
[参考文献]
[1]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 [M]//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钢,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3] 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4] 刘小枫.刺猬的温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