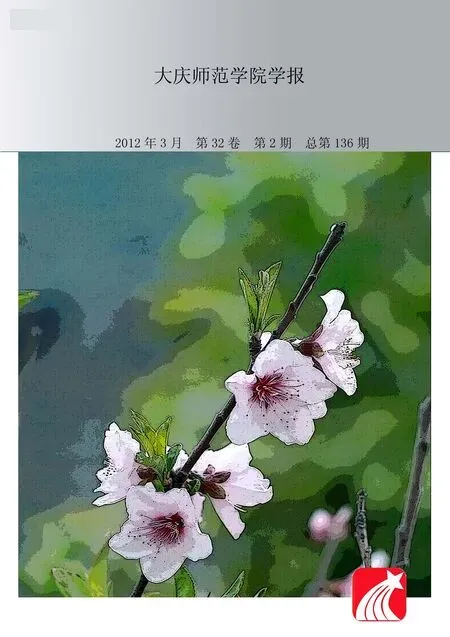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超越
余满晖,方以启
(大庆师范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长期以来,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马克思在新唯物主义阶段对自然的看法的理论特征被设定为唯物主义加辩证法,从而既隐匿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缺点,也遮蔽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本真意义。因此,很有必要探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超越,以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内涵和革命精神。
一、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辩证性及其主要缺点
在传统的解释中,人们认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由此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1]211-243。然而,只要我们根据费尔巴哈本人的著作去理解费尔巴哈哲学,我们就能看到虽然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者,但是在自然观上他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他的自然观不仅存在辩证法思想,而且比较丰富。
第一,费尔巴哈肯定物质的运动、发展变化及其条件性。他说:“地球并不是一直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它只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以后,才达到现在这个状况。地质学已经考查出来,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里,还曾经存在过许多现在或早已不复存在的动植物。……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一个生命的终结与它的条件的终结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生命的开始、发生也是与它的条件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2]449-450“发生的意思就是个体化;个体的东西是发生出来的,……生,的确是羞耻的,死,的确是痛苦的;但是谁要是不愿生与死,那就是放弃做一个生物。永恒排斥生命,生命排斥永恒。”[2]452“我们不能永远说人是人生的,地球某种形态是前期同种形态造成的,我们最后必然要达到一点,那里我们看到人是从自然界产生出来的,地球也是由那行星质体或其他什么元素形成起来的。”[2]596
第二,费尔巴哈肯定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他说:“自然到处活动,到处化育,都只是在内在联系之下,凭着内在联系而进行的。”[2]484“不仅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如此,构成这个感性世界的一切其他的事物和本质也都是如此。这个以那个为前提,那个以这个为前提,这个依赖那个,那个依赖这个;一切都是有限的,一切都是彼此互相产生的。”[2]595自然界的事物,“它们本是互相吸引着的,你需要我,我需要你,这个没有那个就不行的,因此它们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而互相联系起来,譬如氧和氢结合为水,氧和氮结合为空气,如此造成了那种使人惊奇的联系,使得那些没有认识自然界本质而把一切都依照自己来思想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依照计划和目的活动而创造的实体所做成的事业”[2]629。“有机和无机的生命是密切结合着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成立一种必然的联系。”[2]630
第三,费尔巴哈肯定因果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有了条件或原因,就不会没有效果。”[2]632“自然界中,一切都在交互影响,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同时是效果与原因,一切都是各方面的和对方面的;自然界并不构成一个君主国的金字塔,它是一个共和国。”[2]602“每个东西同时是效果又是原因”[2]601。
第四,费尔巴哈肯定肯定与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我的目的绝不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目的,而是一种积极的目的;我否定只是为着肯定;我否定的只是神学和宗教的荒诞的、虚幻的本质,为的是肯定人的实在的本质。”[2]525“人否定自己,可见不是为着否定自己,人否定自己,至少在人性的意义之下,乃是为着借这否定来肯定自己。否定,不过是自我肯定、自爱的一种形式、手段罢了。”[2]568在这里,费尔巴哈表面上是在研究关于人的辩证关系,但是由于费尔巴哈认为自然和人“这两种东西是属于一体的”[3]115,并且“自然是人的根据”[3]116,所以,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中,所谓人并不具有真正独立的人的地位,它消融在自然中。费尔巴哈研究人,就是研究自然。因此,他肯定关于人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肯定自然界肯定与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五,费尔巴哈肯定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必然的规律“在特殊现象和偶然现象中”[3]460。偶然不是必然,但有必然在其中,偶然表现着必然。例如,“人依照不同的年龄,有一定的死亡率,如一岁的婴儿三个到四个死一个,五岁的二十五个死一个,七岁的五十个中死一个,十岁的一百个中死一个,乃是一条自然中的‘神圣秩序的法则’,亦即自然原因的一个结果,可是,恰好这一个婴儿死掉,而那三个或四个活下来,却是偶然的,并不是由这条规律决定的,而是有赖于一些别的偶然原因的”[3]488。
第六,矛盾的观点,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核心。在这方面,费尔巴哈也有不少闪光的思想。他肯定矛盾的存在,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例如他说:“单一是不能生产的,只有二元、对立、不同才是多产的。……精神、机智、聪明、判断,只是在对立之中、只是在冲突之中发展和生产出来的,生命也只有在许多不同的而且相反的质料、力量和事物的冲突中产生出来。”[3]453“灾祸所从来的地方也是福利所从来的地方;畏怖所从来的地方也是欢乐所从来的地方。”[2]531“‘吸引’和‘排斥’,是物质本质上所具有的,人在他的理智中才把它从物质分离出来罢了。”[3]631“东方人见到统一而忽略了差异,西方人则见到差异而遗忘了统一。”[3]45“对立的东西就是这样互相补充。”[3]116
应该承认,就马克思本人来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从来没有说过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马克思甚至还提到“费尔巴哈辩证法”。他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4]114-115
那费尔巴哈自然观的缺点到底是什么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5]54。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包括自然观和认识论)的缺点并不是缺乏辩证法,而是“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感性”。
二、从单纯依赖自然到依赖和改造自然双向互动
费尔巴哈“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感性”使他注意到了“自然不仅给了人双手来制御动物,而且也给了人眼睛和耳朵来赞赏动物”[3]46。它“不仅建立了平凡的肠胃工场,也建立了头脑的庙堂;它不仅给予我们一条舌头,上面长着一些乳头,与小肠的绒毛相应,而且给予我们两只耳朵,专门欣赏声音的和谐,给予我们两只眼睛,专门欣赏那无私的发光的天体”[3]84。另外,我们的“皮肤上有七百万个气孔,我们通过这些气孔进行呼吸”,并且,“我们不仅呼吸,我们也吃和喝”。为此,费尔巴哈提出:“我们是存在于、生活于并活动于自然界里面;自然界笼罩着人类,拿去了自然界,人类也就不存在了;人依于自然界而存在,人每做一事,每走一步,都惟自然界是赖。要使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这就等于要使眼睛离开光,使肺腑离开空气,使胃肠离开营养资料。”[2]579
应该承认,费尔巴哈断定人依赖自然,表明他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立场。因为在发生学上我们确实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上我们也首先需要呼吸、吃、喝,才能有感觉和热情。然而,费尔巴哈坚持人依赖自然,虽然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他“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感性”,“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6]50,因而他也只是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而没有注意到人是“万物的灵长”,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不仅依赖自然,人还能动地改造自然,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闭上了他的眼睛。于是,我们见到了费尔巴哈非常“滑稽”的样子:他的两只眼睛一只睁开着,一只紧闭着。睁开了的眼睛仅仅紧盯着人依赖自然;而紧闭着的那一只眼睛面对的却是人对自然能动的改造。尽管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吃着他们自己精心烹制出来的花色繁多的饭菜,穿着他们自己费尽心机缝制出来各式各样的服装,在家坐着舒舒服服的躺椅,出门乘着平平稳稳的马车,甚至,住的也不是靠自然力天然形成的弯曲曲的岩洞,而是借助人力千辛万苦搭建的漂亮的住房,躺的也不是自然生长的绿油油的草坪,而是自己动手耗费时日制作的鎏金的木床,可是,费尔巴哈却从来都没有认识到所有的这一切只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生成的,只是因为人对自然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能动的改造后才会有的享受。他重视的是与人的“创造性活动”无关的清新的空气、灿烂的阳光、碧绿的草地、静静的流水,并在他的著述中一再提到他的所见所闻,一再说他“需要空气才能呼吸,需要水才能喝”[3]125,然而,人对自然能动的改造却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外。
正因为费尔巴哈否定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的重要意义,只关注人对自然的依赖,因此他招架不住诸如康德、休谟等唯心主义者的攻击。这些唯心主义者或者人为地把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断定人的思维只能达到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或者认为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我们的感觉,至于感觉以外的东西,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总之对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都持怀疑态度。本来,“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1]225,但费尔巴哈却偏偏“看”不到人的实践,所以,费尔巴哈对这些“怪论”能说的只是诸如“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2]630等一类“俏皮”话。然而,“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1]225。他只是运用独断论,僵硬地宣称不可知论“与自然不睦”,而实际上,他这样做不可能也并没有真正使康德和休谟等人的“怪论”完结。
与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感性”不同,马克思认为,应该把“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5]54。这即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人现实生活的感性世界是一个人通过自己能动的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化的世界。这一方面表明人并不生活在自然界之外,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人就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正因为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所以人必然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必须依赖于自然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并不是像动物一样,只知道被动地向自然界索取自己的所需。人总是使用自己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化”或者改造自然界,主动地创造而不是被动地索取自己所需要的“衣、食 、住以及其他东西”[6]31,从而创造出一个属人的物质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上述两个方面说得非常清楚:“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6]31
正是由于人们每日每时都在进行这种作为“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的“历史活动”,因此,“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43,人依赖和改造自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活动。
这样,康德、休谟等人的不可知论也就必然会“销声敛迹”。因为当马克思断定人不仅依赖自然,人还同时能动地改造自然时,人们就可以在他们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证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5]55。而此时,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1]225-226,就可以“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225-226。
三、从单纯的自然观到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相互融合
由于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感性”,因而在费尔巴哈的视阈中,自然界中的全部感性事物都仅仅只是自然感性、自然存在,都是先在的、既成的。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6]48-49。这也就是说,虽然费尔巴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生活在工业时代的“现实的历史的人”,但是,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诸如自己一样的那些一代接一代的“现实的历史的人”早已经把先前“纯粹的自然”变得不“纯粹”了。他的意识活动指向的自然界中的东西,实际上无一不是“工业和社会状况”或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打个比方说,诸如樱桃树,“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6]49,因而“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6]49。即使“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6]49,没有“人们的感性活动”,“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6]49也绝对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6]50。
这样,当唯物主义“在场”时,费尔巴哈的视阈里就没有了历史,没有了人类社会,好像自然和历史“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6]49。所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当费尔巴哈“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6]50。他荒唐地提出:“幸福主义是人生来就有的,所以若不利用它,或不知道和愿望它,那末将完全不能思想和谈话。”[3]547同样,“人的幸福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根据和任何的基础,而不过是人自身创造的幻想”[3]553。至于“不爱清洁——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恶德,它根源于人本性的守旧心理和懒惰,根源于人爱好平常的习惯和舒适,这种恶德不只蔓延到个别人身上,而且也蔓延到整个民族和部落。例如苏门答腊的住民‘从来不给自己的孩子洗澡,霍屯督人不洗自己的身体。因此,泥垢是这样深入到他们的皮肤中,以致很难区别什么是皮肤的真正颜色,他们黝黑如煤炭’。……为了把人由他的肮脏污秽提高到有清洁教养的程度,就得需要摩尼、琐罗斯德、摩西、穆罕默德这样一些人物;因此,人只是由于依靠宗教、依靠神的启示才学会了区别恶臭与芳香,小便与水,虱子与食物,肛门与口”[3]563。
因此,费尔巴哈尽管写了《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等著作来专门批判宗教,但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还是不彻底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6]55,也“已经证明,宗教之内容和对象,道道地地是属人的内容和对象”[2]315,然而,当宗教的“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5]55时,费尔巴哈并没有“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5]55,“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5]55。而“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55,即使争论一万次,辩驳几百年,也不能真正肯定或否定某种思维的客观真理性。所以,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驳倒宗教,并没有使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5]55。事实上,费尔巴哈也不想真正消灭宗教,而只是试图通过批判世俗的宗教如基督教等,达到顺利地建立他理想的“爱”的宗教的目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也还是没有看到,所谓“爱”等“宗教感情”本身也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什么“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2]315。
费尔巴哈只有单纯的自然观,没有历史观的理解方式随着马克思提出人现实生活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而得到了扬弃。这种人化的自然观表明人一来到世间,为了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他们不是像一般动物那样消极地等待,而是主动地利用自然界既有的原材料如石头等去打制石器,削制棍棒等。这些活动使自然物不断作为一个要素进入人的实践活动中,积淀出了各种各样的人创造的劳动产品。而人在创造这些劳动产品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就在生产着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人化的自然界。这个感性世界是与作为“一般”的单纯自然界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地属于“个别”的自然界:它不仅仅必须有自己的一般自然基质,而一方面必然表现为自然的存在;另一方面,它更是人自己生活和创造的世界,也即是社会的存在。
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化的自然界的发言一方面是表达他对这种以自然的存在而存在的东西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阐发他关于人现实生活和创造的自然界即社会的存在的“意见”。换言之,此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1845年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曾特别强调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6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