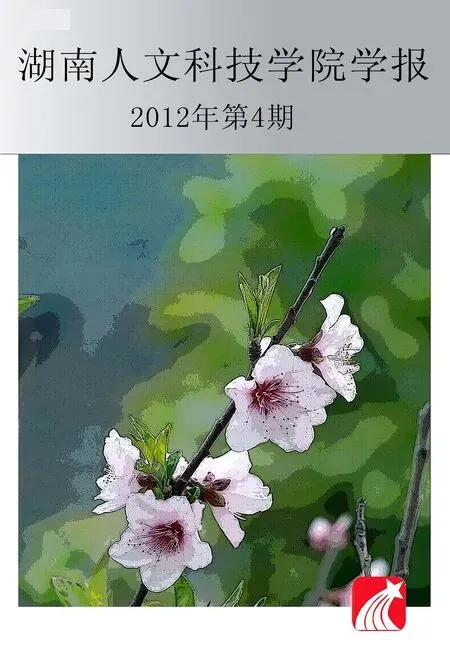《类说》独存之笔记小说条目及价值
薛琪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曾慥,福建泉州人,字端伯,生活于两宋之交,是北宋名臣曾公亮之四世孙。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四月,他撰成《类说》一书,其自序云:“余侨寓银峰,居多闲日。因集百家小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类说》。”[1]该书精于裁鉴,博而精要,后代学者多有著录和征引,对本书颇为重视。《类说》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有些确已被他书收录或单行,但《类说》所录多出了一些独有之条。笔者经过整理统计,这些书共33种,条目186条。《类说》独存的唐人笔记小说之条,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的史料价值。限于篇幅,现举要略为考析,以见这些条目的补史作用和《类说》保存文献的价值。
一 《邺侯家传》
《类说》本《邺侯家传·门匠》条载:
唐时运漕,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纲船夫并牵一船,仍和雇侧近数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礁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中,更不复见。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陕人云:“自古无门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门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谷堆。每纲上三门,无损伤,亦近百日方毕,所以漕运艰阻。[2]46
按《资治通鉴》卷232唐德宗贞元二年正月条载:“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原注:底柱两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过,世谓之三门。车道者,陆运之道,舍舟而车运也。)是月道成。”[3]7468可见,《类说》本《邺侯家传·门匠》条,颇为详细,可以丰富《资治通鉴》的记载。
《类说》本《邺侯家传·李晟功与郭子仪异》条载:
初,李晟将建家庙,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庙,有名封者祀五庙,五品以上祀三庙,三品以上不须兼爵。时泌以为四庙非古,且礼有降杀,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古制也。上许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后五代孙祀既祧诸主,以晟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远长之图。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庙。”泌曰:“李晟功与郭子仪异。至德收复,玄宗虽幸蜀,肃宗自灵武至凤翔,时先皇为元帅,亲总戎行。外蕃及诸道之师共十余万,子仪自同州来会战,只朔方节度耳。战胜收复,回纥及四镇之功多。晟之收复也,陛下再幸梁洋,旁有怀光以朔方之强又反,诸道已抽兵回者。收复之日,浑瑊在咸阳,亦不来会。其时又无元帅,骆元光等皆有所统率也。此乃克复,全在于晟,子仪岂可比哉?”上曰:“诚如卿言”。于是许立五庙而空西室。[2]47
按《唐六典》载:“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庙;五品已上,祠三庙;六品已下达于庶人,祭祖袮而已。”[4]《旧唐书》卷 43《职官志》记载与之同。唐代依官爵品阶立庙,六品及以下无庙。开元十二年(724)朝廷对家庙制度做了修正,《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5]345开元二十年(732),《开元礼》颁布,再次修订家庙制度,从而成为唐代官人立庙的主要依据:“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夹注曰:三品以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袮于正寝。”[6]据之可知,唐制三品以上无爵亦可立庙,四、五品则一定要兼爵始可立庙,最高可立四庙。李泌称“李晟功与郭子仪异”,德宗许李晟“立五庙而空西室”,超过了尚父郭子仪的庙制,是对李晟收复长安之功的莫大肯定和恩宠。《类说》本《邺侯家传·李晟功与郭子仪异》条与正史记载一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 《番禺杂记》
《类说》本《番禺杂记·雷藏》条载:
村民凿山为穴,以多品供雷,冀雷享之,名曰“雷藏”。[2]102
《类说》本《番禺杂记·雷郎》条载:
民家女或为神所依,即呼为雷郎,得子曰“雷子”。[2]103
以上两条所载,反映了广州地区的雷神崇拜,对于研究岭南的宗教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类说》本《番禺杂·歌堂》条载:
南人尚乡歌,每集一处共歌,号歌堂。[2]103
《类说》本《番禺杂记·腊一伏二》条载:
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2]103
《类说》本《番禺杂记·盪风》条载:
广俗,未见妻之父母,所嫁女先饮一大杯,谓之盪风。[2]103
《类说》本《番禺杂记·占卜》条载:
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篾竹卜、俗鬼故也。[2]103
以上四条记载,岭南对歌、占卜、节庆婚俗等民风,反映了当地的文化习俗。唐人笔记小说专记岭南地区故事的并不多,《番禺杂记》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而《类说》独存此书的条目,更显得弥足珍贵。
三 《秦中岁时记》
《类说》本《秦中岁时记·酴醿酒》条载:
寒食内宴宰相酴醿酒。[2]173
按钱易《南部新书》载:“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醿酒。”[7]则《类说》本《秦中岁时记》所载,唐时寒食节风俗,堪与《南部新书》记载相印证。
又《类说》本《秦中岁时记·中和节》条载:
二月一日中和节,百官进农书,内出中和历,敕赐群臣。[2]173
按《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贞元五年春正月条载:“乙卯,诏:‘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儤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8]367《旧唐书·德宗纪》关于中和节的这一记载,与《新唐书·李泌传》,《唐会要》等所记同。《类说》本《秦中岁时记》关于中和节的记述,有“内出中和历”一句,为正史所无,可补史阙。
四 《河洛记》
《类说》本《河洛记·知世郎》条载:
大业末,宋寇先起,邹平人王薄拥众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作歌以招征役者,歌云:“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横矟侵天半,轮刀摇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豕,斩头何所伤?”人多附之。后杨玄感反,山东遂成大乱。河北有张秤、王秡须等凡二十七项,多至十余万,少不下万人,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酋帅,亦有名称,或云“乞见敌”,或云“嫌头方”,或云“彻眷顽”、“勿惜死”。又结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白社”、“青特”、“胡驴”之号,“浮云贼”、“忽律贼”。最后李密起而隋亡。[2]181
按《类说》本条,介绍王薄起义的事迹和影响。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九年)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所败,孝慈死之。”[9]86又同书大业十一年(615)二月条载:“丙子,上谷人王须拔反,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刁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9]89则“张秤”即为张金称之别名,“王秡须”则系“王须拔”之误。
《资治通鉴》卷183隋恭帝义宁元年二月条载:“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皆归密。(胡注曰:黑社、白社,盖贼之号,非人姓名也。)”[3]5722此处指“黑社”、“白社”等盖贼之号,与《类说》本《河洛记》同。而据《新唐书·地理志》毫州谯郡条载:“大业十三年,县民田黑社盗据,号涡州。武德三年来降,复为县。”[5]990又《旧唐书·窦建德传》载:“(武德)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海公及徐圆朗之众来救世充……秦王遣将军王君廓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获其大将张青特,虏获甚众。”[8]2241则“黑社”、“白社”、“青特”、“胡驴”等,皆应为人名而非号称也。显见,《类说》本《河洛记》此条记载,可以补充纠正正史记载的不足。
《类说》本《河洛记·檄暴》条载:
李密自立为魏公,檄喻郡邑,暴炀帝之恶云:“先皇嫔御,并进银镮;诸王子女,咸储金屋。”又云:“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邀逆旅。”[2]181
又《类说》本《河洛记·再檄》条载:
李密云:“贺若弼以上将诛夷,高颍以大勋受缢。薛道衡文宗学士,遂处极刑。痛结人心,悲缠华夏。”又云:“多营宫殿,广立池台。罄珠玉之珍奇,穷丹青之丽饰。歌姬舞女,终日荒淫;走狗飞鹰,盘游无度。桑间濮上,听亡国之音;漕丘酒池,为长夜之饮。”又云:“汉朝星动,岂曰劳人?晋国石言,未为烦役。”又云:“一时收十岁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费。夫行妇寡,父出子孤。百川沸腾,十日并出。”[2]181
按以上两条,均为记载李密起事时传播的檄文,第一条“檄暴”见于《旧唐书·李密传》所载祖君彦檄文:“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镮;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袒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要逆旅。殷辛之谴为小,汉灵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8]2213又《新唐书·李密传》载:“密令幕府移檄州县,列炀帝十罪,天下震动。”[5]3681第二条“再檄”条,则不见他书记载,尤为重要,可证李密等发动的反隋宣传攻势不止一次。
五 《封氏闻见记》
《类说》本《封氏闻见记·钓鳌客》条载:
张祐(祜)谒李绅,亦称钓鳌客。李怒曰:“即解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为竿。”“以何为钩?”曰:“以月为钩。”“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为饵。”绅默然,厚赠之。[2]189
本条前半段叙王严光自号钓鳌客事,见于《封氏闻见记》各版本。后半段“张祐谒李绅”以下部分,则为《类说》本独存。《唐才子传·张祜》条载:“同时崔涯亦工诗,与祜齐名,颇自放行乐,或乖兴北里,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尝共谒淮南李相,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绅壮之,厚赠而去。”[10]可两相印证也。《类说》本《封氏闻见记》之“张祐”,则应为“张祜”。又《唐语林》云:“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竦然。”[11]492可见,“钓鳌客”的典故由来已久。
六 《献替记》
《类说》本《献替记·行中书》条载:
文宗恶朋党,指杨虞卿为首,实李相宗闵所引。上令出知常州。宗闵见上怒,即顺旨云:“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为行中书,每日聚议,所以臣不与好官。”德裕曰:“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闵失色。[2]224
按《新唐书·李宗闵传》载:“久之,德裕为相,与宗闵共当国。德裕入谢,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曰:‘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帝曰:‘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浣为党魁。’德裕因请皆出为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为常州,元夫为汝州,萧浣为郑州。宗闵曰:‘虞卿位给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党人不如臣之详。虞卿日见宾客于第,世号行中书,故臣未尝与美官。’德裕质之曰:‘给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闵大沮,不得对。俄以同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5]5235-5236两者比较,基本史实相同,但《类说》本《献替记》所言“实李相宗闵所言”之语,更加明确交待了杨、张、萧诸人与李宗闵为同党,或可与正史相互印证。
《类说》本《献替记·判停卫送》条载:
德裕初作相,两街使请准例,每早朝令兵卫送。予判曰:“在具瞻之地,自有国容。当无事之时,何劳武备?卫送宜停。”[2]225
按《唐语林·政事》载:“开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镇江陵。自此诏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卫公复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国容;居无事之时,何劳武备?所送并停。’(原注:李卫公初入相是太和七年,居李石之前,卫兵不因李事。记之者有误。)”[11]75王谠原注有误。李石之事,据《新唐书·李石传》载:“(开成)三年正月,将朝,骑至亲仁里,狙盗发,射石伤,马逸,盗邀斫之坊门,绝马尾,乃得脱。天子骇愕,遣使者慰抚,赐良药。始命六军卫士二十人从宰相。”[5]4516李德裕初入相为大和七年,“判停卫送”非此时,而是复相之时。《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五年条载:“九月,甲戌朔,至京师。丁丑,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3]7945则“判停卫送”当在开成五年(840)九月复相之初。又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注此条不知出自何书,很有可能就是源自《献替记》,而《类说》独存了《献替记》此条,可见其史料价值。
七 《金銮密记》
《类说》本《金銮密记·不草制》条载:
韦贻范于凤翔围城中,挟李茂贞起复作相。渥当草制,抗疏论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使中人也。语渥曰:“学士勿以性命为戏!”渥不答,扄户而寝。明日,无麻制宣读,茂贞曰:“陛下命相,学士不肯草制,与反何异?”昭宗曰:“卿荐贻范,朕不敢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2]229-230
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二年七月条载:“韦贻范之为相也,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甲戌,命韩偓草贻范起复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韩侍郎不肯草麻,闻者大骇。茂贞入见上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卿辈荐贻范,朕不之违;学士不草麻,朕亦不之违。况彼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3]8577-8578《类说》本《金銮密记》记“韩渥”,即韩偓,误也。虽然《类说》本《金銮密记》所言比《资治通鉴》简略,但两者所述史实大致相同,反映前者此条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八 《芝田录》
《类说》本《芝田录·陆贽何面孔》条载:
陆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门,盐菜由狗窦中,端坐抄药方。儿侄亦罕与语。会转运使至京,上问:“尔峡中过,闻陆贽何面孔?”具以状对,上恻然。拜太子宾客,已卒。[2]344
按《类说》本《芝田录》,记录了陆贽在忠州的待罪生活。《旧唐书·陆贽传》云:“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韦皋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8]3818显然,《类说》本《芝田录》的记载更加具体。
九 《玉泉子》
《类说》本《玉泉子·一叉手一韵成》条载:
温庭筠文思敏妙,李义山尝得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温对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温每作赋,一叉手一韵成。令狐綯多托为文,恶其漏语,疏之。温谤曰:“中书岂坐将军处耶?”讥其无学也。[2]760-761
按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温庭云字飞卿……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晋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12]两书比较,《北梦琐言》此条记载更为详细,然《类说》本《玉泉子》云“赵公”,即长孙无忌也,而《北梦琐言》云“召公”,明显误也,可见《类说》本辨正的史料价值。
《类说》本《玉泉子·大帽子》条载:
本野老之服,后魏戴之,唐初以纱縠为之,以隔风埃。[2]761
按马缟《中华古今注·大帽子》条载:“本岩叟草野之服也,至后魏文帝,诏百官常以立冬日贵贱通戴,谓之温帽。”[13]129《类说》本《玉泉子》所言“唐初以纱縠为之,以隔风埃”,叙述了唐代大帽子的情况,可与《中华古今注》的记载互补。
《类说》本《玉泉子·席帽》条载:
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鞔以故席,女人亦戴之,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谓之席帽。炀帝幸江都,御紫云楼,观市,欲见女人姿容,诏令去网子。[2]761
按马缟《中华古今注·席帽》条载:“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饰。至炀帝淫侈,欲见女子之容,诏去帽,戴幞头巾子帼也,以皂罗为之,丈夫藤席为之,骨鞔以缯,乃名席帽。至马周以席帽、油御雨从事。”[13]129《类说》本《玉泉子》云“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鞔以故席”,叙述了“席帽”最早的来源,以及何时传入汉地。尤其是《类说》本《玉泉子》有关隋炀帝“诏令去网子”的记载,使我们可以明确理解《中华古今注》此条所言“诏去帽”之意,实际是去网子不去席帽,也即女子戴席帽去四缘网子装饰。可见,《类说》本《玉泉子》此条记载很有参考价值。
《类说》本《玉泉子·髻名》条载:
髻者继也,女子必有继于人。女娲氏以羊毛绳之,向后系之,以荆木竹为之笄,贯发。赫连氏造梳,二十四齿,取疏通之义。尧舜以铜为笄,舜加女人首饰,钗梳杂以象牙玳瑁为之,间以玉。髻上加朱翠翘花,傅之铅粉。其商髻名凤髻。又有云髻,加之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始皇宫中梳望仙髻,汉宫有迎春髻。汉武时诸仙从王母下降,皆梳飞仙髻、盘龙髻,贯以凤首钗、孔雀搔头、云头篦。扫八字眉。汉明帝宫人梳百合分稍髻,同心髻。扫青黛蛾眉。魏武宫人扫连头眉。晋惠帝宫人梳芙蓉髻,通草五色花子,扫黑墨眉。一画连心,细长,曰“仙蛾妆”。隋文华宫中梳九贞髻,唐武德中梳平蕃髻、长乐髻。开化中梳双环望仙髻。贞元作偏髻子。[2]762
按马缟《中华古今注·头髻》条载:“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系也。女子十五而笄,许嫁于人,以系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为笄,笄以约发也。居丧以桑木为笄,表变孝也。皆长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铜为笄,于两旁约发也,为之发笄。殷后服盘龙步摇,梳流苏,珠翠三服,服龙盘步摇,若侍,去梳苏,以其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周文王又制平头髻。昭帝又制小须变裙髻。始皇诏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至汉高祖,又令宫人梳奉圣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堕马髻。灵帝又令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作白妆,青黛眉,有郁髻。隋有凌虚髻、祥云髻。隋大业中,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妆。贞观中,梳归顺髻。又太真偏梳朵子,作啼妆。又有愁来髻,又飞髻,又百合髻,作白妆黑眉。”[13]126以上有关女子髻名的记载,《类说》本《玉泉子》记载了“女娲氏”、“赫连氏”、“尧舜”、“始皇宫中”、“汉宫”、“汉武时”、“汉明帝宫人”、“魏武宫人”、“晋惠帝宫人”、“隋文华宫中”、“唐武德中”、“开化中”、“贞元”等不同时代女子头髻的变迁,而《中华古今注》叙述了“夏后”、“殷后”、“周文王”、“昭帝”、“始皇诏”、“汉高祖”、“武帝”、“灵帝”、“魏文帝”、“梁天监中”,“隋”、“隋大业中”、“贞观中”、“太真”等不同时期的头髻流变,两者正好交叉互补,有利于全面了解女子头髻的流变,由此亦可见《类说》本《玉泉子》此条所录保存史料的价值。
十 《卢氏杂说》
《类说》本《卢氏杂说·黄贼打黑贼》条载:
宣宗时,京城卖枣团,以黄米黑面为之,云“黄贼打黑贼”,乃巢贼之谶。一云巢寇。[2]1473按《新唐书·五行志》云:“黄巢未入京师时,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谓之‘黄贼打黑贼’。”[5]922两者比较,可以发现,《类说》本《卢氏杂说》此条所言用“黄米黑面”做成“枣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唐书·五行志》有关“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的记载。
《类说》本《卢氏杂说·押山字》条载:
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2]1474
《类说》本《卢氏杂说·炼腿》条载:
僖宗在藩邸好筑毬,有炼腿之语。[2]1476
按以上两条,未见于两《唐书》的记载,颇可补正史之阙。
十一 《戎幕闲谈》
《类说》本《戎幕闲谈·神撼绦》条载:
翰林院有悬铃,以备夜中警急,文书出入,则引索以代传呼。长庆中,赞皇为学士时,河北用兵,铃数有声,终不见人。声急则军事急,声慢则军事慢,曾莫之差。元相亦在院,元诗有“神撼绦”是也。[2]1548
按元稹《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大夫本题言赠于梦中诗赋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和者,亦止述翰院旧游而已,次本韵》诗载:“吏传开锁契,神撼引铃绦。”[14]可与之印证。《类说》本《戎幕闲谈》此条记载,翰林院悬铃“备夜中警急”一事,未见他书所载,应是有关唐代翰林院制度的主要记述。
综上,《类说》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比原书单行本或丛书收录本多出一些独有之条。经笔者统计,这些书共计33种,条目186条。《类说》独存的唐人笔记小说之条,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考证史实等作用,据此可知唐时的社会风尚、官场典故、宫廷遗事、地域文化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曾慥.类说[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6.
[2]王汝涛.类说校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3.
[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御撰.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4.
[7]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21.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0:177-178.
[11]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89-90.
[13]马缟.中华古今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