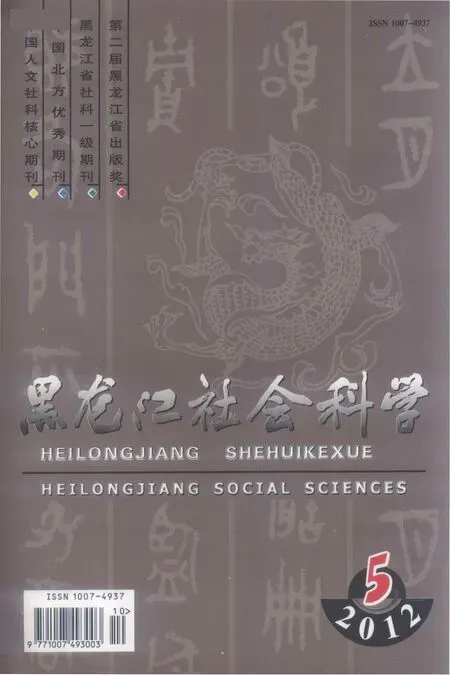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
张 亮
(南京大学a.哲学系;b.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界对“教科书体系”,即源于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教科书体系”的权威地位,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重建进程,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认识,使得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某些阶段、流派、著作、学说等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微妙有时乃至剧烈的改变。在这个方面,列宁阶段的遭遇最具代表性:过去,学界非批判地接受了源于“教科书体系”的哲学史叙事,默认列宁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现在,人们则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反“教科书体系”而力图否定这一阶段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价值。毋庸讳言,这种认识的剧烈改变已经导致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也由此使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成为一个亟待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一、列宁阶段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掀起了一轮研究、宣传列宁思想遗产的高潮。党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陆续发表论述,阐发自己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评价。尽管在定义问题上存在分歧乃至争论,不过,他们都从社会政治理论这个角度出发定义、评价列宁主义,肯定列宁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差别主要在于这个新阶段是否具有普遍性或国际性。那么,列宁主义是否也同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呢?他们基本上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在1924年四五月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在第二部分“方法”中简单涉及哲学问题,认为列宁的哲学成就主要在于“恢复”、“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1]。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联共(布)党内的主流观点。例如,在创作于1925—1926年间、得到列宁夫人肯定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中,与列宁交从甚密且有多次理论合作的季诺维也夫也认为列宁哲学思想的精髓在于辩证法,虽然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不相上下,但在辩证法的运用上,即“把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斗争,运用于群众运动,运用于社会发展,运用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等方面,普列汉诺夫是“完全软弱无力的”,而列宁则是“一位真正的巨人”[2]。在被晚年列宁赞誉为“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看来,作为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实践观点”是列宁的哲学思维最重要的特点。之所以列宁总是能够透过现象的乱麻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在于他纯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3]。
那么,专业哲学家们是如何评价列宁哲学思想的呢?在1924年出版的《思想家列宁》一书,德波林给出了一种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的看法。《思想家列宁》由三篇论文构成,在第一篇论文《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中,德波林旗帜鲜明地提出,列宁“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反抗者,不只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不只是工人阶级的英明领袖,而且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思想家——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家类型,“革命思想家”列宁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4]417-421。在第二篇论文《辨证论者列宁》中,德波林提出,之所以列宁能够在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斗争中战胜第二国际正统派,归根结底是因为列宁真正继承、坚持并成功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列宁的一切著作都贯穿着辩证法”[4]549。在第三篇论文《列宁和现时代》中,德波林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就思想家应当表达时代的本质、运动及需要并能引领现实的发展而言,“列宁是现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4]830。
如果把德波林的观点和前述政治领袖们的论述略加比较,就会发现:第一,两者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出发点,即证明列宁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思想家、哲学家;第二,两者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即都是从在实践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运用和发展这一维度出发,证明列宁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哲学家;第三,在肯定列宁是思想家乃至现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余,两者都无意做进一步的哲学史判断。当然,两者的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系的评价上。在《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条后来被删改掉的注释中,德波林实际上说出了当时哲学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不仅如此,“这两位思想家是相互补充的。普列汉诺夫首先是一位理论家,而列宁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领袖。”[4]817撇除这一点歧见,德波林可以说是以高度学术化的方式证明了政治领袖们的判断。
经过政治领袖和专业哲学家的双重努力,1924年以后,在列宁与哲学这个问题上,人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1930年德波林学派与青年红色哲学家发生争论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改变。当时,在争论中处于下风的青年红色哲学家指出德波林“褒”普列汉诺夫“抑”列宁无疑是错误的。但这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推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既然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立的新阶段,那么,列宁主义就应当在各个方面都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论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组成部分’来说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方面来说,它是正确的。……不懂得哲学上的列宁主义,在目前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列宁体现着新阶段、新时代。”[5]显然,青年红色哲学家对列宁阶段的论证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从列宁在社会政治理论上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中,并不能必然地得出列宁在哲学上也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结论。可是,随着斯大林的介入,这场争论以青年红色哲学家的完胜告终,哲学政治化的错误进程也由此开启[6]。最终,上世纪30年代初以后,在这种哲学政治化进程的推动下,列宁阶段这一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观点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教条被固定下来[7]。
二、列宁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上世纪30年代早期,已是苏联哲学界风云人物的米丁领衔主编了一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正是在这里,“教科书体系”被系统地建构了出来。也正是在这里,列宁阶段被当做一个确凿无疑的哲学史事实第一次写进了教科书:“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发展中的新的更高的阶段。”[8]此后,“教科书体系”始终肯定列宁阶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以列宁哲学的真正继承人和忠实阐释者自居的“教科书体系”则因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正统性和权威性[9]。事实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试图否定列宁有哲学,并且这种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阶段是否在性质上已经超越其他阶段,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进而它是否达到了相对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而言的“更高”水平,从而成为一个“更高”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已经成熟地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显然可以超越“教科书体系”的桎梏,对列宁阶段作出更加符合哲学史事实因而更加令人信服的判断。
首先,列宁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介环节。无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十月革命问题上存在怎样的分歧,以及无论列宁在辩证法问题上怎样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我们都无法否定一个事实: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依靠普列汉诺夫的启蒙才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就像列宁晚年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俄国,“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0]419。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首先是19世纪俄国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正因为如此,较之于同时代其他第二国际理论家,他更加重视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及其思想史来源等的论述,并且从哲学史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证,从而建构出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解模式。从本质上讲,这种理解模式是在斯宾诺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回到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但它却因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内在需要,而在现代俄国思想中深深扎下根来,从而影响和塑造了包括列宁在内的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哲学笔记》在辩证法问题上超越了普列汉诺夫,不过,十月革命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体系的理解却是“接着”普列汉诺夫往下“讲”的,即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基本路线。正因为如此,在1922年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列宁认为对还处于相对落后和不发达阶段的苏联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发展俄国既有的唯物主义传统,和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做斗争[10]646-655。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评价“教科书体系”,都必须看到,该体系确实——以问题重重的方式——落实了列宁的上述指示,从而让普列汉诺夫开创、列宁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进程获得一种完成。
其次,列宁阶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到了一个更自觉、更高效的新阶段。作为一种以革命地改造世界为使命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要求超越自己的精英性,以大众化的形式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9。因此,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曾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大众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上,列宁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创作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新的大众化经典,而且在于升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认识。基于对俄国革命实践的深刻认识,列宁提出,群众不可能自发地获得革命的理论,而必须从外部加以灌输,他因此要求俄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应该帮助工人领会它并制定一个最适合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12]。正是在列宁灌输论的指导下,包括联共(布)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并自觉运用各种政治手段推进这一工作,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更自觉、更高效的新阶段。
最后,列宁阶段因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精髓而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四大潮流之一[13],“西方马克思主义”真实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一新阶段的形成却直接导源于列宁哲学: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葛兰西、卢卡奇和科尔施这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或者说正统不在于理论教条而在于方法,即列宁所强调的唯物辩证法,正是基于这一全新认识,他们随后分别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哲学建构,从而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1924年的《列宁》一书中,卢卡奇非常具有代表性地阐明了他们对列宁哲学的认识:“列宁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经历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几十年的倒退和扭曲后,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重建了自身的纯洁性,而且使它的方法得到发展并日益成熟。”[14]
三、列宁阶段的哲学史意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学界掀起了一轮反列宁主义的新高潮。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改变是,作为对原有哲学史叙事的一种逆反,现在很少有人去关注作为哲学家的列宁。在人们眼中,即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列宁阶段,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排除苏联学者有意抬高列宁的政治需要和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误解,以客观的态度看,列宁尽管在哲学问题上投入的时间有限,但他以过人的睿智,对不少问题的思考都非常深入,有其独到之处,提出的不少思想至今仍然很有价值”[15]。
那么,从今天的角度,列宁阶段都具有哪些哲学史意义或价值呢?
首先,列宁阶段的哲学史意义在于强化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新世界观。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56然而,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大大地失落了。正是列宁恢复并强化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地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6]不仅如此,列宁还把这种实践精神转化为行动的策略指南,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因此,必须根据实践用新的方式提出问题,否则,“就是为死教条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17]。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全部理论贡献,都是建立在列宁的这一哲学遗产基础上的。
其次,列宁阶段的哲学史意义在于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在1908年所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坚持实践论与反映论的统一、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对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著名论断[18],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进而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因为在认识论上,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19]唯物主义就是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
最后,列宁阶段的哲学史意义在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空间。在1914-1916年间创作的《哲学笔记》中,列宁着重研究了唯物辩证法问题,首次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观点;概括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要素,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还从世界观的高度提出了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重要思想,具体论述了认识过程中的辩证运动。不仅如此,列宁还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哲学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丰富了对立统一学说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综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列宁开创性的工作,辩证法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进而丰富和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完善和成熟程度的。
[1] 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9.
[2]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M].郑异凡,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307.
[3] 布哈林文选: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3-75.
[4]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M].李光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5] 张念丰.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G].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208.
[6] 张亮.在哲学政治化的起点上——重读斯大林1930年12月 9日的谈话[J].山东社会科学,2010,(11).
[7] 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贾泽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31.
[8] 米丁.辩证法唯物论[M].沈志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52.
[9] 张亮.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教科书体系”?[J].福建论坛,2011,(7).
[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列宁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4.
[13]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14] GEORG LUKACS.Lenin: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0:88.
[15]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7.
[16]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3.
[17]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9.
[18]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4.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