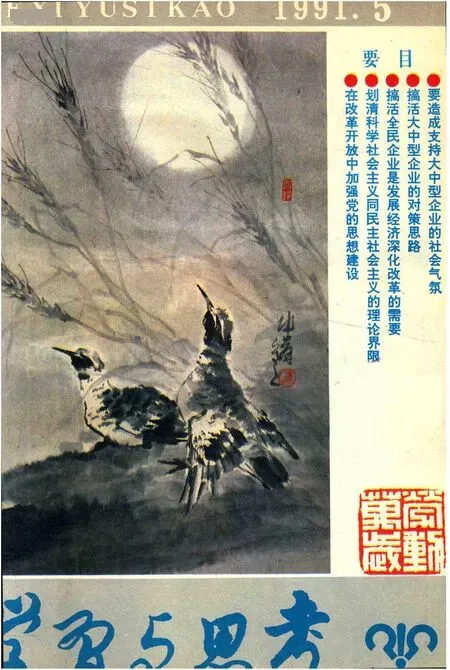国际危机事件与中国公众舆论方向*
□ 余金城
国际危机事件与中国公众舆论方向*
□ 余金城
影响一国国内公众舆论方向并进而对该国外交和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危机事件主要分三类:宗教—政治性的危机事件、事关历史认知心理的危机事件和事关国家现实利益的危机事件。中国当代公众舆论方向深受这三类国际危机事件的影响,经此,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也深受影响。新世纪,业已浮现世界强国前景的中国需要认真应对这些国际危机可能给国内舆论带来的影响。
国际危机事件 公众舆论 国家安全
一、影响一国公众舆论方向的三类国际危机事件
根据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能够影响一国公众舆论并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外交和对外政策的国际危机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宗教—政治性危机事件、事关历史认知心理的危机事件和事关国家现实利益的危机事件。
宗教—政治性国际危机事件多与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冲突相关,实际上是信仰之战、意识形态之争、政治制度相斗的结果,这里的宗教性也多具有政治性内涵,多与政教合一的社会相关。这类危机事件发生的肇始地既可能在第三方国家或地区,也可能在敌对双方的一方国内。如果发生在第三方国内,则第三方国内发生的事件往往得到互有敌意的双方国家中的一方或明或暗的支持,是该国对外政策目的追求的结果。这类政策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政治感染性,能够迅速扩展到其他地区,进而可能影响甚至扩展到互有敌意两方国家中的另一方国内,成为主导该国公众舆论发生转向的主要因素,以致引起该国社会—政治动荡,危及国家安全。如果国际危机事件发生在两方国家的一方国内,则这种危机事件可能成为变革该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推动因素,而发生了变革的国家可能进而向包括敌对国在内的国际范围内输出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无疑会受到敌对国家的官方抵制,但这种抵制未必敌得过国内公众舆论对输入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的狂热追随,以致严重危及国家安全,使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方向可能因此发生剧烈变化。由此,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的大战略也就可能发生重要的修改甚或更替。
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宗教—政治性国际危机事件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教派之间,甚至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宗教信仰之战往往是宗教—政治性国际危机事件发展的极端形式,但这类极端形式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它往往使一国旋即登上世界权力的巅峰,也会使一国瞬间就从政治地图上消失。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自由、民主思想日益取代宗教信仰而成为国际危机发端的肇因。这类国际危机事件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次展现了其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深刻影响无论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在现当代社会,随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民族世界大同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之争成为目前影响一国国内公众舆论方向,进而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以致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的国际因由①对于当今民族世界大同主义的分析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第7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7页-420页。,它在当下的主要表现就是“颜色革命”。
第二类国际危机事件与国家间在历史认知的心理层面存在的相互猜疑、刻骨仇视和内在冲突相关。这类国际危机有时又会与第一类国际危机事件发生交互性影响,如果发生冲突的国家之间还存在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矛盾的话。第二类国际危机事件往往发生在具有历史心理仇视和冲突的对象国中。两国之间特别是具有深深的受伤害感的国家对对方国家的社会个人或群体,尤其是对方国家的政府官员甚至官方机构发生的一言一行非常敏感,并时刻将这种言行与历史心理认知层面的冲突性的经验体会联系起来,一旦感觉对方国家的言行侵犯了自己的历史心理认知,这一事件就会在瞬间酿成重大的国家间的外交危机,并主导着国内公众舆论方向的变化。法德在历史上敌对、一战之后的德国对于凡尔赛体制代表的英法国家集团的敌视、前南斯拉夫国家在解体后民族间的敌视都属于这一类矛盾。在当前,比较敏感的东欧与俄罗斯之间、俄罗斯与独联体、中亚其他国家之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类历史认知心理层面的矛盾。
第三类国际危机事件涉及到国家的现实利益问题。领土、领海之争、海外人权、海外经济利益保护以及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等都属于国家现实利益中的常见问题。这类问题尤其是领土、领海之争在不少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多数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问题,因而构成了第二类历史心理认知方面仇视和冲突的现实基础。这两类问题如果夹杂在一起,处理起来就更为棘手、复杂。
二、当代三类国际危机事件对中国国内公众舆论方向的影响
中国当代公众舆论常常受到上述三类国际危机事件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向非西方民主国家推行他们的民主政治战略,政治性国际危机事件在世界舞台上不断上演,这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仍然是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重大的政治性国际危机事件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21世纪初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近一年来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些重大国际危机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对别国国内社会公众和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动效应。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往往以民族自决、人权、民主、公平选举、反官僚腐败、反政府治理无能等理由为幌子,在别国国内塑造政治反对派、煽动政治反对派掀起反政府的社会—政治运动(常称之为“街头政治”)。这一类社会—政治运动一旦在一国获得进展就很容易对周边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冲击波,以图进一步在其他地区扩展影响,开花结果。中国公众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的历史记忆最深,因为此次国际危机事件引起了中国公众舆论的激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波动,以致中国公众心理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阴影在此之后的若干年仍挥之不去。21世纪初在独联体、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和近年来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给世界其他地区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动。中国政府和国内公众的心理和精神对这些事件一度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然而,比较自信的是,此时,中国公众心理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比,对国家自身的建设保持了更大的信心,“颜色革命”难以撼动国内舆论变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7月13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以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在世界排名一直高居第一。其中,2011年的满意度调查显示达到85%,不满意仅有10%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报告参见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apter-5-economic-issues/。。
就第二类国际危机而言,中国与周边不少国家也都存在着历史认知心理方面的矛盾。但是,让中国人最为敏感,也常常作为受伤害的感觉者的矛盾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华人的待遇问题上,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往往使中国人成为受伤害的感觉者。中美之间,则由于历史上美国政府在国共内战时期采取的援蒋反共政策和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之间发生的面对面的战争、冲突、对峙,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此类矛盾。但是,与中日之间问题的敏感性相比,中美间的这类矛盾没有中日间的矛盾记忆深刻,感受强烈。但是,在遇到重大的国家间的外交危机时,中美之间的现实冲突往往会勾起中国公众的在历史上的受伤害感,因而在公众心中急遽地激起对美国的仇视,这对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国家的对美政策甚至是中国国家安全都形成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美国炸馆事件和21世纪初的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公众都展现了此类受伤害的政治情感。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些国外学者比较片面地认为,当年中国国内公众公开而有序的对美抗争事件是中国官方操纵鼓动的结果,而非真实的民意表达。实际上,事情并非如这些学者估计的那样,如果不是官方的有序管理,民间对美抗议的极端政治事件的出现也并非不可能。充斥在中国公众心中对美国的愤怒情感是真实而非虚假的。相对而言,中俄之间、中国和欧洲的英德法等国家之间,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尽管历史上也出现了后者对中国的长久伤害,但是,较近历史上长期的友好交往使这种源于历史认知的受伤害感逐渐淡出人们的近期记忆之中而潜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里。但是,这种对早时历史经验感情的记忆并没有消失,一旦现实中发生的重大的国际危机事件伤害了这种民族感情时,知觉的选择性往往使这种历史上受到伤害的情感记忆又可能被重新提取出来,并展现到现实之中。近年来,中国与欧盟个别成员国之间屡次发生外交危机时,国内部分公众就表现出了对这些国家人和物的敌视情绪,特别是民间在近年来因故宫文物在欧洲国家被拍卖而表现出的强烈的受伤害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侵略中国这段痛苦的历史记忆引起的受伤害感的重拾。
相较于中国与以上国家之间在历史认知心理层面的冲突而言,中日之前的这类矛盾则显得极为深刻和复杂。有关日方靖国神社的参拜,历史教科书的撰写、审定和使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的否认甚至对这一事件中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具体数字的质疑、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质疑、侵华日军遗留的弹药、毒剂的重新发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等等,这些都已深深刻在了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历史基因之中,成为高悬在日本人头上的达摩斯之剑。根据中国社科院对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的一项提及率调查—“提到日本你首先会想到的”,“侵华日军”、“靖国神社”、“太阳旗”赫然跻身于前六位之列;根据北京—东京论坛每年在中日两国间开展的同步调查资料显示,自2005年至2011年,“南京大屠杀”的提及率多年高居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也都居于第二的位置。历史问题对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所以,只要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中日之间就会因此而出现轩然大波,而这样的事件几乎每年都不断发生。今年2月份的名古屋市长的言论再次引发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层面的矛盾,并进而将两国中央政府也牵连进来,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勾起了中国人对日本侵华特别是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的沉重记忆,中日关系再一次在短时间内处于风口浪尖之中。回忆2003年发生在民意领袖和中国普通民众中有关中日历史问题、中日战略方向问题的激烈争议,当时,中国有部分民意领袖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中国要宽大地处理这一历史认知问题,对中日关系采取新的战略思维,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主张在当时小泉顽固参拜靖国神社肆意挑战中国人在历史问题的心理认知层面的受伤害感的背景下受到了国人普遍的猛烈批判,这些民意领袖本人也多被视为异类、汉奸。在这种激烈的国内舆论背景下,很少再有民间智库人士敢于大张旗鼓地呼吁呐喊要宽大处理中日间的历史认知问题了。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对日关系的外交实践方面实际上基本采纳了上述战略学者的思想,中日间也已经确定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在面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时,中国的战略学者们在这一历史问题上则逐渐趋于沉寂,从而表现出了对中国公众舆论的很大程度上的屈从而非抗争。所以,在面对历史认知心理方面的外交危机挑战的时候,民意不可逆的强大压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对此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以防违逆此种民族主义情绪带来不测的政治后果。
就第三类国际危机事件而言,中国的公众舆论和外交也深受其扰。中国漫长的陆路边界和海岸线使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领土、领海问题之争。其中,陆路边界矛盾多数已经通过两国间的相互协商在官方层面得到解决,但中印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依然矛盾重重;领海划界和部分海岛的归属问题则广泛存在于中国与周边的日本、东南亚诸国之间,特别是中日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矛盾每年都可能多次展现出来,并因而牵连出相关的历史记忆,今年也毫不例外,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交锋你来我往,连续牵动着公众的心绪。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与表现活跃的菲律宾和越南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执较为抢眼,这些争执受到国内公众的持续关注,由此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民间话语在此问题上展现的火药味也非常浓烈,从而成为考验中国政府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组织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大量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的海外人权和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并时刻牵动着国内公众的神经,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中国在非洲、中东、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能源开发地的经济利益和为运输这些能源、资源而对海上航道和陆上管道安全的关注对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的外交政策的选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利益的扩展同样涉及发达国家。近年来,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广泛展现在气候与环保政策领域、贸易政策纠纷和贸易逆差、经济并购的设限与发达国家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持续施压、市场开放与市场国家之争、原材料资源(特别是近来热议的稀土)出口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牵涉面较广,任何政策性的变化都会波及并影响到国内利益攸关方的高度关注。因而,对这些问题国内公众的基础不能不察,对这些问题在国际领域交锋动向的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国内结果不能不多作研究。
现实利益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利益就是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在战略安全领域引发的国际危机事件对中国国内舆论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它往往与多类矛盾夹杂在一起,既可能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相关,也可能进一步勾起中国公众对受伤害历史的记忆,造成战略安全矛盾与历史认知心理矛盾彼此相互循环加固的作用。以中日之间在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矛盾为例,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美同盟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不信任感,加固了前述的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人的消极心理认知,因而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现实原因。尽管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自身合理的安全需求,但中国公众对此难以理解。所以,一旦日美在国家安全战略领域出现任何新的举措,如日美合作部署反导系统,都会在中国公众的心理上投下沉重的阴影,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除此之外,中国公众同样难以理解日本人扩大自卫队功能、修改和平宪法、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大与印度的战略合作等做法,并对日本走和平国家道路的说法深表怀疑。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公众认可的未来日本国际身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大国、和平国家方面,而非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方面①李慎明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中印之间在战略安全领域存在类似的冲突:印美日多边合作或印美、印日双边合作以及印度的东向战略都会挑战中国公众心理承受力,引起一定的社会震动。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成员国之间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战略安全的矛盾冲突。在上述中国与周边国家潜在的战略利益冲突背后,始终闪现着一个大国的身影—美国,美国积极发展与中国领海、领土周边国家的双边军事—政治战略合作关系,并积极对有中国参加的多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美国的这些战略行为的意图不让中国公众怀疑都很难,这正如中国如果在美国全球利益的周边发展类似的军事—政治战略合作关系一样,中国要不让美国公众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也很难。
三、结语
综合以上的分析,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上述三类国际危机事件的划分主要是为了分析便利起见,实际上,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上述三类危机往往相互夹杂在一起,比如宗教—政治性国际危机事件中可能夹杂着事关历史心理认知冲突或国家现实利益矛盾的根源,而事关历史心理认知冲突或国家现实利益矛盾的根源彼此夹杂在同一国际危机事件中的情况就更为常见,并相互加固了另一矛盾的存在。
第二,在三类国际危机中,由于第一类国际危机可能会在国内造成政治反对派,因而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稳定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是致命性的;而第二、第三类国际危机激起的国内公众舆论既可能会凝聚起国家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力量,强化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它也可能会使政府因顾及民情的压力,而无法在当下执行国家既定的对外政策。所以,中日外交中出现的所谓“走廊外交”和“电梯外交”与其说是展现了两国政府和外交官的睿智,还不如说是中国公众舆论情绪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得到释放的一种表现。
第三,针对三类国际危机事件在影响国内公众舆论功能、性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应对第一种危机事件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要正视自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积极的努力创造条件,在发展和改革中渐进式解决自身的不足;应对第二、三类危机的办法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逆,但耐心合理的引导策略也绝不可或缺,否则,熊熊燃起的民族情绪固然可以构筑起一道保家卫国的火网,但是,一旦失控也可能蔓延以致摧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何希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国内舆论引导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CZH219)。
作者余金城,男,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北京 100048)。
责任编辑:孙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