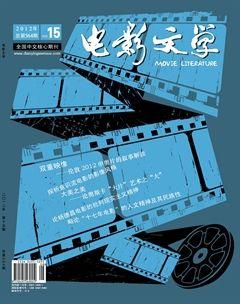第五代电影传播与农民启蒙主体(一)
[摘 要]电影《菊豆》表现了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搏斗和较量。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分别对应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两种主体:“统一主体”和“过程主体”。前者相当于拉康象征秩序中的主体,而后者则相当于象征秩序中的异端,具有一定的反抗性。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女性个体的身体,成为其反抗象征秩序的动力。菊豆的身体欲望一旦喷薄,便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她凭借女性的身体本能,充当了封建宗法制的叛逆者,成为第五代农民主体电影中具有启蒙特征的文化主体之一。
[关键词] 《菊豆》; 克里斯蒂娃;统一主体;过程主体;女性;身体
新锐视点MOVIE LITERATURE
MOVIE LITERATURE新锐视点
如果说《红高粱》表现了对一种无拘无束感性生命力之张扬的礼赞,那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揭示了“铁屋子”对自由生命的禁锢与扭曲。有着新思想、倔强叛逆的女学生颂莲,一步一步自觉地沦为封建宗法制和父权制的受害者和迫害者。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压抑人生命自由的外在因素,而且还揭示出人内心深处的奴性意识是导致人自身被压抑、被奴役的根源,反映了封建集体无意识传统对人思想的历史惯性作用和影响。与《红高粱》的酣畅淋漓相比,这部电影的基调阴郁沉闷。一个自由奔放,一个压抑阴沉,代表了自由和不自由的两极。相比之下,张艺谋的“红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菊豆》,则介于两者之间,它表现了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搏斗和较量。
一、“统一主体”与“过程主体”,
“符号态”与“象征态”不甘受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与不甘被挑战的象征秩序分别对应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两种主体概念。克里斯蒂娃区分了两种主体:“统一主体”和“过程主体”①。这两种主体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类事物,而是同一主体的不同构成部分。“统一主体”相当于拉康象征秩序中的主体,“当代精神分析学理论提供了一种主体理论,将主体视作分化了的统一体,它产生于一种缺失(根据文本的不同,可以是空、无、零),并由这种缺失所决定,它对由换喻式欲望所代表的不可能的事物进行一种未得到满足的追求。这个主体,我们将称之为‘统一的主体,在一(one)的法律下,结果证明是父名(the Name of the Father )。”②“过程中的主体”产生于象征秩序建立之前,但在象征秩序建立之后,“过程中的主体”并未消失,而是存在于象征秩序内,并受父法、权力压抑而不断产生抵抗冲动。
根据拉康的理论,语言符号及其系统(词语、句法等等)都是象征秩序的产物,而“过程”则对这个包括语言符号及其系统在内的一切象征法体系具有消解作用。过程主体的冲动,在统一主体身上组织起来,并超越统一主体的身体,构成一个破碎的形状;这种冲动反映在艺术上,就形成一种反抗性,即所谓的“先锋艺术”:“‘文学先锋——即便仅只在边缘上——用过程的主体表现了社会,向统一主体的全部僵化壅滞发起攻势,它攻击封闭的意识形态系统,也攻击社会统治(国家)的结构,并完成了一次革命,却不是其乌托邦或无政府的时刻,而事实上指向了革命本身对进行革命的运动的盲目性。”③而过程的活动发源地所被命名为“子宫间”(chora)。④“子宫间”这个术语源自柏拉图,意指一种“母性容器”,相当于一种本源性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子宫间”应该是与“菲勒斯”相对应的东西。拉康所言的象征秩序就是以“菲勒斯”中心建立起来的,“子宫间”是一种前象征秩序的事物,是一个二元不分的混沌之所,与人的欲望和本能相联系。如果说“菲勒斯”是“有”,那么“子宫间”则是“无”;象征秩序是在“菲勒斯”之“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子宫间”之“无”则以否定性(或者拒斥)的形式对象征秩序进行破坏和消解。“子宫间”是符号活动的聚集之地。
克里斯蒂娃用“符号态”(The Semiotic)和“象征态”(The Symbolic)⑤的区分来替代拉康的“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区别。“符号态”的运动发源于子宫间,当然也是前符号领域内的事物,同时它们也存在于象征秩序之内,是象征秩序所压抑和排斥的异端,时常以断裂、破坏、颠覆象征秩序的面貌而呈现。“符号态”虽然与女性紧密相连,但绝对不是女性独有的特征。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乔伊斯、塞利纳等男性作家的语言也是符号态性质的。因此,克里斯蒂娃关于主体构成的“符号态”实际上是“主体的他者”,是主流话语形式的边缘,具有对象征秩序的整体符号系统进行反抗、颠覆的冲力。这样“符号态”就与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相连。
在主体理论的构成中,克里斯蒂娃在拉康话语主体理论基础上,区分了符号态与象征态在主体生成与意义构成中的不同作用,前者是通过符号运作而建立结构的意义系统,后者是符号系统的驱动力,它与节奏、音调、身体姿态等相连,是超语言或者非语言的。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关系使意义生成过程得以进行。正是这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使得符号表意过程成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使得话语主体成为过程中的主体。
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主体”以及“符号态”阶段,实际上是整个象征秩序中的他者,它的驱动力是充满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及本能欲望。“统一主体”以及“象征态”阶段对应的是整个象征秩序,它有一套固定的结构模式,将每个个体纳入到它既定的位置和轨道中去,这个过程相当于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召唤”。“象征态”排斥作为异端的“符号态”,因为后者老是不安于既定的文化秩序、规则,并对其所在的象征秩序有着反叛、颠覆的功能。
二、《菊豆》中四种“名不副实”的关系
电影《菊豆》所要传达的全部思想可以通过片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图来表明。
四个人组建了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跟别的家庭结构不太一样,归根结底是一种名与实或能指与所指或符号态与象征态之间的二分法的错综交杂。从名义上看,家庭结构是:菊豆与杨金山是夫妻关系,菊豆与杨天青是叔嫂关系,杨金山与杨天白是父子关系,杨天青与杨天白是兄弟关系。但从血缘上看,这四个人之间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菊豆与杨金山是夫妻关系,菊豆与杨天青是情人关系,杨天青与杨天白是父子关系,杨金山与杨天白没有任何关系。
儒家思想十分注重礼仪,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礼仪界限清楚分明,否则就乱了伦理纲常,这是传统文化之大忌。从封建宗法制度上讲,菊豆和杨天青的关系是非法的(封建礼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乱伦。然而,是不是真的乱伦呢?电影对此提出了与传统不一样的看法。
儒家礼仪文化建立于血缘关系基础上,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无来制定不同的礼仪制度。“父子”的名义当然也要有真实的血缘关系做基础,所谓名副其实也。电影《菊豆》中,杨金山与杨天青并不存在血缘关系。那么他俩的“父子”关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
再来看杨金山与菊豆的关系,是第二个名不副实。杨金山与菊豆结合,实乃买卖关系。洪水峪的小地主杨金山用三十亩山地的家当,换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菊豆。而杨金山买菊豆的目的,也只不过想要一个子嗣。杨金山曾经有过一个老婆,前妻跟着他30年,没有生育。事实证明,是杨金山本人缺乏生育能力,却把责任怪罪于他所娶的女人。在这场交易中,菊豆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她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任人摆放,任人宰割。小说《伏羲伏羲》写道:
对于王菊豆,她是他的地,任他犁任他种,她是他的牲口,就像他的青骡子,可以随着心意骑她抽她使唤她。她还是供他吃的肉饼,什么时候饥馋了就什么时候抓过来,香甜地或者凶狠地咬上一口。在女人眼里,他成了野兽。
一个20岁的鲜活的身体,面对的却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却又垂死挣扎的野兽。电影中,菊豆夜里凄惨的叫喊以及布满伤痕的身体,都在充分说明这是一个被古老封建宗法和男权社会所伤害的女性个体。
菊豆和杨金山的夫妻关系,实际上也是有名无实。在这种情况下,菊豆和杨天青的结合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小说里杨天青只有16岁,电影中杨天青的年龄却“小四十了”了。杨天青名义上是杨金山的侄子,实际上不过是他家的长工。年近50却没有生育能力的杨金山,用象征财产的土地换来了青春貌美的女人。而真正年富力壮、生命力旺盛的杨天青,却因为贫穷而一直光棍一条,而贫穷的原因正在于无法占有生产资料。而菊豆也是因为家里贫穷,其父贪财,才把她嫁给年老的杨金山。不管是菊豆还是杨天青,都是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民,都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可这两具青春的肉体却结合了。这种结合来自于一种内在的生命欲望,一种压抑已久的原始生命激情。生命激情的迸发唤醒了他们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属于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符号态主体。它必然要受到来自象征秩序的压制。象征秩序首先通过命名来定义菊豆和杨天青的“非法”结合,这个罪名就是乱伦。也就是说菊豆和杨天青的结合犯的罪只是符号性质的——对封建宗法制和家长制的冒犯,即符号态对象征态的不轨和挑战。
然而这种基于原始本能欲望之上的反抗是自发的,缺乏自觉性和持久性。面对瘫痪失语的杨金山,杨天青的内心依然充满恐惧。虽然在身体上他富有激情和干劲,但在精神上,他已经萎缩了。这一点,他与余占鳌形成鲜明对比。杨天青自觉认同封建孝道,对杨金山一直不离不弃,甚至在本该帮助菊豆而应该伤害杨金山的时候,他仍然站在杨金山这边。当菊豆指责他因守孝道而缺乏勇气时,他劈头给了菊豆一个耳光。这个时候,他行驶的是夫权。影片将杨金山的死设计成一个偶然的失误:杨金山在逗杨天白玩时,杨天白误牵水桶将杨金山翻入染缸,而不让杨天青亲手结束杨金山的生命,符合人物性格发展内在逻辑。杨天青不是封建社会的逆子。尤其他对菊豆的暴行更是彰显了封建思想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功能,让人感觉到思想启蒙和解放的艰难。而菊豆前方的路则更为艰难,比封建宗法制、家长制更甚的还有封建夫权制,压迫无止境。
第四个名不副实是杨金山与杨天白的父子关系。
杨金山一心想要一个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乃大”,这是封建思想意识最为典型的表现。在封建宗法社会,“儿子”的意义在于对家族命脉的延续,对“父亲”权力的巩固和“父法”地位的加强。杨金山曾经因为杨天白不是自己亲生的,而欲除之而泄心头之恨。但身体瘫痪的他却没有能力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尤其当他看着菊豆和杨天青在他面前无所忌惮亲热的样子,内心的愤怒、嫉妒以及报复的欲望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可恰恰是杨天白——他名义上的儿子,做了他想做却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杨天白自认为是杨金山的儿子,从而杀了杨天青。这一举动正是借用“父权”的力量,替名义上的父亲杀死了实质上的父亲。杨天白知道了杨天青与菊豆的苟合,将杨天青扔到染缸里,在菊豆非人的哀告声中,他用木棍冷酷而准确地砸上了杨天青攀在绞轮上的手,杨天青落入染缸而死。
尽管是一场“弑父”场景,但这个场景所昭示的却是“杀子”的实质。衰老的“父亲”,借“儿子”的生命来延续他的力量——杨天白对着杨金山而不是对着杨天青喊“爹”,这一声命名,给衰弱的杨金山补充了新的能量。杨天白以杨金山的名义杀死了僭越了父子秩序的不孝子。在“杀子”的寓意中,历史的巨大阉割力被再度呈现。即便杨金山去世了,他的棺材仍然作为统治者,高高在上,折磨着活着的人。电影用仰角特写镜头反复拍摄棺材,造成一种叙事功能。棺材的象征意义说明死去的只是个体的肉体,而封建宗法制度形成的权力却永远是缺席的在场者。
综上所述,如此多的“名不副实”,展示了一个“名”(符号)构成的象征系统,它用各种所谓伦理道德等名义编织了一个坚实、强大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一切都是设定好了的,它决定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遮蔽和替代了个体真正的存在,——那就是具有符号态意义的人的生命本身。
三、女性主体的悲剧
从故事情节看,《菊豆》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从买卖婚姻到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再到纵火烧园,菊豆的自我经历了一个从零开始的爆发过程。性意识的觉醒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叛逆首先从身体开始。女权主义符号学在个体层面上得出一种“身体性”(corporeality)理论。⑥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身体性是人类符号过程的主要地址;正是“子宫间(chora)”,是欲望、姿态和节奏的自动王国;而覆盖在子宫间上的是作为一种压制网络的符号秩序。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女性个体的身体,成为其反抗象征秩序的动力。菊豆的身体欲望一旦喷薄,便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她形成了爱恨鲜明的性格。一旦背叛了杨金山,她便异常决绝和果断。而杨天青的精神血液受封建宗法思想的侵蚀较深,通过他对瘫痪和失语后的杨金山的敬畏照顾以及对菊豆的暴力可以看出,封建宗法思想已经内化到他骨子里去了。他只有在秩序内享受和菊豆偷情的快乐,却无法和菊豆一起充当封建宗法制的逆子二臣。
无论是对于杨金山、杨天青还是杨天白,菊豆都不是一个主体。主体是对象征秩序的认同和臣服。只有臣服于象征秩序,才能长大成人,才能借助象征秩序的权力巩固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我们明白了杨天青何以对瘫痪失语的杨金山如此“孝顺”和“忠厚”,因为他想成为封建宗法秩序中的主体,或许杨金山的位置就是他潜意识里所渴望的。他最终没有勇气解决杨金山,也是因他和菊豆的“乱伦”行为无法获得象征秩序所认同的力量,所以他终于胆怯了。杨天白也正是通过二度“弑父”,而成为象征秩序的主体,而每一次“弑父”,都是对象征权力的利用和对自我的象征主体地位的巩固。
对于片中惟一的女人菊豆而言,她也只有成长为象征秩序的主体,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力和力量。而事实上,女性身体的本能使她天生成为也将永远成为象征秩序的异端,因此,她永远也不会有能力完成颠覆象征秩序的革命任务。也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对象征秩序的革命,只有通过男性才能完成。这里的男性,并非指生理意义上的男性,而是指象征秩序的权力获得者。女性永远只是象征秩序动荡不安的灵魂。
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电影《菊豆》采取的是象征的表达方式。电影中的人物、环境、背景等符号都并非仅拥有单一的能指,所有的一切都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再加上时间空间的抽象化以及造型设置上的中国风和民族色彩,使这部电影超越了单一的个体叙事,而成为整个传统中国的寓言和象征叙事。
于是,《菊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⑦的文本,通过寓言的方式,对传统中国人的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及主体构成进行了形而上层面的探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建立在对个体力比多高度压抑基础上的符号象征秩序,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正是整个象征秩序符号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个符号空间里,每个个体的位置都预先安排好了,只有压抑个体的自我才能进入到象征秩序中来,这正是象征秩序内的生存法则。真正自由自主的个体在象征秩序之内是没有地位的。对此,张光芒曾经批判道:“中国传统道德形而上太虚伪,其‘人只是伦理秩序中的一个符号。”⑧
注释:
① 这两种主体概念参考[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见汪民安主编:《后现代性 的哲学话语——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
②③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前引文,第120页,第124页。
④ 此术语,源自古希腊语“khora”,陈永国译为“容器”,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罗婷译为“子宫间”,见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⑤ 这两个概念参考Julia Kristev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Chapter1: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年版,第19-25页。
⑥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Indiana Univestity Press,2000年版,第20页。
⑦ 参考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原话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⑧ 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5页。
[作者简介]颜小芳(1982— ),女,湖南常宁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批评、现象符号学及叙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