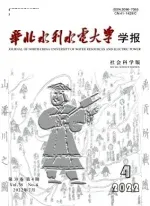价值理性与创新人才培养
田 逸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人文艺术教育中心,河南郑州450011)
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为此,高等教育任重道远。美国高等教育专家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是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P23)我国历史学家章开沅也指出,教育不能简单迎合市场,“科技决定民族命运”的论断是偏颇的,教育应该比市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就是说,我们培养创新人才,不仅要着眼于促进现代物质文明,还要着眼于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否则,前者的成果也保不住。换句话说,培养创新人才,不能只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考虑,还应该对价值理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创新人才需要价值理性的熏陶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二者是人的理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的理性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两个目的:一个是物质性,即工具理性,往往将金钱、技术、财富、效率等作为现实追求的主要目标,功利色彩较浓;另一个是精神性,即价值理性,体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从概念上不难理解,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给人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不断满足和提升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生理欲望。两者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考虑到两种目标取向,两者缺一不可。在教育教学中,既要爱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培养其探索精神,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教育学生胸怀理想,志存高远,关注人类未来,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拥有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创新人才。
价值理性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其动力性,它决定着创新人才的步伐能走多远,成就能有多大。爱因斯坦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这种品格体现为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对事业的极端热爱,摆脱了金钱、权势、地位的诱惑,完全超然物欲之外,以平静之心对待世俗。钱学森先生也是这样,以淡定之心面对权力地位,以淡然之心面对物质利益。他曾坚决拒当科协领导,甚至为此发火,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也决不退让。他之所以放弃“做官”,就是为了心不二用,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科学探索之中。也只有这样,钱学森才能成为优秀的创新人才。这种品格还体现为有志存高远的理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北宋哲学家张载说:“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即没有长远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是毋谈创新的,更不可能有造福人类的创新之举。
创新还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于峻岭矣”(《抱朴子》)。被称为“科学疯子”的诺贝尔经历了发明过程中多少次惊心动魄的爆炸和荆棘丛生的阻力,才获得了成功。“两弹元勋”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总是出现在第一线。在原子弹坠地被摔裂的情况下,他把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查。所有这些,都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品格在创新中的作用非常强大,价值理性的价值不可估量。
二、价值理性缺失的现实表现
为什么创新人才缺失,在我们思考“钱学森之问”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糟粕,比如:急功近利的实用思想;追逐名利的人生哲学;重做人、轻做事的价值取向;重服从诠释、轻质疑批判的思维习惯等都可谓价值理性在中国文化中的缺位。造成的后果是:不愿意探究真理,喜欢模糊,应付了事;不敢超越,宁要面子,不要真理。
在高校,由于价值理性的缺失,工具理性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学生纷纷报考“热门”专业。就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来说,该院自称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能吸引全国优秀的中学生报考,连续几年每年都有五分之一的全国各省、市高考第一名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其中2008年招收文、理科高考状元24名[2](P14)。工具理性思想弥漫在学生求学的过程中,不少学生缺少对课程本身的兴趣,满足于拿够学分,顺利毕业。学生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各种证件的考试上,目的是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在一次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调查中,当问到理想的前进方向时,只有15%的学生选择追求真理,在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中创造自己有价值的人生;而有57.9%的学生选择了有称心如意的工作、幸福的家庭;4%的学生选择随遇而安,没什么理想;还有23.1%的学生选择开创事业,但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其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暴露无遗[3]。所以,有学者说,大学校园里走过的都是匆匆的脚步,都在追逐一个近在咫尺的目标,没有人坐在那里痴迷于学问,静静地发呆,思考一些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4]。
反观美国的大学,越是好的大学,就越是设置一些看似没用的课程,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最流行的专业通常是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已故的创新大师乔布斯就是这样,喜欢那些看似无用的课程,比如英文、书法课。他曾说:“如果我在大学里,没有旁听过英文书法课,Macintosh电脑就不会有那么多漂亮的、比例匀称的字体”。乔布斯还迷恋禅宗,品读《禅者的初心》。在这本书里,乔布斯看到了一个洁净、澄澈、可以任由思维自由行走的理想世界。他的各种独具创新的战略思考和产品设计,都反映了他参禅悟道的思想。为了参禅求佛,他不远万里到印度旅行,在那里他看到田间劳作的人使用的还是几千年前的原始工具,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好用的工具将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帮助。为此,他油然而生一种激情:我要改变世界[5](P35-36)。
三、大学应为价值理性的培育提供沃土
2011年10月20日至22日,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创新人才组)和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联合召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与会人员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拔尖创新人才不是“拔”出来的,而是在适宜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创新人才的成长有规律可循,比如在幼儿园是播种期,小学是萌芽生根期,中学是生长发育期,大学是开花期,岗位是结果收获期。也就是说,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个环节各有其使命。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如何为创新人才的“开花期”提够足够的动力和养分,在价值理性的培育方面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一)在创新精神的塑造上,要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
科学精神首先体现为求真精神,一种相信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相信这个世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吸引着人们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精神还体现为一种求实精神,即以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态度和作风,通过耐心、细致地观察以及周密严格的推理,从而得出结论并接受检验。人文精神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是对高尚和人性美的追求。没有人文精神支撑的创新必将误入歧途,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就像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各种人体试验,就像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让人口诛笔伐的“瘦肉精”。人文精神也是创新的源泉,如果一个人投身的事业不是立足于为人类、为社会做贡献,而只是给自己带来名和利,那么他的创新活动是不会持久的。所以,作为创新精神的组成部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在大学教育中,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使大学生志存高远,心系天下,放眼未来,把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学校要努力营造浓厚的“崇尚真理、热爱科学”的文化氛围,形成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
(二)在创新品格的锤炼上,要做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行
专业教育是学生未来的立身之本,也是创新的基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开专业教育来谈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新品格的锤炼。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流行职责专门化,但事实上正是专门化使我们达到了今天的高度,而且只有更高程度的智力专门化,才会使我们更进一步向前发展。”[6](P46)当然,狭隘的专业教育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创新品格的养成,所以,必须有通识教育的跟进。通识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学生知识丰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思路开阔,从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古今中外杰出的创新人才,很多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素养于一身。正像钱学森先生所言,科学上的创新仅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维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通识教育除了解决创新的思想和方法问题,还能解决形成健康人格、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提升团队精神和管理能力的问题,这也是创新品格的应有之义。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行,要求我们在大学教育中,除了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外,更要培养其宽广的人生视野、开放的胸襟、良好的表达能力及独立成熟的人格。在专业教育上,注重学术性、针对性和时代性;在通识教育上注重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
四、在创新习惯的养成上,要做到从严治校与尊重宽容并举
作为工作、创业的准备期,大学教育将为人才创新习惯的养成奠定基础。这种创新习惯表现为:对规律、规则的坚守,对数据、结论的尊敬,对权威、传统的怀疑。为此,大学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坚持做到从严治校与对学生的尊重宽容相结合。
从严治校要求教师从严执教,以一丝不苟的教风带动严肃认真的学风,从作业到考试,从实验到设计,从论文到成果,都严格要求,确保质量,不能有迁就照顾的思想,否则,学生就会有投机取巧的心理,那是创新的大敌。从严治校还要求教师及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从严治校要求学校净化学术空气,铲除功利与浮躁的土壤,对抄袭、剽窃不姑息,对伪造、篡改零容忍,让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无立锥之地。
从严治校,严格要求并不意味着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相反,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挑战权威,要保护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要以灵活的方式开展教学。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不同意见,对那些确因兴趣原因想转专业的学生,应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在学籍管理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或者给予老师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在西南联大,有学生在杨振生老师所教的古诗课上,就“车轮生四角”写了一篇名为“方车轮”的研究报告,杨老师看后很满意,随即宣布该生免于期末考试[7]。西南联大培养了一代影响深远的杰出创新人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既严格又自由的教风和学风。
[1]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薛涌.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3]万远新,等.大学生理想信念问题调查[J].卫生职业教育,2011,(1).
[4]陶东风.从大学精神看高校软环境建设[N].中国教育报,2008-12-29.
[5]王咏刚,周虹.乔布斯传[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6]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李光荣.一所大学和一代英才[N].中国教育报,2009-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