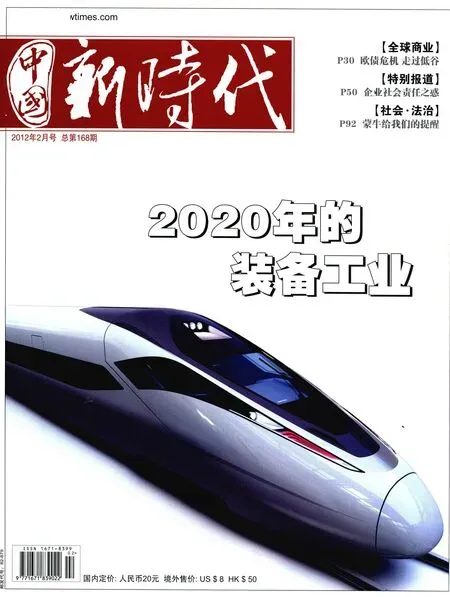解开这个千年结
| 文· 李明
政商关系不正常,是中国两千年企业发展史中的死结。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开这个历史千年结的最佳方法

《浩荡两千年》作者:吴晓波出版:中信出版社时间:2012年1月
牛气的巨鼎
许多人从历史课本中知道“司母戊大方鼎”。这只重833千克,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的精美绝伦的商代青铜大鼎,现在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好思考的人忍不住要问:3000年前是怎么造出来它的?总工程师是怎样的人?他组织了怎样的制造团队?他通过怎样的管理办法以保证质量和效率?
北京大学的学者如此描述这个大鼎的铸造:
第一,大鼎的铸造者是位化学家,娴熟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大鼎的铜占84.77%,锡为11.64%,是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第二,他是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第三,他必须是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才能熔化,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才行。第四,他还是位冶炼家,大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千克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是位优秀的管理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至4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总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总之,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产物。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绝对可称为伟大的企业家。你也不能不惊叹中国人在商业上的早慧。
“费正清难题”
然而,你也不能不感叹中国迟迟仍未建立起完善的商业文明。中国人是善于经商且乐于经商的民族。从经济要素看,中国也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例如,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像宋代出现了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元代有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但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中国竟停滞而远远落后了!以铸铜冶铁业为例,商代能造巨型铜鼎,汉代冶铁作坊规模已达千人以上,清朝末年的冶铁作坊却几乎没有扩大。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却与之大体一致!据台湾学者赵冈研究,唐宋两朝,中国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晚清时竟只有6.9%。更让人觉得悲凉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被妖魔化和边缘化。
面对商业文明与史实的矛盾,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提出:“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我们可以仿照科技史上的“李约瑟难题”而将之称为“费正清难题”。
吴晓波以司母戊大方鼎为起点,在《浩荡两千年》中,试图厘清公元前7世纪至1869年的漫漫两千年中的中国企业发展史,对费正清难题进行分析解答。
四个经典困境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吴晓波认为,钱穆总结的这两条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角度;中国两千年企业史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经过众多制度创新,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支柱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稳定,以国有专营制度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抑商”。由此出现了四个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一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界限分明,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
二是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中国民间的商品交易极度活跃,初级市场发达,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非常清晰,但从来没有确立政府与民众间的对等契约关系,国家机器常常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维稳,对于工商阶层及其财产拥有不受约束的处置权。
三是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授权不明等,又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都发生在“顶层”。同时,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利,从而催生出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著名经济史学家王亚南和傅衣凌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四是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中国商人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富不过三代”,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脆弱的、不对等的关系,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在财富传承上远不如保持政商关系的能力重要。费正清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如何解开这个结
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下,中国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中国历史上,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任民间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6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回到高度的中央集权,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而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下降,就会迅速产生大的社会动荡,直到最终新的威权树立。商人阶层在此常常成为最早受到大动荡侵害的族群。
两千年历史中,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政府如何与工商业者平等相处,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的正常关系是一个结。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