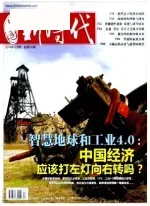未来 我们在哪里养老
| 文· 本刊记者 陈婧
如果老人问题现在还不是你的问题,它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你的问题。而在整个行业处于萌芽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公司的经历都值得关注和肯定,因为正是这些创新、经验和教训,在一点一滴地推动行业的发展
截至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3.3%,而10年前,这一比例刚略高于10%。
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超总人口的1/4,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这是个庞大的市场”,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黎雪荣表示,2010年国内养老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而从老年人制造用品市场来看,预计十年后,中国中老年人用品市场份额将上升至2万亿元。
尽管如此,在黎雪荣看来,中国的养老产业目前仍还处在“沉睡”阶段。
以养老机构为例。国内的养老机构类型大致分为三类:福利性质的养老院、政府和社会合办的敬老院以及民营养老院。其中,以价格低廉,条件稍简朴的福利性质养老院居多,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计算下来,65岁及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只有约23.6张,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多达50-70张。
需求、缺口意味着商机?
外资涌入养老领域
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逐利者。老龄化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吸引很多外国投资者将目光瞄准至中国,而同时由于中国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和投资房地产市场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因此外国投资者转向这个新的投资机会——私营养老院产业。
德国最大的社会服务企业奥古斯汀集团旗下银龄养老院是首批进入中国新兴养老院产业的外资企业之一,它接下来的计划在北京市中心西北40多公里的小汤山建立拥有525幢房屋的养老住宅区。

美国医疗国际集团宣布在中国杭州建设大规模的国际旅游医疗中心
早在2006年6月,德国奥古新诺颐养中心就落户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并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建成投入运行。在德国本土,知名的奥古斯汀养老院针对的消费群体是月收入1000欧元、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老人,但奥古新诺上海颐养中心锁定的客户人群是所谓的“高端”人士,如当地的富裕家庭、华侨、中国留学生的父母,以及跨国企业外籍主管人员父母等思想较为开化的老人。顶级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所需的费用自然不菲,老人入住时所交付的押金数额,大致等同于该房间的产权价格。
而在2008年10月,一家名为“夕阳红康乐中心”的外资养老院落户于江苏省江阴市,由美籍华人虞觉惠投资1000万美元建成,号称要把欧美最流行的社区养老模式引进到这个富庶的江南小城。老人们住进来后,吃饭、疗养、康复、学习、娱乐、购物、休闲,一切问题全部解决,其模式与奥古新诺颇有些类似。如今,在这里入住的老人已有上百人。
还有更多甚至更大的玩家。
皇家养老庄园管理公司是日本的专业管理高端度假型养老、养生设施的管理公司。它在中国走出的第一步是,与投资方合作,建养老庄园,然后负责管理运营。目前,皇家养老庄园管理公司已在海南、绍兴、昆山、杭州找到了投资合作方。
美国对冲基金与收购集团城堡投资(Fortress Investment)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运营着规模最大的老年人独立居住设施。明年,城堡投资计划募集一只约10亿美元的基金,面向中国迅速扩大的老年人口住宅。
显然,与国内的民营养老机构不同,这些大资本所看好的都是价格不菲的高端养老机构。鞠川阳子(Yoko Marikawa)是一名侧重于养老行业的日本顾问,她表示,在其客户中,有近一半的人在中国已经或计划推出养老机构,预计总投资额在150亿-250亿元之间。
“关键是企业和投资者要找到准确的下水点。”鞠川阳子认为,老龄市场是动态的,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可以引导。企业在开始可从某一个细分市场进入,再慢慢扩张到其他市场,逐步完善产业链。“日本、欧美等都是很发达的老龄产业市场,其经验、技术和商业模式经过一定的本地化过程可以为中国企业拿来使用,这是最快捷的方法。”她说,“现在,一些投资者认为这一产业具有高回报率,因为政府提供了减税措施。”
与中国很多养老服务的参与者相比,这些外资机构在发达国家已经运营多年,拥有足够成功经验来满足中国社会将要面临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部分老人失能化等“四化”叠加引发的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精神慰藉等需求。
但让它们难以启齿的现实情况是,“目前我们国家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不到1%,而发达国家的机构养老达到57%,”鞠川阳子说。依据国际经验,西方国家的老人在养老院度过晚年的比例大约是5%左右。而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比例偏小,大约在3%上下。在提供高端服务的同时,养老院也将面临客源难觅的困惑。

文化桎梏
在北京市新建的一家外资养老中心内,方连山(音译)弓着腰,吃着一盘炒牛肉。
回想起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和41岁的独生子生活在一起时,这位78岁的老人说:“我们之间有代沟,最好给彼此留些空间。”
以前,由于住宅短缺,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起,但方连山表示,人们如今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影响。“我的许多朋友都独自生活。他们不喜欢和子女住在一起,”而他也在一年前搬进了这家养老院。
2010年,据奥美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6%的受访者表示同意到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居住。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出对养老院的抗拒。
在北京城区的东山墅小区内,刘先生已经快60岁了,生意做得很成功,作为儿子,他说:“我父母肯定还是愿意和我在一起,再说,把他们送养老院人家也会说我不孝顺。”作为父亲,他说:“孩子要是想让我去我就去,也给他们减轻点负担。不过,从内心讲,我还是愿意和孩子住一起。”
王先生刚刚从美国回来,在一家外企任CEO。他坚决反对将父母送到养老院去:“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对中国老人来说,家庭还是第一位的,家庭成员间互相依赖的程度非常高。在养老院的话,生活等等可能会比较方便,但和亲人见面交流的机会很少。况且,送到养老院和请家庭护理的费用差不多,那还不如留在家里,每天还能见到。请保姆在家,医生可以定期上门,什么事都解决了。”
他的母亲也不愿意离开家:“我的老头去世好几年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媳妇和孙子。虽然孩子都比较忙,不能老在身边,但我们毕竟住在一起,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也感觉离他们很近。他们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我不愿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再豪华也不去,里面没有亲情。”
这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在西方等发达国家,高端养老产业在社会总体趋势的发展下应势而生,而在中国这个尚未成形的市场中,这些外资养老机构不仅要担负着开拓市场的指责,更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启蒙者的角色。
而与这些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正处于一代一代向前开发的开放状态,“在西方或者日本社会中,一般来说六七十岁的老人会比三四十岁的人更富有,他们是高端养老机构的直接销售对象,而在中国,大多数三四十岁的人会比自己的父母有钱,这些儿女的意见才是决定是否去养老院的主要因素。”鞠川阳子说,另外,文化变迁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根据中国引以为豪的长期孝道传统,上了年纪的父母决不能单独居住。
鞠川阳子是“银色之城”一词的发明者,和当下谨慎的投资者一样,在中国,她观察了五年才决定注册这家专门提供养老产业专业管理公司,“很多国外投资人认为,养老产业在中国是不可碰的一个产业,如果这是能赚钱的买卖,中国人这么精明,怎么没人做呢?况且在中国这是个很麻烦的产业,不光是伺候老年人麻烦,管的部门多,更麻烦。”
但在她看来,这种文化的迥异在不断地改变, 根据中国市场的情况,一些外资机构在进入后也相应调整自身的服务定位,将养老引入到家庭中的相关实践已经开始。任爱华是美国最大养老护理公司之一,2011年6月9日,其首家经营所落户北京,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以个人护理和专业护士为主、家庭照护为辅的团队入户服务。“其实,不少城市都有类似模式: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包括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日常护理等多项服务”鞠川阳子说。
“商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业今后肯定会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现在这个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由于文化等隔阂,这些公司还没有找到好的商业模式,且盈利能力不强,现在只能将目标锁定在高端客户。”
理想与现实
事实上,外资养老院进入中国市场还将面临很多挑战。而目前,无论是外资养老机构抑或是本土民营养老院,养老机构的发展越来越困难,其中房价的不断上涨是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养老机构得以发展,原因之一是在房价较低的时候抓住了机遇。如今,即使政府非常鼓励社会力量办养老院,但是有心大规模投资养老院的社会资本还是首先在拿地环节就遭遇了困难。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认为,土地是稀缺资源,批给房地产商,马上就有一大笔收入;批成工业用地,马上就有税收;批成养老院,什么现成好处都没有。
按规定,投资养老院,国家有许多扶持政策,如免缴城市建设和房屋建设费用,免缴煤气增容费和城市供排水设施的收费,免收营业税,对所得税减免照顾等。
8月14日,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首次全国范围内的民办养老机构状况调查中显示,民间包括国外资本进入养老机构者越来越多,到目前比重超过60%。而同时调研还发现,对私营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尤其在地方。
不过,这些对于觊觎中国庞大老年市场的外资来说还不是最棘手的。
按照市场经济理论,需求会刺激供给,即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我国养老市场庞大,开个养老院挣钱营利来弥补优惠政策似应不费周折。然而,现实却大相径庭——只有部分地理位置优越,档次较高的养老机构有所盈利;而少部分位置偏远、新开张的养老院由于交通、成本等问题,入住率低,亏本负债经营。很多热情高涨的国际资本带着巨额资金准备一番作为时,遭遇了市场的冷水同时受到政策的限制,最后落得惨淡的下场。
2011年1月底,城堡投资的创始人韦斯·艾登斯(Wes Edens)为来中国投资的事拜访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在埃登斯看来,“做好这件事非常复杂与困难”,政府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为这类项目提供支持”。
“目前还不知道城堡集团如何在国内投资筹建养老机构,这几年外资投资国内房地产都是以开发或购买商业办公为主,但是外资私募股权基金准备投资国内养老地产,还是第一回听说,相信将会面临不小的障碍和难题。”鞠川阳子说,这在国内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外资能够如愿进入这一领域,仍然有待政策的放松,等待的时间也会相当漫长。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艾登斯也坦言做好这件事的困难。他想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运作经验带来中国,为老年人住宅业务提供在住房和饮食、精神层面以及医疗服务方面全面的保障。
而问题的关键就是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对于城堡投资而言,10亿美元投资只是一个小数目。“首先这10亿美元基金如要换成人民币,要获得外管局的批准,目前外管局对于外资股权投资基金(QFLP)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上海准备试点也仅限于不大的规模;其次外资投资国内养老社区这是第一家有意向的,政府是否同意也是关键因素,还有需要找到合适的国内合作企业,如果由外资单干,肯定是行不通的。”鞠川阳子说。
艾登斯想打造的是在养老模式上全世界最推崇的美国太阳城。美国太阳城从1961年开始开发建设,如今成为佛罗里达州乃至全美最好的老年社区,设计建造了各种户型以适应不同类型老人的要求。现有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住户1.6万,且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社区内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开设的课程和组织的活动超过80种。根据美国一项调查表明,生活在这样环境的老年社区中,平均寿命会延长10岁。而这些显然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在中国养老产业这片蓝海中,任何国外的行业巨头都会变成步履蹒跚的创业型公司,它收获阶段性成果,却也面临发展通则。一个年轻产业的成熟,往往需要无数浸满鲜血和泪水的失败来作为祭奠,不过也正是这些创新、经验和教训,在一点一滴的推动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