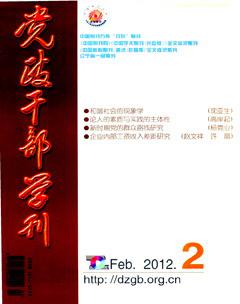基于绩效“行为
——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
蒋文能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 南宁 530021)
基于绩效“行为
——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
蒋文能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 南宁 530021)
SMART原则是衡量基于绩效结果观的指标的,当把绩效界定为行为或素质时,SMART原则将不再适用,必须寻求新的指标设计原则。本文认为指标设计原则来源于某种“关系”。据此,本文利用指标与评估目的、评估主体、评估客体和评估工具等四个绩效评估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来确立基于绩效“行为——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使得这些原则既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又可以整合成为一个系统。
绩效行为观;绩效素质观;指标设计原则;原理
指标设计原则是确保指标质量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因而在指标设计中都会给出相应的指标设计原则。然而,学者们在论述指标设计原则时要么只提“SMART”原则,要么阐述不深刻,寥寥数语,而且指标设计原则的内容和数量因人而异,差别极大,系统性和稳定性极低。究其原因,一方面“SMART”原则“剥夺”了人们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没有深究指标设计原则确立的原理 (或思路)。其实,“SMART”原则是设计关键绩效指标(KPI)的基本原则,而KPI主要是来源于战略目标的分解,因此“SMART”原则原本是目标设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基于绩效结果观的指标设计原则,正如波伊斯特所言:“真正实用的项目目标应该遵循SMART规则来建立。”[1]然而,如今的个人绩效评估已经不再局限于绩效结果观,也不再是绩效行为观,而是出现了一种素质观(潜力观)的绩效评估[2]。而基于绩效行为和素质观的绩效评估指标设计就很难受SMART原则的规制,必须寻求新的指标设计原则。而新的指标设计原则确立思路并非学者们没有想到,而是他们的思考是碎片式的,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很难整合成为一个原理。那么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来确立基于绩效行为和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呢?
一、绩效“行为——素质”观及其与SMART原则的冲突
不坚持绩效结果观的原因:一是许多工作结果并不必然是员工的工作带来的,可能有其他与个人所做工作无关的促进因素带来了这些结果;二是员工完成工作的机会并不是平等的,而且,并不是在工作中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与任务有关;三是过度关注结果将使人忽视重要的过程和人际因素,使员工误解组织要求。[3]在绩效行为观看来,绩效是“与一个人在其中工作的组织或组织单元的目标有关的一组行为”[4],“不论这些行为是认知的、生理的、心智活动的或人际的”[5]。换言之,无论是先天的身心因素还是后天的学习因素所形成的,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对组织目标有贡献的行为和过程。根据Borman等人以及后来研究者的实证研究,这些行为可以聚合为两类绩效,即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1993年Borman& Motowidlo[6]将Campbell(1990,1993)的八因素结构模型[7]中的特定工作任务熟练程度、非特定工作任务熟练程度、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监督、组织和管理等5个因素归为任务绩效范畴,也分离出了周边绩效的五个主要方面:(1)主动承担工作以外的任务活动;(2)为了成功地完成任务,必要时会付出额外的热情与努力;(3)帮助他人并同他人合作;(4)即使在个人不便的情况下也照常遵循组织的规则程序;(5)赞同、支持并捍卫组织的目标。显然,这些行为特别是周边绩效行为尽管是具体的(Specific)、现实的 (Realistic)、可实现的(Attainable),通过行为锚定量表也是可以度量的(Measurable),然而却是没有具体时间限制的 (Timebound)。如工作任务熟练程度必须是经过长期至少是数年时间的实践,才能加以比较特别是纵向比较,试图在短时间内如一年(绩效评估的通常年限)就对之加以评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也不能将高绩效者与低绩效者区分开来。换句话说,用可度量(Measurable)原则来衡量工作任务熟练程度就会得出这个指标是没有意义的,并会将其舍弃掉,但实际上它却是评估行为绩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同理可以推论其他的绩效行为指标。
与绩效行为观的外显理论不同的是,绩效素质观是一种内隐理论,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兴起了一种 “内隐领导理论”(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y)[8]。虽然学术界即便是心理学界对素质和行为并未加以严格区分,但一般都把素质与人的特质联系起来,而行为则是特质、认知、情境等因素相互作用而外显化的过程。“素质是能区分在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工作绩效的各种个人特征的集合(包括技能、知识、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等)。”McClelland和 Spancer的冰山模型对人的素质进行了较好的建构。之所以要把素质纳入绩效的内涵,是因为“以目标或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技术无法回答:是什么导致了绩效水平的高低差异?这就必须把素质考虑进来。”[9]实际上Borman在建构任务绩效——周边绩效模型时就是把原来作为评估误差处理的情感、性格特征等人际因素作为绩效的一部分——周边绩效——来处理的。与西方强调个性特征的素质观不同的是,我国的素质观比较强调品德,这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凌文辁和方俐洛的CPM结构模型中就单独有一个品德维度(Character and Morals),此外,孙健敏和焦长泉的三维度结构(工作任务绩效、个体特质绩效和人际绩效)、王登峰、王重鸣等论述了个人品德在绩效评估中的重要影响。所以,张泰峰和Eric·Reader博士也认为,“现代公职人员考核内容选择的基本导向:将个人绩效评价取向纳入到考核中,实行个人品质与绩效考查相结合的考核方式。”[10]然而,由于内隐的特性,素质指标就很难用SMART原则来衡量了。比如Jone Warner博士编制的“Janus绩效管理系统素质库”中就有36种核心素质,有分析能力、前瞻性能力、成本意识、商业意识、情感互动、激励/动机、责任感等。这些素质是目前人员绩效评估中的重要指标,虽然它们是现实的(Realistic)而不是想象的;是可以通过培训、实践锻炼来实现的 (Attainable),也是可以设置成富有挑战性的;但是它们都是抽象的,不是具体可察的(Specific),需要通过操作化定义和行为化才能被测量的(Measurable),而且更加没有具体时间的限制(Time-bound)。
二、基于绩效“行为——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确立思路
那么,基于绩效“行为——素质”观的指标应该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呢?而这些原则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来确立而成为一个系统呢?其实,任何指标设计原则都是基于某种“关系”而确立的,比如“有时限的(Time-bound)”就是针对指标必须有助于衡量组织战略目标的不断实现而确立的。因此,寻求指标设计原则确立原理实际上就是寻找指标与绩效评估过程中某些重要事物之间存在的重要“关系”。众所周知,任何绩效评估都存在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1)为什么评估?(2)评估什么?(3)谁来评估?(4)怎样评估?而这四个方面可相应地转化为四个组成部分:(1)评估目的;(2)评估客体(包括评估对象)(笔者采纳萧鸣政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绩效考评的客体是指考评所作用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如职工、干部、职位或岗位等;而考评对象常常是考评客体的一些属性特征[11]);(3)评估主体;(4)评估工具。那么,指标设计原则就可以根据指标与这四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立。指标只有通过这些“关系”才能被这些组成部分所认可或者说符合这些组成部分的要求,才是有效的。据此,本文将基于绩效“行为——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的确定原理用图1来表示。
三、各指标设计原则解释
1.导向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和指标体系与评估目的之间的一种导向性关系,即指标和指标体系必须以评估目的为依归,符合既定的价值导向。正如波伊斯特所说:“绩效指标应该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们应该与工作的使命、目标和预期结果直接相关。”[1]导向性原则包括价值观导向、战略目标导向、评估定位导向等方面。例如对于县级领导干部绩效评估的行为和素质指标设计而言,这个导向性原则主要有:一是要贯彻党和国家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民生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二是体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和战略目标,如发展农村经济的理念和能力、联系群众的能力、维护基层稳定的理念和能力等;三是紧扣绩效评估定位,如绩效改进、干部选拔、奖励激励等。

图1 基于绩效“行为——素质”观的指标设计原则确定原理
2.现实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与评估主体之间的一种可理解性关系,即指标必须是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评估主体可以证明和理解的。但要注意的是,现实性原则并不要求指标一定是具体的、可视的,指标也可以是抽象的,但必须是可以通过行为而外显化的,或者说评估主体能够通过行为来理解或间接观察的。这个原则就可以衡量SMART原则中的“具体的(Specific)”所不容许的一些行为和素质指标,如个人品德、个性特质、认知能力方面的指标。例如对领导干部的绩效评估而言,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它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过它又能通过行为特别是心理行为体现出来。但,也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现实性原则是针对某项绩效评估的特定评估主体而言的,而不是泛化的评估主体或者与某项绩效评估不相干的主体。例如对县级领导干部绩效评估而言,其评估主体一般是上级组织部门、同事和下属,鉴于文化素质的差别,一些只为专家甚或心理学专家才能理解的指标如移情性、恃强性等最好不要选用。
3.针对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与评估对象之间的一种契合性关系,即指标必须有明确的来源地,一定是针对评估客体的某个或某些属性 (评估对象)而设置的。这就需要对所评估的客体进行规范的工作分析或职务分析,收集评估客体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认知能力、态度、个性特质、品德等方面的绩效信息。评估客体的属性会因地区、组织、层级乃至文化等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别人的评估指标虽然可以借鉴,但切不可全盘照抄,不可省略规范的工作分析。譬如,就县级领导干部这一评估客体而言,既要依据县级政府组织职能,更要特别依据县级领导干部这个层级的主要职责任务及其特点来设置指标[12]。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多具有外向型特征,而中西部的县域经济基本上是围绕“三农”做文章,搞产业化,延长产业链,由此导致两个地区的县级领导干部职务属性在工业与农业、外向与内销、农民工与农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据此设计的指标及指标权重也应有所不同。
4.代表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与评估客体之间的一种代表性关系,即指标与评估客体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最能反映评估客体的内容属性(即内容效度很高),具体有三重涵义:一是本质性,即绩效指标必须是针对评估客体的本质属性而设置的,决定着评估客体的基本走向,而不是针对无关的次要属性设置的,否则就没有代表性可言;二是精简性,就是在针对评估客体的某一或某些属性而设置的指标中,某一个指标覆盖的绩效信息最广,即最符合管理学中的“二八”原理;三是普遍性,即指标在同一类评估客体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也就是指标对同一类评估客体都具有代表性。如维护稳定能力在如今的县级领导干部绩效属性中就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5.系统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体系与评估客体之间的一种反映性关系,即任何一个评估客体都是一个系统,有着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各种属性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的有机系统,与此相适应,依据这种性质的属性而设置的指标也一定是一个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科学、全面地评估客体的绩效。“在给定的考评系统的范围和目标以内,一套绩效指标应该是全面的和综合的。”系统性原则要求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建构起指标体系的逻辑框架和概念体系,使得各种指标获得足够的解释力。
6.可比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与同类评估客体之间的一种区分性关系,即指标必须具有良好的鉴别力,能够较好地区分高绩效者与低绩效者。这就需要找到同一类评估客体所共同具有而程度上又有差异的属性来设置指标,“只有那些既不全然相同,又不完全不同的事物,才是可以比较的。”[13]在绩效行为、素质指标设计中贯彻可比性原则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对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中的理想信念指标的可比性就不太强,很难区分高绩效者与低绩效者,因为在当今的和平建设年代,理想信念很少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也很难为人们所体察。但它又是很多考核中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以为,用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指标来代替或融合理想信念指标更为可取,因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肯定会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涉及政治性的事件显现出看法、态度乃至行动,而这就间接反映了其理想信念情况。
7.可测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与评估工具之间的一种再现性关系,即指标必须可以通过某种评估工具来再现并加以测量,从而比较、辨别不同评估客体的绩效差异,换言之,指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测评工具来保证具有一定的信度。如果没有任何测评技术工具来再现这个指标,或者不同的评估者或运用不同的测评工具来再现这个指标所获得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差异,那就表明指标的信度不高,可测性不强,那就不宜选用。但要注意的是,符合可测性原则的指标并不都是定量指标,随着测量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定性指标都是可测的,如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服务理念、科学发展观念等指标都可以通过行为锚定量表、图尺度评估表等方法来测评。
8.独立性原则。它来源于指标与指标之间的一种独立性关系,“即设立的考评指标在同一层次上应该相互独立,没有交叉。”设定独立性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绩效信息的重复使用进而扭曲绩效评估结果,使得绩效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公平性受到损害;同时也是为了降低绩效评估的成本。当然,指标之间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而且指标之间还需要有相互制约的一面,以保持指标体系的平衡,避免目标转换(目标转换是指由于指标选择不当,或者指标之间缺乏制约导致指标体系不平衡,使得被评估者通过转换工作目标来获得高的分数,但却会给绩效带来负面影响)。
[1][美]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M].萧鸣政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3.
[2]Ashford.S.J.Self-Regulation forManagerialEffectiveness:The Role of Active Feedback Seek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251-280.
[3]付亚和,许玉林.绩效管理(2)[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Murphy,K.R.Dimensions of job performance.In R.F.Dillon& J.W.Pellegrino(Eds.),Testing: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Perspectives(pp.218-247)[C].New York:Prager, 1989.
[5]Campbell,J.P.Modeling the performance prediction problem in a population of job[J].Personnel Psychology, 1990,43:313-333.
[6]Borman,W.C.,Motowidlo,S.J.Expandingthecriterion domain to include element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A].Schmitt,M.J& Borman,W.C.Personnel selection in organizations[C].San Francisco:BJossey-Bass,1993:71-98.
[7]Campbell,JP.Modeling the performance prediction problem in industria1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In Dunnette MD,Hough LM(Eds.).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M],2nded.Palo A lto,CA: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l990:687-732.
[8]Lord R G,FotiR J,DeVaderC L.A Testof Leader-ship Categorization Theory:InternalStructure,Information Processing,and Leadership Perception [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1984,34(3):343-378.
[9]麦斯特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员工绩效考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10]张泰峰,Eric·Reader.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100.
[11]萧鸣政.现代绩效考评技术及其应用(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吴江.论基于能力建设的领导绩效评估制度[J].中国行政管理,2007(5):30-34.
[13][德]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M].李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责任编辑 侯 琦
D60
A
1672-2426(2012)02-0068-04
蒋文能(1973- ),男,广西全州人,管理学博士,中共广西区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政府绩效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