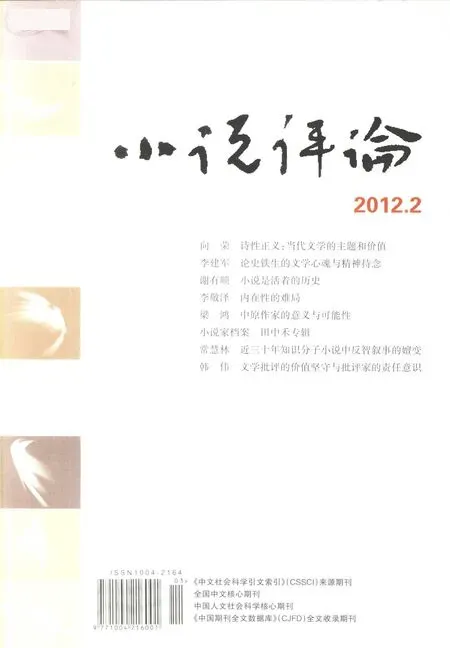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田中禾访谈录
李勇,田中禾
李勇:田老师您好,非常高兴采访到您!首先祝贺您一年之内推出了《父亲和她们》、《十七岁》两部长篇。读过之后,感触良多。两部小说叙事手法迥异,一个延续了您一贯的忧患写作,但是更老到,大气,形式更富于创新;另一个则非常不同,对时间和记忆的书写诗意而伤感、沉迷又超脱——我觉得,对您过去的整个创作,这两部长篇构成了新的爆发力,不但没有陈旧、乏力的迹象,而且更具现代性、更有活力。这里便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中国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力往往会日渐衰退,您现在看来却似乎相反,我想问,您写作的激情来源于什么?不断超越的创造力是怎么保持的?
田中禾:“因为好作品还没写出来,所以不敢老。”我常用这句玩笑话回答别人关于“老”的提问。今年总算把写了十年的两部长篇拿出来了,可文学对于我还像初恋的情人,我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初出道的文学青年,我所做的一直是在为写点好东西做准备。人生的准备,学养的准备,艺术的准备。转眼人就老了。人老了反而有更多优势。阅历多了,社会俗务少了,功利心淡泊了,不再有养家活口的压力,更有时间读书、写作,如果能保护好一份童心,人会更纯粹。也许退休后才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光。读书、写作本身就是激情的源泉。语言是一个浩瀚绚丽的世界,它激发你历险的激情。
李勇:国内外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呢?能不能回答?
田中禾:恐怕我也很难回答。中国作家我最崇敬鲁迅。他骨子里的反传统、对现存体制与秩序、道德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文字的辛辣、尖锐、幽默,艺术上的先锋迄今无人超越。在犬儒主义泛滥的今天,在精英向权势、金钱投降,向庸俗大众化靠拢的潮流中,鲁迅精神更加可贵。我是相信了鲁迅的话,从中学时代起就注重读外国作品,诗歌、小说、戏剧、哲学。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最近十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比较喜欢奈保尔和库切,拉美作家中我更喜欢略萨。虽然我也读了不少冷僻的作家,一些另类的作家,他们给了我很多启迪,可我更喜欢历史感、人性感、忧患感强的作家和作品。这跟我的文学观有关,我不保守,也不先锋。我崇尚超然的、坦荡的自我状态。
李勇:从您的文章里可以看到,您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作家的理性能力、批判意识对写作来说并不一定都是有益的,您认为呢?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偏于感性还是偏于理性?您又是怎么处理二者关系的?
田中禾:你提出了一个对于重视思想、理性的作家至关重要的问题。作家不能靠理性去创作。作家不能靠理论来支撑。文学作品不是政治、文化论文,如果不把思想融入情感,化为艺术,理性就成了作家的制约。我不很喜欢萨特,他作品里的思想驾驭了他笔下的形象;我也不怎么喜欢卡尔维诺,他美丽文字中哲理的闪光并不能掩盖他叙事艺术的乏力;中国作家大多崇拜博尔赫斯,可他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的智慧,不如马尔克斯对拉美历史的奇幻讲述更大气。然而,中国作家的确缺乏萨特的思想修养、卡尔维诺对表象世界的哲理表达、博尔赫斯对内心智慧的开掘。作家不靠理性写作,却不能忽视自身的学养建设。批判意识是文学的本质,是文学的价值所在,作家必须有批判意识,但不能靠批判、靠政治来支撑。像库切那样既有宏大的对人类、人性、现存世界秩序与体制的深刻理解力与批判力,又能把思想融入感性的生活故事,以形象与情感诉诸读者,他就是处理思想与艺术的成功的范例。他的近作《凶年纪事》胸怀宽广,批判人类体制和西方政治锋芒锐利,情感故事又很流畅,构思巧妙。我把一部好小说归纳为:讲一个新鲜的、有趣的、有意思的故事;把一个故事讲得新鲜、有趣、有意思。尽管新鲜、有趣、有意思是一部好小说的基本元素,但我主张宁可没意思也不可乏味、落套。我认为,文学作品的感性是第一位的,美是第一位的。有趣,新鲜,比有意思更重要,虽然我更欣赏有思想内涵而又惟美的作品。
李勇:在《父亲和她们》中,您对“娘”是持批判态度的,说她代表着“传统”,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娘”却是慈悲善良美好的,寄寓着强烈的情感认同。您否定“娘”,其实否定的也正是这种“情感认同”,也就是说,您在作品中实际上也在否定着自己。可以这样理解吗?
田中禾:批判,是一个思想者的知性;文学形象,是一个作家诉说历史的感性。“娘”的形象也许正好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我是怎样处理理性与创作的关系的。做为我在思想上的批判对象,呈现于读者的并不是一个理论概念。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可怕,正因为她有自己的人性逻辑、伦理原则、善恶是非,她是中国母亲的典型。在写作中我对她投入了深厚的感情,理性上却不能认同她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她就是社会体制改造自由思想、消灭个体价值的帮凶。社会体制使用的是政治高压、思想扭曲,而“娘”用的是忍辱负重的生存哲学,几千年中国儒家奴化教育的行为方式。“娘”的感人之处正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政治高压、思想禁锢最终必然会被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冲决,传统文化却无法用革命来改变。传统深入我们的道德、行为,它的再生能力、衍生能力无法遏制,所以,“娘”是这部小说里惟一的胜利者,她始终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
李勇:“父亲”马文昌左突右冲最终还是回到了“娘”身边,以致他忍不住感叹自己是在“兜圈子”。马文昌的处境是不是也是您的、我们大家的处境?我们都摆脱不了“娘”,摆脱不了传统——您是否感到了绝望,当您谈论“自由”的时候?
田中禾:《父亲和她们》是一部对自由和人性被改造的思考的书。人性被改造的历史不自马文昌这一代始,人对自由的追求也不会止于马文昌这一代。人的自由与个人价值的追求如人类文明史一样是一个混沌运动,它在旋转回荡中前进,看似轮回,其实是在前行。历代作家不断重复这个主题,因为人类面对现实从未绝望。揭示无奈,无望,是一种念念不忘地追寻。用一句流行歌词说,“至少我们还有梦。”自由,对于人类是个永恒的梦。
李勇:您强调文学的“激情与幻想”,是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您实现自由?如果我们只能在幻想中获得自由,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即使文学帮助我们实现了某种自由,对自由的焦虑其实仍然存在。您让儿子“我”飘泊海外,大约是想要象征下一代追寻自由的空间更为广阔吧?
田中禾:“出走”与“回归”是现代人的两种精神选择,也是当代作家的两大梦境。回归自然,回归纯朴,回归传统,是疲于奔命的现代人在精神焦灼与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的梦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出走后的漂泊感让现代人怀念精神家园,回归就成为自由的憇园。《父亲和她们》由身在异国的“我”来讲述,以一个美国小镇为讲述背景,“我”的怀旧、思乡的情调,的确就是对现代人宿命的隐喻,暗含了回归的情感。然而,对于现代人,出走和回归都只是白日梦,只能在文学里实现。连续多年,以写非洲、怀念非洲来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作家特别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青睐,戈迪默、莫瑞森,莱辛、勒克莱齐奥,……都因对非洲的饱含怀恋的描写而获得诺贝尔奖,可他们当中没有一位作家真正回归非洲。库切离开非洲,移民澳洲,然后又把澳洲批得一塌糊涂。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我们不但丧失了精神家园,连物质家园也不复存在。弗洛伊德说“文学就是白日做梦”,让人在文学里为自由出走,让人在文学里为厌倦回归,这正是文学的真正使命。
李勇:如果说《父亲和她们》是出走,您的另一部长篇《十七岁》是不是可以看做是回归,故土家园的情感回归?全书在写您的个人记忆,非常个人化。小说对“时间”的描写非常动人,“过去”和“现在”相隔大半个人生,隔着这样大半个人生去回望青春和过往,它的写作过程和写作感受与《父亲和她们》肯定大不相同。
田中禾:《十七岁》没什么深意,谁都读得懂。它是情感的吟哦,生命记忆的弦歌。我希望她能在喧嚣的社会潮流中构筑一片小小的清幽天地,让人的心灵能在这里找回温情和宁静。发表之前,我曾经把它命名为《乐园》,记忆的乐园,失落的乐园。我认为这种境界更接近文学本质。由于选取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特殊时期,《十七岁》的记忆不只是我个人的,它其实是民族记忆的一个切片,是大时代的个人印记。
李勇:《十七岁》和《父亲和她们》,一个温馨一个厚重,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风格,您更钟情于哪一种?以后会继续顺延着写下去吗,还是……?
田中禾:从《匪首》到《十七岁》,这几部长篇有着各不相同的结构手法和叙述方式,思想上却只有一个主题:人性在体制与传统力量作用下的境遇和困惑;艺术上也有一个共同风格:以饱含民间智慧和书卷气的叙事,充分发挥写实艺术的魅力,诗意地展现苦难人生。我一直在努力以文学手段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这是我毕生的主题,我会沿着这个主题继续开掘。我认为写作应该跟着感觉走,我会不断变换结构和叙事方式,根据要讲的故事内容来决定怎么写,不会遵循固定程式。
李勇:您一直强调写作者的“慈悲感和怜悯心”,这似乎是您小说中总出现那些美好善良女性的原因,这好像也跟您的成长经历、母亲给您的影响有关吧?您的小说总透出一种多情、温暖的个性;而河南作家,相当多的却是笔力“凶狠”,比如阎连科、李佩甫,好像是阎连科说过的吧——这跟河南人的生存环境有关。您怎么看?
田中禾: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哲学和风格,这与各人的性格、经历、童年记忆有关。我对生活的理解是诗意的、多愁善感的,值得热爱和珍惜的。温柔敦厚之道,是中国传统写作的标准要求,我这个骨子里反传统的人,笔下的作品却大体符合这个要求。这与儿时的教育有关。《十七岁》可以看做是我的自传。你可以从中看到我的童年,因而窥见我内心成长的经历和写作风格形成的精神因素。
李勇:大家经常谈论“河南作家群”,您认为河南作家的共性是什么,有什么共同的优长、欠缺?
田中禾:我不赞成作家群的提法。文学艺术的灵魂是个性,什么军,什么群,有意无意抹杀了个性,给作家画地为牢。博尔赫斯曾经批判一些阿根廷作家的意识只属于地方,不属于人类,自甘于一个地方作家,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作家和理论界尤为严重。我们不会把歌德看做魏玛军,把鲁迅称为浙军吧?正如我上面所说,同一个地域的人千差万别,同一个地域的作家更是千差万别。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我们可以从地域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找出一些作家背景研究的课题,在艺术上,我更重视各自的不同。
李勇:您强调文学的“慈悲感和怜悯心”,对当下流行的“苦难叙事”、“底层写作”,您有什么看法?忧患意识强,对作家不一定是好事,您似乎也这么说过,但是当下的中国现实,确实不能不让忧患意识强的人有所忧患。您认为,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下的写作,应该如何才能做到不让人遗憾?
田中禾:我的确曾经告诫一位朋友,不要让忧患意识拘泥了情感和视野,但忧患意识、批判意识是作家的基本品格,没有忧患意识的作家不过是一个文学投机者。即使是通俗文学,也应该以忧患和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我的劝告是作家不可沉溺于苦难而使艺术的翅膀过于沉重,局限了想象力和激情的发挥。超越苦难才能审视苦难。用超越的态度去写苦难,苦难才能呈现出更深刻的意义。如果审美是第一性的,我们就应当在苦难中发现美。爱因斯坦说他反对宗教迷信,但他主张人应该有宗教意识。我觉得这个论述也可以用来论述忧患,我反对忧患遮蔽审美,但主张审美应该有忧患的底蕴。慈悲感和怜悯心,是鲁迅引用日本作家德田秋声的话,我记不起出处了。它比忧患更宽阔,忧患只是慈悲与怜悯的一个方面。我最近重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论著,回头看马克思,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知识分子,坚持站在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坚持为劳苦大众的利益写作。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已变为既得利益者,接受利益赎买,与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甘做他们的吹鼓手和卫道者。作家的忧患写作就显得更其重要,坚持清醒的边沿写作、民间写作、底层写作,更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