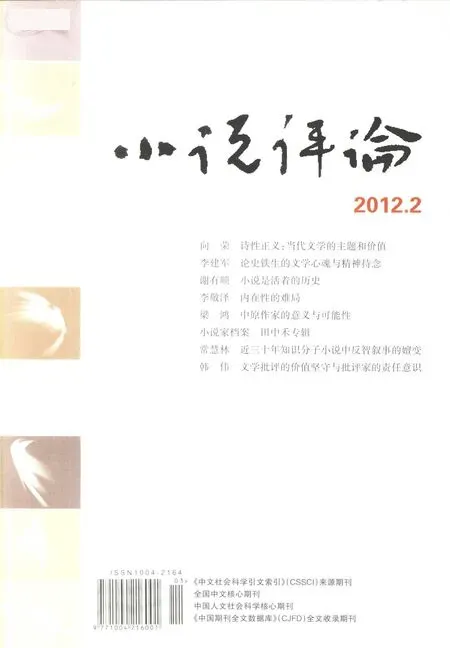思想者的苦恼和艺术家的逍遥:论田中禾的小说创作
李勇
一
田中禾上世纪40年代生于河南唐河,高中时便出版过诗歌,60年代因不满大学中文教育的落后而主动退学,并立志在人间的“大学”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此后做过农民、教师,办过工厂,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二十年后才成为专业作家。田中禾写作起步早,享有声誉却是在80年代,短篇小说《五月》的发表与获奖,使其作为一个乡村小说家初闻于世。对转型期农村深刻而富有前瞻性的把握、对人性温暖和良善本质的体味与表达,使《五月》发表后广受称赞。但田中禾后来却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选择了不断挑战和突破自我。从《五月》到《明天的太阳》,到《落叶溪》、《匪首》,再到《父亲和她们》、《十七岁》,田中禾的自我挑战与突破是全方位的:从乡村到城市、现实到历史,从社会历史反思到文化人格批判,从写实、白描到意识流、“笔记体”、多角度叙事——既有题材上的,又有主题、艺术和语言上的。多变的风格体现着作家倾向于冒险的个性,但有一种较为恒定的东西在他身上却似乎一直没变,那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五月》等早期乡村小说里,它体现为对农民生存现实的观照和对农村出路的寻找;在《明天的太阳》等城市题材小说里,它体现为社会转型和文化冲突所造成的主体压抑和痛苦;在《落叶溪》、《匪首》中,它体现为历史重构所暗含的文化忧思和人性透视;在《父亲和她们》中,则体现为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批判性审视。
可以说,《十七岁》之前,田中禾小说显现出来的作家主体精神气质一直是深沉的、富于担当的,而《十七岁》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完全取材于作家的自我家族史和人生经历,以“自传”和“回忆录”的方式记述了作者的祖辈、父辈和自己一代家庭成员的生长经历,尤其对姐姐、哥哥和“我”的青春成长作了浓墨重彩的记叙。小说充满了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回忆中灌注着作者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人世生存的苍凉而温暖、诗意又伤感的生命体验。将《父亲和她们》与《十七岁》进行对比就会看出明显的不同:前者是写“他人”,后者是写自我;前者寄寓社会担当,后者是生命诗意的挥洒与流淌;前者苍茫滞重,后者轻盈洒脱。二者的差异是鲜明的,借用前面的话来说,《父亲和她们》(及田中禾此前的创作)更看重“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十七岁》则更体现着文学言说的“自由”和“有限”。如果把田中禾《十七岁》之前的创作看做是一条连续的河流的话,那么《十七岁》便像是一次突转,但突转并非中断,它不是无迹可寻的,对田中禾来说,《十七岁》变异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一致性。那么,这种一致性是什么?
二
新近发表的《父亲和她们》据作者说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思考,这说明他一直没有摆脱焦虑,也没有放弃抗拒的努力。从主体的道德自觉,到历史文化的价值寻找,田中禾企求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改变,这一次他将希望寄托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省视。小说主人公“我”的“父亲”马文昌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典型,和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经历了一个被改造和驯化的过程,但小说所表现的却不仅仅是“革命”对知识分子的驯化和改造,从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到抑郁苦闷的中年干部,再到老年安享荣誉和回忆的布道者、人生导师,作品表现的更是一种超出“革命”的强大的社会性外力对所有叛逆个性的改造。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娘”这一形象,父亲在爱情、事业上的每一次“出走”,都以回到“娘”的身边为终了,以致“父亲”忍不住感叹他的人生不过是在“兜圈子”。“娘”像大地般仁厚宽广,但正如作者说的:“宽容、善良、坚韧的娘,其实扮演着政治上对父亲改造的帮凶的角色。她对父亲的改造深深植根于传统观念之中,它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甚至我们的潜意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思想找不到向它进攻的突破口。”①“娘”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任何生于、长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因此可见,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省视其实从一开始便陷入了绝望,因为他质疑和批判的是深植于强大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现状”,在这种“现状”下,生存便意味着妥协,自由便意味着逃离或死亡。“父亲”选择了妥协和活着,邹凡作为与“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他抗争、叛逆——毋宁说他象征了“父亲”心中那个被压抑泯灭的自我,但他却被早早地安排了死亡,这更清楚地透露出作者的绝望:“独立人格,个人自由,这看似简单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国人,可以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②
《父亲和她们》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生存处境的发现,它是对自由的绝望,更是对知识分子自身(包括作家本人)的绝望。从《五月》到《父亲和她们》,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到历史文化反思,再到文化人格批判和自我批判,从中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一条由焦虑/抵抗焦虑到走向绝望的路。焦虑起源于担当,最终收获的却是绝望,这是田中禾作为知识者和思想者的苦恼,也是田中禾作为一个作家在理智与观念层面遇到的苦恼。
《十七岁》却似乎摆脱了这样一种苦恼,小说从内容和写法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从内容上看,它讲述的完全是个人史和成长史,“十七岁”是个特别的时间点,因为“十七岁”的生命还没有完全融入社会和历史的过程,饥荒、战争、革命、运动……历史在波澜壮阔地进行,“十七岁”的生命们却在出嫁、夭亡、躲在阁楼里烤疥疮,抑或刚刚打点好离家远去的行囊,他们此后将参加革命、被打成右派、上山下乡,但在“十七岁”的时间点上,他们只有初恋、升学、离家和感伤。所以,“十七岁”的“历史”是更为私人化的历史,对“十七岁”的回望看不见家国、责任和担当,而仅仅是对昨日的一种眷念,对青春的缅怀,衬以发黄的历史底色,让人唏嘘,让人感慨。而在写法上,作者此次也似乎完全放弃了对形式和语言的一贯重视,它用的是最朴素的写实手法:人物脱胎于现实,事件遵循时间的自然流动,“第一人称”叙事者拥有实际上的全知全能。田中禾一贯重视小说的语言和形式——“讲一个有意思的、有趣的、新鲜的故事,首先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的讲法”③,“讲法”往往包含了丰富的理智和意图,《十七岁》这一次却似乎是对所有智性操作的放弃,它率性而为、自由自在。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十七岁》的这种个人化叙事是否意味着作者对焦虑和绝望的逃避?
三
整体地阅读会发现,田中禾作品中其实一直隐现着两个不一样的作家自我:思想者的自我,艺术家的自我。思想者的自我介入、担当、焦虑、忧愤,但对这个思想者的自我,作家本人却始终有所警惕——他没有否定过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但对功利主义的文学态度却极为嫌厌,他说:“中国作家处境的尴尬在于唐宋以降的实用主义文学观经过明清苛繁的文字狱,再经建国以来极左路线的发挥,文学的品性几乎丧失殆尽,人们习惯了文学是政治的附庸,读者要求文学作品必须是对社会政治表明态度的社会思想载体。中国的读者似乎早已忘却了文学对于人的性灵的温柔、愉悦和美的享受。”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田中禾有一种艺术的自觉——“对于人的性灵的温柔、愉悦和美的享受”也好,或者其他别的也好,田中禾相信,文学有且应该有一种属于它自己的、与生活和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表明“态度”和“思想”,但前提是以文学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文学的自觉,而这样一种自觉也便造就了田中禾作为艺术家的另一个自我。
“艺术家的自我”首先(也是最明显地)表现于田中禾对文学情感本质的守护。他说,“文学的关注焦点应该是人的命运,人性的状态”,由此引发的作家的“悲悯”是文学的真正触发点:“从内心深处,我更认同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是慈悲感和怜悯心。”⑤田中禾小说中的女性便以这种慈悲善良的女性特质与追求理智、冒险的男性形成了鲜明的映照,她们以一种醒目的情感力量对男性主导的理智世界构成了有效的滋润和缓冲。对“情感”的突出和侧重,使田中禾始终贴紧的是人性,而不是“观念”和社会性,这使他的小说始终表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品格,也使他的作品在自身内部形成着对“焦虑”的抗拒。
除此之外,艺术家的田中禾还有另外一种自觉——追求创造的自觉。在《匪首》“创作札记”中,田中禾这样说过:“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不是靠生活阅历和学识积累,尽管这二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激情与幻想,阅历生活,积累学识,都是为了丰富、建设直觉智慧,而不是框限它、磨钝它。作家的佳势状态是天马行空,他一生能达到的高度就是张扬自己的激情与幻想的程度。”⑥倡扬“激情与幻想”,一方面可能与其叛逆、冒险的性格有关,但另一方面却更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贯体认与反省:“中国人的人性被强大的传统改造,中国人的创造激情在这改造和压抑中受到制约,严重影响了民族的活力。这不光是我个人的人生感受,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切身体验。”⑦文化传统及其构成的生存“现状”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最大障碍,这是田中禾在《父亲和她们》中得出的结论,而艺术通过“创造”、“激情与幻想”却能够破除这种障碍、实现“自由”。也就是说,田中禾在此已经发现:其艺术家自我的充分实现便是对陷入绝望和苦恼的思想者自我的有效拯救。
思想者田中禾的绝望和苦恼,现在成了艺术家田中禾确证自身价值的理由,而其所依凭的就是艺术通过“创造”、“激情与幻想”对“自由”的实现。当然,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田中禾明确地表示道,“我是个很看重心灵自由的作家”,⑧只是这种心灵的自由在《十七岁》之前却一直是被压抑的,介入、担当导致的“悲悯”纠结于心(田中禾当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曾如你一样在这样一条路上满怀热情地走。今后也许仍不会丢弃它。但我觉得我们的忧患拘泥了我们。”⑨)——那时,“自由”仅仅表现为对“情感”的守护和对外在“观念”的远离,“激情与幻想”也只能在语言和形式的创造中获得暂时和有限的满足。然而艺术家的自我终究渴望更充分的实现,而思想者自我亦能藉此实现对苦恼和绝望的摆脱,于是对一种更充分的“自由”的实现也便成为了必然,而这种“更充分的自由”势必是排斥任何心灵负累的、自我的、内敛的,《十七岁》便是它的直接产物。
从渴望自由,到自由的充分实现,这便是田中禾从《十七岁》之前的创作到《十七岁》的“一致性”。不过,这里留下的唯一的问题是:艺术家田中禾所实现的“自由”是否是思想者田中禾所企望的“自由”?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个逍遥的艺术家是对自由的最高实现,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艺术家通过创造、激情和幻想所打开的是通往“无限”和“可能”之路,而这也正是艺术实现“自为”的根本路径。所以,田中禾通过对艺术家自我的充分实现而实现、获得了自由,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荣耀与自豪,但是,自由惟通过艺术(家)来实现,这是否是“自由”的悲哀?或者换句话说——艺术家田中禾的逍遥未始不是思想者田中禾的又一重苦恼。然而,苦恼又能如何呢?这个问题田中禾解决不了,所有的艺术家也都解决不了。
注释:
①②⑦⑧墨白、田中禾:《小说的精神世界——关于田中禾长篇新作<父亲和她们>的对话》,上海《文学报》,2010年10月14日第7版。
③⑤田中禾:《田中禾小说自选集·自序》,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⑥《超级玛莉的历险——<匪首>创作札记》,《小说评论》,1995年第1期。
⑨田中禾、墨白:《人性与写实》,《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