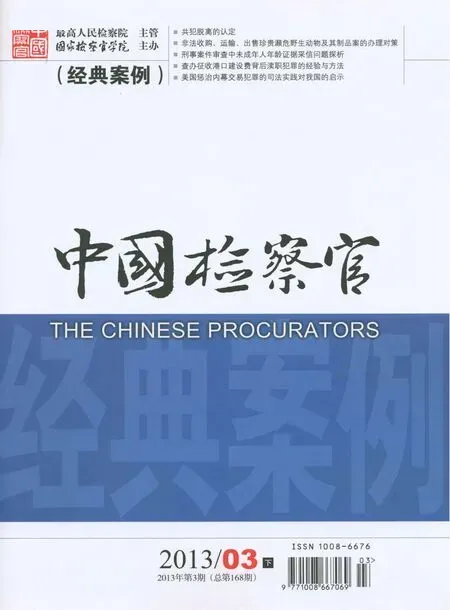青少年犯罪的实践及立法思考
文◎彭国全 段 征
青少年犯罪的实践及立法思考
文◎彭国全*段 征*
本文案例启示:由于青少年在成长中必然与成年人有着较多的生理和心理差异,因此刑法对于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规定也必然要有独立的理论基础,不能简单的用成人刑法的视角去探视青少年犯罪,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时也不能简单比照成人从轻、减轻处罚,而应当从未成年人的视角出发综合衡量。
*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462000]
[基本案情]2011年11月2日下午,胡某和董某发现陈某一人在操场,两人叫上张某、李某一同将陈某强行抬到操场草坪上,并将手伸入被害人陈某胸罩内摸被害人乳房达5分钟左右,胡某和张某捂住被害人陈某的嘴以防止其呼叫,董某则按住陈某双腿以防止其挣扎。随后,胡某骑在被害人肚子上抑制被害人反抗,张某又将陈某皮带扣解开,但并未将裤子脱下,后因被害人陈某喊道:“再不放手,我告你们”,四人由于害怕而离开。
一、个案处理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相结合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条文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分为三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以及未成年到成年之间缺乏一个必要的过渡,每个独立个体不能在过完十八周岁生日起第二天就明确拥有成年人的心理特质,正如姚建龙在《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形象地描述:“一滴墨水滴落至宣纸上,墨水慢慢渗开,在边缘逐渐模糊,直至纸墨浑然一体。墨水边缘与宣纸不会突兀地界限分明。人的成长也是一个逐步散墨的渐进过程。绝不会在十八岁这一界限就突然从未成年人越为成人,或者在十六岁就突然有了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作为个体自然人来说,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演变必然是一个逐渐成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以某一个刻度性的年龄将辨认和控制能力截然断裂,是不符合人成长的特点的”。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而特别制定的少年刑法,我们依然应当严格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去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未成年人直接当做成年人的缩小版去审视,而是应当按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综合分析其主观恶性和行为方式。结合本案来看,根据现有证据,嫌疑人张某并非犯意挑起者,从其主观恶性上来看,张某处于青春萌动期,青春期是身体迅猛发育的时期,也是人生的转折期,在经历了短暂的异性疏远期后,随着心理和生理的迅速发育,个体进入青春发育高峰期,对异性的敏感、好奇逐渐被吸引和愿意接近的情绪所替,正常的异性交往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但是由于青春期动荡性的影响,有些未成年人会出现异性交往偏差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违反特定场合的管理规范的交往行为、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交往行为、自毁行为、不适当行为。张某即是在青春期阶段出于对异性的好奇而发生的异性交往偏差的现象,其主观动机是一时的冲动好奇,这与成年的社会青年相比,其主观恶性并不强烈。从刑法的保障性和谦抑性出发,在此个案中,如果将在犯罪行为中非起主要作用的张某作为犯罪处理,则难免使刑法的打击力度过大。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的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张某的行为情节轻微,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来处罚。
二、未成年人青春期不良行为的防治
未成年人进入青春期后,由于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思维的独立性和深刻性增强,从心理变化来看,主要是交往能力增强,性意识萌发,有好胜心,易冲动,有较强的独立意向。但是其认知能力和理智程度均未达到成熟指标,心理发展难免会滞后于生理发展。这种发展不平衡难免导致未成年人抵抗外界干扰能力较弱,例如不良同伴的影响、家庭教育的失当,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不良网络传媒的侵蚀等等,一旦遇到外界的不良刺激就会做出越轨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
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防治,家庭应当是第一道防线,家长应当在子女教育上多花时间和精力,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家长首先有良好的心理状况和健康的行为,然后才能对未成年人开展家庭心理教育,良好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应当掌握科学的方法,注重内容和策略并最终与学校教育行为合力。
学校教育是青春期教育特别是性教育的重要阵地,尤其是要上好中学阶段的生物课,并辅以各项有益活动。目前一些学校存在着只关注学生成绩,而忽视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同时也有一些老师不好意思或是不愿讲述生理健康方面的课程。学校要积极改变这种状况,认识到性教育、性法制的教育对于青春期的中学生的重要意义。上述张某涉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案中,如果学校在平时注重中学生的青春期教育,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一些未成年人在异性好奇的心理支配下作出不良行为。
同时,青春期教育应当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例如瑞典的青春期性教育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瑞典不仅在学校开设完备的青春期教育课程,而且其全国已经拥有200多个少男少女门诊,门诊成员主要由心理学界人士和医学界人士组成,免费向23岁以下的青少年开放与治疗。
青春期一直被称为金色年华,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青春期也是人生成长路上的一道险关,青春期教育应当形成系统化、制度化、法制化的体系,例如美国从1912年就开始培养中小学性教育师资,70年代开始,所有中小学校就都开始了性教育课程。在我国,处理青少年青春期犯罪个案时,使人感受最深的便是学校青春期教育的缺失所导致的未成年人无法抵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蚀。
三、少年刑法之域外借鉴
从20世纪开始,各国开始纷纷针对青少年犯罪单独立法,将少年犯罪与成年犯罪区别对待,少年刑法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客观主义刑法理论支配之下,少年刑法不可能从普通成人刑法中脱离出来,由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认为,对少年刑法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产生,而主观主义刑法理论也进一步为少年刑法铺垫了理论基础。
少年刑法的存在首先要承认两个理论:“打破抽象‘理性人’假设”以及“未成年人观念”。在打破抽象的“理性人”假设下,“个人”被刑法所接受,未成年人与成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需要设立特别的刑法加以保护和规制,特别的少年刑法应当遵循与成人分离以及放弃报应刑等原则。
其次,少年刑法的设立也涉及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博弈问题,按照比利时哲学家佩雷尔曼的观点,形式正义是指“对每个人同样的对待”。实质正义则是取决于制度本身的正义,正如罗尔斯认为的,形式正义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是目的。少年刑法的产生也正说明了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已绝非简单的“度”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适用“从轻、减轻处罚”等规定,特别是洛克“白板说”的产生使得成年人对少年犯罪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感,也催生了少年刑法的产生。
最后少年刑法也必须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发达的前提下,只有这样,少年刑法才具备了实践性。目前各国的少年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瑞士联邦刑法典》为典范的单列专门的编或章来规定,例如《瑞士联邦刑法典》将第四章规定为“儿童和少年”,第五章规定为“刚成青年”。二是在普通刑法外,单列单行的少年刑法,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以及《日本少年法院法》。三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将相关规范散列在普通刑法之中。而基本的少年刑法应当包括“少年”的概念、范围;少年刑法的适用范围;少年罪错的性质、少年刑事责任;少年刑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