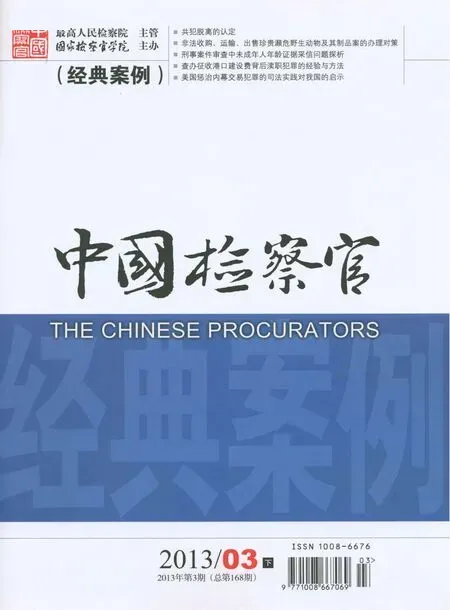以假币购买毒品的司法定性问题研究
文◎郭 莉
以假币购买毒品的司法定性问题研究
文◎郭 莉*
本文案例启示:在行为人使用假币骗取毒品等违法财产利益的场合,由于法律体系并不允许相互冲突的规范同时存在,并且行为的可罚性系建立在施予不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刑事制裁也并非是维持毒品交易中诚实信用的恰当方法,因此,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102206]
[基本案情]2007年4月20日16时许,黄某某与赵某某在云南大理市大红帆酒店咖啡厅交易毒品时,被当地公安局缉毒民警当场抓获,后发现黄某某用于购买毒品的货币全部是假人民币,并从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查获用于购买毒品的假人民币89.35万元、假港币4.8万元,从赵某某处查获毒品海洛因15000克,甲基苯丙胺40000粒。当地检察院遂以黄某某涉嫌持有、使用假币罪,赵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2007年12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某某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赵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宣判后,黄某某不服提出上诉。2008年3月14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赵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并无异议,讨论的焦点在于黄某某的行为定性问题,具体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黄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持有、使用假币罪。本案中,黄某某违反国家货币管理法规,持有大量的假人民币和假港币购买毒品,且根据行为人的知识、经验、假币的流向、获得假币的渠道、隐匿假币的场所和方法以及实施行为的次数等可以推定行为人应当知道其所携带的是假币,同时现有的证据尚不能证实黄某某持有假币与其他假币犯罪相关,根据我国刑法第172条的规定,黄某某的行为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
第二,黄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未遂)及持有、使用假币罪,并实行数罪并罚。本案中的被告人黄某某除了非法持有、使用数额特别巨大的假币外,还以假币购买毒品,符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构成要件,鉴于黄某某是在购买毒品的过程中被缉毒民警抓获,未能实际完成诈骗,故应当论以未遂。由于黄某某的行为侵犯了不同客体,触犯了不同罪名,因此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三,黄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未遂)。理由在于黄某某持有假币并将假币投入流通用于购买毒品的行为系诈骗犯罪的手段行为,亦即其持有、使用假币的犯罪行为与诈骗犯罪行为形成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根据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法理,应当仅认定成立诈骗罪。
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本案争执的焦点在于黄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亦即行为人使用假币购买真毒品的行为能否成立诈骗罪。对此,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学界及实务界一般认为,诈骗罪的本质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基于此错误的认识实施了处分财物的行为。但本案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使用诈术骗取的对象是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毒品,换言之,行为人通过抵触法秩序而占有的经济价值状态,如毒品等是否属于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
二、理论阐释
对此问题,虽然理论及实务界并无直接回答,但与此相似的问题已有讨论,如抢劫毒品的能否构成抢劫罪,并且目前形成的普遍性看法是肯定毒品等违禁品仍处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所持的理由是,刑法所保护的财产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财产,对于财产的占有者而言,不管该财产是否系违法取得或保有的,只要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在刑法上就应当受到保护。如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财产具有有价性的特点,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毒品虽然是违禁品,但不可否认其凝结了劳动者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同时尽管法律明令禁止持有或流通毒品,但毒品的地下流通一直存在,有非法的市场交易价格。因此毒品可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1]司法实务部门往往也倾向于将毒品等违禁品纳入刑法的保护范畴,对于抢劫毒品、赌资等“黑吃黑”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2]并且这一认识和做法已为相关的司法解释所采纳,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关于抢劫特定财物行为的定性,就明确规定:“以毒品、假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为对象,实施抢劫的,以抢劫罪定罪;抢劫的违禁品数量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定罪。”虽然上述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诈骗毒品的应当构成诈骗罪,但诈骗罪与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同为侵犯财产的犯罪,既然毒品能够成为盗窃罪、抢夺罪及抢劫罪的对象,理应也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
然而,如果我们从法秩序的体系、目的论、以及规范逻辑的方面进一步考证的话,上述结论便颇令人怀疑。
(一)体系上的论证
就整体而言,法律规范是一个自足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与其他规范发生关联。因此,在对某一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时,就必须观察其与其他规范的关系。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各法律规范之间彼此应当无矛盾,这是因为法律是对于人民设立的行为指示,有指引功效,若指示相互矛盾,就无法被执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同一情况中,执行a又同时不执行a。[3]因此就同一个事物而言,法律不可能既允许又禁止。具体到行为人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情况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认定使用假币施诈的一方构成诈骗罪,对贩毒者提供刑法关于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保护,便会与上述要求相抵触,即一方面法律禁止进行毒品交易,另一方面又要求在进行毒品交易时购毒者应当使用真币来购买,而“禁止缔结与进行毒品交易”在逻辑上与“应诚实地缔结与进行毒品交易”是矛盾的,换言之,当法秩序宣示了一个禁令,禁止缔结、履行某种交易时,它就不能对当事人违背此禁令的情形再提出应当如何缔结或履行此交易的规则。由此,对于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一方并不能论以诈骗罪。
(二)目的论的论证
根据通说观点,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公私财物所有权,而刑法设置诈骗罪的目的即是防止他人以诓骗手段侵占公私财物,亦即诈骗罪的规范意旨并不仅仅是强调受骗的人应当受到保护,其重点在于施诈者应当受到刑法谴责。由此,对于使用假币意图占有他人毒品的行为人以诈骗罪进行规制则是恰当的。这样的推断乍看之下似乎合理,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其立论的前提仍有瑕疵。其实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来看,之所以采用刑罚这样严厉的手段来惩罚某种行为,是因为实施此行为的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行为的可罚性并不是建立在行为人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的基础之上,而是要以行为人对国家、他人实施了不法行为为前提。那么,对于使用假币意图蒙混过关骗取他人毒品的行为人而言,由于受骗者被骗走的利益是他根本就不应拥有或保有的利益,所以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人并没有实施侵犯国家、他人利益的不法,也就不能成立刑法上的诈骗罪。
(三)规范逻辑的论证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规范逻辑的角度反证上述观点。假使对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行为人论以诈骗罪,那么刑法就会成为维持毒品交易人之间诚实守信的保护伞,这从规范逻辑的角度显然是无法说通的。更何况,此种担保毒品交易诚信的规范也不公正。比如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人一旦诈术失败即是如此。当交易过程中,贩毒者发现对方交付给他的是假币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购毒者出于种种考虑,如想要继续从贩毒者那里购买毒品,或是贩毒者具有某种实力使其不敢不继续交付,甚至是购毒者良心发现,而交付了真币;二是即使对方发现其给付的是假币,购毒者仍置之不理,拒不交付真币。对于第一种情形,如果对施诈者处以诈骗罪,由于对方已经发现其给付的是假币,即使其随后又交付真币,犯罪依然成立,构成诈骗罪的未遂;对于第二种情形,如果对施诈者论以诈骗罪,仍应论以诈骗罪的未遂。如此便会出现规范逻辑上的不合理,即诈术失败后无论施诈者如何行事,法律所给予的评价是相同的。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鼓励诈骗者在诈术失败后继续抵赖。那么,本身是籍由刑罚的惩罚树立交易主体廉耻心,促使骗徒诚信的规范在面对更不老实的行为人时显得束手无策,成为变相鼓励施诈者滑向更不诚信境地的推动器,这样的刑罚设置就是既不公正又不合乎目的的。
三、相关思考的延伸
从上述法规范的体系、目的论解释、以及规范逻辑等方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行为人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并不能构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但是换个方位思考,如果是毒品卖家通过有瑕疵的供货来欺骗买方,对于贩毒者应该如何论处?对此,我国司法解释早有规定。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及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明知是假毒品而冒充毒品贩卖的,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当作毒品贩卖的,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一)明知是假毒品贩卖的行为定性
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知是假毒品而冒充毒品贩卖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此一来,前述结论便可能遭到质疑,因为如果我们对使用假币购买毒品的一方不论以诈骗罪,而对提供假毒品以获取真币的一方论以诈骗罪,便会使买方与卖方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形成不对称的刑法保护。不过,从刑法保护法益的更深层次探究,这种貌似不公正的处理结果可以得到解释。这是因为,对于给付伪钞的购毒者来说,其所骗取的利益是贩毒者原本就不应拿来交易的毒品,也即贩毒者根本不应当从此项法律禁止的交易中获得任何的好处;而对于提供假毒品的毒品出售者而言,其所骗取的却是毒品买家“干净的钱”,虽然法律禁止进行毒品买卖,但到头来被贩毒者骗走的利益却仍然是法律上认可的、毒品购买者应当保有的财产,正因为如此,在毒品交易的情形,法律便维持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即购买毒品者给付毒品卖家的是假币,毒品卖家不会受到保护;而贩卖毒品者交付给毒品买家假毒品的话,则要追究贩卖者的诈骗刑责。
(二)不知是假毒品贩卖的行为定性
司法解释对不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进行贩卖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这一结论获得了学界的赞同,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然而,将非毒品物质冒充毒品贩卖的以贩卖毒品罪处断在理论上有无法说明之处。首先,以非毒品冒充毒品进行贩卖并未侵犯刑法设置贩卖毒品罪所意欲保护的法益。因为假毒品并不能对使用者形成像真毒品那样的依赖与瘾癖,进而危害公众的身体健康。其次,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贩毒者的无知或失误就将不是毒品的物质认定为毒品,进而论以贩卖毒品罪,否则不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有主观归罪之嫌。[4]再次,将行为人不明知是假毒品而贩卖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有时还会造成量刑的失衡。如行为人甲谎称绿豆糕为毒品向乙兜售,同在现场的丙不明就里,积极协助甲进行出售的,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甲应当构成诈骗罪,丙应当构成贩卖毒品罪(未遂)。果真如此,丙可能要承受远重于甲的刑罚。然而,在此情形下,显然是甲起主要作用,更应受到责难,但适用法律的后果却使得因为受到同伴欺骗的丙遭到更严重的惩罚,这样的处理难说公正。
四、结论
在行为人使用假币骗取毒品等违法财产利益的场合,虽然我们可以承认行为人违法取得或占有的财物也能落入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但是如果法律已经无条件的禁止从事某种行为(禁止毒品交易),它就不能再提出应当如何进行此种行为(应当以真币购买)的指示,否则该禁止性的规定便无法得到贯彻。并且从行为可罚性的基础看,只有当行为人真的对他人实施了不法,这种惩罚才可以说是正当的。最后,以刑事处罚的方式来树立毒品交易过程中的诚信价值观,会导致施骗者滑向更不道德的境地。因此,行为人使用假币骗取毒品等违法财产利益的,不宜认定构成诈骗罪。
注释:
[1]林晖:《抢劫毒品不宜认定为抢劫罪》,载《检察日报》2005年1月19日。
[2]陈运亚、刘春林:《图过瘾抢劫毒品 “黑吃黑”涉罪被诉》,载《检察日报》2011年4月6日。《男子“黑吃黑”持枪抢劫毒品获刑五年》,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2/12/id/799298.shtml,访问日期2013年1月26日。
[3][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4]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