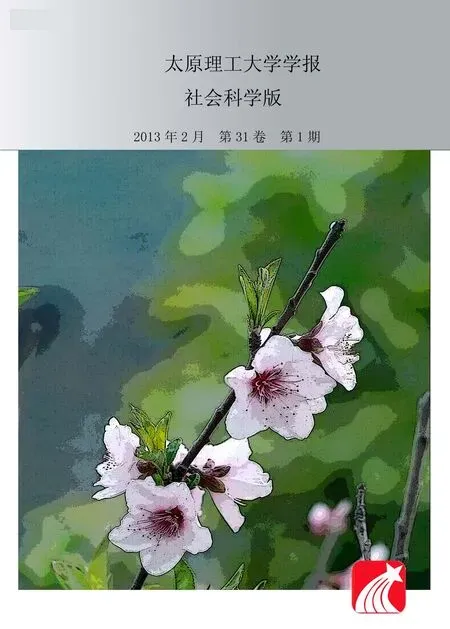刍议我国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
周 乾
(中国政法大学 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8)
一、 法治文明概述
厘清法治文明的含义首先应明确何为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有多方面的要求,包括依法办事、法律至上、法律工作的专业化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等等,但对其定义并不统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西塞罗在其代表作《法律篇》中写道,“法律统治执政官,所以执政官统治人民——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这是法律在政府行政中作用的经典表述。洛克在《政府论》对法治原则的内容概括如下:首先,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国家权力应该分立;其次,法律较为完备且被良好执行;再次,法律的主治仅限于已经公布的法律。国内有学者认为,法治具有十个标志:法律完备、法律平等、 法律至上、主权在民、保障人权、权力制约、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公正、党守法律[2]。
笔者认为,法治最基本的内涵应包括:第一,法律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第二,法律是公开透明的;第三,法律体系内部完整、一致;第四,法律被执行和遵守;第五,法不溯及既往;第六,程序正当。同时,“文明”与“文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明与科学、制度等技术性因素相联系,具有可变性和普遍意义;而文化与非技术性因素相联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地域性。”[3]法治文明属于社会政治文明的范畴,是指“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4]。法治文明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权利[5]。
二、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之必要性
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6]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一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法治文明的文化传统而言,“首先,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没有现成的文化伦理资源可供继承;其次,我国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还不长,还缺乏供法治的文化伦理生长的深厚土壤;再次,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还不发达,不足以承担建构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重任”[7]。“在我国现阶段……仅仅有了良好的法律制度远远不够,还必须花大气力去建构和重铸民族的‘法治的理性’;如果这个任务不能实现,我国法治化的目标势必因为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落空。”[8]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必须设计出符合市场化、民主化进程的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设计,更需要制度背后的文化支撑,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文化层面的创新与重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法律层面就要求实现法治,法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在文化层面进行改良、吸收与借鉴。在新的文化理念中,“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和首要目标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价值和基本目标”[9]。
格尔兹指出,“没有文化模式的指导,人类行为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10]文化要素是“把法律制度联结起来的价值和态度,它决定法律制度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中的地位”[11]。当代中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则体系,建成法治文明的新文化。
三、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之基本思路
对于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有学者认为,当前需要特别注重对公权力的制约和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努力避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12]。也有学者认为,“强化程序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由之路”[13]。笔者认为,“观念改变着世界。新观念的力量是变革我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引擎”[14]。在我国,进行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需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把法律宣传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抓
“从法治文化的理论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主要体现为法律观念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观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保障。”[15]进行社会管理创新,首先要把法律宣传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抓,让人们形成法治文明必备的思想观念。比如,在西方,婚姻也是一种契约。在中国,夫妻间的忠诚协议是否有效以其契约能否在感情领域适用,并没有形成多数意见,所以,相关的婚姻法律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可见,我国的契约观念虽有所增强,但与西方人的观念并不是一回事,与法治文明高度相关的契约观念之深入人心还需假以时日。
(二)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
主体意识是指主体在法治生活中要积极参与,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一种主动参与、积极承担的方式参与法治文明建设,要让每个人像关心自己的事业一样去关心法治事业的发展。这种主体意识的形成,需要政府的引导,需要社会成员自下而上的参与。“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16]文化创新要从法治文明构建的大局出发,改变民众极私的心理状态,使其关心社会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每个人为什么却像关心自己的事业那样关心本乡、本县和本州的事业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参加了社会的管理”[17]。我们现在对于游行、静坐等表达行为主要采取“堵”的方式,而较少适用“疏”的渠道。我国可以考虑培养公民的游行文化来提高其参与意识,通过实行批准制,明确游行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责任人,实行有组织的个人负责制,游行活动就能有序进行,因为无序的结果是有人要承担责任。这种方式能够减少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心理)对抗,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也是民主的体现,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三)把提高公民的幸福指数作为法治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
客观来说,我国人民当前的幸福指数并不尽如人意,正因如此,党和政府提出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进而增加人民的幸福感。人们感到幸福指数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劳动法律制度不完善、休假补贴法律制度执行不到位,以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共同作用,导致人们工作压力大,休息和休闲变成了一种奢侈,幸福指数大打折扣。西方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早就将“幸福”纳入法的价值序列。我们以前在法治文明构建方面,往往是局限于法律本身谈法律工作,开展法治建设。现在,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圈,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工作的着力点,法治文明的构建要形成让公众感到幸福的文化氛围,要把提高公民的幸福指数作为法治工作的重要目标。
(四)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黑格尔说:“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18]“一定的法律文化现象只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20]“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1]同时,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很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影响角度,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化 ”元素。[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反西化’的斗争任务。”[23]而且,“法治是一个文明过程”,“法治趋同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冲突”[24]。“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25],所以,“文化创新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6]。同时,文化的创新要面向世界。“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原则。”[27]我们应合理借鉴西方法治文明的有益成分,如契约自由、程序正当等,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没有继承,文化发展就失去了根基;没有创新,文化就失去了活力与生机”[28]。文化创新要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五)把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法治文化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
创建法治文明的文化基础,需要人才支撑。法律人才队伍的壮大是法治文化创新的保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中央要求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在法治文化的培育中,我们需要着力造就一批改革意识强、综合质素高的领导型人才,一批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一批拥有理论积淀又掌握实战经验的专家型人才。胡锦涛同志指出,“要用事业吸引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在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我们应做到以光辉的事业吸引法律人才,用法律实践锻造人才,用公平顺畅的机制激励人才,用具有执行力的法律制度保障人才。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法治文化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
“法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制度文明。”[29]文化作为软实力,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作用重大。就像有学者谈到温州模式时所说的,“没有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区域法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就没有温州模式的后续活力”[30]。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谁就能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的争夺[31]。“只有高度发达、高度完善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催化和孕育高度发达的和高度完善的法治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包括契约精神、责任意识、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通过以上努力,我们力争形成法治文明的人文精神,即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法治文化。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9.
[2] 李步云.法理探索[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8-14.
[3] 尹保云.“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70-75.
[4] 肖立民.法治文明的历史溯源及其当代启示[J].社科纵横,2009(5):71-74.
[5] 杨春福.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J].北方法学,2008(2):5-1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2.
[7]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6.
[8] 蒋先福.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J].法律科学,1997(6):3-9.
[9] 习裕军,宋国春.社会生态视阈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创新[J].实事求是,2012(2):59-61.
[10]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53.
[11] Lawrence M· Friedman.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J].Law and Society Review,1969(1):29-34.
[12] 刘炳君.论我国法治文明的两个重要范畴[J].政法论丛,2006(2):28-33.
[13] 江必新.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的几个新命题[J].中国法学,2010(4):70-75.
[14] Richard Stengel.The Power of Ideas[J].Time,2008(12):6.
[15] 刘作翔.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创新[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2):66-72.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
[1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70.
[18] 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56:104.
[19]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架构[J].法律科学,1998 (4):3-12.
[20] See J ·H·Merryman.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in M.Cappelletti( ed.),New Perspectives for a Common Law of Europe [M].Boston:Sijihoff Publishing Co.,1987:222-227.
[21] 俞吾金.培植公平正义观念的文化土壤[J].中国社会科学,2009(1):51-57.
[22] 姚建宗,黄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2):3-13.
[23] 张文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J].中国法学,2009(6):5-14.
[24] 舒国滢,程春明.西方法治的文化社会学解释框架[J].政法论坛,2001(4):135-148.
[2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9.
[26] 王 琳.文化创新与构建有中国特色新文化体系[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97-201.
[27] 王志华.解读西方传统法律文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1):53-67.
[28] 章剑华.把握文化工作的规律性[J].艺术百家,2009(3):1-3.
[29] 张继宗.走向法治文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青海社会科学,2008(4):38-41.
[30] 方益权,项一丛.从温州模式到温州法治模式——温州模式与区域法治文明论纲[J].探索与争鸣,2010(12):48-51.
[31] 韩 震.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观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9(1):4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