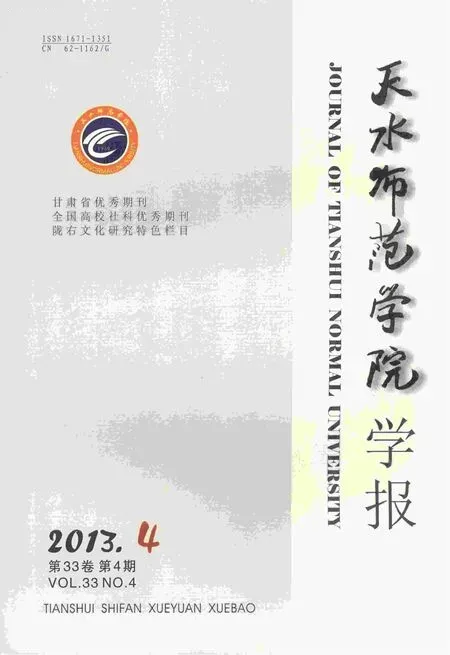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基础——“性三品”与社会化思想
周晓红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重庆 401331)
一、董仲舒对先贤“人性”的批判和发展
董仲舒关于人性的界定是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的基础。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儒家的先贤孔子、孟子和荀子等都曾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董仲舒用“扬弃”的视角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关于人性的定义。
孔子就人性问题上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1]263的观点。孔子非常注重后天的教育与环境,他认为人自出生以来,在本性上是基本上相近的或是相似的,但是仍然存在先天禀赋上的差异。人从诞生之时人性上的相似或是相近,发展到以后的相差很大,这与后天所处的环境以及所受到的教育不同有关。
儒家的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孟子,他从“心”出发提出了儒家性善论。孟子主张通过后天的教化,将人性中共同的品质发挥出来。
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同属战国时期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主张要采取礼与法来抑制人性中的欲望,使其按照既定的礼乐秩序生活,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治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荀子的性恶论较之孟子略显进步,其强调的重点在于人的欲望是“性”的一种表达形式,统治者可以根据人们不同的欲望表现从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控制方式。
董仲舒关于“人性”的观点,可以说是批判地继承了儒家先贤提出的观点。董仲舒在《实性》中有“性者,天质之朴也”,在《深察名号》中有“性才,生之质也”,又《天人三策》中有“质朴之谓性”等,这些关于人之性的界说无一例外地指出人的天生资质或禀赋便是人性。他关于“性”的定义,不仅包含了人的自然属性,而且包含了人的社会属性。“性”也是有等级、有差别,依照等级上的质的规定性,将社会上的成员分为“上民之性”、“斗筲之性”与“下民之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便是“情”。“情”是三种人性在量上的差别,不同的人性有不同的“情”,并通过自身的行为方式等各方面表现出来。董仲舒依据“人性”中善质的含量将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也就是“性三品”说。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提到了这三种人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董仲舒划分这三种人性的主要依据是其人性中所含“善”的多少,“善”就是“性”与“情”相结合的统一表现:
首先,第一阶层“圣人之性”。“圣人之性”中包含的是至纯至美的善,是人性发展到最后的追求和目标;董仲舒说:“行天德者谓之圣人”,[2]309那些具有像天一样德行的人是圣人。由此观之,董仲舒所说的圣人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具有高尚德行因为被授命为天子的者。第二,某些至贤至圣的三公或大臣,“三公之位,圣人之选也。”[2]125第三,作《春秋》,被称为“素王”的孔子。这些“圣人之性”都具有“纯仁淳粹,而有知之贵也,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积美阳芬香,以通之天。”[2]276
其次,第二阶层“中民之性”。中民之性中所包含的是一种向善的可能性——善质,这不是善,是一种趋向善的发展趋势。中民之性是指除了圣人之性和社会上斗筲之性以外的一切人。它不仅包括了除圣人以及统治阶级中的斗筲之民以外的统治阶级的成员,还包括了被统治阶级中的除了斗筲之民以外的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即中民之性包含了封建社会中绝大数的成员。董仲舒这样界定中民之性正符合了维护封建皇权以及圣人的神圣性的绝对权威的需要,如此便更好地维护了以皇权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政权。
最后,第三阶层“斗筲之性”。斗筲之性是冥顽不化的人性,其人性中不包含任何的善和善质,有的只有恶。故而,那些不能遵守封建伦理道德,不行仁义不讲人伦的人,都不能算作人,亦不具有人性。“斗筲之性”者没有“上民之性”者所表现出来的“情”,他们所具有的“情”,也就是“性”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是和鸟兽没有什么区别。斗筲之性在本质上不能算作人性,而是一种鸟兽之性,这种人性毫无善质,只有绝对的恶质,即使加之以王教也不能使其从善。
董仲舒根据人性中善、善质与恶质三者的比例关系将社会中的人分成了上述的三种人性。自古以来,每个思想家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开始几乎都是从人性的善恶判断开始的。从便于统治者采用其思想的角度出发,便不难解释其原因:通过一个关于人性界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人性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
二、性三品与社会化方式
一个有效的社会控制方式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采取与之相应的合理的统治方式。在董仲舒的性三品理论引导下将社会成员划分为若干社会阶层,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社会化方式,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
“圣人之性”者,也就是“上民之性”。“上民”主要包括上文中所提到的三类主要的人,他们的人性是至善至美的,因为他们的“善”是“性”与“情”的最完美的结合,具有“纯仁淳粹”之性,是一种“过善之性”,受于上天。圣人之性要转化为圣人之德是不需要借助外界的教化或是刑罚等其他的社会化手段,他们自幼生活在帝王之家,其生活环境以及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都使得“圣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社会化,“四法之天施符授圣人王,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2]113天施符所选出的王君,都是按照他们的祖先的品行、“性命”以及行为举止来确定的,这样使得这些被选中的君王具有一个王君该有的形象。他们不要刻意地进行“善”的社会化,他们只需要法天而行,“行天德”即可。圣人之性自身的善不但不需要教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发挥出来。此外,“圣人”还被规定为成民之性的教化者,“圣人之道,同诸于天地,荡诸四海,变习易俗。”[2]223“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3]2515只有经过圣人的教化,民性才能为善,“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除去至善至美的“圣人之性”以及冥顽不化的“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包含了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故又称为“万民之性”。“今万民之性,侍外教然后能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从中民之性的性质中可以看出其人性中包含了善质和恶质两方面,所以其发展也包含了两个方向。
对中民之性的社会化,主要是依靠教化和规范两种力量,同时中民之性社会化的完成也必须是内外因共同作用下才能完成。首先,中民之性必须具有能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2]174此处所讲的茧和卵便指代的是中民之性中的善质,丝和雏则指代的是善质经过教化后成为的善。中民之性中包含了这样向善的可能性,上天立王以教化百姓,王立社会规范道德来约束百姓,“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实性》)这样,在内外因的作用下共同完成了中民的社会化。
具有斗筲之性的人,董仲舒并没有将他们算在在人的范围之内:“弗系人数而已”。他们只具有和鸟兽一样的品性,他们不能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和仁义人伦,本质上没有一点善质,只有纯正的恶质。这一阶层的人虽不在社会化主体的范围内,但是其存在也对封建统治有影响。要完成这一阶层的社会化,使其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是完全不可能了。斗筲之性的人要完成社会化,符合要求,要采取的是刑罚和惩治等具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化手段。
董仲舒利用“性三品”进行社会分层从而明确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并且进一步针对不同的阶层采取有效的社会控制方式与步骤。社会控制就是对君主以下的不同阶层的控制,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汉武帝要建立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理想社会,就需要根据董仲舒所划分的阶层,按照不同阶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尧舜禹一样品性的“上民之性”是君主主要的依靠力量,君主要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社会控制,从而使其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力量,并且成为教化和引导“中民之性”的重要力量。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这“圣人之性”的王公大臣以及“中民之性”中能够向善的社会成员都符合汉武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要求。同时,对于具有善质而未能善的“中民之性”,统治者要对其进行教化,使其向自己的统治力量靠拢,符合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任由他们向着与大一统相背离的方向发展。至于“斗筲之性”由于天性顽劣已经不能通过教化和引导的手段来使其纳入统一的潮流,对于他们的控制则需要采取强制的打压手段。
三、结 论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认为,要顺利实现对不同阶层的统治,首先要顺利完成不同阶层的社会化,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社会化方式:“圣人之性”是先天就具有纯善至美之善的,他们的社会化无需外界的力量,只要遵从他们的内心,自然流露的便是善,便是稳定统治所需要的;“中民之性”中包括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即善质和恶质,因此作为社会成员的大部分他们社会化的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统治的稳定与否,他们的社会化除了本身要具有向善的可能性这个内因外还必须有外因的共同作用,通过统治阶级的教化以及制定的社会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使自己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至于“斗筲之性”,他们的人性中只有纯恶的东西,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和外界的教化和规范都不能顺利完成社会化,这一阶层的社会化必须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用刑罚等方式进行社会化。根据不同的人性将社会成员分类,并对他们采取不同的社会化方式,顺利完成各阶层的社会化,尤其是政治上的社会化。民众政治社会化的完成是一项政治制度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一项政治制度得到民众的信任、支持和愿意承担的必要保障。社会成员只有在人性深处承认统治者采取的统治是“合法”的,他才能愿意服从,愿意承担义务,才能完善社会控制,从而不但可以减少政治管理成本而且更达到建立封建统一社会的理想以及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团结与整合。
[1]张燕婴.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阎丽.董子·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康喆清.董仲舒人性学说的重新诠释——对“性三品”说的质疑[J].前沿,2011,(18).
[7]张国妮.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J].社科纵横,2011,(8).
[8]王先亮.论董仲舒与王充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J].衡水学院学报,2011,(6).
[9]曾振宇.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J].史学月刊,2002,(3).
[10]徐睿.董仲舒人性论思想及其评析[J].科教导刊,2011,(5).
[11]周春兰.论董仲舒的理想人格[J].唐都学刊,2009,(6).
[12]刘永艳,杨国玉.董仲舒社会控制规范体系探析[J].求索,2007,(9)
[13]张文英.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君主教化责任[J].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9,(4).
[14]刘力.董仲舒大一统帝国的社会控制思想[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