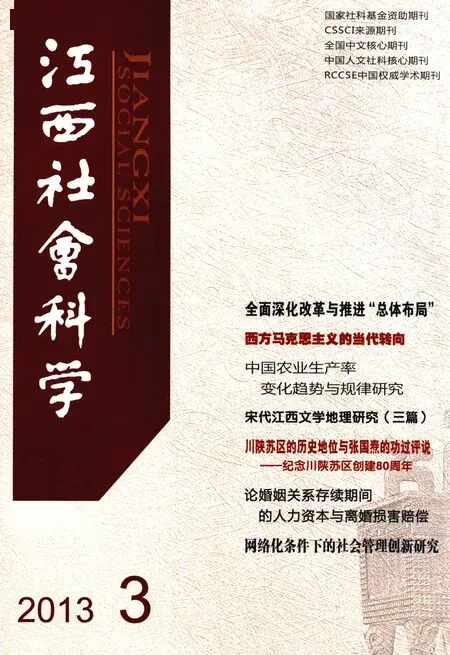伽达默尔解释学和两种“事情本身”
■陈赛虎
“面对事情本身”(Zur Sache selbst)为胡塞尔所提出,也是现象学运动的一句著名口号。法国现象学家亨利把它作为现象学的四条基本原理之一。[1](P25)“事情本身”这一概念,意在追问正确的认识所由之出发的根据和基础。“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2](P179)
相对于现象学着眼于事情本身的本体论层次而言,解释学比较强调事情本身的认识论层次。通常在人们看来,认识的根据和基础其实也就是认识的对象,两者是一回事。所以“事情本身”这个概念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真正的认识对象。希望我们的认识总会有一个真正的对象或者有一个可被理解的“事情本身”,这种“善良意志”几乎是所有解释学的共性。稍微比较下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的区别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伽达默尔自述他“以新的方式达到后期海德格尔所想完成的工作。为了这个目标我容忍自己坚持意识概念,尽管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批判正是反对这种意识概念的最终建立作用”[3](P648)。利科也认为:“相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伽达默尔的研究标志着从本体论返回认识论问题的开始。正是依据这一点,我在这里讨论他的贡献。……如果说海德格尔通过一种重要的超越运动避免了与某些人文科学的争论,而伽达默尔只能插足于一场更为痛苦的争论中,确切地说,这因为他认真地考虑了狄尔泰的问题。”[4](P60)
追寻认识的真正对象,在现象学上相当于事情本身所显现的内容,而认识所由之出发的基础和根据则更加本源化,相当于事情本身的显现性或者显现方式。于是在现象学那里,事情本身的两层含义问题被转化为显现之物与显现的关系,或者显现内容与显现方式的关系。然而从认识的根据和基础到认识的真正对象,从显现到显现之物,伽达默尔解释学是否正确地处理了这一现象学基本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下在伽达默尔那里“事情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伽达默尔对浪漫主义解释学的批判
浪漫主义解释学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有一句名言:“要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5](P61)这一句话里包含了施莱尔马赫解释学至关重要的两个要点:作者本人及其话语两个层次。
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作者的意图,而不是理解文本的真理内容。理解作者意图仅仅依靠文本本身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各种方法来说明作者的意图,因此施莱尔马赫认为,误解是一种普遍现象,为此他创建了普遍解释学理论。按照狄尔泰的看法,普遍解释学的建立使得解释学从独断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施莱尔马赫因为区分作者意图和文本内容而建立普遍解释学,而他的解释学之所以被指责脱离了真理问题,也是相同的原因。伽达默尔的批评主要有两个角度:(一)解释的对象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文本本身的可能真理;(二)解释始终受解释者的历史境遇所制约,不是对作者意图的“客观”认识。如果从事情本身这一概念来理解,那么显然事情本身不是作者意图,而是文本的可能真理。其次,寻求对作者意图的客观理解也不符合解释行为的事情本身。
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3](P220)也就是说,事情本身已经改变了,在时间距离中事情本身发生着意义增值、信息湮没等种种变化,因此修复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3](P222),这句话仿佛是接着上面一句话来讲的,但实际上已经换了一个角度。说修复是无效的,这是把历史对象的内容作为事情本身,是从内容出发。说历史精神不在于修复,这是把理解方式作为事情本身,是从方式出发。
伽达默尔并不阻止我们进一步去追问作者的意图,但这种行为却会发生在对文本真理的理解试图失败之后。首先此观点指出了两种解释动机:一方面,我们有关心作者意图的“客观性”动机;另一方面,我们总是会有从自身应用出发而去关心文本真理的“动机”。现在的问题就是,哪一个动机更加根本?伽达默尔的回答显然是后者。关键词“之后”就指出了解释学并不否认追问作者意图的“客观性”研究意义,而是指出这种追问从属于对文本可能真理的兴趣,并且归根到底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出。因此追求“客观性”解释的行为,其实是真正的解释行为的一个分解动作,并不能作为完整的解释行为理论。追问作者意图对应用有一种从属性,这才是解释行为的事情本身。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浪漫主义解释学的批评中出现了两种“事情本身”的运用思路:一方面,事情本身是文本本身的真理内容,即认识的真正对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事情本身之所以是文本内容而不是作者意图,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理解方式总是从自身出发去理解的缘故。理解内容的事情本身依据于理解方式的事情本身,内容之所以如此显现,是因为显现方式之如此这般的缘故。理解方式着眼于正确认识的基础和根据,而理解内容则着眼于认识的真正对象。这里事情本身就凸显出了显现内容和显现方式的张力。
二、面对事情本身与回到事情本身
为了保证第一部分提出来的事情本身作为显现内容和显现方式的张力的问题确实存在,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返回解释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的现象学文本上来。这种对显现内容和显现方式之间的区分,我们可以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找到大量的依据。
胡塞尔认为:“根据显现和显现之物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一词有双重意义。”[6](P18)现象一词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指的是显现内容,显现之物。现象一词也可以作为动词来用,指的是显现之物的生成和构成过程,即显现之事件。
显现之事件也就是显现之物的被给予方式。显现就是有一个东西被给予某“人”,因此“显现”和“被给予”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回事。“被给予”是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而言,即被给予的承受者是意识活动,“显现”是从意向相关项而言,即显现的结果一般是呈现出一个意向对象。当然,“被给予”的用法更广泛,因为给予的被动者除了意识活动之外,也可以指被给予之物,即显现之物。换言之,显现一词只涉及被给予之物,而“被给予”则同时涉及被给予之物以及被给予之“人”。
从显现之物的被给予方式出发,很容易就建立起和事情本身的关联。胡塞尔晚年就谈到了被给予方式和事情本身之间的一种先天相关性(Korrelationsapriori)。他认为真理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视阈被掩盖了:“世界(即我们总在谈论的世界)和我们的主观给予方式的相互关联,从来也没有引起哲学上的惊异。”[7](P200)然后,胡塞尔回忆他现象学的突破源头:“当第一次想到经验对象和给予方式的这种普遍关联的先验性,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以至于从那以后,我毕生的事业都受到系统阐明这种相互关联的先验性的任务的支配。”[7](P202)
只有站在这种先天相关性的高度上,我们才能理解到,被给予方式既不是被给予内容上的样式,也不是被给予的具体过程,而是事情本身的被给予性的纯粹显现。或者干脆通俗地说,被给予方式就是并非来自显现之物,却在显现之物身上所环绕、所“呈现”(因为通常我们视而不见)的一种被给予性。值得一提的是,被给予性在法国当代现象学家马里翁那里被提高到现象学最根本的地位上。
被给予性就是现象学用来刻画事情本身的最终概念。被给予性不仅通过被给予方式直接显现了自身,也通过被给予内容间接显现事情本身。被给予方式和被给予内容在被给予性的基础上自然有着根本联系,两者并不是脱钩的。在被给予方式之中,虽然还没有对象,却可以说已经含有了对象内容的“种子”。否则被给予方式就变成了一种与对象无本质关联的主观意识形式了。因此胡塞尔强调,认识并不是一个始终相同的空口袋,这次可以放入此物,另一次可以放入他物,相反,“我们是在被给予性中看到,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起自身”[8](P179)。
由此我们有了两种询问事情本身的思路:一种把现象看成事情本身的显现内容,即从显现内容来询问事情本身;一种是把内容的被给予方式看成真正与事情本身相关的东西来询问事情本身。如海德格尔所说:“我必须忽视事物内容的什么而只关注这一实情:对象是一被给予者,是以切合姿态的方式被把握的。因而,形式化起源于纯姿态关系本身的关系意义,而不是源于‘一般事物内容的什么’(Wasgehalt)。”[9](P68)国内学者陈家琪也区分了面对事情本身和回到事情本身这两种说法。他说:“以讲述方式描述事情本身是一回事,而在事情本身中通过对意图和信念的领会来让事情本身自己呈现自己,自己显示自己则是另外一回事。”[10]显然,面对的事情本身朝向的被给予的内容,所回到的事情本身才是被给予方式。
三、伽达默尔两种“事情本身”的背离关系
我们有很明确的文本证据,可以说明伽达默尔的“事情本身”意思是真理内容而不是真理内容的被给予方式。伽达默尔对“事情本身”做了一个很明确的解释:“所有正确的解释都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察觉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并且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本文,而本文本身则又涉及事情)。”[3](P345)“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谈话模式来考虑诠释学现象,那么这两个表面上是如此不同的情况,即文本理解和谈话中的相互理解之间的主要共同点首先关于某事情取得相互理解一样,解释者也试图理解文本对他所说的事情。”[3](P490)可见他表达得很明确,事情本身就是文本意义内容所关联的事情。洪汉鼎也持这种看法,“‘事情本身’就是被讨论的主题”,“作为真理内容的事情本身”,“因此,‘事情本身’就是我们要理解的文本以及谈话要取得理解的对象或内容”。[11]
然而我们又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伽达默尔那里,“事情本身”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和用法,即从真理内容的被给予方式来理解“事情本身”。伽达默尔在一篇私人书信里回应贝蒂的批评时说道:“从根本上说我并未提出任何方法,我只是描述了实际情形……例如,当你阅读莫姆森所写的古典论文时,你也立即就知道这篇文章只可能在何时写成。即使是历史方法的大师也不可能使自己完全摆脱他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试图超越现代科学的方法概念进行思考并在根本的一般性中考虑一直发生的事情。”[3](P689)这里面所谓的“一直发生的事情”指的就是作为一个事件而言的理解本身。
伽达默尔对理解的著名定义是:“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3](P387)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效果历史事件并不是单纯指理解,真正的效果历史事件是“人和历史对象的某种统一体,关系”[3](P387),理解则在这个作用机制中浮现出来。历史事件和我们的理解一样都从属于它,正如同作者意图不是真正的文本内容,原始事件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后者是在时间距离中才逐渐成为它自身。如果把历史事件看成一个词语,那么时间距离更像是一张文本之网,词语在文本之中才具有我们所看到的意义。时间距离正是效果历史事件发挥作用的基础,历史事件是在效果历史事件中“被给予”。因此我们又回到第二部分的观点,作为事件之给予方式的效果历史事件比普通的历史事件更接近“事情本身”和“历史实在”。
理解首先意味着对某种事情的理解,而理解本身又是一效果历史事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伽达默尔那里,事情本身确实存在着两层含义:第一层为他的具体论述所支持,第二层却能在他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中找到根据。值得一提的是,洪汉鼎也表现出相似的分歧。一方面如上文所引,他把事情本身看成是真理与文本内容,另一方面,他又作出结论说伽达默尔的事情本身就是历史性。[11]
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两种事情本身的名义和实质的背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多义性,而是一种重话语意义轻话语事件的理论倾向。上文已经指出,伽达默尔把对话所说的、所围绕的东西叫做事情本身。然而,“所说”是一件事情,“说”本身又是另一件事情。说与所说的关系在利科那里被发展成为事件和意义的辩证法。利科认为,话语就是某人对他者指向某一事情的一个事件。可见在伽达默尔名义上事情本身的框架里,只包含话语意义,而不包含话语事件。这种倾向也能够在伽达默尔的“时间距离”和利科的“间距化”的比较中凸显出来。利科的间距化四种形式[4](P14),前两种涉及了意义的间距化,后两种涉及了事件的间距化。而伽达默尔的时间距离概念仅相当于利科间距化四种形式的前两种。
其次,伽达默尔解释学这一重意义轻事件分析的倾向,也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批评。后者主张一种批判理论应当先行于解释性理解。比如在精神病理学中,病人的自我理解是被扭曲的,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发生学解释和批判理论。“只有在能够同时回答‘为什么’,即在根据系统歪曲本身的初始条件来‘解释’症状景象出现的情况时,系统被歪曲表达式的意义内容是什么,才能被‘理解’。”[12](P284)这要求超出解释学对意义的关注而去到他称之为“关联体系”(reference system)[13]的东西,关联体系也可翻译为指称系统,由权力关系和社会内的社会劳动条件所组成。解释学如果缺乏这一指称系统,即全面的社会理论,就可能停留在表面层次而不能进入意识形态批判这一深度层次。查理德·德伯恩斯坦批评说,在伽达默那里,“我们找不到对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实践被扭曲原因的任何详尽的系统的分析”[14](P198)。值得一提的是,指称在利科那里也从属于话语之事件,而不是意义。指称是说之事件,而不是所说的事情。换言之,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应当首先对事件有一个说明,才能真正理解在事件中所表达的内容背后的含义。
伽达默尔重意义轻事件的倾向可以用他所谓的保守主义来刻画:即过于相信事情本身的被给予方式,因此用对这种方式的服从代替了人的方法论介入。人可以参与,但不是主导。例如他说:“理解甚至也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是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事件的行动……因为诠释学理论过多地被某个程序、某种方法的观念所支配。”[3](P375)这里就包含了一个貌似悖论的主张,伽达默尔十分重视这个“置身于传统事件的行动”,同时又反对“某个程序、某个方法的观念的支配”。这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无为思想,人应该顺应并参与历史性,但不应该把自己的人为因素 (方法论)带入。这种重视却又在方法上回避事情的被给予方式的做法,让伽达默尔抓住了事情本身又失落了事情本身,解释学的重心最终落在对内容和意义的关注上,缺乏一种对事件的分析和批判,从而不能真正让解释学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两种事情本身缺乏一个方法论中介,也使得显现方式和显现内容的关系实际上处于脱节或者扭曲状态。
四、法国现象学运动对伽达默尔两种事情本身问题的处理
海德格尔说:“我们把领会使自己成形的活动称为解释。”[2](P173)解释总是追求让对象“成形”,试图赋予对象以一种可理解的形式,从而达到对象自身的融贯,以及对象与我们之间的融贯。这在解释学那里被表达成一种根本的信念,即我们任何言行、交往,哪怕是独白和沉思,都是为了寻求理解或自我理解和一种善良意志:即我们总是能够达成一致的理解。套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解释学关于理解的信念和善良意志,其实是对这种“赋形”欲望的表达。
赋形欲望相当于我们上文所提及的“面对事情本身”。解释学总是企图面对一个事情本身,导致它经常游离于真正的事情本身之外,而且反过来还会遮掩了事情本身的另外一种显现模式。这就使得两种事情本身的对峙,成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根本特征,进一步地,可以看做是所有类似的解释学的共性。
列维纳斯通过对死亡的精彩分析让这种面向一个事情本身的欲望受到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抓住死亡事件的本质。面对死亡,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开始了筹划,开始去“存在”。然而列维纳斯却认为,死亡的真正意义恰恰不是筹划,而是打破我们的筹划,撕裂我们的存在,让我们不知所措,死亡事件无法被看成是一种“意向性或实存性设计”。死不属于我们与存在的关系,不在前理解之中,处在经验之外,也就是说死无法被赋予一个可理解的形式。
死亡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存在之外还有他者,理解之外还有不可理解的东西。这正是列维纳斯对我们的启示中最宝贵的东西。因此列维纳斯认为在表面看起来,“哲学本质上是存在的哲学”,然而,更深层的动机来自“对始终作为他者的他者的恐惧”[15](P35)。我们一切寻求安身立命,寻求“向死而在”,其本质都是一种逃避无法被纳入自我理解的他者,试图在虚假的存在和总体化中寻求安全感的行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意向性对明证性的偏爱,以及解释学对成形与赋形的欲望,是一种关于被给予内容的独断论,因此反过来遮蔽了被给予方式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亨利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归结为“世界的显现”模式。[16]“世界的显现”模式已经预设了世界的存在先于显现,即显现是向着某种预设了的东西 (在胡塞尔那里是明证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在世界中存在)而去的,这种预设限制了显现的纯粹性。也正是这种预设使得胡塞尔把显现和直观性等同起来。也使得海德格尔把显现和“出离”等同起来,如海德格尔说:“世界随着诸绽出样式的‘出离自己’而‘在此’。”[2](P414)
因此,从亨利的理论来看伽达默尔解释学两种事情本身的运用分歧,其根本原因显然在于事情本身的被给予方式被意向性和出离式的显现模式遮蔽了,限制在一种对象性的显现模式之中。相应的,解决方法就是返回到纯粹的现象性(显现)上来。而纯粹的现象性才是现象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和所追求的事情本身。关于这纯粹的现象性是什么,见仁见智,亨利当然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五、结语
施莱尔马赫有句话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开花乃是真正的成熟,而果实只是那种不再属于有机植物的东西的杂乱的躯壳。”[3](P299)尚杰提出了一个命题,即“解释学”的没落与“描述学”的兴起[17],批评解释学违背了时间的绵延性。他认为解释学没落了可能有过于激进之嫌,但确实切中了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尚杰和法国现象学对解释学的批评的可取之处,并不仅仅是说我们从显现之物返回被给予方式的事情本身上来,我们能得到不同的解释学果实,而在于指出,在显现之物的果实成熟之前,含苞待放的被给予方式就已经直接给出了事情本身,当我们对文本还处于不得甚解的时候,我们还无法讲述关于生活的故事之前,文本和生活已经在此。
[1](法)亨利.现象学的四条原理[J].王炳文,译.世界哲学,1993,(1).
[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3](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法)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5](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A].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7](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9.
[9](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M].孙周兴,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10]陈家琪.作为一个释义学话题的“回到事情本身”[J].开放时代,1998,(2).
[11]洪汉鼎.论伽达默尔的“事情本身”概念[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2).
[12](德)哈贝马斯.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A].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3](德)哈贝马斯.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J].郭光义,译.世界哲学,1986,(6).
[14](美)乔治亚·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英)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M].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6]方向红.手势的现象学:从胡塞尔、德里达到亨利[J].南京社会科学,2004,(10).
[17]尚杰.“解释学”的没落与“描述学”的兴起[J].哲学研究,2011,(7).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