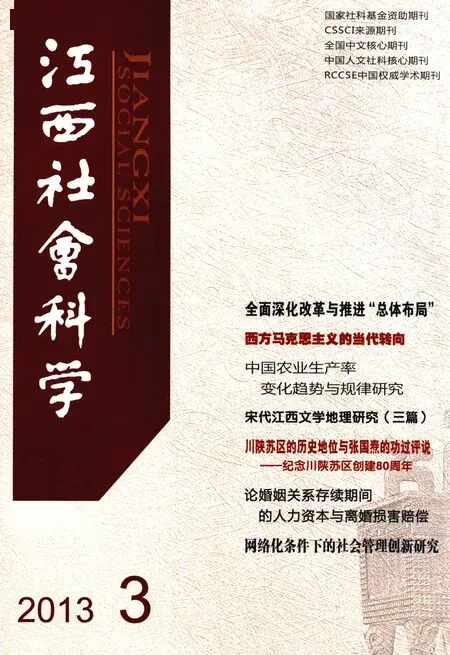作为乾嘉汉学阐释目标的“是”
■崔发展 宋道贵
乾嘉时,汉学家普遍认为宋学有蹈虚之弊,故而主张回归原典,并自觉地将这一工作定性为“实事求是”之举。不过,对于汉学家们的这一自我定性,当时已有质疑之声。如对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龚自珍明确指出该书“名目有十不安”,而首要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1](P346)。一般的讲,读书人固然可以普遍抱有“实事求是”之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实事求是”被明确地作为口号,被强化为一种自觉意识,乃至于被虔诚地尊奉为治学的基础观念,则是首次在乾嘉汉学家这里才真正实现的。[2]
由此,在阐释学的视域中,或可以“实事求是”作为进一步研究乾嘉汉学的一个突破点。作为一个经学阐释命题,“实事求是”或可细分为“实事求是者”(阐释主体)、“实事”(阐释对象)、“求”(阐释方法)与“是”(阐释目标)等几个层面。而其具体内容亦可概括如下:乾嘉汉学家认为,只要自己(“实事求是者”)从坚实的、客观的阐释对象(“实事”)出发,通过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的阐释方法(“求”),就能将客观的经文、经义或儒道(“是”)阐释或还原出来。①
本文的主旨,将着重对“是”进行探讨。就阐释目标的设定(而非事实或结果)而言,乾嘉汉学家辨伪原文的工作最终只是为了重构其中的原义。一般而言,在汉学家“实事求是”的阐释活动中,“实事”指原文、礼仪、典章制度等阐释对象,而“是”则指原义、礼义、义理等阐释目标。虽然求“实事”最终仍是为了求“是”,但二者的具体所指并非截然二分。在汉学家这一考证群体中,与求是(求原义)相比,求事、求实(求原文)同样会被视为合乎“实事求是”的举动而得到称许,汉学家考证典章制度虽然首先是为了求原文,但作为求原义的基础性工作,这种考证仍往往被置入到求原义的大方向下而得到某种职业性、群体性的认同。虽然汉学家多有将“实事”与“是”等而视之的错位理解,但原文作为原义的基础层面,必然被保存于原义之中,或者说,实事求“是”包孕着实事求“事”。由此,汉学家所设定的阐释目标(“是”),就应蕴含原文与原义两个层面。
在汉学家这里,“实事求是”乃是为了消除人们对经书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文与原义的客观认知。由此,在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活动中,如果说“实事”是客观认知的对象,“求”是客观认知的行为,那么,“是”(原文与原义)就是客观认知的结果。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一认知结果进行考量。
一、思想与思想性:汉学家有无义理
乾嘉乃至乾嘉之后的清儒,几乎都认为汉学家在追求义理上乏善可陈。且不论宋学家一以宋儒义理为义理,自然不会承认汉学家有什么义理可言,然而即便是在汉学家群体内,义理上的不足,亦被视为汉学自身的一个毛病。
其实,汉学家之所以常常忽略义理,并不是不自觉,而是他们并不主张建构义理或思想体系,这乃是由其所遵循的学术或思想规范所决定的。对于他们,发挥义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因为发挥义理与蹈虚之间的必然关联,一向是汉学家斥责宋学的惯用逻辑,以致由此而来的杯弓蛇影之情形,在汉学家中可谓屡见不鲜,如王鸣盛甚至明言“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3](《序》,P1)。对于多数汉学家而言,不要说发挥义理往往被视为重蹈宋儒之覆辙,即便是采用宋儒的概念或言论,也往往被汉学家在群体意识形态上强化为不可接受的东西。如戴震虽以阐发大义的《孟子字义疏证》为其得意之作,但此书并没有在汉学家这里得到群体性认同[4](P157);再如章学诚旨在发挥义理的《原道》,亦因篇名陈旧而被诋为“陈腐”[5](P41),等等。汉学家之为学或有暗承宋学者,而这也常常是被刻意隐讳的事情,如焦循说:“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姓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6](卷七,P104)这种讳莫如深的警惕或担心,阻碍了汉学家通向义理的道路。由此,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的义理主张,在当时之所以遭到诸多质疑,不能不与这种学术环境大有关联。
清代以后,汉学家的义理问题逐渐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在学术界的研究中,所谓“义理”(思想、哲学),几乎专属宋明理学,而清代汉学家除戴震、焦循、阮元等极少几个人外,大多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于是乎,清代汉学家有考证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的看法,几成定论。梁启超、钱穆、徐复观等人是如此看法,而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如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对清代考据学更是不屑一顾。但学界亦有不同看法,像侯外庐、余英时、张寿安等学者,都认为清代儒学并非只有学术史上的意义,并提出了“清代新义理学”或“乾嘉新义理学”的主张。
那么,汉学家究竟有无思想可言?不可否认,恰如余英时所说,汉学家有确定的思想走向(思想性),其考证的背后有义理或价值信念的支撑。[7](《自序》,P2)汉学家所向往的境界可以说是寓“思”于“学”,即以博实的经典考证来阐释原始儒家义理的确切含义,而这就表明,汉学家追求原文与原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诉求,因为哪怕是追求原文这一举措,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思想走向,更何况是对原义的追求。其实,“实事求是”的主张本身,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体现。换句话说,知识论述不可能完全没有价值观的体现。
不过,我们虽然应当承认乾嘉乃至清代汉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但考据学家是否提出义理主张与其是否有思想史上的意义,恐怕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这里就有一个心理事实与历史事实之区分的问题。心理事实体现出一定的思想或义理走向,而历史事实则是他们对考据的偏执与执迷。由此,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才都会对这种执迷有诸多批评。而由此而来的补救措施,基本是在如下两个方向展开的:第一,寄希望于仍旧在汉学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主要是纠正偏执于训诂而忽略义理的倾向,注重在训诂的基础上推阐经书之义理;第二,希望借助宋学来填补汉学在义理上的空白,强调汉宋兼采的必要性。这既说明了乾嘉时期、尤其是乾嘉之后,汉宋兼采何以逐渐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但也从反面表明汉学家在义理探求上的不足。
其实,一如宗教性不能等同于宗教,思想性(思想走向或动向)也并不等同于思想本身。尽管每个人都会有价值取向,但我们绝对不会认为任何人都是思想家。汉学家无疑有一种“道问学”的思想走向或价值取向,但不可否认的是,义理上有所创见的、尤其是主动建构思想体系的清代汉学家,在整个汉学家群体中都是极个别的,而基本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甚至只有戴震、焦循一二人而已。从整体上讲,清代汉学的义理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不愿意讲任何义理仍旧是汉学家们的鲜明色彩。因而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即便是程朱义理的支持者,对所谓汉学的新义理也没有清晰的察觉。汉学的最大弊端,始终被认为是只做考据不讲义理,而不是讲一套与宋儒针锋相对的新义理。[8](P71)而主张汉学“新义理”的学者们,需要花大力气才能从汉学家零星的文字中将这种所谓的新义理发掘出来,亦表明汉学家其实对它们并不重视。
二、求古与求是:复古主义还是客观主义
在追求原义方面,汉学家或是义理观念淡漠,或是对推阐义理有心而无力,因而总体上其义理成绩并不像其训诂成就那么显著。但是,并非所有的汉学家都不涉足义理,如哪怕是指责汉学家偏执于训诂之弊的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仍旧承认部分汉学家是有追求义理的明确意识与行动的。[9](P4)总体来说,无论是乾嘉义理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几乎都认为戴震、焦循、阮元、凌廷堪等人体现出了汉学家亦讲求义理的一面。问题是:如果说汉学家旨在追求经书之原义,那么,这几个汉学家的义理,是否合乎六经的原义?
汉学家缘古求是,所以“求是”只能以“求古”为前提。但信古往往会带来盲从,以至于有些汉学家直接将理论上的是非问题 (求是),完全等同于是否合于古训(求古)的问题,如最先标举“汉学”之旗帜的惠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10]。
但是,遵循“实事求是”之教的大部分汉学家,却有一种求真是的客观主义精神,这使得他们不至于像惠栋那样陷入以古为是的复古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惠氏虽是其之后的汉学家为学的一个标杆,但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可供后来者吸取经验教训的反思对象。如戴震虽高扬惠氏之学,但却强调“定宇求古,吾求是”[11](卷二十四)),以示二者为学之异;而王引之曾致书焦循,亦提及惠氏为学之弊以求共勉。[12](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由此,汉学家群体虽以古为师,但却并非尽信于古。
那么,何谓“是”?前文说过,“是”包含原文与原义两个层面。在指涉原文时,“是”无疑有比较确定的版本,通过考证、辨伪、辑佚等工作,基本可以将之复原出来;但当指涉原义时,“是”却又不得不陷入种种争议之中。对于何谓经书之“是”这一问题,且不说汉儒与宋儒有着诸多不同乃至根本上的差异,即便是在汉儒之学内部,义理的统一性或共识也从未达成,这一点恰如方东树所说:“汉儒虽专精,然岂必皆是?当时五经,已各异议。”[13](P362)由此,当汉学家以复原经义为鹄的时,如何才算是复原出了经书的本义,恐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如,依焦循的说法,戴震自有一套戴氏义理,这套义理固然不同于宋儒之义理,但它是否合乎六经、孔、孟的原义,或者它是否合乎汉儒之原旨?恐怕很难这么说。对于清代汉学与汉儒之学的异同,章太炎、刘师培、熊十力、徐复观等早已有论,至少从二者的相异来看,很难得出戴震所阐发的经义与汉儒之经义相同的结论来。[9](P60)不唯戴震、焦循等所阐发的义理与原始儒家、汉儒不同,即便是他们之间的义理主张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曾详细地指出了戴震与其后学(焦循、阮元、凌廷堪)之间的不同,虽意有偏颇,但亦不能不谓之有所创获。[14](P132)这说明即便是在追求义理的乾嘉汉学家内部,其所求之“是”并不是什么定论,它体现出的仍旧是不同的思想类型而已。
事实表明,乾嘉汉学家阐发出的义理,并不是向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归。由此而言,乾嘉汉学家对原义的主观诉求与其最终所阐发义理的客观结果,并不是同质性的问题。而这就意味着,汉学家口口声声的惟从其是的客观主义诠释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究其本源,乃在于这之中有个“客观主义”如何可能的根本性问题。
三、求是与求用:合法性还是有效性
针对汉学家这种类型的客观主义,方东树常常提出“言各有当”的原则予以反驳。[13](P39、49)此时,“言各有当”所指的乃是语词、概念乃至命题在当下的有效性。在方氏看来,面对佛老的冲击,旨在维护儒学正统的宋学正是遵循着一种当下化的、有用性的解释原则。试想,如果这一原则成立,汉学家对宋学陷入非客观主义的诸多指责,自然会大打折扣。
不过,若是针对惠栋 (以古为是)等复古主义者而言,方氏所提出的有效性原则,或可说是有力的批驳。但如前所述,多数汉学家虽主张师古、复古,却并不是复古主义,因为他们普遍重视的乃是“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15](P390),这也就是说,他们看重的是经义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有效性。当然,汉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否认有用性,他们只是强调,在阐发经书大义时,并非有效性而是合法性,才应是阐释者首先持守之原则。如阮元说:“‘寂然静明,感照通复。’以此为事,可以练身体,可以生神智,可以为君子,可以为高士,可以为名臣,可以守廉介,可以蠲嗜欲,可以澹荣利,亦有用有益也。然以为尧、舜、孔、孟相传之心性,则断断不然。”[16](P342)阮元并不否认宋学的有用性,所以学界常常将之视为汉宋兼采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阮元却坚持认为有用性(求用)与合法性(求是、存真)有着实质上的不同,二者并不能相混淆。由此,方氏的申辩,若仅仅是着眼于有效性或有用性,那么,他其实已经跳出了汉学家的既定论域,而其论辩的有效性毕竟还是有限的。
不过,汉学家对合法性的强调,无疑体现了他们对“实事求是”的独特理解,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却又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既然求是而非求用才是第一原则,那么,对这一原则的贯彻势必导致为学与为用的分离,而这反而证明了通经与致用之关系的非因果性。事实上,汉学家身上的确体现出了这种为学与为行的分裂[17](P20),而宋学作为兼采的对象,在乾嘉后期越来越被倚重乃势所必然。
其次,对于经学阐释而言,汉学家希望通过回归原始文本来确保文义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文本的合法性与文义的合法性并不直接等同,因为即便是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阐释者从中发明的大义总会有所差别。而这就意味着,文本对于阐释者的限定性,只是合法性阐释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汉学家注重文本的合法性,但亦明显有以此取代文义合法性的倾向。
再次,汉学家对合法性的强调乃是不对称、不全面的,因为它只是考察了经书对义理之合法性的限定,却丝毫没有顾及到阐释者自身追求客观性之能力的合法性问题,亦即“实事求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四、求虚与求实:虚实的相对性
学术重心的转移,从特定的角度看,正表现为虚实之间的转换。比如,我们可以说,程朱以理学之实代佛老之虚,陆王以心学之虚救理学之实,清代汉学又以实纠心学之虚。但问题是:何谓虚,何谓实?
严格来讲,说汉学家将宋学的阐释方法与义理尽皆归于凿空,既有违于宋学的实际,也与汉学之实际不尽相符。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总是可以在汉宋双方那里找到相反的例证②,而且也是基于对虚实问题之有效性的合理化判定。
汉学家批评宋学之虚,既指宋学偏于形上思辨与空凭胸臆的学术方法,亦指宋学偏于谈论心性之体而终至脱离现实的无用。所以,乾嘉汉学既主张在为学方法上求实证,又主张在为学目的上求实用。但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目的上,汉学家对宋学凿空的批评都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因为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一系,在方法上并未完全抛弃训诂,只是不偏重于这一面而已;而宋学在目的上,更不可能是完全无用,试想,一无是处或一无用处的宋学何以能够维系几百年的独尊地位?就宋学偏于形上实体一面来看,宋学看似用实体保证实用,实际上却是以实用来佐证实体。一旦实用上出了问题,实体就会遭到质疑。阳明格竹,就是在工夫(其实就是实用)上推不走了,才质疑朱子的理之实体,并重建一个心性实体。而明清之际更是从实用上质疑宋儒的实体,并重建实体以为实用提供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由于实用本身 (其实是生活本身)在不断变化,实体的内涵也只能不断调整。所以,汉学家对宋学无用的批评只能是局部有效的。简言之,虚实的判定取决于有用无用,而有用无用则依赖于解经者的当下需求,这就是有效性的判定。
虚实的界定依赖于具体的语境或场景,不可一概而论,所以钱穆说:“桐城派古文家,议者病其空疏。然其文中尚有时世,当时经学家所谓‘实事求是’者,其所为书率与时世渺不相涉。则所谓‘空疏’者究当何属,亦未可一概论也。”[18](P637)汉学家批评宋学家蹈空,并由此而寻求经验层次的普遍性,所以他们注重对具体的、可实物化的名物典章制度进行考证,但繁琐的考据带来的却是碎义难逃、无所用于经世的支离、空疏之结果。其实,过实必虚,过虚必实,只是要想处于中庸的位置总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中庸难能者也。由此而言,虚实之间的转换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并非就是一个悲观的结论,而应将之接受为实际发生着的事情本身的不断地、不同地显现罢了。
当然,以上主要是就有效性的判定来说的。就合法性的判定而言,宋学毕竟有脱离经书的倾向。尤其是在心学末流的鼓噪下,经书成为糟粕,而经典的至尊地位也就丧失了。由此,由宋学衍生出来的效果历史,最终才会成为汉学家对之进行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主要缘由。这就清晰地表明,在合法性(通经)与有效性(致用)之间仍旧是有某种关联的,只不过它并不是因果性的关联罢了。
注释:
①对于这一命题的综合性解读,参见拙文:《“实事求是”作为经学阐释命题的展开》(《孔子研究》2012年第1期)、《乾嘉“实事求是”命题的结构与层级》(《东岳论丛》2013年第2期)、《“实事求是”作为经学阐释命题的定性》(《前沿》2011年第6期)。对于这一命题各要素的分别解读,参见拙文:《“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乾嘉汉学对“实事”的定位及其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求”作为经学阐释的方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②如朱子也强调训诂,反对师心之用,强调“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黄宗羲:《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案语);再如戴震的治学路径,一定程度上正是对程朱的继承,这点早被章学诚在《朱陆》与《浙东学术》中揭示出来。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崔发展.乾嘉汉学之“实事求是”话语权的起兴[J].燕山大学学报,2010,(4).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4]戴震.戴震全书(第7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
[5]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6]焦循.雕菰楼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0.
[8]张循.论十九世纪清代的汉宋之争[D].上海:复旦大学,2007.
[9]吴通福.清代新义理观之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10]纪昀.《左传补注》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1]王鸣盛.西庄始存稿[A].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方东树.汉学商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4]胡适.戴东原的哲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5]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阮元.《性命故训》威仪说的初步研究[A].彭林.清代经学与文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1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