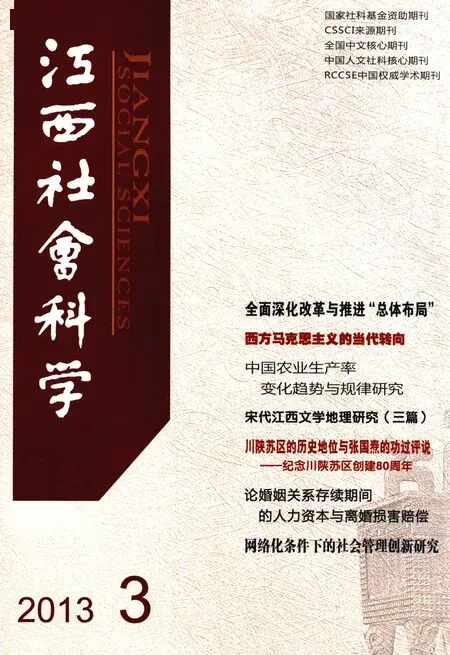从清代坟山风水争讼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之殊相
■魏顺光
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风水争讼具有独特性、典型性和代表性。风水缘何容易引起争讼?官府如何看待风水问题?清代州县官府如何处理风水争讼?风水习俗同儒家思想之间是否存在契合?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给出某种合理解释。当前关于风水问题的既有研究多从民俗文化的视角进行考察,而对于清代的坟山风水诉讼问题则尚缺乏足够的关注。
四川巴县档案是目前保存相对完整的清代地方档案,对于研究清代的地方司法运作问题,巴县档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坟山风水争讼案件为中心素材,以清代四川巴县为地域范围,以清代的整体法律运作为参照,探讨清代的坟山风水争讼问题。在当今社会,坟山风水争讼依然存在,剖析传统社会的风水争讼问题对于今天的司法实践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清代的风水信仰及其法律规制
清政府虽没有明确支持风水,但是也没有制定法律来严厉打击风水信仰。不过,倘若风水信仰危害到国家的统治秩序时,政府便会制定法律加以严格规范。缘于坟山风水的重要性,清代的家法族规中也多有相关规定。
(一)清代社会的风水信仰
“风水”一词最先出自于晋代郭璞撰的《葬经》。《葬经》中提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在《辞海》中被解释为:“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深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在营造坟茔时,一般都会慎重选择风水好的“吉地”,即所谓“卜葬”。古人相信人死有气,而气能够感应,从而影响活着的人,所以要选择能生气凝聚之地安葬。“对于中国人来说,坟墓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存在。明显象征着视祖先和子孙为一个‘气’之展开的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就是坟墓。祖先不是作为个人而生、作为个人死去,而是作为无形之气的一个环节曾生存过。如果这个成为许多子孙目前正在繁荣者的话,祖先也就继续活在他的子孙之中。”[1]
风水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儒家宗法伦理思想影响,儒家的礼制精神强化了古人的坟山风水观念。儒家思想认为“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从清代社会中的坟山风水争讼,可以看出风水与儒家的“孝义观念”有重要关联。由于风水观念和孝义观念的影响,再加之风水资源的稀缺性,缘于风水的争讼也在所难免。正如学者所指出:“堪舆之说,原出阴阳家者流,至近代变本加厉,酷信青乌家者话,谓富贵出自坟墓,沈迷风水,争讼盈庭,椎埋盗骨,假穴占山,冒坟盗葬,在在发生争端,争之不已,就引起械斗,甚至造屋竖碑,建稠植树,也称有碍风水,横加把阻。”[2](P551)
(二)清政府关于风水的法律规定
风水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中国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都很重视风水信仰的存在,或褒之,或贬之。然而,历代政府对于风水的态度一直以来都很隐晦。清代政府对于民间的风水信仰并未明文强加禁止,但是对于“棺柩浮厝”、“盗葬”现象以及盗伐风水树等行为,清代法律则会进行惩治和劝禁。因为这些行为不仅明显违背了儒家的礼教精神,而且有碍统治秩序。
1.清代法律中专门针对风水的条文
清代顺治皇帝在其御制法律中,曾立专条来打击“棺柩浮厝”现象:“凡愚民惑于风水,擅称洗筋检筋名色,将已葬父母及五服以内尊长骸骨发掘检视,占验吉凶者,均照服制以毁弃坐罪。帮同洗检之人,俱以为从论。地保扶同隐匿,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阻,首律仗一百,若有故而以礼迁葬,仍照律勿论。”[3]
清代乾隆皇帝也曾下令禁止“停柩浮厝”的行为:“朕又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葬埋,以妥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美风俗之要务也。”[4](《丧葬》)
清代的《大清律例》列有专条针对“惑于风水”而作出违背传统礼教的“停柩浮厝”行为。《大清律例》之《丧葬》条规定到:凡有(尊卑)丧之家,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若弃毁死尸,又有本律)。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从卑幼,并减二等。若亡殁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而烧化者,听从其便。其居丧之家,修齐设醮,若男女混杂(所重在此)。饮酒食肉者,家长杖八十。僧道同罪,还俗。本条规定了居丧之礼。“居丧有礼,安葬有期。”《大清律例》认为,如果迷惑于阴阳家风水祸福之说,及借口其他原因而停柩在家并长时间不葬,这种作法既违背了丧礼的规定,又使死者暴露不安。对此法条的立法用意,沈之奇注解为:“人死以葬为安,故曰安葬。葬者藏也,不藏即是暴露矣。风水之说起自后代,本谬妄不足信,乃将所亲已朽之骨,博儿孙未来之福,以致等候年久,暴露不葬,最是不孝之大者。”[5]
2.清代法律其他关涉风水的条文
清代法律专门针对风水的条文虽然很少,但是《大清律例》中针对其他问题的法律规范仍然关涉风水问题。例如“盗葬”行为不仅关涉地权问题,而且也同风水问题相关,“盗葬”的原因有时是钦羡他人风水所致。因此《大清律例》严厉打击“盗葬”行为:“于有主坟地内盗葬者,杖八十,勒限移葬。”
坟山荫木不同于普通树木,其不仅是祖坟的尊严所在,而且还有重要的风水功能,因此也叫“风水树”。清代法律对于盗窃他人坟茔内树木的行为处罚明显加重。《大清律例》中的《盗园陵树木》条有如下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不分首从,而分监守、常人)杖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首)杖八十(从减一等)。若计(入己)赃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各加监守、常人窃盗罪一等。若为驮载,仍以毁论)。”
(三)清代家族法规对坟山风水的保护
因为坟产具有重要的“敬祖收族”功能,加之风水信仰的盛行,在清代的宗法族规中经常能看到保护坟山风水的规定。例如浙江《上虞雁埠章氏家训》中提到:“至坟墓坍损,亟宜修理。盖祖、父体魄,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也。”章氏家训中提到了祖、父的体魄应当入土为安,如果遭到破坏,要及时修理。湖南《湘阴狄氏家规》中也提到:“祖墓为体魄所藏,务当时修理。倘不肖子孙悄窃树木、戕毁坟茔者,送惩不贷。”
古人认为,祖先坟山不可多葬、乱葬,这样会泄了坟山的“气脉”。江苏常州《长沟朱氏宗谱》规定:“祖先坟山,不可多葬,以泄气脉。如侵近前后左右,层堆连砌,不啻义塚,甚至子孙居祖父之上,族人公鸣,治以不孝之罪。”安徽《寿州龙氏宗谱》中也规定:“凡我族人,有希图吉穴,在公祖坟山强行添葬者,族众无论尊卑,立时掘起。”先人坟墓除了禁止多葬、乱葬外,还禁止侵葬。湖南湘乡《上湘龚氏族规》中提到:“先人坟墓最宜爱护,子孙不得进葬侵犯。每岁经管亲自挂扫,随时修抚,以昭慎重。”
坟茔树木具有培护坟山风水的功能,一般在清代的家法族规中都有关于祖坟“风水树”的保护性规定。江苏常州《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茔墓树木,所有遮护风水。有偷伐一株者,拿获以窃盗论。至自己祖坟,敢行伐卖,更以不孝论。”清代家法族规还有对于“风水树”进行保护的规定,如浙江余姚《江南徐氏家谱》中就说:“祖宗坟墓栽植树木,所以荫庇风水,妥安灵爽者。子孙如私自柝砍,致伤庇荫者,族长告官治之。”
二、坟山风水争讼的基本类型
在清代民间社会,因坟山风水受到侵犯而控官的现象比较常见。侵犯坟山风水的情形多种多样,清人钱琦曾在其颁发的《风水示诫》中,列举了十种坟葬纠纷。本文通过对巴县档案中的坟产争讼案件进行梳理,发现坟山风水争讼主要包括“侵害祖坟‘龙脉’”、“谋占风水”、“盗伐风水树”和“玷污风水”等几个方面。
(一)侵害祖坟“龙脉”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祖坟的“龙脉”是祖坟风水之根本,祖坟风水的好与坏同祖坟的“龙脉”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清人特别注重保护祖坟的“龙脉”。在侵犯祖坟风水的案例中,因“截脉”而告官的现象最为常见。在巴县档案中涉及侵害“龙脉”的行为主要有“截脉”、挖毁“龙脉”、“玷污龙脉”等。
在巴县的习俗当中,禁止在已葬坟茔的坟头或坟尾连接处另行修坟,因该行为将祖坟的“龙脉”阻断,因此被视为“截脉”行为。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巴县的杨国伦同胞兄杨国贵将祖先的遗业进行均分,其祖坟葬在杨国伦所分山业之内,后杨国伦将其祖坟后的一块地卖给张盛荣迁葬其母,不料杨国贵认为,张盛荣将母亲葬在杨家祖坟后面,有碍杨家祖坟的“龙脉”。经过邻里的调解,杨国贵愿意个人出钱将地赎回,这种作法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乾隆二十七年(1762)四川巴县的彭尔聪也因为“截脉”问题而将杨茂兄弟具控官府。彭尔聪的告状如下:
乾隆二十七年智里六甲民彭尔聪告状
本月初三,蚁以惊冢惨害事具告杨茂弟兄在蚁祖坟侧掘塘积水灌冢,并坟后截脉葬坟情词在案。蒙批:准查。赐差陈忠协同约邻查复。情蚁业昔卖与伊继父刘元甫时,当凭地方踩明坟冢,托伊照□,原蚁不许惊犯截葬。今伊截脉葬坟,情理难甘。痛恨坟左又掘堰塘一口,塘高坟低,且又只隔五尺五寸之地,水□骨,鬼哭何安。可怜生者目击,情惨剐心。蚁以词投两邑约邻皮洪才等验明可讯。泣思杨茂弟兄田广地阔,无处□堰,明系不惜人墓,便伊贪谋吉地,乘蚁远贸,即以掘塘截葬,人鬼何甘。若不再恳怜究,讯押迁补,恐伊弊嘱祖禀,终埋冤抑。为此叩乞本县正堂太爷台前俯准施行。[6](P289)
本案中,彭尔聪的讼因有二:其一是杨茂兄弟“贪谋吉地”在其祖坟后葬坟,已构成“截脉”行为,并且,彭尔聪认为此种“截脉”行为属于“情理难甘”。其二是彭尔聪认为,杨茂兄弟所挖塘堰在其祖坟的后面,并且该塘堰的位置又比祖坟高,同时,该塘只隔其祖坟五尺五寸,这样对于其祖坟来说构成威胁。宋代的名儒程颐在《葬说》中曾提到“五患”之说:“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7](P623)因此,杨茂兄弟的行为也属于程颐提到“五患”之说。
(二)“谋占风水”
受坟山风水习俗的影响,人们通常会找民间的风水先生来卜得一块合适的“风水宝地”作为坟地。不过,要找到所谓的“风水宝地”并非易事。于是就有人钦羡他人风水而发生“盗葬”、“估葬”和“侵葬”等行为。虽然盗葬的原因有多种,但因“谋占风水”而进行盗葬的不在少数。例如巴县档案记载的“郭来宾具控吴开爵盗葬案”,吴开爵之母本已安葬,但是吴开爵贪念郭来宾田业内的风水,而将其母尸骨盗葬在郭来宾的田业之内,因而发生纠纷,后来官府断令吴开爵将其母骨起迁另葬。
有人为了达到“谋占风水”的目的,甚至挖空心思去精心谋划。嘉庆十一年(1806),巴县的赵富荣知道彭儒魁的田业之内有一处“吉穴”,于是便想谋占。为了达到谋占的目的,赵富荣便与张定镒和万邦元串谋。赵富荣先作中让其表弟张定镒佃种彭儒魁的田业,然后张定镒又将佃种的田业分股与万邦元耕种,而彭儒魁卜到的“风水吉穴”正好处于万邦元的佃业之内。赵富荣与万邦元串通之后,便将其母亲的尸棺盗葬于彭儒魁所卜到的“风水吉穴”之内。该案后经亲邻调解,令赵富荣将其母尸棺起迁另葬,并立下服约给彭儒魁保证日后再不滋事。[8]
(三)盗伐风水树
古人认为,“风水吉地”除了觅寻之外,还能够通过栽种“风水树”进行培植。因为“风水树”除了具有养护坟土的功能之外,还是培植风水的重要途径之一。清人在田业买卖当中,如果田业关涉坟茔,通常在契约中特别写明对于风水树的保存。比如乾隆十三年(1748)巴县人霍明选在卖田地文约中特别写到:“凭邻族人等踩踏分明,兼之祖坟前后柏树一共八根,永作二姓阴阳二宅风水,勿许砍伐,其余随意砍取。”[8]
在清代,因“风水树”遭到砍伐而告官的现象屡见不鲜。其讼因一则是由于“风水树”属于财产利益,再则是因为“风水树”同祖坟风水密切关联。乾隆三十五年(1770)巴县的王仲一由于砍伐唐应坤祖坟的“风水树”而被告官。从唐应坤的状词中,可以感受到清代人对于“风水树”的特殊情感。
节里七甲民唐应坤告状
为清理愈横,再叩赏究事。
缘本月二十五,蚁以估砍惊犯具控。王仲一听讼棍王连山主唆,统率伊子王大中等砍伐蚁祖坟后千百年护蓄风水大黄连古树一根,惊犯祖坟等情在案。蒙批:如系久管坟树,凭众清理可也。切伊砍树之时,蚁已投约邻众凤昌、陈仕荣等,再三理论,众令赔树醮坟,以免争讼,莫奈伊何。等语。惨蚁祖坟,子孙攸关,千百余年,无敢惊犯。今被王恶砍伐古树,惊犯祖坟,生死被害,人鬼两冤。为此,再叩恳准讯究,以杜□害,存殁均沾。伏乞本县正堂太爷台前俯准施行。[6](P291)
在该案中,唐应坤认为,对于其祖坟后风水树的砍伐是对祖坟的严重惊犯。唐应坤的言辞吐露出对于祖坟“风水树”的特殊情感:“惨蚁祖坟,子孙攸关,千百余年,无敢惊犯”。唐应坤认为,砍伐“风水树”的行为不仅仅伤害了活人,同时死去的人也受到了伤害。
(四)玷污风水
在巴县的民间习俗中,严禁在祖坟前后挖池积粪以及在祖坟私宰耕牛等玷污祖坟风水的行为。在“彭永楷具控彭永树私卖祖坟山案”中,彭氏分家时事先言明祖坟后脉的山土不得私自出售,该块地土在彭永树所分得的田业之内。但是,后来彭永树私自将坟山后段山土出卖与苟大明,而苟大明在彭氏祖坟后段的土地上私宰耕牛并挖池积粪,该行为引起了彭永楷等人的不满。彭永楷等人认为苟大明在坟地私宰耕牛和挖池积粪的行为是对祖坟风水的破坏,于是要求赎回该块山土。官府同意彭永楷的诉讼请求。
对于在“坟禁”内栽植庄稼、挖掘祖坟坟土等行为也被认为是对祖坟风水的侵犯,甚至对于在坟土上割草的行为也要严加禁止。清代乾隆年间,巴县的刘天贵将其田业卖给谢天寿,该田业中有刘天贵的几所祖坟,后谢天寿将所卖田业招佃汪朝宗、袁景常和李维知耕种。刘天贵在状词中称,在佃种期间,汪朝宗在坟尾拴牛、割草烧灰,并且还在禁步内开垦种植高粱。而袁景常将猪拴在坟茔处,导致猪拱崩坟土。李维知在佃种期间,将一所坟茔挖掘种小菜和栽植烟叶。刘天贵认为这些行为严重地侵害其祖坟风水。他在“告状”中提到:“蚁祖冢子孙攸关,且蚁祖茔,六房人丁约有数百,况叔祖刘斌、刘福均皆举人,出任福建福清县。由曾祖母坟茔所拨曾祭,监有桅杆,遭恶贱犯,理法奚容。”[6](P294)
通过上述坟山风水争讼的诸多表现可知,在清人心目当中,祖坟的“龙脉”神圣不可侵犯。不论是严重的“截脉”行为,还是在祖坟山地进行挖池积粪等玷污祖坟风水的行为,被侵害的一方当事人都会通过各种努力来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为了保护祖坟“龙脉”而诉诸公堂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有时,为了避免祖坟的“龙脉”被侵害,有些人还会将已经出卖的田土重新赎回来,或者将他人的田土收买过来,借此来加强对祖坟风水“龙脉”的保护。由此可见,风水信仰的盛行对于民间秩序的构建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风水信仰不仅影响了民间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选择,有时风水问题还会引发严重的矛盾冲突。
三、引发坟山风水争讼的原因
(一)“敬祖收族”观念的影响
坟山风水不仅关乎与“尊尊”相关的“敬祖”问题,而且也是“亲亲”原则的重要体现,还具有“收族”的功能。祖坟除了安放先祖的体魄之外,其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则有另一意义,即祖坟乃人生之根基,子孙应当“报本”。清代《合江李氏族谱》的家规、家禁中提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但有心知,亦可共明此理也。”活着的人要“慎终追远”,要感激祖宗生身养育之恩。清代同治年间,四川《开县唐氏族谱》中提及:“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茔所在,根本系焉。”清人认为:“朝廷以宗庙为重,庶民以祖冢为尊。”
正是因为祖坟具有“敬祖收族”的重要意义,保护祖坟的尊严是每一个家族成员的重要职责,特别是当祖坟的风水受到侵犯时,其关系到整个家族的繁荣发展,每个家族成员都会为保护祖坟风水而竭尽全力。在清代的风水纠纷案件中,往往卷入整个家族的成员。
(二)风水的稀缺性容易引发争夺
清人认为,风水能够带来子孙的繁荣和家族的兴旺,对“风水宝地”的拥有显然是一个家族引以为豪的荣耀。因此,坟山风水无疑成为一种重要的财富象征,是一种重要的隐性财产。不过这种隐性财产总是依附于坟地等显性物权之上。风水争讼也经常表现为田土之争。
《清史稿》记载:“宪德奏:‘四川昔年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繁衍。奸猾之徒,以界畔无据,遂相争讼。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亦非勘丈以判其曲直。’”[9](卷二百九十四《宪德传》)
清代中期正是四川经济向东转移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该时期也是巴县人口急剧增加的历史阶段,嘉庆十七年(1812)时,巴县人口为二十一万九千人,到了道光四年(1824)时,巴县人口发展到四十五万一千八百人。[10](P195)人口的增长加剧了对于土地的掠夺,而依附于田土之上的坟山风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更容易引发争讼。
(三)坟山风水容易成为诉讼的借口
由于官府和民间社会都高度重视坟山风水争讼问题,讼师和一些无聊之徒便利用人们对坟山风水的敏感性,挑拨和唆使他人进行“藉坟滋讼”。清代的巴县政府用告示对于巴县民间社会中的“官代书”提出批评:“近查各属民风,往往卖业以富户为鱼肉,高价估卖,有意逞刁。其有为富不仁之徒,短价狭掯,多方勒买,彼此寻衅兴讼。书役贪图需索,即官代书亦希图多取写状钱文,久之贫益无聊,富渐困乏,种种陋习,殊堪痛恨。”[8](P195)清政府为了打击教唆之人,特针对“争挖坟穴山场”的争讼,要求“代书”要“据实直书,如敢以毁冢、减骸、盗发等词架词装点,希图耸听者,除不准外,定将代书究革”。[11](P276)
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十七日,四川省按察使司发布的告示中提到:“川民惑于风水,听堪舆之哄骗,受墓佃之串唆,见人穴吉,即生觊觎;川民本系好讼,讼棍从中拨弄;争山,则状开发冢抛骸;雀角,则词列持械抄抢。”对于此种“藉坟滋讼”行为,官府规劝民众:“至尔百姓亦当各知醒悟,息讼安生。”[12](P350)由此可见,“藉坟滋讼”现象已经引起官府的高度重视。
四、坟山风水争讼的官府救济
坟山风水纠纷发生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通常会邀集约邻进行调处,如果调处失败,当事人便会向官府提起诉讼。官府受理后一般还会以“批词”的形式指令亲邻进行调处,亲邻得知案件起诉到官府后,也会主动进行调处。民间调处的结果一般会得到官府的认同。但是,当案件不得不由官府审断时,官府便会依据契约、碑文、族谱等证据对案子进行审断。官府在审断中会参照民间习俗,同时结合“情、理、法”对案件进行综合考量。关于坟山风水的民间调处问题,笔者将另署专文,本文将重点讨论坟山风水争讼的官府救济。
(一)官府对于风水争讼的重视
清人汪辉祖指出:“大端有四,曰风水,曰水利,曰山场,曰天界。”在这“四端”中,“唯风水、山场有影射,有牵扯,诈伪百出”。[13]风水容易导致“诈伪百出”的原因是因为风水往往同房屋、坟地等不动产密切关联。对于坟山风水而言,其特殊重要性更容易引起官府的重视。“葬地惑堪舆家术,尽诚致敬,听凭指挥,又必合乎年命,均其房分,故常寄厝多年,强者每贪吉地,恣意占葬,牙角交讼,虚词退迁,破耗赀产不恤,近山乡鳄,藉伤煞为词,挟制阻挠,掯索贿赂,不厌不止。”[14](卷十三)
考察巴县档案的诉状发现,多数控告人都会在诉状中提及对方有暴力行为,或暴力倾向。受“敬祖收族”之影响,坟山风水之讼往往会将整个家族成员卷入其中,这样不仅让当事人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刑事犯罪,轻者会导致“发冢”行为,严重时还会引发人命案。在有清一代,因坟山风水争讼而引发群体性械斗的案件并不鲜见。[15](P729)因此,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官府对于坟山风水争讼极为重视。
(二)官府通过“官批民调”化解纷争
在清代社会,当民间纠纷发生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通常会邀集约邻进行调处,矛盾解决的首要途径是“约邻理处”。但是当初次的“约邻理处”失败后,一方当事人就会将对方具控官府。官府受理案件后,通常都会在书状上对当事人的指控作出批示,表明官府的态度,官府的此种书面批示即为“批词”。受儒家“无讼”思想影响,官府仍然希望案件能够通过民间调处的方式结案,官府便会用“批词”的形式指示亲邻进行调处,即所谓的“官批民调”。
对于民间“细故”纠纷,官府有时并不想通过审断结案,特别是对于坟山风水这类敏感的民间纷争,官府为了让当事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解决纠纷,他们会指示亲邻(约邻、中人等)对案件进行“调处理覆”,如果调处能够成功,案件可以就此了结。概括巴县档案的记载,巴县官府对于彭尹民具状的“批词”可以窥知官府的用意:“彭尹民既在己业修茔,与彭学健有何干涉,辄行籍竭索诈庸等;既系族邻业已查知底里,应即秉公调处明白,取结销案,毋庸以细事请讯,即使伤情滋讼也仍委业族。”
(三)官府对于风水习俗的认同
在清代州县的司法实践中,民间习俗得到了州县官府的普遍认可。清代州县的官员都把“入乡随俗,入境问禁”看成是其体察民情和掌握断案依据的“必修课”。清人陈宏谋曾指出:“因俗立教,随地制宜,去其太甚,防于未然,则皆官斯土者所有事也。苟非情形利弊,熟悉于心胸,焉能整饬兴除,有裨于士庶?”[16](卷二十)风水习俗是乡民在长时期的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关规则,具有很强的秩序整合功能,在处理坟山风水纠纷中,风水习俗具有较大的约束力,也容易为广大乡民认可和接受。
例如巴县档案记载的“肖朝泰控肖朝聘估葬母坟截脉压葬案”,肖朝泰的已故先祖肖长清于乾隆年间葬于巴县的江北,多年相安无事。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肖朝泰之堂兄肖朝聘的母亲肖王氏病故,肖朝聘听信地师的哄惑便将其母尸棺紧挨其先祖肖长清的坟边安葬。该行为遭到肖朝泰等人的强烈反对,便要求肖朝聘将其母尸棺起迁另葬,但肖朝聘借故择期另葬却一直没有起迁,道光十四年(1834)肖朝泰等人于是将肖朝聘具控官府,控告他估葬母坟“截脉压葬”。官府审断认为,肖朝聘“截脉压葬”属实,“姑准宽限一月择期迁葬,毋得藉此延宕滋事,致干提究。”
在风水习俗当中,祖坟的“龙脉”是决定祖坟风水好坏的关键因素。凡是对“祖坟龙脉”有妨碍的行为均会遭到对方强烈的抵制,乃至发生“经官动府”的举动。从上述案例的处理结果来看,巴县官府认同了巴县地区关于“祖坟龙脉”的风水习俗,在审断中巴县官府依据坟山风水习俗来对案件审断。
(四)“情、理、法”的综合考量
清代的乾隆皇帝在御制《大清律例序》中提到:“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由于风水的特殊重要性,清代地方官府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不仅参照《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同时还考虑了情理因素。
根据巴县档案,道光五年(1825)赖凤吾将其分受田业出卖给张光宇,该田业之内有赖凤吾的祖坟。张光宇买受田业之后便在赖凤吾的祖坟后修造生茔。张光宇修造生茔的行为遭到了赖凤吾之堂兄赖凤珍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是赖凤珍等人以“私卖祖坟连接之地”具控赖凤吾,并具控张光宇“截脉进葬”。官府审断认为,赖凤吾不应私卖祖坟接连之地,于是将赖凤吾薄责示惩,而张光宇新修坟茔着即拆毁,赖凤珍缴还原买契价钱九千五百文给张光宇具领完结。
出于对祖坟的特殊保护,清代的法律禁止子孙盗卖祖坟旁边的余地。上述案例中,赖凤吾认为其所卖之地属于其受分之祖业,属于出卖己业之行为。赖凤珍等人认为,此地虽为赖凤吾所有,但是由于其位于祖坟连接之处,赖凤吾不应该私卖给张光宇。并且从风水习俗来看,张光宇在赖氏祖坟后修造坟茔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截脉”行为。从官府的最终处断结果看来,官府认为赖凤吾的行为违法,张光宇新修的生茔构成“截脉”。但是,官府权衡各方的利益,基于“情、理、法”的综合考虑对案件做了变通处理,对于张光宇所支付给赖凤吾的九千五百文由赖凤珍缴还。
五、坟山风水争讼的现实思考
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的传统法律范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西式的法律规范。然而,“法律表达”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背离至今仍然存在。清华大学调研组曾对广西进行的一项调研发现:“一个乡镇司法所一年处理的重大坟山纠纷有10宗左右,但是还有相当部分坟山纠纷经过多年甚至十多年无法调处达成协议,隐患难以消除,加之坟山纠纷往往和宗族势力相交织,恶性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而现行法律并没有相应的规定,法院也往往不受理此类纠纷,进一步增加了此类纠纷危害社会稳定的风险。”[17]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面对坟山风水争讼问题,法官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如何破解该难题?“回采历史”,从清代官府处理坟山风水争讼的策略和方法中或许能够找到合适答案。
首先,要正确看待儒家伦理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式微,但是传统和现代并没有完全“断裂”。儒家的孝义观念仍旧遗存于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在林端先生看来,儒家伦理成了贯穿大小传统的最主要力量。[18](P10-16)坟山风水是“大传统”的儒家伦理同“小传统”的民间习俗的有效契合,其契合点就是儒家的“孝义”观念。考察风水的起源可以发现,风水一开始就有谶纬之学的一面,虽然现在的学者们也认同风水具有科学的一面,但是风水能够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风水习俗同儒家的“礼制”之间并不冲突,特别是坟山风水同儒家的“孝义”观念形成了某种契合。风水观念同儒家伦理的契合强化了民众的风水信仰。
其次,要尊重民众的风水信仰和善良风俗。风水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风水习俗成为中华民族的、未经反思的社会记忆和民俗信仰,成为中华民族一个爱恨交加的‘文化幽灵’,成为日常的文化与生活世界的一部分。”[19](P2)坟山风水浓缩了地权观念、风水习俗和儒家伦理等众多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其蕴含了传统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情结”。而且,在当代中国的民间社会,风水信仰仍然存在。吉登斯说过:“传统是惯性,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在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上,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的紧密联系上。”[20](P92)
再次,重视坟山风水纠纷,发挥民间调解的功能。缘于坟山风水同儒家伦理的契合性,清代司法官吏在处理坟山风水争讼的法律运作中也渗透了儒家思想精神。清代的官府在解决坟山风水纠纷时,受儒家“和为贵”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视民间调处。由于坟山风水往往涉及整个家族,如果矛盾纠纷不能有效化解,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群众性事件。对于敏感的坟山风水纠纷,今天的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在思想上务必引起高度重视。由于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风水问题的相关规定,因此在处理该问题时要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的功能和效用。
最后,注重思想教化,灵活变通处理风水纠纷。对于坟山风水纠纷,地方政府和司法工作者要从思想上对民众进行规劝,教育民众要相信科学,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鉴于风水纠纷的高度敏感性,在处理相关纠纷时,既要坚持法律原则,又要灵活变通。我们要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依法处理,同时也要有传统儒家“哀矜勿喜”之情怀,要依照“情理”,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客观情况来进行酌情处理。
六、余论
近年来,法律史学界开始呼吁要关注中国法律史的“自我”,要回到中国历史的本真世界中去,才能破译中国法律文化的遗传密码。[21]在传统中国,风水既是一种信仰,还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为中国所独有。因此,古代社会的风水争讼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种“殊相”。文化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很快消解。在当今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风水信仰仍然存在,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与传统的“乡土社会”仍然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国家正式制度在不断渗透和扩张,但是民间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因此如何破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张力是摆在当前社会中的一个难题。
自清末变法以来,我国法制变革走的是“外援型”的法律移植之路。西方法文化的精华内容被我国吸收和借鉴。但是,必须承认,在我国法制改革的进程中,仍然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我们必须正确面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不能走舍近求远的“单边之路”。经验告诉我们,走法律移植的“单边之路”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社会发展,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还要“回采”中国的法律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1](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陈支平.福建宗教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3]大清律集解附例[Z].顺治四年刻本.
[4](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Z].光绪十二年刻本.
[5](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M].怀效锋,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7](宋)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9](清)赵尔巽.清史稿[M].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0]王笛.清代重庆城市人口与社会组织[A].隗瀛涛.重庆城市研究[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2]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13](清)汪辉祖.佐治药言[M].光绪十年刻本.
[14]左树礑.金门县志[Z].上海图书馆抄本影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1921.
[15]杨一凡.历代判例判牍(第七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6](清)陈宏谋.咨询民情土俗谕[A].(清)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清华大学调研组.坟山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N].法制日报,2007-12-09.
[18]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9]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1]俞荣根.寻求“自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承与趋向[J].现代法学,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