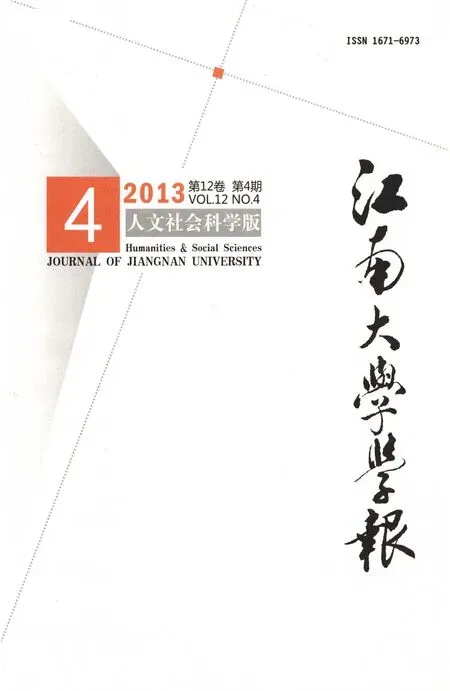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高 旭
(1.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所,安徽 淮南232001;2.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墨家曾是先秦思想史上煊赫一时的重要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1]20,甚至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孟子·滕文公下》)[2]269,但到战国后期,学派却日渐沉寂,至西汉时已是“湮没无闻”,罕有以“墨者”自许之人,因此,作为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学说之一,墨家思想也逐渐随之成为历史的遗响。虽然墨家衰落,其思想对于现实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大为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家思想已经完全成为历史陈迹,相反,墨家思想“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仍起到一定的作用”[3]41,其基本理念及精神继续为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所汲取,成为后者构建新的政治学说的重要理论资源,产生于景、武时期的《淮南子》即是如此。
《淮南子》“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要略》)[4],在秦汉思想史上以所谓“杂家”而著称,有着极为多元的思想构成,充分显示出开放而包容的理论胸怀,因此墨家思想作为先秦之“显学”为其所关注和吸纳,这并不出人意外。但墨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实际存在却耐人寻味,一方面其确对《淮南子》有着深刻影响,不容忽视,而另一方面,其理论地位在《淮南子》中却无法与道、儒相较,甚至存在内容之多都不及法家和阴阳家,应该说,这与墨家曾经所拥有的思想地位毫不相称,个中因由,值得深思。本文即试图从政治思想的视角着眼,深入剖析《淮南子》与墨家之间的思想关联,具体揭示《淮南子》批评、反思与融会墨家政治思想的理论过程,进而探讨墨家具有“民本”意蕴的“圣王”观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此仅以鄙陋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尊禹——《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
墨子是先秦时期思想界之巨人,其所创立以“兼爱”、“非攻”等为核心的墨家思想学说也是当时学术、政治领域中蔚为壮观的一大思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这在产生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中就有着显著的思想反映,“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氾论训》)。虽然《淮南子》对墨子充满政治之敬意,将墨子与孔子同视为“先圣”、“圣人”,“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氾论训》),“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修务训》),但若具体而言,《淮南子》则对墨家政治思想具有复杂的理论态度,体现出内在的双重性:一方面,《淮南子》对墨家政治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受其影响凸显出“尊禹”的政治意识,对其“兼爱”、“非攻”、“节乐”、“尚贤”等基本主张有所认同;另一方面,作为黄老道家之著述,《淮南子》对墨家思想又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评,对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赞成与接受,而是力图“以兼容的气度加以吸收”[5]225,从思想上进行融会和超越。因此,《淮南子》对于墨家政治思想,实际上是基于西汉王朝的现实政治发展,重新予以历史的审视,在理论上有所借鉴,将其作为自身政治思想体系得以构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淮南子》所受墨家思想的实际影响来看,显著的尊“禹”意识,可被视为其与墨家在政治上的契合之处,成为二者能够实现内在思想之沟通的历史前提。在《淮南子》而言,“禹”不论是作为“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人间训》)的英雄,还是作为能“为天下兴利”(《主术训》)的“圣王”,都值得其敬仰与崇拜。《淮南子》的这种政治认识与墨家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深刻影响所致。因为,在先秦诸子那里,虽然对“禹”都有所称道和赞扬,但唯有墨家具有极为突出的“崇禹”意识,甚至于在思想上坚持“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6]1077,认为“兼即仁矣,义矣”,“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墨子·兼爱下》)[7]76,始终将“禹”视为能够充分彰显出墨家“必兴天下之利,除去人下之害”(《墨子·兼爱中》)[7]64的思想及精神的历史典范。墨家这种强烈的“崇禹”意识对《淮南子》,不论是讲求“事功”的政治思想上,抑或“民本”为重的政治精神上,影响都极为深刻,不容忽视。
若就政治思想具体而言,《淮南子》之尊“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颂扬“禹”之“平治水土”,安宁万民之功。“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地形训》),“禹疏三江五湖,辟开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本经训》),“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主术训》),“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齐俗训》),“决河濬江者,禹也”(《诠言训》),“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人间训》),“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修务训》),“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泰族训》),“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要略》),从中可以清楚认识到,正是因为“禹”在历史上曾“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吕刑》)[8]636,所以《淮南子》在思想上对其充满政治之敬意,表现出显著的尊“禹”意识,认为“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9]1708-1709的历史功绩不容忘记。
(二)将“禹”视为三代之时“贤臣”与“圣王”的政治典范,认为其有安邦定国之能。“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缪称训》),“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齐俗训》),“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禹无十人之众,……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禹劳天下,而死为社”(《氾论训》),“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说林训》),“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人间训》),“禹胼胝。……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修务训》),“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泰族训》),基于这些历史认识,“禹”在《淮南子》看来,既为尧之贤臣,又是继尧之“圣王”,充分体现出卓越的治国之才,值得钦仰。
(三)用黄老道家之眼光审视“禹”的政治意蕴,将其政治实践作为对黄老治术的历史反映,塑造其道家化的统治者形象。“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原道训》),“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视物亦细矣。……观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细也”(《精神训》),“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 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主术训》),“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侈俭之适者也”(《齐俗训》),“禹决江河,因水也”(《诠言训》),“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修务训》),“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泰族训》),显而易见,这些文字记述中的“禹”已被《淮南子》用黄老道家的政治标准重新予以审视和诠释,充分显示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的政治意趣,已非墨家之“禹”的概念了。同墨家政治思想相较,《淮南子》中对“禹”之政治内涵的理解,政治形象的塑造,既有一致之处,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一则,肯定“禹”的治水之功,将其塑造为三代政治的“圣王”之一,这是《淮南子》与墨家的共同之处。如“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墨子·兼爱中》)[7]67-68,“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墨子·尚贤中》)[7]35,“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墨子·非攻下》)[7]92等,从中可知,墨子也是从治水与治国两个方面来肯定“禹”之历史功绩和政治才干,表达其“崇禹”之情。二则,墨家是基于“兼爱”,“兴天下之利”的思想来塑造“禹”的政治形象,阐发其独特的政治理念,而《淮南子》则截然不同,主要是从黄老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来重新诠释“禹”的政治内涵,将其塑造为道家化之“圣王”,认为其治国之道乃是对黄老道家思想的历史性体现,因此,应该被作为西汉统治者在政治上积极效法的君主典范之一。
由此可见,虽然《淮南子》受到墨家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从后者那里接受了有关“禹”的政治认识,但毕竟二者的政治立场与基本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与其说《淮南子》“崇禹”,毋宁说是“尊禹”,因为在《淮南子》而言,“禹”只是其用以阐发黄老“治道”思想的政治手段,并非其理想的政治偶像,只有“至人”、“真人”才值得《淮南子》去真正的崇信,而这已绝非“禹”作为“圣王”的政治内涵所能简单取代的。
概而言之,对“禹”的政治崇敬,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决定了《淮南子》中虽然多有以黄老道家的政治立场对墨家的批评,但仍然能能够秉持一种思想之敬意对其有所反思和汲取,而远非像对待法家那样严厉的批判与谴责。因此,《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政治态度虽然复杂,具有内在的双重性,但总体上比较温和、包容,着重于进行理论之借鉴和融会。
二、求治——《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共识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氾论训》),在《淮南子》看来,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不论存在着怎样的异、同,其根本的政治目的都在于“求治”,兢兢竭力于专制君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墨家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如果说“尊禹”为《淮南子》实现与墨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沟通奠定了必要基础,那么坚持“求治”的根本原则,体现出“强烈的致用色彩”[10]233,则使得《淮南子》能够站在黄老道家的政治立场上,深层次地汲取墨家政治思想,从“治道”与“治术”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融会其中积极的思想因素,以此构建出自己关于西汉王朝的现实政治发展的理想方案。
从“治道”来看,《淮南子》坚持黄老以“道”治国的根本原则,贬低儒、墨、法等家。“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俶真训》),在其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思想与法家一样,没有真正“通之于天地之情”,懂得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真谛。实际上,对《淮南子》而言,唯有黄老道家的“体道”而“自然”,“清净”而“无为”才能称之为“治道”,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原道训》),“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本经训》),“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主术训》),因此,在《淮南子》中,若就“治道”来说,没有那一家能够与黄老道家相颃颉。虽然墨家“兼爱”、“尚同”的治国理念在政治上有别于儒家之“礼乐政治”,但其本质上都是积极“有为”者,而《淮南子》认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说山训》),由此《淮南子》批评道:“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主术训》),对墨家的“治道”自然不会持有肯定和赞扬的政治态度。实际上,儒家之“治道”在《淮南子》中也是同样的遭遇。尽管《淮南子》在批评“墨、杨、申、商”时,并没有明确提到儒家,但事实上与黄老道家相对的儒家也包括在内,只不过由于武帝时期儒家的政治地位处于历史的抬升之中,且《淮南子》的编撰群体里有儒者的存在(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故而《淮南子》在思想上表示出要“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览冥训》)的政治姿态,不为己甚,没有点名批评儒家的“治道”。
与对待“治道”的政治态度不同,《淮南子》对墨家关于专制君主政治具体发展之“治术”表现出相当的思想包容性,既有深刻的批评和反思,也有积极的借鉴与融会。
其一,对墨家的“尚贤”主张,《淮南子》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墨家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烈的贤人治国意识,主张“尚贤之为政本也”(《墨子·尚贤中》)[7]29,“圣人之为政,列德而尚贤”,甚至于认为统治者在用人上应该不拘一格,只要是贤才之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7]28,都应该大胆任用,可以说,在“任贤而治”这点上,墨家所体现出的平民化立场,诸子中少有其匹。《淮南子》对墨家之“尚贤”表现出两种有所冲突的看法:一方面,出于黄老道家的立场,《淮南子》认为“智术不可以为法”(《泰族训》),“贤不足以为治”(《主术训》),追求“虽贤无所立其功”(《本经训》)的政治发展,反对墨家的“尚贤”主张;另一方面,《淮南子》中也有从儒家立场出发的认识,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应该“惟贤是亲”(《主术训》),“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氾论训》),“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兵略训》),而且还警戒统治者“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说林训》),“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泰族训》),如从这些观点来看,《淮南子》对墨家“尚贤”之说也有着相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会有如此情形,这是由于《淮南子》的思想构成比较复杂,黄老道家虽然“究居优势”[11]118,但并非完全处于“一家之言”的地位,儒、法等家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对墨家之“尚贤”,《淮南子》才会表现出“治道”上坚决反对,“治术”上有所认同和接受的矛盾思想。
其二,对墨家的“非儒”、“非乐”主张,《淮南子》也有深入的反思和认识。墨子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受到儒学的深刻熏染,但“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氾论训》),“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要略》),最终反叛儒家,独立己说。因此,墨家在思想上坚持“非儒”的立场,以实用化、功利化的政治态度抨击儒家,贬称孔子为“孔某”,极力“毁儒”,认为“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7]180。与墨家的政治主张不同,《淮南子》基于“持以道德,辅以仁义”的基本立场,在思想上批儒而不“毁儒”,将孔子看作是“圣人”,始终表现出相当的敬意,而且对儒家的“礼”、“乐”主张,并不完全否定,认为“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本经训》),虽然并不理想,但也能发挥一定的政治效用。与此同时,《淮南子》也以黄老道家的政治态度对儒、墨两家都进行批评,认为明王“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悲哀抱于情,葬薶称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都有背于“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认为其根本无法相较于道家“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侈俭之适者也”(《齐俗训》)的主张。
其三,对墨家的“节葬”,“节用”主张,《淮南子》有所认同和接受。墨家之所以主张“节葬”,“节用”,根本原因是出于对儒家的“反动”,认为儒家“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要略》),“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墨子·非儒下》),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缺乏“利民”的现实效用,因此儒家在墨子眼中显示不出有助于“治天下”的益处,反而其繁缛礼节,崇乐贵葬的做法只能对有限的社会资源造成更大的浪费,让民众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墨家在政治上坚决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7]159,“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墨子·节用上》)[7]99,表达出对儒者仰赖民众而生,又以贵葬之礼消耗民财的极大不满。墨家这种反对过度浪费民众财富和社会资源的认识,对以黄老道家为指导思想的《淮南子》来说,能够产生很大的政治共鸣。“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在《淮南子》看来,儒家的“礼乐政治”违背“清净无为”的“治道”,只能使“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造成“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俶真训》)的消极结果,因此对民众而言,“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齐俗训》)。由此可见,在对待民众财富与社会资源的多寡问题上,虽然《淮南子》和墨家的政治出发点不同,一从黄老“清净无为”的理念出发,反对多材以乱民心,另一从政治功利的立场出发,反对无谓地耗费民众的有限资源,但若从现实政治着眼,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节制统治者过度浪费民力和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在现实政治发展中能够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
其四,对墨家的“天志”、“明鬼”主张,《淮南子》的思想认识与之存在很大差异。墨家在政治上,强调“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将是否顺应“天之意”视为“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的重要标准,认为只有统治者在政治上“爱人利人,顺天之意”,才能“得天之赏”,反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就必然会“得天之罚”(《墨子·天志中》)[7]126-127。而且墨子还认为“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於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7]120,将统治者的政治地位也与“天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氾论训》),墨子的鬼神观与其“天意”观实质相同,在其看来“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墨子·明鬼下》)[7]138,统治者只有“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才能“谓之圣王”,反之,即为“暴王”(《墨子·天志上》)[7]133,因此墨子倡言统治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墨子·明鬼下》)[7]154。墨家的这种“天意”、“鬼神”观与《淮南子》大异旨趣,存在很大差异。《淮南子》虽然也讲天、人感应,认为“上天之诛也,虽在圹虚幽间,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览冥训》),“抱德炀和,以顺于天”(《精神训》),甚至认为“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窃肢体,皆通于天”(《天文训》),但《淮南子》所言之“天”根本地缺少墨家那么强烈的“神化”人格的政治意识,其内涵更多倾向于道家化的自然性,着重强调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而非“天”作为超凡的统治者对于人类的监管性、惩罚性。墨家所言之“鬼”,也非《淮南子》可比,“伤死者其鬼娆,时既者其神漠”(《俶真训》),“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览冥训》),“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本经训》),从中可见,“鬼神”在《淮南子》中没有墨家那样大的影响力,虽然统治者在政治上也要注意祭祀之,但并不需要将其作为自己政治实践的特别对象来对待。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在黄老道家影响下,虽不妄谈“鬼神”干政说,但也受到墨家“鬼神”观的一定影响,认为“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氾论训》),“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略训》)。
总之,基于相同的“求治”意识,《淮南子》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从“治道”与“治术”两个方面对墨家政治思想有所批评和反思。对墨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淮南子》既有批评,也有认同,存在具体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总的看,虽然墨家在《淮南子》中或许不如道、儒、法等外在化的凸显,但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实际上墨家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绝非“并不明显”[12]24可简单而论。
三、圣王——《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理想
与儒家的重义轻利不同,墨家在政治上不仅不讳言功利,反而表现出“尚利”的政治倾向,但墨家所言之“利”是基于“必兴天下之利,除去人下之害”的核心理念,在显示出强烈的“民本”精神同时,与其独特的“圣王”观密切相联。在墨家而言,“尊君”仍然是第一位的,但统治者应该成为“圣王”,能够在政治上为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非庸君“暴王”。因此,墨家的“利民”思想根本地建立在“圣王”观之上,这是墨家思想“尊君”的政治实质所在。墨家这种内含“民本”意蕴的“圣王”观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对后者有着深刻的思想影响,换言之,在《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墨家的“圣王”观具有一定的理论作用,并非可有可无的思想存在。
崇尚“圣王”政治,这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根本理想。《淮南子》认为,“圣王以治民”(《缪称训》)是专制君主政治的理想发展,能够在现实中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既有益于王朝政治,也有利于普通民众。在《淮南子》眼中,墨家所尊崇的“禹”就称得上是古之“圣王”,因为“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禹”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的政治特质,所以其最终才能够“有阴德”于百姓,获得人心,建立夏王朝,所谓“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人间训》)。而且《淮南子》还认为,所谓“圣王”既要能够为民除害,兴民所利,也要“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泰族训》),能够在政治上“尚贤”,知人善用。“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统治者只有在政治上将“利民”与“尚贤”视为首要任务来对待,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所规范,才能在政治上清源巩本,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乱政、虐政,“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在《淮南子》看来,这正是“圣王”在政治上“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泰族训》)的政治先见之体现。因此,“利民”和“尚贤”是《淮南子》“圣王”观的重要政治内涵,在其看来,只有“圣王”才能在政治上以“尚贤”为要,以“利民”为本,推动王朝政治走向“圣王之治”,实现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
《淮南子》的这种“圣王”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墨家政治思想影响的历史产物。墨家具有强烈的“圣王”诉求,先秦诸子中谈及“圣王”之多,几乎无过于墨子者。“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也认为所谓“圣王”者,需“布德施惠”于百姓,而且强调这是“法”天之所行,其结果也是能够真正获得民心。在墨子看来,“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而“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这正是“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7]13的历史反面。因此,墨子认为只有“圣王”才能“爱人利人”,所以“圣王”能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墨子·七患》)[7]16,能够出于“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的政治目的为民“作为宫室”,能够“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墨子·辞过》)[7]18,而且也只有“圣王”才能“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7]29-34。在墨子看来,只有能够“利民”和“尚贤”的专制君主政治,才具有正义性、合理性的思想内涵,因此墨子试图以这种独特的“圣王”观去影响现实中的统治者,推动其进行“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墨子·尚贤下》)[7]43的政治实践。
由上可见,《淮南子》的“圣王”观在内在地反映出墨家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对墨子“圣王”观的思想汲取和融会。当然,墨家政治思想并非塑造《淮南子》“圣王”观的唯一理论资源,二者也绝非能够简单等同。
一方面,黄老道家思想对《淮南子》的政治影响是根本的,所以《淮南子》之“圣王”,所体现出的实际是道家化的内涵。“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主术训》),“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圣王执一而勿失,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齐俗训》),这里的“圣王”显然非墨家意蕴,而是道家化的理想君主,体现出鲜明的黄老思想及精神。
另一方面,墨子所言“圣王”的思想内涵,也并没有能完全影响《淮南子》。墨家在政治上极力主张“尚同”的“治术”思想,试图实现政治文化上的“一言堂”,认为“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以治也”(《墨子·尚同上》)[7]46,“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墨子·尚同下》)[7]59,“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中》)[7]53。墨家这种强调政治思想一元化的做法,在《淮南子》中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完全被冷落。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是由于《淮南子》深刻借鉴秦王朝“独尊法术”的历史教训之后所得出的政治认识。墨家的“尚同”之义,与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异曲同工,虽然前者的尊君并未走向极端,但其所主张“尚同”的政治发展最终也难免走向禁绝百家的思想一元化方向,历史证明,这对于任何王朝的现实发展而言,都必然是条绝路。《淮南子》正是基于秦王朝的惨痛教训,所以在政治上坚持对先秦诸子进行兼收并蓄,有所融通的思想实践,由此体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的理论色彩,这与墨家所言之“尚同”的政治理路截然不同,所以“尚同”在墨子“圣王”观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淮南子》中缺少回应,影响甚微。
在墨家的“圣王”观中,不论是“尚贤”,抑或“尚同”,其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影响都远不及“利民”之说。墨家所主张的“兼爱”、“利人”,《淮南子》有着极为深切的政治认识,特别是西汉王朝建立在秦之速亡的基础上,后者所反映出的政治教训,更能凸显出墨家这种“利民”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淮南子》在战争上坚决反对“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的“不义之兵”,主张战争必须体现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的正义性内涵,所谓“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兵略训》),这与墨家的反对“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非攻中》)的不“义”战争,强调“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人下之害”,应该“中人之利”的“非攻”主张具有内在高度的一致性。从中可见,墨家具有“民本”意蕴的“圣王”观对《淮南子》的影响之深。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墨家政治思想成为《淮南子》“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精神深为后者所认同和汲取。
综上所述,作为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学派,墨家虽然在秦汉之际趋于衰落,但其对秦汉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仍具有难以忽视的历史影响,这在《淮南子》中表现突出。尽管墨家政治思想在《淮南子》不如黄老道家那样处于核心地位,也不如儒、法、阴阳等家有着显著的外在化表现,但实际上不论是尊崇“禹”的“身执蔂垂,以为民先”的政治精神,还是内在强烈的求“治”意识,以及“圣王”政治的积极追求,都深刻地凸显出墨家的历史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墨子所倡言“兴天下之利,除去人下之害”的“民本”思想及精神,得到《淮南子》由衷的政治共鸣与认同,进而在其政治思想中着力予以汲取和阐扬,这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基础”、“根本和核心”的“民本论”[13]368而言,无疑是秦汉时代背景下一次极大的丰富和充实,有力地促进了秦汉“民本”思想史的历史发展。
[1](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2](清)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J].孔子研究,1995(2).
[4]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孙纪文.淮南子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6](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清)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汉)毛亨传.(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王效峰.《淮南子》所见之墨家[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
[13]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