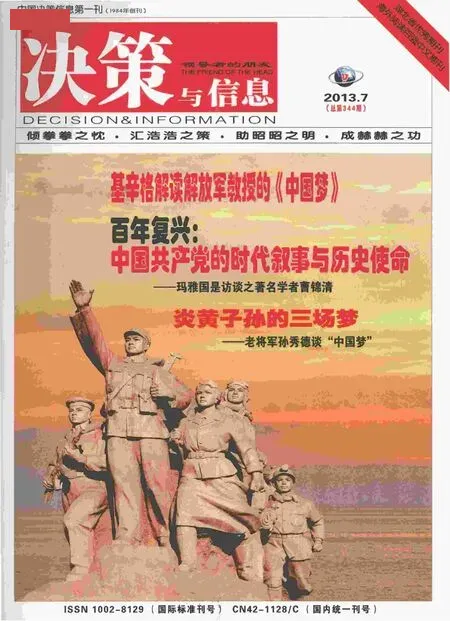百年复兴: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专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
玛雅
百年复兴: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
——专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
玛雅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走出理想的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中国七问》、《黄河边的中国》、《如何研究中国》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黄河边的中国》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中国革命史观,共产党政权的正统叙事
玛 雅:3月17日,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共产党的叙事来说,如何理解中国梦这个命题?
曹锦清: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百年”是一个历史叙事,与原来那种历史叙事不一样。这个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玛 雅:这个叙事与原来的叙事不一样在哪?原来的叙事是如何解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曹锦清:原来的叙事是马列主义的叙事,也是共产党的正统叙事。共产党对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表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这个建构过程的完成,以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的。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是,中国曾经经历了和人类其他社会一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导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在哪里?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我们未来要走向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套在中国这个龙的身上。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这个不是美国梦,是典型的中国梦,也只有在中国比较强劲。这个梦没有这几个条件不行——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近代在西方压迫下急剧衰落而激发的一种奋起抗争,摆脱积贫积弱的苦难,在较快的时间里富强起来,与列强并驾齐驱。这真的是百年之梦,它成为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精神旗帜。
玛 雅: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史观。重建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她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我觉得是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合理的包装,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所以这个叙事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来,到延安去。
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解释
玛 雅:从马列主义叙事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叙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如何适应这种语境变化的?
曹锦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与社会性质没关系。公有制可以和市场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邓小平那种解释重要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没有脱离原来的历史叙事,和毛泽东的理论是接轨的,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这是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重大解释。这个解释是说,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百年。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发展生产力,不必拘泥于姓社姓资。
但是1996年以后发现,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似乎不太兼容。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市场缩小,维持公有制;一个是把公有制企业改制,来适应市场经济。1996年的选择是后者,叫与时俱进,因为关闭市场是不可能的。
玛 雅: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削所有制之足来适市场经济之履。
曹锦清:1980年代中期就有争论,市场经济不断扩大,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维持住吗?当时有个“鸟笼理论”,即把市场套在一个较大可控的计划范围内。邓小平主张拆掉笼子,让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和深化。
市场扩展以后,公有制不再单一存在,私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按劳取酬这种分配形式也不再单一存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参与利润的分配,按资本分配产生了。再后来,知识和管理也作为要素参与分配,获得比一般的按劳取酬更多的报酬。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相适应,实际上是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按要素分配。到了十六大就把诸要素说清楚了:劳动作为要素,获得工资;管理和技术作为要素,理论上讲获得年薪;资本这个要素,获得利润。
只要承认市场经济,市场就会选择自己的所有制形式,市场是比所有制结构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你选定一种所有制结构,就可以任意选择一种运行方式,或计划或市场。你选定市场,把它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市场本身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自然会按生产的诸要素、按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加以配置——劳动力和资本按市场条件配置,知识也按市场条件配置。接下来还有两大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权力。
玛 雅:土地和权力并没有直接参与分配,怎么能成为要素?
曹锦清:土地作为要素如何参与分配?它的主体是谁?升值的部分应该给谁?现在法律没有规定。依照法律,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享有使用权。1988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变为国有之后才可以进入非农使用,这等于是授权地方政府,它可以正式成为地主了。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部分成了分配要素,掌管土地的地方官员通过这个要素配置可以去寻租,就使得权力也成为参与分配的一个要素。权力控制了土地,资本要获得土地必须通过地方政府,这样腐败的空间就扩大了,权钱交易就不可避免。
玛 雅:市场经济带来所有制的变化,对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产生了什么影响?
曹锦清: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原来的叙事里加入了市场和私有制,来为当代的现实改革服务,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经济上也是有效的。但是它带来一个理论难题:市场不但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是阶级和阶层分化的有效手段。这个时候再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在哪里呢?如果不在第一次分配里,是在第二次分配里吗?如果第一次分配完全是市场分配,无所谓什么主义了,那社会主义就只能退居到二次分配领域,退居到社会保障领域吗?
还有,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可以逻辑地推导出,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然后还要导向共产主义。那就是说,共产党现在的存在,是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奋斗的,只不过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这个发展阶段非常长,以至于初级阶段就要一百年,共产主义非常遥远。现在“共产主义”几个字在党的文件里还出现,《党章》里还保留,说明共产党还承认原来的那个叙事,这就是它的信仰支柱。这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作出的解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来仍然要通向共产主义。
西方政党是代表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玛 雅:共产党今天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它要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叙事,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你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
曹锦清:原有的叙事中断后,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叙事,但是重新建立一个史观谈何容易。所以前几年党内就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换旗是为现时的改革开放叙事,但是原来的旗子是为1949年的新中国叙事,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叙事。所以说,重建史观谈何容易,必然遭遇许多困难。
玛 雅:主张换旗是痴人说梦。十八大说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曹锦清:中共十八大报告讲,中国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正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苏联和中国当年用马列主义武装,达到了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抗衡的程度。但是马列主义也是西方的,最高境界不过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是缺少自己的叙事。日本的整个崛起就没有自己的叙事,只是脱亚入欧,它的悲剧归根到底就在于不自信。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没有这三个自信,遇到一场大的危机怎么办?我指的是经济较大规模的收缩和较大规模的失业,这是我们30年来没有经历过的。另外对腐败的治理以及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中央都提出来了,但是怎么解决?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告诉这个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玛 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不同的地方。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
曹锦清:所以我叫它代表党。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里面组成不同的利益,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上台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有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叙事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叙事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西方政治学偏重于经验主义,所以把民意测验、四年一选看得很重,当然有些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不对了。在多数老百姓的即时表达里隐含着背离公意的可能,比如美国打伊拉克,百分之七八十的民众支持率,现在看来背离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西方现在福利政策需要调整,支出多,收入少,借债多了出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事,谁都知道。可是2008年到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就是调整不过来,因为各个不同阶层要分担不同的成本,谁都不愿意。公意在那里也没人提,没有一个政党敢代表这个公意。这个时候的公意要求各个阶层,尤其某些阶层把裤带收紧一点,谁愿意呀?西方政治家们在危机面前吵吵闹闹,可是决策不了,贻误了很多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他们转过头来看我们,我们的决策集体能够发现整体的利益,有一个长远目标,能够领导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实现这个目标,就凭这三点他们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玛 雅:西方政要是选票驱动的,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曹锦清: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在当代人的意识里还存留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中国复兴,百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叙事
玛 雅:前面你谈到,原有的叙事中断了,造成理论上的困境。中国梦的提出能否在理论上破局,重新进行有效叙事?
曹锦清:中国梦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其实是回到整个近代民族救亡、富国、追赶那个叙事了。民族主义叙事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它是讲,中国近代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现在我们强大起来了。这个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是可以接轨的,它唤起一种近代百年的屈辱意识以及加快追赶的要求,是有相当强吸引力的。
现在讲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是根据发展成果来讲的。平心而论,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体保持了转型过程的相对稳定,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西方人也感到吃惊。中国国力的提升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尤其2008年以后,不要说周边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国家——欧洲、美国、日本,也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信息返回到国内,毫无疑问对激发民族自信心起了很大作用,认为30年来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现在是如何总结这条道路的时候了。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模式存在?能不能概括出几条经验来?最近五六年很多学者在做这件事。道路自信在知识界的这部分人当中被唤醒;有了这种自信,反过来要对西方学说和我们的传统学说有一个再评估。
但是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在知识界认识和论述是不足的。制度自信是说,是哪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使得这30年能够高速增长。这里面存在很大分歧,核心问题是,现有的一党执政体制在30年高速增长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西方人的评价比我们自己还要高。这背后还有理论自信,怎么建立一套说辞。这些归根结底还依赖于民族自信,民族自信高度依赖于现代化的成功,而现代化成功的标准我们在百年前就设定了——赶超,与西方并驾齐驱。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来看这个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它。
我和国内很多搞科技的人谈过,世界先进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花钱是买不来的,用市场也是换不来的,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路,我们突破这些重大尖端技术大概还要二三十年时间。30年后,简单来讲,中国也能把大型客机飞上天,整个工业化就达到了一个全新的与西方同等的水平。大型客机,包括航母,这些比一般的航天技术更依赖于一个庞大工业体系的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如果能在这些技术上全面突破,我们的综合国力就可以进一步上升,大量的中产阶级职业将会形成。这些职业归根结底是从国际市场来的,这将使发达国家的就业进一步流失,可能进一步流向中国,那它们的发展就会成问题。这对西方来讲怎么办?说太平洋能装下中美两个大国,其实也有一定的零和博弈,有相成的一面,也有相对的一面。对中国来讲,到那个时候就真正崛起了。
一个贯穿百年的诉求,一个典型的中国梦
玛 雅:外媒评论,中国梦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梦想,而不是从美国梦追求美好生活出发的中国人的梦想。你对中国梦如何解读?
曹锦清:中国梦是从三个层次来讲的,第一是民族的梦,第二是人民的梦,第三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为什么把民族和人民分开?民族的直接指称是国家,第一个梦的主体是国家。第二个梦恰恰存在一个问题,它的主体是人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是被市场划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有不同的要求。第三个层次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的主体是诉诸个人的。这些个人是被市场划分成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个体,他们是与职业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
玛 雅:谈到每个中国人的梦,很自然就想到美国梦。或者应该说,个人奋斗,追求成功,实现自我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曹锦清:美国梦有各种表述,最早的美国梦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形成的。它是个人的、奋斗的、圈地的、发财的,就是个人成功主义。这种个人成功是以土地的无限供给为前提的,代价是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杀戮。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美国梦不在土地里了,在职业里。很多贫困的移民到美国去,只要努力工作,有稳定的职业,就能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但条件是全世界的机会都向美国输送。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占全世界50%以上,这个优势没人能比。这个时候的美国梦比较讲机会均等了,但是只有机会均等还不够,还有大量的机会被创造出来。这和特定的时代是有关系的,今天的美国已经创造不出机会来了,而且机会还在流失。它现在的机会集中在所谓的金融领域,少数人暴富了。
玛 雅:所以美国现在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富悬殊巨大,99%和1%的对立产生了。
曹锦清:这样来看,中国梦的第三个层次——每个人的梦,只要努力都可以活得精彩,在目前情况下只是一种愿景。只讲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机会被大量地创造出来。现在每年本科以上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有几个能真正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在房价的高压下,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艰难,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让所有勤劳努力的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梦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实现起来有困难。市场经济展开了,资本在那里活跃着,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基本趋势。这是一个大问题。
玛 雅:如果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也能实现梦想。如果由少数人垄断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权贵社会,普通人梦想成真就希望渺茫。中国今天就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防止出现权贵社会,不要有钱人的孩子上“贵族学校”,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无门。
曹锦清:中国近代除了要富强,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太平。严复当时研究了英国富强背后的不足,在《原强》中写道:“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意思是说,西方虽然富强了,但是治理得不好,像儒家讲的那种太平盛世,还远远没有达到。太平盛世体现在几个方面:“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尤其重要的是家给人足,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都是《大同书》里的话。今天这些话也进入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叙事了,用的句法都一样,“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严复还说,“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意思是,贫富不相悬殊。所以,中国梦包括家给人足,还包括贫富不相悬殊。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具有社会意义,否则不平则鸣,就仇富仇官,社会就不太平。
玛 雅:市场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不可避免,但是要限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
曹锦清: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难以承受了。邓小平晚年和他堂弟邓垦讲,分配的问题要比生产的问题复杂严重多少倍。我们要用千百种方案、千百种手段、千百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内需不足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意味着分配不公,在马克思的叙事里是一回事。阶层是正三角形,分配是倒三角形;上面10%的人拥有那么多,下面10%的人拥有那么少,下面就出现巨大的需求不足。他有现实的需求,但是收入太低,不能形成购买力。
玛 雅:所以,相比美国梦,普通中国人梦想成真的机会小很多。美国地大物博,欧洲人刚到新大陆的时候,那里不光是无限的土地,而且是富庶的土地。再加上美国早年对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都是后发国家望尘莫及的。中国今天13亿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梦想,消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曹锦清:所以,第一个层次的中国梦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没有赶上西方,还得继续追赶,在赶上之前这个气不能泄。这种追赶的要求把自由主义那种内在的要求消减一些,否则以自由主义为本位,中国就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功尽弃了。毕竟现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来和国际力量竞争抗衡,没有国家的力量,没有巨大的国有企业的力量,在全球的竞争中怎么可能不败下阵来?一旦败下阵来,政治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再彻底开放,已经积累下的财富很快就会被吸光。中国要是“民主”了,西方势力马上会涌入,各种NGO、反对党哗地就来了,很快可以控制你,操纵你的国家政治,甚至让你国家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追赶的任务在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确实比有史以来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再给我们二三十年的和平,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百年的屈辱可以彻底被清洗,民族的自卑感从此消失。
所以对第一个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这批人已经在中产阶级以上,基本是精英了,但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还是寄予深切希望的。这个不是美国梦,是典型的中国梦,大概也只有在中国比较强劲。这个梦没有这几个条件不行——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近代在西方压迫下急剧衰落而激发的一种奋起抗争,摆脱积贫积弱的苦难,在较快的时间里富强起来,与列强并驾齐驱。
玛 雅:这真的是百年梦。就像外媒所说,中国梦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旗帜。
曹锦清:这是百年梦。“富强”这个概念是洋务运动时期被召唤到当下意识的。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机中,它进入到中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意识中——富强。甲午战争后有了“救亡”的概念,因为列强要瓜分中国,在那样一个形势下,救亡第一,所以救亡的意识是被甲午战败呼唤到我们民族的意识当中的。在救亡意识中,严复将西方的进化论吸收进来,使得一个讲循环史的民族、一个讲退化历史的民族,变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一个讲进化、讲自强的民族。进步、发展这些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召唤到我们民族意识里的。现在讲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这些概念已经牢牢树立起来了。
玛 雅:因为我们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
曹锦清:中国向西方学习,都是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富强。富强和复兴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主线,甲午战争以后就深深地注入到这个民族的主体思维中了。以后的各种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列主义,某种意义上都是作为实现富强这个总体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富强作为目标,在中国人当中达到了高度共识,没有不赞成的。那么如何富强?各派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教育能富强,有人说实业救国能富强,有人说自由主义能富强,有人说马列主义才能富强。
总之要富强,学习追赶西方,而且时间要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日本辩政考》就讲,按他的方案改革,10年就能与列强并驾齐驱。孙中山也讲10年。毛泽东当年也曾讲,10年超英赶美;1964年第三届人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把时间拉长了一点,分三步走,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邓小平没有说追上发达国家,但是他心里可能会想到,如果那时中国14亿人,人均GDP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肯定世界第一了。这是一个贯穿百年的诉求,这些话你去和香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讲,尤其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讲,和海外老华侨讲,一般都会认同的。

但是另一个价值诉求——个人的诉求,比较难。而且里面装进了自由主义的叙事——人权、自由,将来还要选举民主。个人梦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有民主诉求的。所以民族和个人这两个目标,你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也有相对的一面。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诉求要做主导,至少在20年之内是这样。一旦转型完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去年开了十八大,顺利完成了一个比较有序的过渡。这个过渡稳定10年,10年后再一个有序过渡,再稳定10年,20年时间我们就够了。就这样照着中国梦的叙事再干20年,中国一定会很好,中华民族一定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