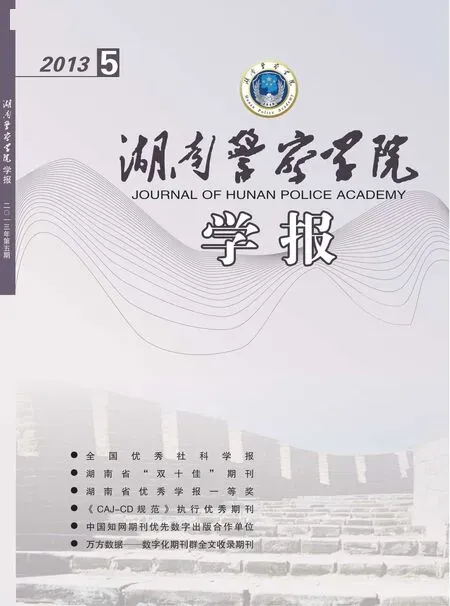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司法资源配置研究
——以法官资源为主要对象
胡志斌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当代中国农村法治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司法资源配置研究
——以法官资源为主要对象
胡志斌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专栏主持人语:统筹城乡发展是在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来的,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主题,以此为标志,统筹城乡发展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实质就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一体化,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建立以公平、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乡关系。司法资源作为深刻影响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效果,能否合理地配置农村地区的司法资源,特别是法官资源,决定着城乡司法统筹发展的成败。
司法既是一种社会管理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手段。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中,统筹城乡司法的发展既是统筹城乡发展应有的子课题,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法治保障。司法资源作为司法活动的必备条件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其能否公平配置直接影响着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效果。针对以法官资源为代表的城乡司法资源配置的偏失,应当通过为农村地区弥补法官资源、适当下移上级法院优质法官资源、提高农村地区基层法官待遇等路径,优化和稳定农村地区法官资源,逐步缩小城乡法官资源“剪刀差”,以促进城乡司法的统筹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地区;司法资源;法官资源;优化配置
虽然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已届10年,但就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事业而言,城乡发展状态仍不平衡。正如温家宝曾经指出的那样,“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与城镇仍有很大差距。”[1]为此,应当“围绕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这个重心,尽快扭转资源要素配置向城市倾斜的局面,促进城乡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在我国,司法资源①所谓司法资源,是指司法机关处理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以及非讼案件中所需要的人、财、物力。参见陈卫东,王政君:《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第134-140页。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界定不尽统一,本文所指涉的司法机关特指法院,司法人员或司法人力资源仅指法官或法官资源。既是一种国家权力资源,同时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共资源。因此,在统筹城乡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中,不应忽略司法资源的均衡配置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涉的城乡司法是根据基层法院的位置和司法辖区做出的划分,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构造出来的用作比较和衡量实在概念手段。”[3]城市司法是指设区市的城市基层法院(即区基层法院)在所属的城市司法辖区内开展的司法活动。城市基层法院设在地级以上的中等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其所处理的案件主要是市民社会的矛盾纠纷。而农村司法则是指设在县城的基层法院(不妨称之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所开展的司法活动,它以广大农村地区为主要司法辖区,所处理的案件主要是“三农”方面的纠纷[4]。本文中与城乡司法同根的概念(如“城乡司法资源”、“城乡法官资源”等)也是以此做出的界别。
一、城乡司法资源配置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应然要求
自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以来,国家和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全面放开粮油购销、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保护制度等,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梳理统筹城乡发展的十年成果,我们会不经意地发现,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城乡司法资源的统筹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城乡司法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是统筹城乡社会服务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子课题,应当纳入我们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步的视野,而不应当任其游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环境之外。
(一) 司法资源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资源,理应在城乡社会公众中均等化配置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司法资源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权力资源。但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资源还具有公共服务资源的性质。理由在于:第一,司法资源的开发、配置和利用需要消耗公共财政资源。而公共财政资源并非天然的财资源,其来源于国家向公众汲取的各种税收。作为一种取自于民的公共资源,理所当然要用之于民,反哺于民。就司法资源中的法官资源而言,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既具管理社会的职权,也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责。第二,我国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方针决定了司法资源是一种服务人民的公共资源。自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来,执政党和最高司法机关不断强调司法为民的宗旨。从2006年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执法为民的“执法”是广义的,包括行政机关的执法(即狭义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到2007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司法机关应当坚持“三个至上”②“三个至上”是指党的事业之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司法方针,再到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司法理念,都充分说明了司法资源虽然具有国家性和政治性,但也不乏鲜明的人民性和公共性。
既然司法资源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它就不应当被某些社会主体或利益集团所独占或主占,而应当根据公众的客观需求,在城乡社会均等化配置。这种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还有其法哲学依据,即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最早是一种主张社会公共财富或资源分配结果公正的经济伦理。后来,人们赋予了分配正义理论更为全面的内涵,即不仅社会财富或资源分配的结果应当是公正的,而且分配的形式或分配过程也应是公正的,也即机会均等。在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罗尔斯看来,虽然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完全相同,但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分享权利或资源的机会和过程并不一定公正。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国家有义务平衡资源分配,平抑分配结果的过分失衡[5]。为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基于分配正义原则的要求,司法资源配置应当根据公众需要成比例分配[6],而不应当存在地区“剪刀差”。故此,在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中,应当将司法资源视为基本的公共服务资源,力求其分配的均等化,力促城乡司法服务的均衡化。
(二) 城乡一体化之社会公正价值诉求有赖于司法资源在城乡社会的均等化配置
在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逐步缩小服务和保障水平上的差距,最终迈向城乡一体化。”[1]。从法理的视角解读,一体化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虽然司法的直接目的是追求个案的公正,但其根本目的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可见,城乡一体化的价值诉求与司法的价值目标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司法的功能实际上就是“通过个案判决矫正社会正义,说到底是对社会正义管理的技术。”[7]可以说,“司法越公正,社会才可能越公正,整个社会才更具有凝聚力,并能真正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8]613。与司法公正注重个案的公正性裁判不同,社会公正则立足社会大环境,偏重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性。但因社会公正的价值体系包括司法公正,并以司法公正为保障[9],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追求个案公正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正。如果司法的基础——司法资源——在配置上带有偏私,那么,社会正义的基础也就被动摇了,再公正的司法最多也只是个案的公正。而从社会公正的高度来审视,司法是不公正的,因为公共的司法资源被异化成了偏袒特定社会主体或群体利益的工具,并因此突破了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谐相处的政治底线──社会公正[10]。
因此,司法能否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不是良好法律和完备法律体系本身就能自然成就的,它要求其赖以发挥功效的司法资源在城乡社会或者整个社会中均等化配置。首先,法官资源的配置应当均等化。法官资源是整个司法资源中的第一性资源要素,是司法富有生命力的根本保证。“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律,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如果法官资源缺失或者法官资源劣质,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都将是纸上谈兵。为此,国家不仅应注重科学开发优质的法官资源,更要注重在全社会公平配置法官资源。不管是农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人们的经济状况、政治觉悟、社会处境、文化背景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在分享以法官资源为核心要素的司法资源,以保障合法权益的需求上,不同社会主体应当是无差别的,否则,城乡一体化也就失去了司法保障的人力资源基础。其次,司法物质资源配置应当均等化。司法活动不仅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支撑,因此,要让司法公正的阳光普照到城乡社会的每个角落,必须保证司法物质资源在城乡社会均等化分配。否则,城乡社会公正也就丧失去了赖以实现的司法公正之物质基础。所以,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司法资源的公正化配置是其应有之义。
(三) 司法资源属于公力救济资源,城乡公众权利的平等性要求其均等化配置保护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当社会公众中的任何一员之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国家有职权也有职责通过救济性的司法权力,恢复或最大程度地修复遭受破坏了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决定了权利救济的平等性[11],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等如何,既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实体性权利,也平等地享有实体性权利受到侵犯时获得司法救济的程序性权利。换言之,虽然富人的宝马和乞丐的打狗棍的价值有天壤之别,但是它们一旦受到侵犯,在财产权利保护上,没有大小之分,国家应当给予同等的司法救济机会和待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司法资源的均等化配置。
作为一种公力救济资源,司法资源均等化配置的应然要求是:第一,司法救济机会平等。也就是说,不论社会主体身处农村,还是地处城市,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司法机关和司法资源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存在VIP式的保护[12]。否则,会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结果,从而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这种情况或许在西方国家可以存在,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司法资源的配置有利于富人。正如林德布洛姆所说:“在美国,昂贵的法律救济面向富人敞开,……。”[13]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司法资源的配置不仅要做到形式上的公正,而且也需要结果上的公平,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否则,社会主义的司法也就失去了“公”的属性。第二,司法救济成本平等。对于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权利义务发生争议的当事人来说,司法救济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依法向法院交纳诉讼费、向律师支付代理费等。如果说诉讼费用制度是普适性的法律制度,具有公平合理性①事实上,由于司法资源的利用本身需要当事人具备一定的财力与智力条件,这本身就已经阻却了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当事人诉诸司法的可能性。特别是日益专业化的司法程序和诉讼方式以及案件久拖不决的诉讼耗费,使一些社会主体尤其是农村地区或经济困难又缺乏社会资源的社会成员“临讼却步”。。但是,当司法资源配置不均等时,社会主体分享司法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则会出现差异,造成司法救济成本的不平等。例如,远离法院的当事人与身处法院附近或周边的当事人相比,涉诉时要多出“多余的”成本(如往返车旅费、餐饮费以及误工损失等)。为此,司法机关的设置和司法资源的分配要力求“圆心化”,让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处于司法救济的同一圆周上,使其拥有获取司法资源的相同距离。如果个别主体处在司法救济的圆周外,则应通过变通措施(如建立巡回法庭、减免诉讼费用等)予以平衡或弥补,以司法救济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公平消费,保证同等权利的社会主体获得同等保护。
二、城乡司法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法官资源配置的现实
受我国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的影响,城市社会不仅在医疗、养老、低保、就业、教育等社会服务水平上超越农村社会,而且在司法保障或者司法服务方面,也具有便捷、优质等优点。且不说司法机关普遍设在城市社会,能给市民提供便捷司法诉求,仅就法官这一最核心的司法资源的配置而言,城乡社会不仅法官资源数量不均衡,而且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资源在质量上也弱质于城市基层法院。如果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的基层法院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地区基层法院进行法官资源配置情况的比对,孰优孰劣不言而喻。为了更有力地说明我国城乡法官资源配置的差异性,笔者在负责的“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农村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研究”的项目中,选择了中部地区A省M地级市所属的Y区基层法院(即城市基层法院)、D县基层法院(即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作为对比研究样本②虽然笔者随机选择的研究样本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验证了这一现象。参见山东省高院研究室:《山东法院审判力量配置与法官负荷情况分析》,《人民司法》2010年第19期,第51-53页;周迅,钱锋:《论审判资源及其配置──以基层法院为视角》,《中国审判》2010年第1期,第67-69页;孙新军:《基层法院人力资源配置的现状与出路》,《山东审判》2008年第5期,第73-75页,等等。。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城乡法官资源配置表现出较明显的非均衡性(参见表1)。

表1:A省M市Y区基层法院和D县基层法院法官资源对比表
第一,Y区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配置具有数量上的优势。通过表1数据,可以计算出Y区基层法院司法服务的“人口/法官”比值是2,608,而D县基层法院“人口/法官”比值3,715。很显然,在法官人均服务公众的数量上,城乡社会具有不平衡性,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人均服务对象多于城市基层法院。换言之,城市社会人均法官资源占有量大于农村社会。对此,我们不能完全归因于城市社会案发量多于农村社会。事实上,在司法光芒还不能充分普照农村社会每个角落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抑制了农村社会大量的矛盾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而使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案件”,不少民事纠纷甚至刑事犯罪是通过和解、调解而予以化解的,或者一些农村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司法维权的意识或能力而放弃维权。正因为大量的民间纠纷“自生自灭”,遮掩了农村社会对公力救济的真实需求。虽然通过非诉讼形式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缓和司法供求矛盾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价值,但从城乡社会公平分享司法资源的角度审视,农村社会人均法官资源占有量偏低似乎又有失公允。为此,我们不应过渡地放任农村社会私力救济的适用,否则,法治在农村社会就容易被边缘化,“弱肉强食”、“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都可能会因为公力救济的弱势而成为现实,这显然不符合法治的初衷。为此,“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人的(法治)生活。”[14]
第二,在法官资源的质量上,Y区基层法院明显优于D县基层法院。由于法官专业素质(通常以法官学历和所学专业为衡量指标)是其业务能力等素质养成的基础以及职业准入的重要条件,所以,笔者采用专业素质标准来比较城乡法官资源的优劣。需要说明的是,表1所统计的法官是广义法官①对法官专业素质进行调研,容易涉及法院和法官的“隐私”,被调研对象通常只给定一个模糊数据。所以,这里以广义法官(实务部门习惯称之为司法干警)为统计对象。,即法院在编的所有司法干警,包括狭义法官(审判人员)以及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司法政务人员等。通过表1可以看出,Y区基层法院法官的本科学历达82.6%,而且有36.5%的法官第一学历为全日制的法学本科学历,并有7.0%的法官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而农村地区的D县基层法院只有74.3%的法官具有本科学历,其中11.4%的法官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法学本科专业,分别比城市基层法院少了8.3个、25.1个百分点。而且D县基层法院没有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法官。
第三,城乡法官资源的非均等化配置容易导致司法效果上的城乡差别,并由此造成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城乡差异。司法公正的差异性突出表现在城乡基层司法质量和司法效率上,并通过上诉率和改判率两个司法评价指标表现出来。上诉率和改判率越高,说明基层法院一审司法质量越低,而且上诉和改判本身还会造成司法效率的降低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下降。通过表1可以看出,D县基层法院裁判上诉率和改判率比Y区基层法院分别高出9个、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乡法官资源的配置失衡使得司法效果在城乡社会难以实现统一。
三、优化农村地区司法资源配置的进路——以法官资源为对象
包括司法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服务之城乡差距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各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城市偏向明显、大量要素资源从农村不公平流出所造成的[15]。在司法服务领域,要改变这一现状,应当优化农村地区司法资源配置,以法官资源为例,具体构想如下:
(一) 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定向培养免费“司法生”
近年来,为了解决中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国家实施了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定向为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培养师资,以平抑教育资源城乡分配的不均和不公,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此,可以效仿这一做法,委托政法院校,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定向培养免费“司法生”(即法官、检察官的后备军)②为了缓解西部司法人才的匮乏,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从2008年开始,开展了政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中国政法大学等25所政法院校试点招录政法体制改革试点班,其宗旨就是要为西部地区的县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参见木子:《试点改革:西部司法官困局之解》,《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12期,第13-15页。这种做法有必要从西部地区拓展到我国其他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法院,以统筹城乡司法资源的公平化配置。。具体构想是:根据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检察官资源配置的实际需要,将法官、检察官缺额编制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由中央政法委牵头汇总,在组织、人事、教育等部门的配合下,将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检察院司法人员缺额以免费“司法生”的形式列入高招计划中。在录取免费“司法生”的形式上,可以比照军事、公安院校的录取,列入提前单独录取批次,并规定报考的考生必须达到一本(或者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为了提高培养档次,确保免费“司法生”的培养质量,培养免费“司法生”的任务应当交由全国五所专门的政法院校(即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或者“985”院校的法学院系承担。对于达到培养协议约定标准的“司法生”,例如达到了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线或者最高司法机关认可的分数线,毕业后按照培养协议的要求,定向分配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工作,并规定只有在服务期(例如5-10年)满后,方可调离或辞职。
(二) 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开发返聘型优质法官资源
在司法制度较为完善的英美法系国家,选任法官时比较看重被选任者的“年长、经验、精英”,一些国家规定法官的退休年龄在65-70岁之间[8]454。这种“高龄”退休制度主要是考虑到法官裁判能力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积淀。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这实际上就是对经验型、技术型人力资源特质的形象表达。对于经验性、技能性、社会性都很强的法官职业来说,60岁左右正值司法技能形成和展现的黄金时段,如果一些优秀的法官此时依法退休或退居二线①按照我国领导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领导干部55-60岁就开始退居二线,处于一种准退休状态。所以,法院中一些优质的领导型法官资源,因为国家干部制度的制约,可能会更早地处于被闲置状态。,无疑是司法人力资源的浪费。对于这种“司法经验(人力)资源”,完全可以延期续用,使其在缓解司法供求矛盾中发挥作用[16]。因此,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特别是优质法官资源不足的现状,可以开发返聘型优质法官资源,予以补给。具体构想是:不论是基层法院的法官,还是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只要具有高级法官以上审判职务或获得过市级以上“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的法官,在退休或退居二线时,可以由省级高级法院牵头,并在组织人事、权力机关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依法返聘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规定其退休年龄延长至65-70岁。返聘型法官所需的各项费用,应由国家专项拨付。
(三) 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充实司法辅助性人力资源
法官是法院司法干警中的主体和核心部分,除了过去已经具备了审判员身份的干警外,2002年以后,按照《法官法》的规定,取得法官身份并有资格担任审判员审理案件的司法干警,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干警中具备法官身份的一般不到80%,这其中还有部分是领导型法官,实际办案的法官数量较为有限。法官的司法业务除了审理裁判案件外,还兼负庭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如送达法律文书、布置法庭等)、调查取证、制作裁判文书等非裁判性司法事务。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的司法压力,节省办案法官的时间和精力,对于非裁判性司法事务,完全可以交由没有法官身份的司法辅助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来完成。为此,可以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适时、适量补充司法辅助人员。这些人员可以从优秀法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中遴选。自2008年开始,国家开始准许法学本科专业的大三学生报考司法考试,一些法科学生在毕业前就能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这给农村地区基层法院遴选司法辅助人员提供了契机②目前,我国共有623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29万多人,法科毕业生就业形势连年低迷,造成法律人才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参见杨晨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咨询组工作组成立》,《中国教育报》2011年4月2日。为此,可以鼓励品学兼优的法科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工作,这样既可以解决部分法科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能够消解农村地区司法人力资源不足、不优的问题。。所以,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可以根据需要,直接从应届法科毕业生中录用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专职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并以此储备法官后备资源。
(四) 建立中、高级法院优秀法官服务基层法院的帮扶制度
在我国,中级以上法院法官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普遍优于基层法院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案多人少”的司法供求矛盾并不明显。为此,可以建立中、高级法院优秀法官服务基层法院的帮扶制度,使上级法院优质法官资源向基层法院适度倾斜。第一,构建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指导基层法院法官办案的服务专线或网络平台。这种服务模式可以由省级高级法院牵头组建,规定由省级高院、市级中院具有高级以上审判职务、获得过省级以上“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的法官轮流通过网络为基层法官提供审判业务咨询。第二,建立中级、高级法院法官岗前赴基层锻炼制度。一是规定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初任法官,在正式上岗前,必须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实习1-2年。二是规定中级、高级法院拟晋级、晋职的法官,应当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挂职锻炼1年左右,并规定没有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工作经历的,不得提拔重用,以强制性的下基层帮扶制度的构建和实施,缓解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资源不足的矛盾,并以此促进法官人才资源的良性流动。
(五) 建立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吸引和稳定优秀法律人才的制度
城乡法官资源配置不均等的原因除了法官管理体制的原因外,还与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工资收入较低、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事业发展空间较小等因素有关。为此,在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激励和保障机制的构建,吸引优秀的法律人才流向农村地区,并以优惠政策稳定基层法官队伍。
第一,建立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职级高配制。在县级基层法院,再优秀的法官(除了法院院长外)最多熬到正科级,但这也只是少数法官有此机会,多数法官一辈子也只能是副主任科员甚至科员的级别,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按照职级核定,因此,绝大多数法官的工资也因职级的限制而难以提高。受事业发展空间有限性与工资水准偏低性的影响,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经常出现一些优秀的法官改行做律师或跳巢至经济发达地区从事法律职业。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将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实行职级高配制,并以此核定工资报酬。例如,同等条件下,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行政级别高于城市基层法院或中级以上法院法官1-2级,以此促进该地区的法官“安居乐业”。
第二,规定中级以上法院今后选任法官只能从基层法院特别是农村地区基层法院遴选,“强迫”优秀法律人才先下基层,逐级锻炼和晋级晋职。尽管这样的构想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已有规定,但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所以,有必要通过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完善,将该项制度升级为一项强制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第三,比照国家将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工资纳入中央财政统一供给的做法,将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的工资全部纳入中央财政统一预算和拨付,以解决因地方财政供给不力而造成的农村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法院法官工资发放迟滞的问题。
第四,建立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高额退休金制。建立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更静心、更潜心、更敬业地扎根基层,恪尽职守。具体内容就是规定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退休时,按照其在基层法院连续供职的年限,给予一次性的退休补贴,例如,规定,连续工作20年的,退休时一次性补贴20万,这些费用可以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支付或者由中央财政独立支付。
[1]温家宝.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J].求是,2012,(2): 3-10.
[2]回良玉.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J].求是,2010,(3):3-8.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7.
[4]谭世贵.我国农村司法制度的初步研究[J].法学杂志,2009,(10):17-23.
[5][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50.
[6][英]阿德里安A.S.朱克曼.危机中的民事司法[M].傅郁林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6.
[7]徐显明.公平正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J].法学家,2006,(3):16-19.
[8]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邵景均.社会公正的三重涵义:分配、程序、司法公正[N].人民日报,2010-05-07(8).
[10]孙建军,何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述评[J].云南社会科学,2010,(5):31-35.
[11]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2]顾培东.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资源分享问题[J].中国法学,2008,(3):141-149.
[13][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M].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65.
[14]苏力.为什么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送法下乡》导论[J].法商研究,2000,(3):82-92.
[15]梁謇.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J].行政论坛,2011,(5): 88-91.
[16]黄琰,蔡小林,帅晓东.司法经验资源闲置的样本分析[J].人民司法,2010,(15):67-70.
Allocation of Rural J udicial Resourcesin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TakingJudgeResourcesastheMainObject
HU Zhi-Bi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6)
Justice is a social management tool and a social service means.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the co-ordination justice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ose not only the sub-topics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but also a law protection.As a prerequisite of judicial activities and public resources,whether judicial resources can allocate fairly or not will make some direct impacts on the social effects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In view of partiality of judi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represented by judg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 should optimize and stabilize judges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through making up judges resources for rural areas,appropriately moving quality judges resources of the superior court down to grassroots courts,improving grassroots judge treatment in rural areas,gradually narrowing the judges resources"scissors"between urban and rural,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justic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justice;rural areas;judicial resources; judge resources;optimizing allocation
D902
A
2095-1140(2013)05-0005-08
(责任编辑:王道春)
2013-05-18
2011年安徽农业大学稳定和引进人才科研资助项目。
胡志斌(1967-),男,安徽霍邱人,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诉讼法学与司法制度研究。
-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论警察权力道德制约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