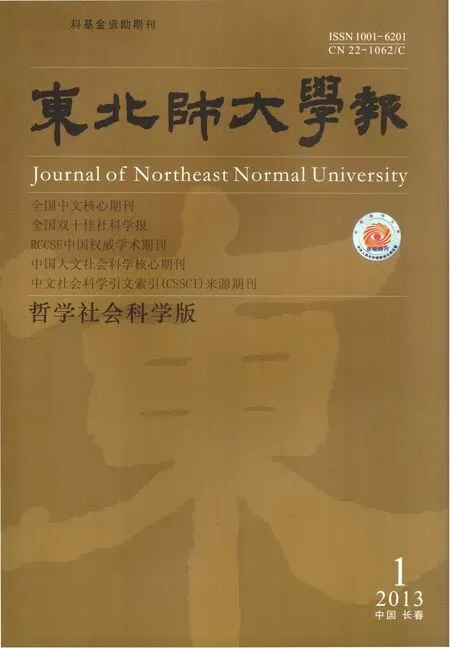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结
杨淑静,丁惠平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海学刊》杂志社,江苏 南京 210000)
精神生活是人内在的精神诉求,或者说是人自身具有的坚固的形而上学情结。正是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结才使人的精神生活不断获得愈益明确、愈益清晰的理论意识,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直指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现状。精神生活的物化不仅严重销蚀了精神生活本应具有的自觉意识,同时对精神生活内蕴的形上诉求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在精神生活获得自觉意识的同时进行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这既是葆有精神生活形上诉求的理论努力,同时也是精神生活形上情结的内在理论张力。
一、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典型特征就是韦伯意义上的“祛魅”,即精神生活的祛魅化、世俗化,“宗教发展中的这种伟大历史过程——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使世界理性化,摒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1],对于此种精神生活现状,马克思也做过相关论述,“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275随着启蒙以理性取代宗教和神话,世界本身去神秘化了,现实已撕去了被神话和宗教包裹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人们已经能够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理性地看待事物本身了,而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就是精神生活不断自我澄明的理论表征。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祛魅化、世俗化,而祛魅化和世俗化的时代就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代。以往的时代,是宗教统治的时代。在宗教的统治下,人类丧失了自己,或者还没有获得自己,人类的精神生活还处于蒙昧状态。宗教时代的精神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样子被接受的,生活与认识的统一是不证自明的,“对此,我们已不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过去的同类是在现实宛如被蒙上面纱的条件下生活的。”[3]1-2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推进,彻底反宗教的斗争开始了,宗教斗争使人们认识到了宗教的本质,人们已经能彻底地撕碎宗教链条上那些虚构的花朵,而反宗教斗争最强烈的莫过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破除了宗教、神话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人作为理性的人不断崛起。启蒙作为理性的倡导者成了现代性的发源地,理性是现时代的时代特征,理性的人彻底摆脱了宗教的幻想,使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了,人从天国回到了人间,找到了人的真实本质,找到本质的人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的太阳旋转。“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3]3回到现实的人能理性地面对此岸世界的真理,人不再迷茫了。现时代的人类,由于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张扬,已经获得了清晰明确的时代意识,人们已经能自觉地反思精神生活问题了,就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到的那样“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4]。以往的时代,生活本身是被遮蔽的,因此,现时代就要不断地使人的生活解蔽、并不断的自我澄明。
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内在理论要求。正是因为人类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人类才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精神生活。自席勒起,现代的头脑已经意识到,关于世界中有神存在的观念已经丧失,人们已经开始不断地寻求自己精神生活的内在理论诉求。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认为西方社会被引向了绝对的虚无主义,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作为总体仍是一种精神化了的存在。“领悟一种状况是导向支配该状况的第一步,因为,审视他和理解他唤起了改变他的存在的意志……一旦成为这种状况中的一个主动参与者,那我就自然地想要干预这种状况与我自身生存之间的相互作用。”[3]20也就是说,我们一边在生活,一边在看我们对生活的意识,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间的区别,“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3]3,这恰恰表征了精神生活形上诉求的内在理论要求。黑格尔在艰深晦涩、抽象的哲学著作《小逻辑》中谈到“世界精神太忙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5]31,回归家园就是回归精神生活的内在性,就是回归精神生活的形上性,也就是人应尊重人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对人而言,生命活动的较高的开端必然始于人的精神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信仰、人文化成的道德伦理、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正义感与生命激情的内心涌动,才能使人以高尚的开端创造真正属于人的生活”[6]。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有言“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成为“大写意义上的人”,而“大写意义上的人”就是不断追求并践行崇高的人,也即成为坚守精神生活内在诉求的人。
二、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
人类获得了精神生活的自主性,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遇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即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不再具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是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人要重新寻求自己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意义。寻求本身就是对精神生活现状的反思和批判。
精神生活的现状是:它被严重物化了。在世俗化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物质性思维方式,即工具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市场的运行逻辑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运行逻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由于工具理性的猖獗导致目的合理性领域和价值合理性领域的分裂,价值理性领域被目的合理性领域侵蚀了,造成了“持久算计的世界”以及“多神和无序的世界”。在目的合理性领域中,人们只需要服从社会的法律法规就可以了,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服从外在的约束,而是要寻求使自己崇高起来的意义和价值,事实领域在面对人自身的这一内在要求时沉默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在“价值合理性领域”完成。所以,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必须诉诸于价值合理性行为领域。这必然会导致如下的结果:首先就是价值的多神化,或者说“终极价值的多元化”;第二就是价值的争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都坚持自己的价值信念,从而造成多元价值的相互冲突。韦伯所揭示的是精神生活物化的典型特征,即“如此被贬抑、被拉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实质”[3]42-43,但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此问题。哈贝马斯明确了此问题,用他的表述就是:“系统侵蚀生活世界,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物化时代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的性质,它只能满足个人的欲望和现实利益的实现,无法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终极关怀的价值诉求,它根本就不能代替传统社会的道德和宗教,就像许纪霖先生说的那样,“在中国社会,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便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活动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当神圣性从人们门前被驱逐出来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7]8,精神生活严重物化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他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他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274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金钱只关心为一切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价值,它把所有性质和个性化都化约在一个纯粹的数量层面”,“知性关系把人当作数字来处理”,“正是货币经济使得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可权衡、算计、清点,以及把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不论是韦伯、马克思、西美尔、哈贝马斯,亦或是许纪霖,进行的都是自觉意义上的精神生活物化的现状反思。
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根源于人类自我意识的不平静,这种不平静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变得清晰起来。黑格尔通过自我意识的自否定,确定了绝对理念的辨证法,“当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这样的进展过程表明其自身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恢复绝对的内容,我们的思想最初向外离开并超出这内容,正是为了恢复精神最特有的最自由的素质”[5]5。绝对理念的辩证法使一切不合理的因素都消化在自身的理论体系内,也即“心灵深入于这些内容,借他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5]5。正是自我意识的不平静,人才能在精神生活形上性内在的辩证张力中,对精神生活的物化现状进行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身同时也是对形上性的一种内在葆有。只有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才能拯救精神的形上性,蔑视辩证法,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深渊(恩格斯语)。
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促进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物化现状的批判,对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也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内在理论张力,歌德写到“人类将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机灵,但是并不变得更好……”这就表达了精神生活内在的理论要求,“聪明”和“机灵”意味着精神生活获得了理论自觉,而“不好”表达的则是精神生活物化的现状。理论自觉是形而上学的内在理论要求,而批判则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内在理论张力。人们之所以有这种批判意识,是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应为这种现状负责,因为它可以被有目的地加以改变,可以重新塑造得更接近于人心的愿望,而人内心的愿望就是精神生活形上性最直接的表达。
三、精神生活的形上诉求
人类获得了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这是精神生活形上诉求的内在理论动力,正是这种理论自觉,使人们能够揭开现实的面纱,意识到精神生活物化的现状。精神生活的形上性不仅具有揭示精神生活物化现状的理论要求,同时还具有批判精神生活物化的内在理论张力。这就是精神生活的形上情结。
世俗化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精神生活的物化,但精神生活的物化不能证明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世俗化转向,这就是精神生活形上性的辩证法。现代文化(在本文中,笔者是在一个意义上运用“精神生活”和“文化”两个词的)的典型特征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平民文化替代精英文化,即现时代是一个英雄主义隐退的时代,是一个大众造星的时代,芙蓉姐姐、凤姐和网络明星,证明了精英文化的隐退,“超女”、“快男”作为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义诞生的精神宣言。精英文化是智性的、启蒙的,诉诸于人们的理性和想像,而世俗文化则是反智性的、反启蒙的,它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和直觉[7]26。造星运动,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一方面证实了精神生活物化的现状,但同时也揭示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人们获得了精神生活的自觉意识,这也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总是以退步的形式实现进步”、“片面性才是历史的真正原则”。有的学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心时代”,“心时代”昭示了精神生活的新样式,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看电影比吃饭重要”、“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意思比意义更重要”等等。“看电影”、“出汗”、“意思”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要求,是精神生活形上诉求的理论表征。
以物欲为标志的时代,若无人类精神生活的形上诉求,将会是时代最悲壮的情景[8]。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它却成了个人不堪忍受的巨大压力。城市里的人彻底原子化了,《大话西游》以“活在当下和现在”为核心内容塑造了现时代人类精神生活样式的经典传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德纲和周立波都是“无厘头”、“大话时代”的弟子。就像赵本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的那样,“现时代,只要快乐就行,我就能把快乐带给你们”,快乐就是人类内在的精神追求,是物化时代精神生活最狂放的吼叫。快乐是精神生活形上性最直接的表达。人类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寻求从内部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接受一种普遍的、像图表一样中规中矩的生活方式。尽管由这些生机勃勃的冲动所指引并赋予特征的生活在现时代并非绝无可能,但是他们还是在观念上与之对立的。由此看来,我们就能解释像罗斯金和尼采那样的人物对于现时代的深切憎恨,这些人只能在非模式化的个人表现中找到生活价值,而这些表现无法化约为准确的等价物,最后,他们只能走向绝对的相对,走向精神生活的虚无主义。康德所说的“历史中的这样一个现象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人性中有个美好的事物的萌芽以及达到这种事物的能力。而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政治学学者曾经从先前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推论出这一点”。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也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他认为即使是在“体育运动中,仍然包含着前进升华的要素作为对僵化的现状的抗议,这种要素虽然不是共有的目标,却是无意识的愿望……人所达到的境界要超出他在生活秩序中所完成的,他要通过表现那指向整体的意志的国家来达到这种境界”[3]60,75。“无意识的愿望”和“生活秩序的境界”一方面表达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精神生活的物化批判,而这既是精神生活形而上性的内在理论要求,同时也是其内在的理论张力。
黑格尔坚守“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而最高尚的东西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所希冀的东西,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作为人成为人”,就是尼采的“高山之巅、冰雪之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这本身就是对精神生活形上诉求的理论表征。精神生活具有内在的坚实的形而上学情结,这是系在人类精神生活链条上一朵纯洁无瑕的、永不凋谢的花朵。
[1][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79,8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7.
[5][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胡海波.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生命精神[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0.
[7]许纪霖.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8]涂良川.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形上意蕴[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