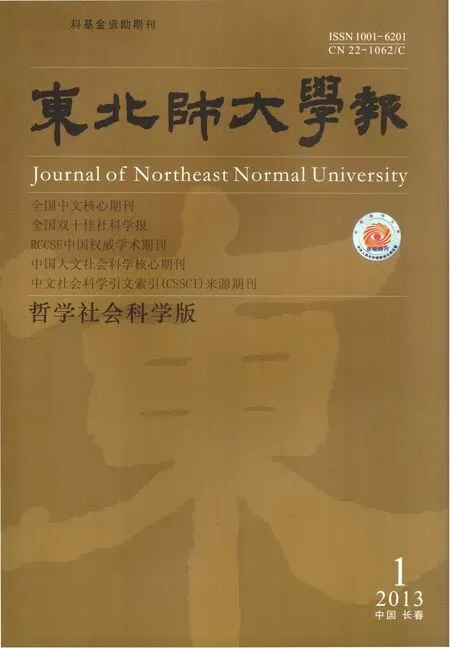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梁诸英
(1.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2.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 安庆246133)
部分由于明清时期地方史料丰富的因素,学界从区域性视角对明清时期的虎患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①比如黄志繁、刘正刚、郑维宽、曹志红、袁轶峰、刘兴亮、蓝勇、闵宗殿、周正庆等先生对明清虎患问题的研究;另,王子今先生对秦汉时期虎患作了专论。。现有“虎患”问题的研究对正史材料利用不多;从时段上来看,对魏晋至元代期间的虎患问题更少有专论。从正史记载来看,晋唐宋元时期虎患多有发生,且唐宋及其后更趋严重。本文拟以正史为资料,对晋唐宋元时期的虎患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对当时社会于虎患问题的解读及采取的应对策略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一、虎患概况
虎是山林中的凶猛动物,被称为百兽之王。虎患是指虎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侵害。正史对魏晋至元代期间的老虎出没及虎患多有记载。从现有记载看,此时期虎患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南北均有分布;二是在唐宋以后呈现更为严重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虎患在南北均有分布。在北方,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北淯郡“尝有虎害”[1]1635;《魏书》还记载:“太祖登国中,河南有虎七,卧于河侧,三月乃去”[1]2923。北朝刘仕儁,彭城人,在母亲去世后“庐于墓侧”而存在“虎狼驯扰”[2]2838的情况。南朝时期,郢州、溧阳、徐州、湘州有虎患(据《宋书》卷74、《陈书》卷34、《梁书》卷23)。《梁书》还记载天监六年(507)零陵地区“郡多虎暴”[3]773;《南齐书》记载,建武四年(497)春“夜虎攫伤人”[4]387。
在隋唐时期,因长安城周围林木的砍伐和森林的破坏,长安地区及附近虎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有虎入长安城周边地区。唐代大历四年(769)八月“虎入京师长寿坊宰臣元载家庙”[5]923。唐代建中三年(782)九月“虎入宣阳里,伤人二”[5]923。唐代显示虎患出没的地点较为广泛,比如北平、登封、韶州、桐城地区(据《新唐书》卷202、卷41,《旧唐书》卷191)。
宋辽金时期也多有虎伤人事件,且记载比前代为多,显示了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时期的虎伤人记载多,而且虎患发生的区域比以前更为广泛,表现在位于长江流域的府州虎患的出现。比如杭州、扬州、江陵府等府州,这应该与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关。《宋史》的记载也反映了虎患问题日益严重的发展趋势。开宝八年(975)十月,“江陵府白昼虎入市,伤二人”;太平兴国三年(978),“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太平兴国七年(982),“虎入萧山县民赵驯家,害八口”;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虎伤人”;至道二年(996)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侧,昼有虎入税场”;绍兴二十年(1150),海州地区“有二虎入城,人射杀之,虎亦搏人”;绍熙四年(1193),“鄂州武昌县虎为人患”;咸淳九年(1273)十一月“有虎出于扬州市”。以上可知,老虎伤人、食人的情况有时很严重,可以推测宋元经济开发活动与虎类生存环境存在冲突。实际上虎类之间,或者虎与其他兽类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相互厮杀也有记载,也可证虎类生存状况之趋于恶化。比如北宋咸平二年(999)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一死,食之殆半”;南宋淳熙十年(1183)“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6]1451-1452。
《宋史》的列传部分也揭示了老虎出没的情况,并且虎患地点甚为广泛。比如咸平年间(998—1003)江阴人陈思道“丧父,事母兄以孝悌闻”,在母亲去世以后,“结庐墓侧,日夜悲恸”,“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6]13396;宋代杜谊,台州黄岩人,在父母坟前“茇舍墓旁”存在“虎狼交于墓侧”[6]13402的情况。《宋史》其他列传显示虎患出没地点还有:韶州、五原、陕州、五原卑邪州、洪州分宁、鄞之通远乡(据《宋史》卷456、卷323、卷308、卷460)。
《辽史》《金史》也记载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虎患。金代元光二年(1223)十一月“开封有虎害人”[7]544。金大定年间(1161—1189),完颜守道“尝从猎近郊,有虎伤猎夫”[7]1957。《金史》还记载,金宣宗时期(1217—1222),开封地区“有虎咥人”“有虎害人”(《金史》卷16、卷23)。《辽史》记载辽国皇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这些捺钵分为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其中秋捺钵又叫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浇林”[8]374,这也可见虎患的存在。
正史对元代虎患多有记载,南方地区虎患发生也较多。比如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福州连江县有虎入于县治”,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福州白昼获虎于城西”[9]1108。《元史》还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高邮地区“有虎为害”[9]3194。《元史·列女传》记载了各地列女为从虎口中救出亲人而与虎相斗的英勇事迹,这些虎伤人、吃人的地区有余杭地区、建德地区、枣阳地区(《元史》卷201、卷200)。《元史》的其他列传也记载了老虎伤人的诸多事件,这些记载显示老虎出没及虎患存在的地点还有松州、长泰、漳州、饶州路、寿州、颍州、余姚、建宁、信阳(据《元史》卷11、卷197、卷 198、卷200、卷 201、卷191、卷193)。
二、虎患的应对措施
在晋唐宋元时期,面对虎患,官方和民间采取了多种措施。面对虎对人类及其家畜的侵害,被侵害者多采取了应急性的捕虎行为。这其中,官府和军营多采取了射杀的应对办法。而民间百姓则有很多是徒手相搏或用手边简单的工具予以驱赶和捕杀。此外,官府面对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还会采取有计划的捕杀行为。
(一)官方的即时性射杀
老虎临时性侵入皇宫及城市区域,官方发现后予以就地格杀,以免老虎伤人。与平民百姓不同,官府和军营往往有射击武器,所以面对老虎的入侵,一般采取的是射杀的方式,这显示出远距离捕虎的优势。这些记载对地方官吏及军士的勇武、忠君为民精神予以赞扬的立场是可以明晰的,反映了封建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比如,太和年间(227—233)有将军杨大眼为荆州刺史,其时“北淯郡尝有虎害”,杨大眼“搏而获之,斩其头悬于穰市”[1]1635。《魏书》还记载了穆崇的第四子穆顗的事迹,将军穆顗“曾从世祖田于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获之”[1]675,世祖对此大为赞扬。
在唐代,建中三年(782)九月“虎入宣阳里,伤人二,诘朝获之”[5]923;唐代大历四年(769)八月“虎入京师长寿坊宰臣元载家庙,射杀之”[5]923。
宋元时期也不乏官方即时性捕杀入侵人类领地老虎的情况。《宋史》记载:绍兴二十年(1150),在海州地区“有二虎入城,人射杀之”[6]1452。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在杭州,大白天有老虎进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6]1451。宋代向宝,其勇猛曾被宋神宗称赞为“飞将”,以之比于薛仁贵,年少即“善骑射”,及成年便以勇闻名,曾“有虎踞五原卑邪州,东西百里断人迹,宝一矢殪之”[6]10468。《金史》记载,泰和八年(1208),“八月乙酉,有虎至阳春门外,驾出射获之”[7]540。
在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高邮地区有虎为害,完者都“挟弓矢出郊,射杀之”[9]3194。《元史》还记载: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在福州地区,“白昼获虎于城西”[9]1108。元代将军也多有善于射猎者,比如张珪,字公端,张弘范之子,“尝从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军尽哗”[9]4071。
实际上,在生存环境受到挤压的情况下,不仅虎类逸入城市,狼豹等兽类也有逸入城市的情况,官方也是采取格杀的措施。比如《隋书》记载: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门,格杀之”[10]640。唐代永徽年间(公元650—656年)“河源军有狼三,昼入军门,射之,毙”[5]922。
(二)民间驱赶及捕杀
除了官方对虎侵入城市、军营等场所的应急性射杀活动,民间常常徒手驱赶或用简易工具与虎搏斗,以应对虎患。这与普通百姓对专门捕虎工具及射击工具的缺乏有关。此类与虎作斗争的行为,远比一些武将远距离射杀虎类以解决虎患更为困难。据正史记载,民间百姓与入侵老虎作斗争的过程惊险迭出,感人至深。这些记载凸显了官方对百姓孝义精神的表彰。
《梁书》记载了人虎相斗的故事:“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母为猛虎所搏,女号叫挐虎,虎毛尽落,行十数里,虎乃弃之。女抱母还,犹有气,经时乃绝。”[3]648
宋代列女传记中也多有与虎相斗的巾帼英雄,比如彭姓列女“生洪州分宁农家。从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将不脱,女拔刀斫虎,夺其父而还”[6]13478。童八娜,因为“虎衔其大母”,于是她“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为释其大母,衔女以去”[6]13491。
《元史·列女传》记载了浙江余杭女子姚氏救母的事迹,“姚氏,余杭人,居山谷间。夫出刈麦,姚居家执爨。母何氏往汲涧水,久而不至。俄闻覆水声,亟出视,则虎衔其母以走。姚仓卒往逐之,即以手殴其胁,邻人竞执器械以从,虎乃置之而去。姚负母以归,求药疗之,奉养二十余年而卒。”[9]4500另如,至元七年(1270)刘平要到枣阳戍守,当夜宿沙河沿岸,这时“有虎至,衔平去”,他的妻子胡氏“觉起追及之,持虎足,顾呼车中兒,取刀杀虎,虎死,扶平还至季阳城求医,以伤卒”[9]4485。王初应,漳州长泰人,在至大四年(1311)二月“从父义士樵刘岭山,有虎出丛棘中,搏义士,伤右肩,初应赴救,抽镰刀刺虎鼻杀之,义士得生”[9]4451。另在元代泰定二年(1325),漳州长泰人施合德的父亲曾出去耕耘,“为虎扼于田”,这时“合德与从弟发仔持斧前杀虎,父得生”[9]4451。
元代石明三“与母居余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归,觅母不见,见壁穿而卧内有三虎子,知母为虎所害。乃尽杀虎子,砺巨斧立壁侧,伺母虎至,斫其脑裂而死。复往倚岩石傍,执斧伺候,斫杀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张目如生,所执斧牢不可拔”[9]4464。石明三的事迹更显示出虎与人为了生存的殊死搏斗。元代还有一些记载,比如方宁之妻官胜娘,是建宁人,“宁耨田,胜娘馌之,见一虎方攫其夫,胜娘即弃馌奋梃连击之,虎舍去,胜娘负夫至中途而死”[9]4500。
(三)官方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
对于临时性的虎患,人们能即时性予以斗争或捕杀。但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区,比如出现群虎为患的情况,虎患便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严重虎患对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而单个百姓难以应付,这时官方就要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捕虎,有时采取招募人员或悬赏捕杀的方式,甚至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悬赏捕虎的措施。此类捕杀常常作为善政的一种解读。官方是否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捕虎措施,也可以作为考察虎患问题严重程度的参照。
六朝时期,周朗为庐陵内史,庐陵郡“郡后荒芜,频有野兽”,周朗之母薛氏想见识猎兽场面,周朗“乃合围纵火,令母观之”,这时“火逸,烧郡廨”,周朗因猎虎而导致的小型火灾事故“为州司所纠”。周朗是这样对皇帝解释此次围猎所致火灾的:“州司举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负陛下。”[11]2101
《宋书》记载了沈攸之被委任“监郢州诸军、郢州刺史”,曾经“闻有虎,辄自围捕,往无不得,一日或得两三”[11]1931。
在宋代,此类事迹亦不少。比如,开宝五年(972)四月,皇帝“遣使诸州捕虎”[6]38。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6]1451。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虎伤人,诏遣使捕之”[6]1451。李继宣,宋开封浚仪人,乾德年间(963—968)“尝命往陕州捕虎,杀二十余,生致二虎、一豹以献”[6]10144。南宋咸淳九年(1273)十一月,有老虎在扬州市出现,“毛色微黑,都拨发官曹安国率良家子数十人射之”[6]1452。
《金史》记载道:元光二年(1223)“十一月,开封有虎害人”,“白日虎入郑门”[7]544;金宣宗时期(1218—1223),“开封县境有虎咥人”,宣宗“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7]368。实际上,宋辽金时期,对于其他猛兽比如群狼为害的情况,也有这种悬赏捕杀的情况。比如在金宣宗时期“陕州群狼伤百余人,立赏募人捕杀”[7]337;宋开宝八年(975)四月,“平陆县鸷兽伤人,遣使捕之,生献十头”[6]1450。
《元史》规定了官方有关捕虎的规定:“诸有虎豹为害之处,有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之。其中不应捕之人,自能设机捕获者,皮肉不须纳官,就以充赏。诸职官违例放鹰,追夺当日所服用鞍马衣物没官。诸所拨各官围猎山场,并毋禁民樵采,违者治之。诸年谷不登,人民愁困,诸王达官应出围猎者,并禁止之。诸田禾未收,毋纵围猎,于迤北不耕种之地围猎者听。……诸年谷不登,百姓饥乏,遇禁地野兽,搏而食之者,毋辄没入。诸打捕鹰坊官,以合进御膳野物卖价自私者,计赃以枉法论,除名不叙。”[9]2686《元史》还记载了诸多元代官方组织捕虎的事迹。比如别的因的事迹。别的因“身长七尺余,肩丰多力,善刀舞,尤精骑射,士卒咸畏服之”,元世祖任命别的因为寿颍二州屯田府达鲁花赤,当时寿颍二州有“虎食民妻”的状况,别的因采取的是诱捕方法,“乃立槛设机,缚羔羊槛中以诱虎。夜半,虎果至,机发,虎堕槛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顿息”,其后在至元十三年(1276),别的因又被授信阳府达鲁花赤,当时“信阳亦多虎”,“别的因至未久,一日,以马裼置鞍上出猎,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别的因以裼掷虎,虎搏裼,据地而吼,别的因旋马视虎射之,虎立死”[9]2994-2995。元代初期大将完者都,曾在福建等处征讨漳州“聚党数万”的陈吊眼,而立有大功,后被授高邮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当时高邮路“有虎为害,完者都挟弓矢出郊,射杀之”[9]3194。又比如,元世祖十八年(1281)秋七月庚戌,“以松州知州仆散秃哥前后射虎万计,赐号万虎将军”[9]232。
上述记载说明了,晋唐宋元时期,面对虎患,官方、民间都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驱赶、射杀,或予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捕杀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射杀、围捕、布置陷阱、火烧、徒手搏击等方法都有使用。这是针对虎患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正史对虎患问题的伦理性和生态性解读
(一)伦理性解读
虎与人各有各的生存空间。虎患的解读本应该从虎类与人类之间生存空间的争夺这个方面来认识,本应注重考察虎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人与虎之间和谐共处的程度。但正史记载对虎患解读的角度却主要是伦理性的。
从记载来看,对虎侵入人类生活领地以及伤人的记载主要在正史的三个部分。一是在《五行志》里,把虎的入侵及伤害人畜的行为作为阴阳五行失调的一种表现,很少对虎类生存环境的变化作分析;二是在帝王和大臣的传记里,通过记载帝王和大臣对虎患的反制措施的描述,来为他们的善政、英勇、贤能、才干作论证;三是在《孝义列传》和《列女列传》里对此类英勇斗虎事迹的描述,此类记载描述了在斗虎事件中媳妇对公婆、儿女对父母的保护,以生动的案例来对中国传统孝道作出表彰。
不仅在斗虎事件中是一种伦理性视角,而且,对“虎不为患”事件的记载也凸显了伦理性因素。本来,极度饥饿,鹿类等食物来源的减少,对人类的恐惧和敌视,均会增加虎类攻击人的概率。反之,虎对人的攻击概率会降低。但正史不是从这些方面解读“虎不为患”的情况,而是从宗教、道德方面解释这种现象。
第一,宗教的角度。虎患是自然灾害的一种,当人们对自然灾害无力抗衡或处理措施达不到预计效果时,人们常常会考虑到宗教的力量。实际上,正史中多有宗教修行者凭借着自己的道德修为而导致“虎不为患”的情况,并且,在此时期官民也有利用宗教祈祷作为消弭虎患的辅助措施。有记载指出高僧修行过程能与虎相伴。比如禅宗六祖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12]5110。道教中也有与虎为伴的修道高人,比如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至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左右,传而至张清志,“其教益盛”,在其传道期间,“东海珠、牢山旧多虎,清志往结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颇为人害。清志曰:‘是吾夺其所也!’遂去之”[9]4529。《宋史》记载:孔旼,是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居山未尝逢毒蛇虎豹”[6]13435。存在为消弭虎患而对山神祈祷的情况,这与人们在水旱灾害发生时对神灵的祈祷具有共性。比如唐代进士顾少连“以拔萃补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连命塞陷阱,独移文岳神,虎不为害”[5]4994。元代有因祈祷山神而帮助虎患消弭的记载,皇庆初,天璋为归德知府,后改授饶州路总管,有向上级请示救灾之先即及时发廪赈民饥使得“民赖全活”之善政,其治理期间,“鸣山有虎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获之”[9]4362。
第二,道德修为的因素。“虎不为患”与虎是凶猛野兽的特征不符。虎具有主宰人间善恶的另一文化意蕴,似乎可解释这一矛盾。正如黄志繁先生在研究明清南方地区虎患问题时所揭示的,在传统社会应付自然灾害时的心态是“民众道德水平的提升与官府政治修明乃是应付自然灾荒之根本”[13]。这种用道德教化的观点来解读虎患的情况同样适应于晋唐宋元时期。这方面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两类人群:一是贤良官吏;二是孝子,都是道德修为很高的人。前者反映传统政治倡导仁政的治国理念,后者是孝道感动万物的体现。地方官吏的善政会对老虎也有所感化,而出现“虎不为患”的情况。比如《梁书》记载了因受良吏之仁政感动而虎害绝迹之事,比如良吏孙谦的事迹。天监六年(507)孙谦出任零陵太守,“先是,郡多虎暴,谦至绝迹”,而在孙谦离任的那天夜晚,“虎即害居民”[3]773。
此外,人们若着意道德修行,或推行孝义之道,也会感化老虎从而出现“虎不为患”的情况。此类记载不少。比如,北朝刘仕儁,彭城人,在母亲去世后“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列植松柏,虎狼驯扰,为之取食”[2]2838;《梁书》记载了庾黔娄这一大孝子的事迹,黔娄常为人讲诵《孝经》,在所治理之县“先是,县境多虎暴”,但黔娄来了以后“虎皆渡往临沮界,当时以为仁化所感”[3]650;《梁书》还记载了南朝梁时期桂阳郡王王象,王象“事所生母以孝闻”,其为湘州刺史治理湘州时,“湘州旧多虎暴,及象在任,为之静息,故老咸称德政所感”。史家因此作评曰:“桂阳王象以孝闻,在于牧湘,猛虎息暴,盖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3]364-365
唐宋时期也常描绘孝子不为虎豹所伤的事情,以作为孝道文化应该通行的例证。唐代张士岩是大孝子,对父母孝行颇多而感人,并且“父亡,庐墓,有虎狼依之”[5]5578。宋代孝义之人也被记入了正史,比如杜谊,在父母坟前“茇舍墓旁”“日一饭,不荤。虽虎狼交于墓侧,谊泰然无所畏”[6]13402;《宋史》还记载:宋太宗期间,江阴人陈思道是大孝子,在母亲去世以后,“结庐墓侧,日夜悲恸”,此种孝道甚至感动了虎豹,即“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6]13396。又如宋代进士李访的孝义之事,李访“庐父母墓,有虎暴伤旁人而不近访”[6]13404。
(二)生态性解读
从正史对虎患记载的特点以及对虎患发生与否的解读,可以看出主要是伦理性的角度。但即便如此,对史料仔细研读,也可看出此时期虎患之状况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虎患的发生是人的生存空间与虎的生存空间发生冲突所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因素是人类行为所致。
首先是人类活动挤占虎类生存环境。从森林角度考察,我国森林资源在远古时代极为丰富,最高时期森林覆盖率可达64%[14]。随着历史的发展,森林资源渐趋减少。到战国末年,森林覆盖率约为46%;到唐代末期降为33%;到明初为26%[15]。唐宋以来,密集性、掠夺式开发使得人与虎的缓冲地带的杂林木变少,老虎的生境遭受破坏,生态失衡,虎患灾害趋于严重。这种情况有直接的例证,比如皖北沿江的桐城地区,在开元(713—741)年间迁徙治所,迁到山区地带,而此山区“地多猛虎、毒虺”,人虎冲突在所难免,最后结果是人类经济开发活动取得胜利:在元和八年(813),“令韩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5]1054。
其次,人的生存空间与虎的生存空间发生冲突还有一种情况,即虎受到人类捕杀。唐宋以来,官方多次派遣专人捕杀为害之虎的状况,如唐开宝五年(972)四月丙寅,“遣使诸州捕虎”;宋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虎伤人,诏遣使捕之”。《魏书》曾记载了高宗好猎之习。朔方人宿石,曾经跟随高宗射猎,“高宗亲欲射虎”,宿石对高宗以危险为由予以劝阻,高宗在高处观看时,果见“虎腾跃杀人”之情景[1]724。《魏书》记载太和二年(228),“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1]1988,此时幸亏有王叡击退此虎。后周世宗期间,世宗好猎,宋偓是射虎好手,曾射虎救世宗:“世宗尝次于野,有虎逼乘舆,偓引弓射之,一发而毙。”[6]8906
虎患的发生还与自然灾害等生态因素有关。比如,苻健僭称大秦天王期间,“关中大饥,蝗虫生于华泽,西至陇山,百草皆尽,牛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断绝”[1]2074。苻健死后,其子苻生僭立,苻生掌权期间,“虎狼大暴,从潼关至于长安,昼则断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杀七百余人,民废农桑,内外忷惧”,由是官吏向苻生奏请禳灾,苻生却言“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终不累年为患也”[1]2075。此记载以显示苻生昏庸为意旨,但虎因饥饿食人的状况也可想见。王朝易代之际土地荒芜,人类一些开发地带因荒芜而杂草丛生,也为老虎的占据及虎患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也体现了虎患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比如元代皖北的虎患即有此情况,《元史》记载了别的因捕虎的事迹,元世祖任命别的因为寿颍二州屯田府达鲁花赤,当时寿颍二州有虎食民妻,即是“地多荒芜”[9]2994的生态背景。
总之,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日益严重之势有着多方记载,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虎患问题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从伦理层面进行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的重视与推崇。当然,虎患的严重态势也反映了人类生产活动与虎类生存环境的竞争与冲突。
[1]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1635.
[2]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74.
[3]姚思廉.梁书[M].中华书局,1973.
[4]萧子显.南齐书[M].中华书局,1972.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
[6]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77.
[7]脱脱.金史[M].中华书局,1975.
[8]脱脱.辽史[M].中华书局,1974.
[9]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1976.
[10]魏征.隋书[M].中华书局,1973.
[11]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
[12]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13]黄志繁.“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143-160.
[14]马忠良,宋朝枢,张清华.中国森林的变迁[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121-122.
[15]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4):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