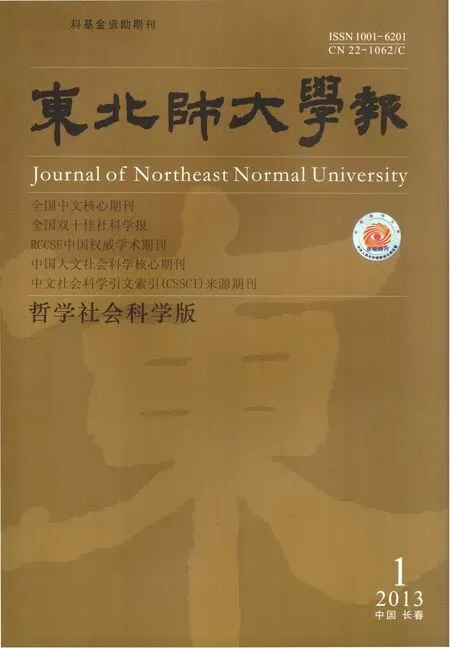叶适道器合一思想与其发展的文学观
郑 慧,张恩普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叶适(1150-1223),曾获得“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的盛赞。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的永嘉学派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全祖望在《水心学案》按语中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叶适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以物为本的道器合一思想,坚持以发展的思想看待文学问题,以“尊古不陋今”的视角提出了文学理论的诸多观点。比其稍年轻一些的诗人“永嘉四灵”就是在叶适的提携、奖掖下,在南宋前半叶的诗坛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足迹。同时,从叶适对“永嘉四灵”的态度表现中,也再次体现了叶适发展的文学观。
一
叶适作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对当时盛行的理学家提出的某些唯心的论点有很多不同看法,他虽然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晚年罢官退居故乡水心村的16年(1208-1223)时间写定的《习学记言序目》一书,记录了他对哲学问题的一些看法。他提出了以物为本的道器合一思想。叶适认为,关于宇宙是什么,回答很简单,就是“物也”。世界就是物质存在并充满着物质的世界。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1]699宇宙之中,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物的不同存在形式、表现形态,“物”乃是客观世界存在的第一性的东西,物具有统一性,有“物之理”,即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他认为所谓的“理”属于客观事物本身或所谓的“物”自身之“理”,是“不失其所以一者”,而物又有区别,统一的物质世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客观世界乃是形形色色的各有其特殊性,即“情”的物的存在总体,这就叫做“物之情”,不论其如何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却都有着“不是其所以一”的“物之理”,也就是物的“一而有不同”。在道与物的关系上,叶适认为道器合一,道在器数和事物之中,反对离开器物而谈论所谓的“形而上”之道。叶适所说的“道”,主要是指事物变化的经验法则和制造器物的技术原理。他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1]697因而,理学认为的道与物统一在道的基础上的观点就是在物之外空言道,从而成为虚空的理论思想。叶适的观点与之相反,他反对离开物空谈道理,要指物所言,以物为本。因为“道”作为世界最高的统一性原理,与“物”之间形成了原理与实体的关系,因而叶适指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2]702他针对理学的观点,指出了“道”是要依存于物才能存在的,没有不依存在物之上而独立存在的道。
叶适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主张要“验于事,考于器”,通过“考详天下事物”来求得“道”和“理”。“考详天下事物”以事物为前提,站在了理学以心性为前提的对立面,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的认识论,是道器合一思想在认识论上的表现。肯定道在物中,是认识的前提。叶适认为,人的认识首先来源于客观世界,人通过耳目之官接触外物从而获得感觉、知觉,“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1]614就是说,认识的来源和对象是客观世界和具体事物,要认识天下万物及其规律,就必须于物求知,要依据事物的真实面貌来反映事物,通过考察天下万物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来论证事物,也没有离开万物的先天固有的虚知、空知。然后通过思维器官的思考将外界的、从客观世界所得来的认识进行加工而成为知识,即“自外入以成其内”与“自内出以成其外”的内外结合,“内外交相成”而取得知识。所谓的“内外交相成”就是叶适所提出的耳目与心官并用:前者所得为见闻之知,后者所得为义理、心性之知;前者相当于感性认识,后者相当于理性认识;前者自外入内,后者自内出外;二者交互作用,沟通心与物的联系。叶适说:“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2]207
叶适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是八物,气又是构成八物的根源。他说:“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而义理生焉,故曰卦”[1]696。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八物其实是“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并且不断地“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这是说八物是由于阴阳二气的互相摩荡,有开有合而产生的,而八物最终又生化为气,故“其卒为化”。“气分阴阳”就是说,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永远都是一分为两,永远也不会有绝对单一的东西,叶适认为“凡物皆两”,他说:“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交错纷纭,若见若闻,是谓人文。”[1]732就是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形状、性质都是由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组成的,这种“交错纷纭”的状况,就叫做“人文”。这种“一分为两”,“所以通行于万物之间,无所不可,而无以累之,传于万世而不可易”[1]732是普遍的,又是永恒的。因为“凡物皆两也”,所以叶适认为:“天下不知其为两也久矣,而各执其一以自遂。”[1]732这种片面的思想,片面的思维方法就是只见一面,不见对面,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种思维方法的结果是“天道穷而人文乱也”。叶适在看到“凡物皆两也”的同时,还指出了“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是导致运动的内部原因,万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因而叶适说“万物皆变”,无一例外。
二
叶适的道器合一思想对其发展的文学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其发展文学观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渊源。叶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运动与相对的静止所构成,在这种哲学观点的指导下,他形成了尊古又不陋今、强调发展的诗学观点。前文引用的“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来说明他的唯物主义倾向的两句话,恰巧出自他的诗论。古诗到了周代能开始流行,是因为存在于物中的理是不可乱的。人们通过物之情,认识物之理,而对事物细致描绘充满了物之情的诗歌,自然就成了可以解释物之理的手段了。叶适总结了古代至当时的整个诗歌发展历史,指出:“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作不作,不系《诗》存亡,此论非是。然孔子时人已不能作诗,其后别为逐臣忧愤之词,其体变坏;盖王道行而后王迹著,王政废而后王迹熄,诗之废兴,非小故也。自是诗绝不继数百年。汉中世文字兴,人稍为歌诗,既失旧制,始以意为五七言,与古诗指趣音节异,而出于人心者实同。然后世儒者,以古诗为王道之盛,而汉魏以来乃文人浮靡之作也,弃而不论,讳而不讲,至或禁使勿习;上既不能涵濡道德,发舒心术之所存,与古诗庶几,下复不能抑扬文义,铺写物象之所有,为近诗绳准,块然朴拙,而谓圣贤之教如是而止,此学者之大患也。”[2]700-701诗歌的体制由古至今发生了诸多变化,“旧制”一次次地被新的形式所替代,然而,古今之诗,虽“指趣音节”不同,“而出于人心者实同”。从这一点上来说,古今之诗应是具有同等价值意义的,不应当象理学家认为的“古诗为王道之盛”。因此叶适对于“自古乐府至本朝诗人,存其性情之正、哀乐之中者,上接古诗,差不甚异,可与学者共由”[2]701的做法十分赞同。
叶适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诗歌的发展,就是对不同时期的各家各派的诗歌都能发现其中的价值,“后世诗,《文选》集诗通为一家,陶潜、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各自为家,唐诗通为一家,黄庭坚及江西诗通为一家。人或自谓知古诗,而不能知后世诗,或自谓知后世诗,而不能知古诗,及其皆知,而辞之所至皆不类,则皆非也。韩愈盛称皋、夔、伊周、孔子之鸣,其卒归之于诗,诗之道固大矣,虽以圣贤当之未为失,然遂谓‘魏晋以来无善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乱杂而无章’,则尊古而陋今太过。”[2]701这里对于只尊古诗而鄙今诗,和只学今诗而轻视古诗的做法都给予了批评,认为这样做都是不全面的做法。宋人学诗,以学习白居易、姚贾、李商隐为开端,形成了江西诗派,但最后还是将目光投向晚唐,这一过程恰恰符合了叶适所提倡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观,他认为万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他说:“时常运而无息,万物与人亦皆动而不止。”[1]156因此,诗歌风格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古体诗、律体诗,江西诗派、晚唐体,这些都是诗歌发展的客观表现。在律体诗“朽败之余”,江西诗派起而弥补其“缺绝之后”,事物的永恒运动没有穷尽,晚唐体又因纠正江西诗派而流行起来。新事物不断地产生,代替旧事物的存在。叶适的运动发展观很好地表现在了对诗歌理论的探讨方面,因而他不拘泥于某一诗歌阶段,在当时江西末流盛行时,提倡“永嘉四灵”的晚唐诗风以纠正江西的流弊,而在晚唐诗流行之际又能及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四灵”反对理学诗派的“尊古”诗学观,“情”被“理”所统辖,音乐美、形式美被枯燥的说理所代替,失去了诗歌的情韵美。他们与理学化诗风相抗争,力图突破诗歌的功利性,重新光大诗歌缘情、言情的特征。“四灵”以律体诗反对理学家提倡的古体诗,坚持“苦吟”精细的雕镂诗歌。叶适的门人吴子良曾说:“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徐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诗,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3]76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把四灵看作是叶适的门人,叶适支持四灵,有其哲学思想上的根源。他重世务,重功利,重外物的永嘉之学与程朱理学相对立,这就决定了他的诗学思想与如朱熹等正宗理学家是截然不同的。元人刘埙在《隐居通议》中提到:“永嘉有言:‘洛学起而文字坏。’”即认为理学家重道轻文的理论,妨碍了文学的发展。江西诗派后学多与理学家有联系,有的本身就是理学家,他们以理学的诚心正意、穷理尽性为根本,加上黄庭坚的心性思想为宣传理论,借助江西诗派以文为诗的形式,导致了诗道式微。因此,叶适对江西诗派提出的批评,也是对理学摧残文学的否定,对恢复文学本真的审美价值的努力。明代学者徐学聚《两浙名贤录·赵师秀传》中说:“自乾、淳以来,濂洛之学方行,诸儒类以穷经相尚,诗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律吕相宜也。潘柽出,始创为唐诗,而师秀与徐玑、翁卷、徐照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4]129这里同时也指出理学家“取足而止”忽视“声病律吕”的文艺观点,四灵兴起唐体与学术思想界对理学的反拨联系到了一起。叶适宣扬四灵的主张也同他哲学上与理学的争论桴鼓相应。
三
叶适发展的文学观也体现在对“永嘉四灵”的具体评价上。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因其字号里都带有一个“灵”字而被合称为“永嘉四灵”。他们生活于12至13世纪的南宋永嘉地区,彼此旨趣相投,诗风相似,《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佑,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5]217在针对江西诗派流弊而进行的诗风改革过程中,诗人们不断探索,发现了晚唐诗歌的别样味道,诗人杨万里的《读笠泽丛书》有:“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的诗句。四灵诗派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钱钟书先生说:“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6]因此,“永嘉四灵”反对江西、提倡晚唐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迹可循。
虽然,在众多的以革新江西诗风为己任的诗人群体中,“永嘉四灵”只是不怎么起眼的一股小力量,但是,历史却给了他们一席之地,因为在光宗朝以后踏上诗坛的“永嘉四灵”,在以晚唐体纠正江西诗派的流弊的同时,也对晚唐诗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晚唐体”有光大之功。叶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写道:“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1]490“永嘉四灵”在青年时期互相进行着文学的交流,从叶适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期,江西诗派已坠入“连篇累牍,汗漫无禁”的末流之中,影响力所剩无几,“永嘉四灵”继承了中兴诗人们以学晚唐来纠正江西诗风流弊的道路,深入发掘,许棐说“永嘉四灵”的诗为“玉之纯、香之妙者”,正是针对江西的破律、拗律,“永嘉四灵”以“浮声切响”的传统,以音律和谐为诗之规范,不断地通过锻章琢句的努力,“语遂极其工,唐诗由此复行”。可见,“永嘉四灵”把对于晚唐诗的学习落到了实处,在倡导晚唐诗风的过程中十分用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宋代诗歌经历几代人的探索开拓,形成独立于唐诗的风格体制,是诗歌合理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其存在有自身的价值和理由,同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偏颇与缺失,于是才有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与改革的途径。叶适与“永嘉四灵”所选择的道路从本质上动摇了宋诗形成的主流的传统,向唐音回归为宋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在江西诗派的作品已经为人们所厌倦之后,四灵以自身诗作的清新秀丽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诗坛可谓“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7]然而,这种新鲜也不是永恒的,加上“永嘉四灵”诗作取境狭窄的缺陷,人们也对其感到单调乏味了。赵汝回《云泉诗序》曾指出:“世之病唐者,谓其短近,不过景物,无一言及理。”说明了“永嘉四灵”偏重写景而很少关注人心灵的感受。叶适对于这种缺陷并非无动于衷,对此,他起初认为是扭转江西诗风的无拘无束的特色,有鼓励的意味,他曾说“然则所谓专固而狭陋者,殆未足以讥唐人也”[1]490,但叶适后来又对四灵的诗作表现一些不满:“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1]221他对唐诗的一些不足已经有所认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了宋诗重视人格道德的内在之志风格的影响。这说明叶适对唐体的缺陷是十分清楚的,对唐诗和宋诗特质的把握相当精辟中肯。
总之,叶适道器合一思想是其文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依据,他的发展的文学观与当时的文学环境相结合,就自然会发现“永嘉四灵”的优长与不足,所以在南宋的文坛上才能因叶适的影响而留下“永嘉四灵”的一席之地,同时,在其谈论“永嘉四灵”的话语间也使他的诗论与学术思想再次得到了统一。
[1]叶适.叶适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吴子良.林下偶谈[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76.
[4]徐学聚.两浙名贤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7.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2:254.
[7]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