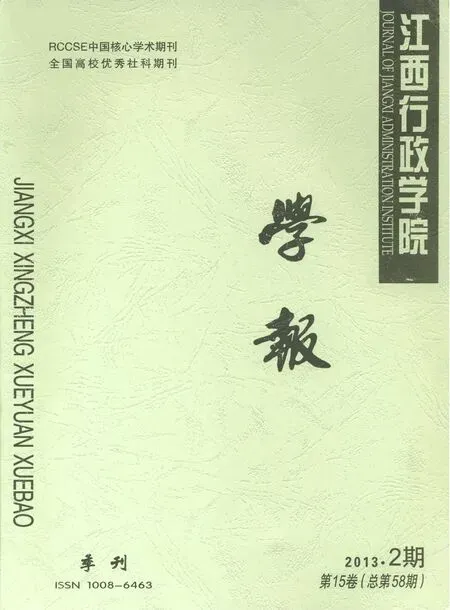论仲裁裁决的既判力
杨朝晖,漆世濠
(1.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一、既判力理论概述
(一)既判力的概念。
“既判力”一词乃从英美法系中“Resjudicata”之概念直译而来,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Resjudicata”指生效的判决可以阻止当事人就“本应在前诉中提出而未提出的事项”再行提起诉讼(“merger”or“bar”),或者阻止当事人就“前诉中已经审理过的事项”再行提起诉讼(“collateral estoppel”)。在大陆法系的诉讼法理论中,既判力的问题实际上是指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包括两方面的效力:其一为消极效力(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即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不能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主张[1](P115),该制度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代“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其二系指生效判决的积极效力(对法院的拘束力),即后诉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须遵循先诉法院对特定事实之判决,无权推翻。
(二)判决的既判力与预决力。
判决的既判力和预决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是关于预决力而非既判力的规定,该条文赋予法院判决的免证效力,若无反证推翻,后诉法院应遵循生效判决。实践中,既判力和预决力对后诉的影响较为一致,且均有助于避免矛盾裁判、维护司法权威、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两者之间仍存在差异。首先,预决力只具有“相对的免证效力”,可以被其他证据推翻,而既判力则要求后诉法院必须遵循,不可违背;其次,仅判决主文之内容具有既判力,而判决主文以及判决理由均可作为免证事实而具有预决力;最后,对于既判力,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查,并须遵循之,而预决力则需有当事人主张援用,且若有相反证据推翻,法院可作出不同之认定。[2](P102)同时,该条文也将生效仲裁裁决列为免证事实,赋予其预决力。
(三)我国现行立法对仲裁裁决既判力的规定。
我国《仲裁法》第9条第1款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款实际上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概括性规定,明确了仲裁裁决的消极效力(即对当事人的拘束力)。
但是我国立法对仲裁裁决的积极效力(即对仲裁机构、法院的约束力)则没有进行规定。有的学者主张,当已经受到既判力消极功能排除的争议再次成为裁判对象时,仲裁庭或者法官都不得受理,因此,也就没有作出矛盾裁判的可能。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当第二次起诉被“一事不再理”原则阻却时,根本不会进入到实质性审理阶段,因此固然不存在仲裁裁决积极效力的问题。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后案虽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诉讼请求和理由均有不同(如继续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分别就对方不同的违约事实先后提起诉讼),或基于相关联的法律关系(如“合同链”中三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显然不能因“一事不再理”原则排除,在此情况下,讨论仲裁裁决的积极效力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仲裁裁决的既判力
在国际贸易发展之初,由于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封建法和教会法不能适应跨国贸易的发展,因此商人们就试图脱离国家控制,自治地确立跨国贸易的规则并在国家法院体制外解决商人之间的争议,逐渐发展出了以意思自治、效益公正为基石的仲裁制度[3](P329)。时至今日,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制度本身特有的性质和价值。笔者认为,承认仲裁裁决的既判力,尤其是肯定其积极效力,是维护仲裁制度自身性质、追求仲裁制度基本目标、推动仲裁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的核心,也是仲裁裁决既判力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根据国内法须服从法院的管辖权;而在当事人通过协商一致积极选择仲裁时,可以推断他们一方面更加偏好仲裁机制的优点,并欲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另一方面他们也默认仲裁机制解决纠纷的有效性,并赋予仲裁裁决类似于法院判决的拘束力。因此,当事人必须遵守仲裁裁决的内容,同时为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满足其选择仲裁的目的与动机,审理后案的法官或仲裁员也必须受生效仲裁裁决拘束,否则将使当事人的合意选择化为一纸空文,也极大削弱了其他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动机。在19世纪早期,持契约论的学者甚至认为仲裁裁决是当事人假仲裁员之手制订约束自己的协议,其以当事人的意志为基础,因此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强制执行。[4](P327)虽然该理论由于过于极端最终被摈弃,但是承认意思自治在仲裁制度中的核心地位,进而确认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二)追求效率。
法院判决既判力理论的目的之一为节约司法资源、促进争议一次性解决,这与仲裁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是不谋而合的。从仲裁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产生的动因即在于排除程序僵硬、耗时较长的法院审理程序,并设立一种更加便捷、灵活的争议解决程序。但是在法律实践中,不可否认的是仲裁程序的效率已经大打折扣,由于仲裁规则中对于证据提交以及仲裁庭审理等期限规定不严格,且当事人有权自主约定仲裁程序,一些复杂的案件通常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裁决,其耗时甚至远远超过诉讼程序。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肯定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是维持仲裁制度效率价值的重要因素。
(三)灵活专业。
相比诉讼程序,仲裁规则中对审理期限、证据规则的规定均不严格,而且允许当事人灵活改变,因此,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对于证据的审查以及对案件真实情况的判断,实际上优于法院审理。有的学者认为很多时候仲裁裁决仅仅是折中各方权益的结果,并不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应承认其既判力,但是笔者认为,当事人选择仲裁之重要理由即为其实体上以及程序上的灵活性,而且实践中这种折中的裁决往往能使得双方当事人都满意,因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意选择及其对仲裁裁决的善意信赖,更应承认仲裁裁决的既判力。
除此之外,仲裁员常常是法律专家或与案件相关的特殊领域的专家,而相比之下法官往往仅专于法律领域,可见,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可能更加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因此,承认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也是尊重案件事实、尊重客观科学的必然要求。
(四)准司法性。
我国《仲裁法》等相关立法确认了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赋予了仲裁准司法的地位。尽管仲裁与诉讼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是生效的仲裁裁决和生效的诉讼判决在确定争议法律关系上却是一致的[5](P276),例如在继续性合同引起的仲裁中,当事人接受仲裁裁决后基于对其权威性的信任而按照裁决书中确认的方式继续履行合同,若嗣后再发生争议,不承认前一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后果。因此,承认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有助于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以及仲裁机制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五)鼓励仲裁。
随着《纽约公约》在我国生效,以及《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仲裁已经成为法院审理之外最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仲裁法》第28条、第46条、第62条等条款分别从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裁决执行的方面对仲裁制度予以支持,并严格限制法院撤销、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可见我国的政策是鼓励仲裁的。为贯彻该政策,有必要确定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一方面,法院需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仲裁制度发展至今,已不是诉讼程序的附庸,其本身有相当独立之机制,如法院审理时可以自己之判断排除生效仲裁裁决的裁定,将严重危及仲裁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仲裁庭也需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以维护制度本身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促使更多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
三、仲裁裁决既判力的适用范围
(一)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人的范围,是从诉讼主体的角度分析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在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判决的既判力仅仅及于当事人,原因是第三人并未参与原程序,为保护第三人的诉权,应限制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但是有学者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基于对“程序经济”、“权力关系安定”等因素的考虑,既判力应扩张于第三人[6](P4)。笔者认为,为保护第三人的诉权,仲裁裁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严格限于当事人之间,不能扩张于第三人,原因有二:其一,仲裁程序的启动需以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若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即第三人并不愿意通过仲裁来解决与其有关的纠纷,那么将仲裁裁决强加于第三人无疑是不公正的;其二,即使第三人与一方甚至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仲裁协议,但是由于在前一个仲裁程序中,仲裁员和仲裁程序均由当事人自主决定,第三人无法预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也不应及于第三人。因此,后案中之第三人仅可基于仲裁裁决的预决力以免除自己对仲裁裁决中确定的事实的举证责任,且对方当事人可以举证推翻之。
仲裁裁决的既判力若及于第三人,极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现象。如甲与乙、乙与丙分别签订了仲裁协议,且三者处于“合同链”之中,如果仲裁裁决的既判力及于第三人的话,那么当事人(乙、丙)之间的仲裁将受制于非仲裁协议当事人(甲)的行为,同时,一方当事人(乙)仅仅需要向仲裁协议之外的第三人(甲)提起仲裁就可能规避当事人(乙、丙)之间仲裁带来的不利后果,这都不利于三方之间实质正义的实现。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随着国际商业交易日趋复杂,多方当事人、连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关联公司等复杂的法律关系频频出现,而我国的仲裁法以及相关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都未纳入仲裁第三人制度,这严重地影响到了争议解决的彻底性和快捷性,与仲裁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背道而驰。在实践中,仲裁员审理“合同链”的几个不同仲裁时,一般会尽量作出前后一致的裁决,以维护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彻底解决当事人争端。但在理论上,仲裁裁决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还是难以解决,目前较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在当事人与第三人的仲裁协议中约定第三人将受当事人之间的仲裁裁决约束的条款。
在美国的HRHConstructionCorp.v.BethlehemSteelCorp.案中,开发商(A公司)与总承包人(B公司)之间,总承包人与次承包人(C公司)之间均签有仲裁协议,且在B、C的仲裁协议中,双方特别约定“任何对A、B之间争议的作出的任何裁判对B、C之间都有约束力(anyissuedetermined betweenAandBwouldbebindingonBandC)”,纽约州上诉法院认为,该特殊规定是对仲裁员的一种指示,并使得A、B之间的仲裁裁决对之后进行的B、C之间的仲裁程序具有约束力,这种约定并未违反制定法、亦不与公共政策相悖,因此没有理由不依照其执行。[7](P45)因此,为维持仲裁裁决一致性,确保当事人(特别是合同链的当事人)之间的争端得到彻底、公正的解决,应鼓励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加入这种特别规定,使在后的仲裁需受到先前的利害关系人之间仲裁裁决的拘束。
(二)仲裁裁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在大陆法系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仅及于判决主文部分,法院对诉讼标的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裁判,而于判决书其他部分阐述之判决理由等则不具有既判力。为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机能、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日本学者新堂幸司借助英美法系的禁反言规则,发展出“争点效”理论,即前诉法院对当事人主要争点的判断对后诉均具有约束力,不再限于判决主文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江伟教授和肖建国博士主张借鉴之,但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尚未被采纳,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界也以传统见解为通说。
笔者认为,仲裁裁决之主文部分与判决一样,均具有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终局效力,应具有既判力;同时,基于对仲裁制度合意性、灵活性、专业性等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在仲裁领域率先“引入争点效”理论。理由有二:其一,仲裁程序具有灵活性和专业性,其在事实认定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其理由阐明部分也较具说服力;其二,当事人合意选择仲裁之时,其内心对仲裁机制以及仲裁裁决的认可度是高于法院判决的,并意欲通过仲裁裁决约束彼此。因此,赋予仲裁裁决事实及理由部分以既判力,既满足当事人主观意愿的需要,也反映了仲裁制度的内在优势。此外,在有约定的情况下,法院或仲裁员可以赋予仲裁裁决超出传统理论范围之外的既判力,因为仲裁之核心即在于意思自治,应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仲裁裁决既判力的范围。[8](P35)
(三)具有既判力的仲裁裁决。
仲裁中的裁决主要有全部裁决、中间裁决、临时裁决、部分裁决、追加裁决、和解裁决这几种类型。其中,全部裁决、部分裁决和追加裁决具有终局效力,应当具有既判力;我国《仲裁法》对中间裁决和临时裁决未进行规定,有学者认为中间裁决是针对有关程序问题的裁决,2012新修订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规则第21条规定:“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可以程序令或中间裁决的方式作出。”在此情形下,中间裁定仅确定程序性事项,不具有解决实体问题的终局效力,因而不具有既判力。值得注意的是和解裁决,这种裁决虽然有终局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但是在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可能利用仲裁机构的调解或和解机制,获得使双方受益而使国家利益受损的生效裁决,或者利用仲裁裁决书这一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和裁决结果对抗初审法院的判决,以谋求其在上诉审中的胜诉[9](P55-63),在此情况下应当慎重认定和解裁决的既判力。
此外,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应当撤销或不予执行的仲裁裁决的情形,这些裁决由于程序严重违法等原因而具有瑕疵。但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种情形以外,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均需依当事人的主动申请,且均有时间限制。因此,在该期限未过之前,若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发现了已生效的瑕疵仲裁裁决,应允许当事人提出撤销或不予执行裁决的申请,同时中止诉讼或仲裁程序;若期限已过,则该仲裁裁决应具有既判力,得以约束之后的程序。而当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有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仲裁裁决时,得直接依职权撤销之,不受该仲裁裁决之约束。
四、结语
诉讼和仲裁都是解决民商事纠纷的程序,且具有一些相同的价值追求,如效率、公正等,不同的只是这些价值在各自体系中的位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诉讼程序中的一些有助于实现仲裁制度价值目标的优点,应当将其引入仲裁制度中来。
既判力理论追求解决纠纷的高效性和彻底性,并维护裁判的权威性,节约司法资源,避免矛盾的裁判,这些价值追求与仲裁制度的目标是吻合的。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理论在经过许多判例的不断明确和修正后,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也确认了该理论,如,《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829条第1款第(8)项规定:“如果本仲裁裁决与之前的不再受追诉的仲裁裁决或者已产生既判力的法院判决相悖,且之前的裁决或判决在本仲裁程序中已被提交,那么当事人有权请求认定本仲裁裁决无效。”《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76条规定:“仲裁裁决自其作出之时起有既判力。”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将仲裁裁决既判力理论在立法中予以确认,当然,在吸收既判力理论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仲裁与诉讼的不同点进行“量身定做”,一方面须阻却仲裁裁决对第三人的既判力(限定主观范围),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仲裁的性质赋予裁决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以既判力(扩张客观范围),逐步地对仲裁机制进行理性的修正,推动仲裁制度的发展。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江伟,常廷彬.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J].中国法学,2008,(3).
[3]丁伟,石育斌.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之理论建构与事务研究[C]//.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李家庆,黄欣欣.仲裁判断有无争点效之争议与讨论[J].仲裁季刊,2007,(7).
[5]谢石松.商事仲裁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常廷彬.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7]M.H.Biren.ResJudicataandCollateralEstoppel EffectofaCourtDeterminationinSubsequentArbitration[J].45Alb.L.Rev.1029(1980-1981).
[8]G.RichardShell.ResJudicataandCollateralEstoppel EffectsofCommercialArbitration[J].35UCLAL.Rev.623(1987-1988).
[9]康明.和解裁决中应注意的问题[C]//.仲裁与法律(第107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