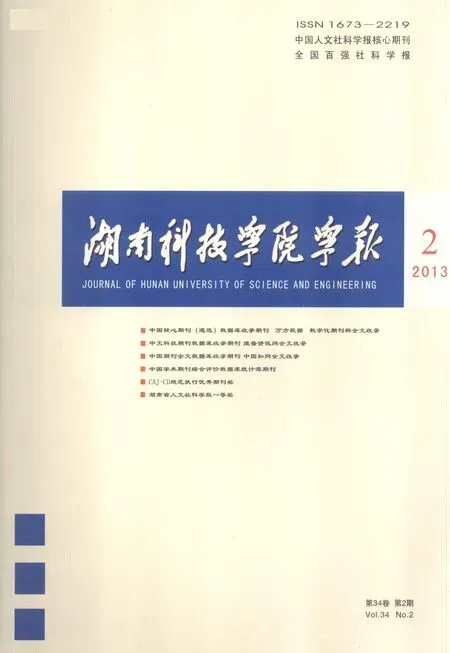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孙 婠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 100081)
一 荀子引《诗》概况
朱自清先生曾在《诗言志辨》中道:“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私家著述从《论语》创始;著述引《诗》,也就从《论语》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诗》;而《荀子》引《诗》独多。……荀子影响汉儒最大。”[1]而《诗经》自秦火及秦末之兵燹,而传至汉有齐、鲁、毛、韩四家。荀子实为汉传《诗》之祖。汪中《述学·荀子通论》考证云:“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助于诸经。”[2]“《经典叙录》‘《毛诗》……一云,子夏传曾申。……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诗》荀卿子之传也。《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由是言之,《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3]清人俞樾亦以为然也,并曰:“今读《毛传》而不知荀义,是数典忘祖也。”[4]即此可知,荀子对于《诗经》的流传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荀子的生卒年已很难确定,各学者之间观点亦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他是活跃于战国末期的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研究并吸收了各家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从荀子存世的著作看,他对《诗经》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诗经》的评论;第二个方面主要是荀子论著中所引用《诗经》之诗句。前一个方面可以说是荀子对《诗经》的直接评价,而后一个方面可以说是荀子对《诗经》的间接评价。且现存的先秦诸子论著中《荀子》为引《诗》用《诗》最多者。同时,荀子对《诗经》的评价也极富特点。本文将对《荀子》的引《诗》和论《诗》这两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回顾漫长的先秦时期《诗经》被广泛使用,用《诗》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在西周到春秋前《诗》主要用于祭祀、宴享、射、丧,是一种歌唱演奏。到了春秋时期,记载此段历史文献的《左传》、《国语》表明这一时期多是宴享演奏歌唱用《诗》、外交言志赋《诗》和以《诗》评人证事。春秋末到战国初年,从此时期文献《左传》、《论语》来看宴会赋《诗》言志日渐稀少,不过其风尚存,所以孔子很重视《诗》的教化作用。战国中后期随着周王朝衰微,礼乐制度崩坏,人们虽对《诗》的内容非常熟悉,但极少用《诗》。此时期存留的诸子《墨子》中用《诗》六首,并且字句多舛误。《庄子》仅用一首,且为逸《诗》。《孟子》引用了三十多首,且多用于以“王政”说服国君时,或者和弟子谈论时引用,有时也作为间接辩说时加强论据之用,所以《荀子》引《诗》用《诗》显得尤为突出。[5]据笔者统计《荀子》中涉及《诗经》的记载多达九十六则,其中引《诗》则达到了八十二则(据洪湛侯《诗经学史》中为八十二则,[6]胡义成《荀况对<诗经>的批判继承》中为七十五则[7])。荀子本人引《诗》为七十六次,其中引《大雅》二十八次,《小雅》二十五次,《国风》十次,《颂》七次,逸《诗》六次,荀子转述孔子所引《诗》五次,荀子弟子所引《诗》一次。分析《荀子》用《诗》的情况,所用《大雅》、《小雅》最多,其次是为《国风》,而《颂》最少。荀子引《诗》为何偏重《雅》,而《国风》则较少呢?胡义成认为“作为地主阶级学者的荀况,对《国风》如此冷淡,只能证明,《国风》的政治思想倾向,至少对于地主阶级是不利的,而且此种‘不利’,不可能随着地主政权的巩固和他们对奴隶主意识形态全面继承日益紧迫而消失。”并且胡义成认为荀子之所以器重二《雅》是因为它们不采用直接怨刺“而是采用礼赞‘先王’文治武功和显赫业绩的手法,向读者灌输奴隶制一套‘先王’的思想。……正是荀况及其所代表的当时的地主阶级急于借鉴运用,借以强化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用部分。”[7]当然,我们可以从当代人的政治角度考虑和论述荀子引《诗》的意图,但是如果仅是简单划归为单一的政治原因,而且仅从当代人所理解的政治概念出发来分析荀子用《诗》,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那么《雅》为何被荀子大量选用并出现在论著中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多角度入手,需要尽可能从荀子所处的时代和《诗经》本体出发来分析,而不是简单的以预先设定的想法出发从文献材料中论证,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二 《荀子》引《诗》时偏于用《雅》
首先,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下《诗》中的《雅》的概念。关于《雅》的解释汉儒郑玄认为“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革免)之,有两纽,疏画。”[8]近代章太炎先生认为“雅”为乐器,用这种乐器伴奏的乐歌叫做《雅》。[5]但是,有许多学者还是相信“雅”为中原正音,即朱熹所说的“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9]《中国文学史长编·先秦卷·释雅》认为“前人关于《雅》的解释甚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雅’即‘正’,又与‘夏’通。周王畿一带原为夏人旧地,故周人时亦自称夏人。王畿乃政治、文化中心,其言称正声,亦称‘雅言’意为标准音,类乎今之‘普通话’。当时宫廷和贵族所用乐歌即为正声、正乐,《诗经》中《雅》便是指王之乐,是相对于地方‘土乐’而言的‘正乐’。这一名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尊王观念。此外,《雅》又有《小雅》、《大雅》之分。由于《雅》在内容、风格上有明显区别,说者各执一端,对于二《雅》之分的缘由,便有不同认识。现在大多认为,《小雅》、《大雅》之分,是与它们音乐之不同和产生时代之远近有关的。”[10]不论“雅”为何,或者说《大雅》、《小雅》是否反映了尊王的观念,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雅》是用“雅言”演唱可以摆脱地域的局限性,让更多懂“雅言”的人接触并熟知。同时,《雅》较地域性的《国风》流播地域广泛,所以《雅》的接受人群分布地区也更为广泛。因此,战国末期游说于各地的士人,必定要选择流播地域和接受人群更广泛的《雅》。这很可能是荀子为何多选用《雅》中的诗句,而不太侧重使用《国风》中的诗句来论证的原因之一。
其二,任何写作都有其预设的接受对象。荀子著书立说也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当时各国的诸侯和上层贵族,以及同荀子处于同一阶层的士人。由于这些人更多接触的是在朝廷隆重场合演奏的《雅》。如《仪礼·燕礼》记载“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郂》、《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苹》……升歌《鹿鸣》,下管《新官》。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8]由此文献可知在诸侯、贵族及地位较高的阶层,他们出席的燕享场合,是多演奏《雅》。即使是演奏乡乐,也采用王畿附近的《周南》、《召南》。正因为荀子著书的预设接受对象更多接触的是《雅》,他们更为熟悉和看重的乐曲是《雅》,所以荀子也因此而在其书中多引用《雅》。考察先秦诸子的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不仅荀子侧重引《雅》,比荀子更早的孟子也是引《雅》居多,《左传》亦是偏重引《雅》用《雅》。[11]
其三,既然荀子本人多引《雅》为立论,那么他本人对《诗经》的评价也会影响到他用《诗》的侧重点。荀子在《大略篇》中说:“《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儒效篇》云:“《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在《儒效篇》中又云:“《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也,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可见荀子认为《小雅》是“疾今之政,以思往者”的刺诗。同时,它又是经过了“圣人之道”文饰的。《大雅》则是光大“圣人之道”的。荀子认为“《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3]荀子此说被后人发展为“《国风》好色而不淫”。[12]从荀子对《风》、《雅》《颂》的评价中不难看出,他对《雅》的评价更高,在荀子那里《大雅》、《小雅》最能体现他所崇尚的“圣人之道”。而且荀子认为《国风》长于抒写性情,即“盈其欲而不愆其止”,《雅》长于议论,即宣扬“圣人之道”的。所以荀子在著书立论时自然会采用自己看重,并为大家公认,且具权威性的经典文字,同时这个经典性文字还能有效的表达自己观点,《雅》正好具备了这样两个特点,既能宣扬“圣人之道”,也能长于说理。这就是荀子为什在立论著书引《诗》时偏重用《雅》的原因。即便在今天人们如果要宣传己的观点,让自己观点更具说服力,能被他人接受,必定会选择一种大家公认的,而又较有权威的经典性文字作为依据来论述。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引用经书之言来为自己立论,于当代的文革时期则引用具有绝对权威的革命语录为之。
其四,为何荀子较少引用《颂》,则是因为在《诗经》305 篇中《颂》仅占40 篇。从篇幅上来说,荀子也不可能在比较少的《颂》中大量征引其诗句。并且《颂》的演奏机率较《雅》更少。它只在祭祀祖先这样重大的场合使用,所以大多数士人经常接触到的基本还是《雅》。同时,各个诸侯的宗族不同,所以这也导致了《颂》的使用范围不可能太大。那么,这也是荀子为何极少用《颂》的原因。
综上,由于《雅》流传地域和接受人群较《风》、《颂》更为广泛,及荀子著书游说的对象上层贵族和与他处于同一阶层的士人更熟悉和重视《雅》。也因为荀子推崇《雅》,认为《雅》能体现“圣人之道”,并长于议论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导致了《荀子》引《诗》时偏于用《雅》。
三 荀子论《诗》
《荀子》中除了大量引用诗句立论外,还从不同角度评《诗》11 次之多,涉及了《诗经》的许多方面。如对《诗经》中《风》、《雅》、《颂》的评价,并且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和对《诗经》的批评。即“《诗》、《书》故而不切”[3],以及以意会读诗的方法,“善为诗者不说”[3]等方面。由于荀子对《诗》评论的角度不同,表面看来相矛盾之处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荀子在具体情况中有不同的意旨罢了。本文只想阐述两点,一为“《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另一个则想讨论何为荀子的意会读诗法,“善为《诗》者不说”。
荀子在《劝学篇》中云:“《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也。”[3]接下来荀子又在《劝学篇》中云:“《诗》、《书》故而不切。”如果不仔细分析此二种言论,则会觉荀子所言前后不一。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这些语句的出处的具体语境来看,其实它们并不是矛盾的。在此荀子认为《诗经》、《尚书》将世间广博的知识都收入其中,但是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并未将它们作为至理名言和人们的行为规范。他只是将《诗》作为前代的文献。因为《诗》既然是前代文献,保留有大量知识,当然可以从中吸取精华。然而,如果只是教条的遵循《诗》《书》则是错误的。这也是荀子要《劝学篇》中所表达的。荀子自己也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米也,以锥餐壶也,不可得矣。”[3]荀子的“《诗》、《书》故而不切”是针对如果不“学莫便乎近人”,则“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3]所以说荀子是辨正地对待《诗经》的,他是推崇《诗》,但是不盲目迷从于《诗》。他所批评的是那些学习脱离现实的“陋儒”之人。因此,理清了荀子批评的出发点,自然不会觉得荀子论《诗》有矛盾了。
荀子在《大略篇》中言:“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3]杨倞注“皆言与理冥会者,至于无言说者也。”又在《大略篇》中言“少不讽,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杨倞注“讽谓就讽《诗》、《书》也”。荀子的这两种说法也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荀子是针对“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这个语境中所论。荀子主张善《诗》者,重在意会,而不过多的假于言说。他认为善于讲解《诗》的人,未必真的理解《诗》的含义。这也是为何他说“善为《诗》者不说”的缘故。而杨倞的注解则认为此是“言”同“理”交融,所以就到了不用言说的程度。杨倞注颇融会了老庄之意。但是,在这里荀子是针对“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这个语境出发的,说明只要达到了用《诗》的目的,就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说”。
同时,荀子在指出了“善为《诗》者不说”之后,又进一步说“少不讽,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3]。就是说如果要深刻领会《诗》,则必须诵读学习《诗》之文本,才能深刻体会理解《诗》的含义。从这里充分体现了荀子的辩证性,要理解《诗》首先要诵读学习它,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善于说《诗》用《诗》而又未必理解《诗》意,则不能说有所成。与荀子并称的另一位儒家大师孟子提出读《诗》要“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孟子的这种读《诗》对后世的影响较荀子这种读《诗》论影响更大。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说。而荀子的这种读《诗》之说则未有多大的影响,几乎是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同孟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孟子的这种读《诗》的方法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即使后学对此争论不休,但是这不失为解《诗》的方法。然而,相比之下荀子的这种“善为《诗》者不说”的解《诗》之论则有些难以运用,所以导致了这样一种被湮没的局面。当然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荀子》一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为人所重视,这与对荀子其人争议颇多不可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荀子这种读《诗》论。通观《荀子》全书,荀子引《诗》,多不作解,而是直接引《诗》,极少说《诗》、解《诗》。虽然,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诗》较熟悉,与我们今天阅读现代作品一样无需作解,但是荀子引《诗》极少作解应该是与他的这个观点分不开的。同时,荀子的这个“善为《诗》者不说”,不是针对讲课授徒,而是从写文章的角度来说的。用《诗》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诗》,而是更好的让人明白所论的观点。而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识是针对学生教授《诗》而用的。所以荀子的“善为《诗》者不说”是有针对性的,若讲此一概而论,就无法解释荀子不说《诗》,又如何传《诗》等问题。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他不仅对《诗经》的传授有极大的贡献,且对《诗经》的评价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荀子在引《诗》中所体现的观念,及他对《诗》理解和阐述,对深入研究《诗经》在战国末期的状况,以及对汉代《诗经》的流传是极有意义的。
[1]朱自清.诗言志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汪中.述学·荀子通论[M].上海:中国书店影印本,1925.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俞樾.曲园杂纂·荀子诗说[M].清刻本,1871.
[5]袁长江.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6]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胡义成.荀况对《诗经》的批判继承[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4):44-49.
[8]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朱熹.诗集传·小雅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刘晖,曾志东,贺平.从《左传》用《诗》看《诗经》的雅[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12):54-56.
[12]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