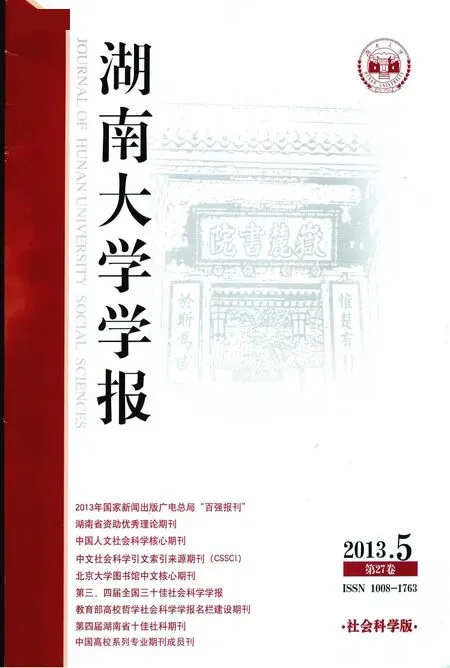宋儒误读佛教的情形及其原因*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 学系,江苏 南 京 210023)
宋儒究竟是否误读了佛教?这个问题在许多著名学者中也存在分歧,比如方东美先生说:“宋人讲佛学,可以说是肤浅——主张佛学的理论是肤浅,反对佛学的也没抓住重心,依然是肤浅。”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绪论》,《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84页。而陈寅恪先生是另一看法:“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以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阐明古学,实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②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那么,宋儒对佛教究竟存不存在误读呢?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 宋儒误读佛教之情形
宋儒是否对佛教存在误读,我想每位学者自己心里都有杆秤。然而,无论是赞扬宋儒佛教素养的高深,还是批评宋儒佛教素养的肤浅,我们只能以事实说话。宋儒对佛教的认识和评价涉及面很广,这里选择宋儒对于佛教本体论、佛教伦理观、佛教轮回说、佛教道体等四个方面的认知情况加以考察,以对宋儒是否误读佛教问题进行回应。
(一)对佛教本体论的误读。佛教关于本体的论述非常多,如《金刚》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绪论》,《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84页。《金刚经》,黄夏年主编《精选佛经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如《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②《心经》,黄夏年主编:《精选佛经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不管怎样的论述,佛教本体论都表现出“空幻”的特点。那么,宋儒对佛教具有“空幻”特点的本体论是怎样理解的呢?综合言之,不外如下几点:其一,指佛教之“空幻”为空无一物之“空幻”。如张载说:“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而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万物相见乎离,非离不相见也。见者由明,而不见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处。彼异学则皆归之空寂,盖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见一边耳。”③《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182页。张载批评佛教见“明”不见“幽”,不知道“幽”亦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形式,而视万物为空寂。胡宏说:“即物而真者,圣人之道也;谈真离物者,释氏之幻也。”④《知言·往来》,《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认为佛教之“空”是无物之“空”。朱熹说:“老氏依旧有,如所谓‘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缴’是也。若释氏则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则是全无也。”⑤《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30页。由这个比较可以看出,朱熹亦是将佛教之“空幻”理解为无内容、无实物之“空幻”。其二,认为佛教所讨论的“心”、“性”诸本体范畴,是空无其“理”的。如张载说:“释氏元无用,故不取理。彼以性为无,吾儒以参为性,故先穷理而后尽性。”⑥《横渠易说·说卦》,《张载集》,第234页。如胡宏说:“今释氏不知穷理尽性,乃以天地人生为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灭者,则以为妄想粗迹,绝而不为,别谈精妙者谓之道。则未知其所指之心,将何以为心?所见之性,将何以为性?”⑦《书·与原仲兄书二首》,《胡宏集》,第121页。朱熹说得最为简洁明了:“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⑧《性理一》,《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全书》(拾肆),第192页。其三,认为佛教无“下学”,没有利用、厚生,故是“空”。如张九成认为佛教“尘垢功业、赘疣五伦、梦幻四季”,他说:“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以其乍脱人欲之营营,而入天理之大,其乐无涯,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是故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尘垢,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为赘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为梦幻,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⑨《少仪论》,《横浦集》卷五,《文洲阁四库全书》集部七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20~321页。如朱熹认为佛教无“治生产业”:“他(佛教)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云云,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至神鬼神仙、士农工商技艺,都在他性中。他说得来极阔,只是其实行不得。只是讳其所短,强如此笼罩去。”⑩《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42页。综上,宋儒的确将是佛教本体论理解“空无一物”的本体论。
但是,佛教本体论是否如宋儒理解的那样,是“空无一物”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一,佛教所谓“空幻”,绝不是宋儒所理解的“空无一物”。在佛教中,“空寂”亦即真如、涅槃、法性、实相、第一义谛等,佛教对“空幻”有怎样的论述呢?《圆觉经》云:“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院觉妙心,犹如空华,从空而有,幻华虽灭,空性不坏。”⑪《圆觉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43页。《佛性论》云:“自性不可得,如见幻事;幻物者,证量所见,不如实有。诸法亦尔,不如所见,而有所见。由体不实故不有,由证量故不无。由体无故,空义得成;以证量故,假有不失。”⑫《佛性论》,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83页。也就是说,佛教之“空幻”乃是“真空妙有、非幻不灭”的,正如僧肇说:“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⑬《肇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45页。亦如法藏说:“谓尘空无性是本,尘相差别是末。末即非末,以相无不尽故;本亦非本,以不碍缘成故。即以非本为本,虽空而恒有;以非末为末,虽有而恒空。”⑭《华严经义海百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可见,佛教之“空幻”乃是描述世界具有真谛、俗谛的双重性。言其为“有”,“有”皆因缘而生,故“有”非真生;言其为“无”,事象纷呈,故“无”非真无。所以,所谓佛教“空幻”非宋儒所谓“空寂”。第二,佛教批判视万物为空寂的“断灭空”论,视此论为“外道”。何谓“断灭”?佛教认为,世间万物因果各别,所以不是“常”;又因果相续,所以不是“断”;那重否认此因果相续之理的观点,即是断灭之见。佛教对此种断灭论的态度是否定的。《金刚经》云:“须菩提,汝莫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貌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貌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⑮《金刚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96页。此谓佛教不说断灭相。《圆觉经》云:“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诸幻灭尽,不入断灭。”⑯《圆觉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43页。此谓远离诸幻、但不入断灭。《楞伽经》云:“若真相灭者,藏识应灭。若藏识灭者,即不异外道断灭论。”⑰《楞伽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58页。此谓若持“真相”或“藏识”灭者即是外道的断灭论。可见,佛教之“空幻”与“空无一切”完全不在一个界面上。第三,佛教所言“心”、“性”究竟有无“理”?一般地讲,“心”和“性”是佛教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也就是说,佛教思想体系的架构及其展开,离不开“心”和“性”。由此而言,佛教之“心”和“性”能无“理”乎?分别地讲,在佛教中,有所谓“心”净垢之说,乃是针对不同众生而说的方便法门。所谓“但为众生谓心常在,故说客尘做染。则心不净;又佛膸众生若闻心本不净,便谓性不可改,则不发净心,故说本净。”①《成实论·心性品》,《大藏经》第32卷,第258页。佛教又有“心生万法”说,万法乃“心”所生所有,此类宋儒“心包万理”说,若谓宋儒之“心”有“理”,岂能谓佛教之“心”无“理”乎?再而,佛教所言“性”真无“理”耶?佛教有所谓“佛性”,佛性者,乃成佛之根据也。由佛性论,佛教生出“理佛性”、“行佛性”、“中道佛性”、“阐提无性”、“五种种性”、“无情有性”、“明心见性”、“顿悟”、“渐修”等理论,所以说“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②《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97年,第50页。故能说佛教所言“性”无“理”乎?然而,宋儒所责佛家所言“心”、“性”无“理”固无道理,而指佛家所言“心”、“性”无儒家之“理”,则为有见也。第四,佛教究竟有无“下学”?“下学”在此主要是指实际的事务或作为。佛教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此是大慈悲、大作为也。细言之,《华严经》云:“如来住于无量无碍究竟法界、虚空界。真如法性,无生无灭,及以实际,为诸众生随时示现。本愿持故,为无有休息,不舍一切众生、一切刹、一切法。”③《华严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165页。是谓佛教示现智慧,不舍一切众生。《维摩诘经》云:“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者,当度一切众生。”④《维摩诘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160页。是谓佛教以渡脱众生为追求。因此亦不能以佛教为无“下学”也,自也不能以此言佛教“空幻”为无物之“空寂”也。由此我们只能说,宋儒根本没有理解佛教“空幻”思想的意蕴,而是一种远离佛教本体论本有意义的错误解读。
(二)对佛教伦理观的误读。宋儒对佛教伦理的误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言佛教灭绝人的天性。如二程说:“人之有喜怒哀乐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尽绝,为得天真,是所谓丧天真也。”⑤《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再如张栻说:“释氏本恶天降威者,乃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则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天,而天之降命者自在。为饮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释氏恶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则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穷极奢侈,释氏恶之,必欲衣坏色之衣,吾儒则去奢侈而已。至于恶淫慝而绝夫妇,吾儒则去其淫匿而已。释氏本恶人欲,并与天理之公者而去之。”⑥《酒诰说》,《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187~1188页。在程颢、程颐、张载看来,佛教的教义及其主张,都是对人天性的扼杀。第二是言佛教绝弃人伦物理。如二程说:“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已尔。”⑦《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第一册,第24页。再如朱熹说:“佛氏以绝灭为事,亦可谓之‘夭寿不二’,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会,所以做底事皆无头脑,无君无父,乱人之大伦。”⑧《孟子十》,《朱子语类》卷六十,《朱子全书》(拾肆),第1940页。在程颢、程颐、朱熹看来,佛教教义中根本没有君臣、夫妇、父子、兄弟等伦理。第三是言佛教缺乏关爱精神,自私自利。如胡宏说:“释氏之学,必欲出死生者,盖以身为己私也。”⑨《知言·修身》,《胡宏集》,第4页。再如陆象山说:“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⑩在胡宏、象山看来,佛教关心、关爱的是自己,只求自己的修行,不问天下苍生。第四是言佛教去弃道德仁义。如陆象山说:“今习释氏者,皆人也。彼既为人,亦安能尽弃吾儒之仁义?”⑪《书·与王顺伯》,《陆九渊集》卷二,第17页。再如朱熹说:“盖佛氏之所谓‘慈’并无缘由,只是无所不爱。若如爱亲之爱,渠便以为有缘,故父母弃而不养,而遇虎之饥饿,则舍身以食之,此何义理耶?”⑫《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53页。在象山、朱熹看来,佛教教义也不讲道德仁义,因为佛教宁可救活一只动物,也愿赡养父母。综上,宋儒的确认为佛教与儒家伦理是完全背离的,佛教的存在就是对伦理的抛弃。
然而,考之于佛教经籍,我们只能说宋儒对佛教伦理的理解是“失真”的。因为第一,佛教没有灭绝人之天性的思想。佛教认为,众生受苦,乃是因为执于贪、爱、欲,因而主张绝去贪、爱、欲等,而要绝去贪、爱、欲等,必须建立对世界为“空”为“幻”的认识,并希望众生由此能够获得“生”的智慧,而远离苦海。所以,佛教的目标并不是要绝去人之衣、食、住、行等“饮食男女”之天性。而且,佛经中随处可以看到对人之“天性”满足和维护。如《妙法莲华经》云:“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婶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⑬《妙法莲华经》,《精选佛经译注》,第262页。“生产”是人之天性,生男生女之要求,则应是此“天性”的延伸,而佛教一概满足。在《地藏经》中,佛告
⑩《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399~400页。诉地藏菩萨,如果有善男、善女,用香花、饮食、衣服供养地藏菩萨,那么将获得二十八种利益,这二十八种利益至少有如下四种属于“人之天性”:衣食丰足有余;欲为男身则男身、欲为女身则女身;可做国王或大臣之女;有求都如愿;家庭亲属欢乐和睦等。①《地藏菩萨本愿经》,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第二,佛教具有深切的关怀精神。佛祖出家,舍去荣华富贵,别离父母兄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为的是渡脱众生,这种牺牲自我、助人成佛的行为,不是关怀精神又是什么?正如《华严经》云:“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涅槃。”②《华严经》,《精选佛经注释》,第80页。佛教提倡代众生受苦、以众生事为自己事的担当精神。如《维摩诘所说经》云:“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萨疾者,以大悲起。”③《维摩诘所说经》,《精选佛经注释》,第187页。这不也是深厚的关怀精神么?第三,佛教不否定伦理秩序。宋儒认为佛教的主张和僧尼的行为,都是对社会伦理的破坏,这种判断显然存在问题。比如,在《长阿含经》中,强调夫妇伦理的意义:“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相待以礼。二者威严不阙,三者衣食随时。四者庄严以时。五者委付家内。”④《长阿含经》,《大藏经》第一卷,阿含部上,第71页。在《无量寿经》中,有父子、兄弟、夫妇伦理规定——“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室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⑤《无量寿经》,《大藏经》第十二卷,宝积部下,第274页。因此,佛教并不像宋儒所批评的那样是仇视伦理的。第四,佛教亦没有抛弃仁义道德的观念。佛教以解救众生之苦为理想,创造了无数的法门,方便众生、饶益众生;佛教提倡感恩、报恩,对有恩之人永志不忘;佛教提倡救死扶伤、积集功德。举例来说,佛教认为父母有“十高厚恩德”,即大地、能生、能正、养育、智者、庄严、安隐、教授、教诫、与业等,因而父母在堂,名之为富;父母不在,名之为贫。由此佛教认为,孝养父母与供佛具有一样的意义:“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应当如是报父母亲恩。”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教经典精华》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94页。可见,对仁爱、道德的坚贞是深入佛教思想根底的。所以,言佛教以道德仁义为虚幻者,是不能真了悟佛教之“道”也。所以说,宋儒于佛教伦理之理解失真者多矣、深矣!
(三)对佛教轮回说的误读。“轮回”是佛教基本理论之一,宋代儒士大多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但可以说都是与“轮回”说本意有距离。比如,李觏说:“佛之徒后出,而言愈远。其称天宫之乐,地狱之苦,鬼神之为,非人可见,虽明者犹惑疑焉。”⑦《重修麻姑殿记》,《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55页。是谓天堂地狱乃人不可见的神秘之物。张载说:“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今浮图极论要归,必谓生死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⑧《正蒙·乾称》,《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64页。是谓“生死轮回”不足以阐明“鬼”的含义,因为“气”是万物本体,所以生死、天人、阴阳、幽明不二,鬼神不过是“气”变化。程颢说:“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⑨《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三,《二程集》第一册,第139页。是谓“生死轮回”仅仅为恐吓、惩治下根人之工具。陆象山说:“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其教之所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⑩《书·与王顺伯》,《陆九渊集》卷二,第17页。是谓“生死轮回”正是执着生死而自私。朱熹说:“窃谓幽明、死生、昼夜固无二理,然须是明于大本而究其所自来,然后知其实无二也。不然,则所谓无二者,恐不免于弥缝牵合,而反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迹(伊川语),乃二气之良能也(横渠语),不但见乎幽而已。以为专见乎幽,似此未识鬼神之为何物,所以溺于轮回因果之说也。”⑪《答吴公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朱子全书》(贰拾贰),第1961页。是谓“轮回”说荒诞不经,因为不明白鬼神究竟是什么,才陷于轮回说不能自拔。概言之,宋儒所理解的“生死轮回”是鬼神的、等级的、自私的、荒诞的。
那么,宋儒的这种理解是否符合佛教“轮回”说的本来意义呢?首先,佛教认为,万物因缘而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不存在恒常不变的灵魂。但不同佛教学派对此有异见,因为既然讲“生死轮回”,就应有受报主体,于是从印度到中国一直延续着“有神”、“无神”的争论,而中国佛教学派大多将中国古代“灵魂不灭”思想与佛教“生死轮回”融合在一起。由此看出,宋儒视“生死轮回”为鬼神论,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增长任何知识。其次,古印度婆罗门教将人类社会分成种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即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司,刹帝利是王族及武士,吠舍即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手工业者等,首陀罗即是奴隶。另外还有无种性的旃陀罗,即是被称为“扫除污物”的人的贱民。婆罗门教宣说“四种性”是为神所造,种性世袭,婆罗门为世界之首,至上高贵。而佛教主张“业报”面前“四性”众生一定平等,所以言佛教“生死轮回”只是蒙骗、恐吓下等人,说明宋儒不知道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差别。第三,佛教认为,一切没有获得解脱的众生,性情、见识无常,恶习、善习交织,因而陷于无休无止的“生死轮回”之中。如《地藏经》云:“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识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界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转轮五道,无有休息。”①《地藏菩萨本愿经》,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3页。而佛祖大慈大悲,就是希望救拔众生,使之超脱生死。《无量义经》云:“是得是失,起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备受苦毒,无量亿劫不能出。菩萨摩诃萨,如是谛观,生怜悯心,发大慈悲,将欲救拔,又复深入一切法。”②《无量义经》,《佛教经典精华》(下)第703页。而对众生来讲,其要超脱生死,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如《地藏经》云:“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像瞻礼者,香华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受妙乐。若能以此回向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③《地藏菩萨本愿经》,第125页。总之,佛家是“但愿众生离得苦海,不为自己求安乐”,因此以“一生便利”定义佛法“生死轮回”未免太草率、太轻浮。第四,“生死轮回”说有无道理呢?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由于欲境,起诸违顺,境背爱心而生憎嫉,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饿鬼。知欲可厌,爱厌业道,舍恶乐善,复现天人,又知诸爱可厌恶故,弃爱乐舍,还滋爱本,便现有为增上善果,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是故众生欲脱生死,免诸轮回,先断贪欲,及除爱渴。”④《圆觉经》,《精选佛经注释》,第281页。就是说,众生皆为欲所困,爱因欲而生,命因欲而有,从而才有生死相续之轮回。因“欲”生出顺境或逆境,生逆境时,便可能产生憎恨、妒嫉之心,而转入地狱、饿鬼之趣;生顺境时,便知欲可厌、恶可弃、乐于善,并最终获得善果,但还是处于轮回之中。只有断去所有欲望、除去憎爱,方可超脱“轮回”。可见,作为佛教教义的轮回说,是指众生于六道中犹如车轮旋转,循环不已,流转无穷,众生由惑业之因贪、嗔、痴三毒而招感三界、六道的生死轮转,恰如车轮的回转,永无止尽。因而“轮回”说内含着引领众生去欲脱苦、欢喜向善的智慧,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而这就是“轮回”说之“理”之“道”。因此,宋儒对“生死轮回”的理解,完全是隔靴搔痒式理解,非但不能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轮回”说内涵,反而使人误入歧途。道衍批判说:“若言轮回生死怕怖而自私,谬之谬矣。大乘菩萨不舍悲念,出生入死为化度一切众生,虽在生死恶道之中,如游园观尔。”⑤《道余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34页。诚哉,斯言!
(四)对佛教道体的误读。明确提出“道体”的是朱熹(参见《近思录》),他说:“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⑥《易十一》,《朱子语类》卷七十五,《朱子全书》(拾陆),第2572页。“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⑦《答黄道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朱子全书》(贰十叁),第2755页。可见,朱熹所谓“道体”是指学说体系的体用结构,有体有用、有上有下、有内有外才是真正的“道体”。“理”、“太极”、“性”、“诚”、“心”等皆可谓“道体”,但都内含着本末、上下、内外一体之内涵。佛教作为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学说,当然有它的“道体”。那么,宋儒对佛教“道体”有怎样的理解呢?简言之,是上下、本末、体用脱节的。正如二程说:“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⑧《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二程集》第一册,第3页。根据这样的标准,宋儒大都认为佛教的“道体”是分离的。比如,宋儒认为佛教“道体”有上达无下学,二程说:“佛氏之道,一务上达而无下学,本末间断,非道也。”⑨《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二程集》第四册,第1179页。胡宏说:“夫释氏之道,上焉者以寂灭为宗,以明死生为大,行之足以洁其身,不足以开物成务;下焉者转罪业,取福利,言之足以恐喝愚俗,因以为利而已矣。”⑩《书·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第97页。朱熹说:“释氏只说上达,更不理会下学。然不理会下学,如何上达。”⑪《论语二十六》,《朱子语类》卷四十四,《朱子全书》(拾伍),第1018页。在程颢、程颐、胡宏、朱熹的观念中,佛教“道体”只有形上而没有形下。再如,宋儒认为佛教“道体”有内圣无外王,二程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释氏,内外之道不备者也。”⑫《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二程集》第一册,第118页。胡宏说:“释氏见理而不穷理,见性而不尽性,故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不能合一,与道不相似也。”⑬知言·往来》,《胡宏集》,第13页。朱熹说:“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本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⑭《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43页。在程颢、程颐、胡宏、朱熹看来,虽说佛教识心见性,但所识性不能付诸于用,因而是体用两分、有内无外。可见,宋儒谓佛教“道体”上达下学脱节、内外不一的意思,是指佛教在“体”、“内”或“上”一节做得还不错,但没有“用”、“外”或“下”,用儒家的术语来表述,就是有“德性”无“学问”、有“道德性命”无“经世致用”、有“内圣”无“外王”。概言之,佛家之学不能用于世,不《能为社会建立功业。
那么,佛教的“道体”是否如宋儒所批判的那样呢?或许不是这么简单。何谓“体用”?哲学意义上使用“体用”二字,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可能是王弼。王弼说:“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①王弼:《老子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67页。在王弼看来,只有以“无”为“体”,才能不失“道”,也才能显其“用”。就是说,“无”是“体”和“用”的统一。据此,我们认为,佛教不仅有“体用论”,佛教的“体”和“用”还是连贯、一体的,而非如宋儒所言是断裂的,即言佛教的“道体”不是支离的。因为第一,佛教广泛应用“体、用”范畴,而且强调它们的关系是相即相入的、相资相待的。僧肇说:“用即寂,寂即用。用寂体一,同出而异名,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②《肇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页。法藏说:“观体用者,谓了达尘无生无性一味,是体;智照理时,不碍事宛然,是用。事虽宛然,恒无所有,是故用即体也。如会百川以归一海。理虽一味,恒自随缘,是故体即用也。如举大海以明百川。由理事互融,故体用自在。若相入,则用开差别;若相即,乃体恒一味。恒一恒二,是为体用也。……今体为用本,用依体起。”③华严经义海百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可见,佛教所言“体、用”的含义有:“体”是“本”,是“一”,“用”是“末”、是“多”;“体”见之于“用”,“用”因“体”而起;“体”和“用”是相入相即的。其次,佛教理论体系是有“体”有“用”的,而且是连贯的。在佛教中,真如、法性、涅槃、佛性等,皆是佛教之“体”,是不生不灭的;而正见、正思、正悟、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所谓“八正道”,皆是佛教之“用”。并且,“正思”源自真如,真如见之“正思”,所谓“从无住本,立一切法。”④《观众生品第七》,《维摩诘经》,台湾佛光事业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162页。佛教的所有法门,只不过是普渡众生、只不过是引导众生成佛的“用”,但这个“用”是与真如、法性、涅槃、佛性等是“同一”的,而非“二”。第三,佛教所追求的是“以用见体”,“体”和“用”是相资相待的。如《金刚经》由“性空”之“体”出发,讨论如何保护善心、如何降伏恶心的问题,告诉人们“无所住”、“远离一切诸相”。《心经》则根据众生“根器”之不同,授之不同的了悟法门。《维摩诘经》告诉人们,佛法就是使众生远离诸病、生如来身:“诸仁者,此可患厌,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三十七道品生;从止观生;从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⑤《维摩诘所说经》,《精选佛经注释》,第179页。佛教又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以教化众生。也就是说,佛法从来就是以渡脱众生、教化众生从善、净化心灵为务的。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正是佛教之“体”的落实,所以佛教“体用”是相资相待的。第四,佛教之“体、用”具有特殊性。虽然我们认为佛教有“体”有“用”,而且其“体、用”是相资相待、相即相入的。但必须注意的是,佛教之“体、用”与儒家之“体、用”是有差别的,即佛教之“体”,是真如、涅槃、空寂之类,儒家之体是仁、诚、理之类;佛教之用“是”教化众生做善人、为善事,以“治心”为务,儒家教化众生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世”为务。概言之,佛教“养心”之“道体”非儒家治生之“道体”。因此,宋儒谓佛家“道体”异于儒家“道体”可,而谓佛教“道体”支离、断裂则不可。
通过对宋儒关于佛教本体论、佛教伦理观、佛教轮回说、佛教道体的理解与评论的考察,我们不能不说,宋儒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确存在失真性、片面性。正如道衍所说:“三先生(程颢、程颐、朱熹)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⑥《道余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二册,第21页。就宋代儒学界实际情况看,这个评论虽只及二程兄弟与朱熹,宋代其他儒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 宋儒误读佛教的原因
如上考察表明,宋儒对佛教存在失真性解读是客观事实。那么,才高八斗、智慧超群的宋儒,为什么对佛教存在如此严重的误读现象呢?根据我们的初步分析,一方面,佛教来自西域,名相复杂,义理艰深,宋代儒士理解起来的确存在认识论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佛教中的基本观念、教律教规,与宋儒信奉的孔孟之学在价值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宋儒对佛教的理解必须根据儒学的精神与主张进行,这是宋儒理解佛教价值上的障碍。如下我们展开初步的分析。
(一)认识和判断坐标的儒学化。所谓“认识和判断坐标的儒学化”,就是指宋儒对佛教的认识和评价自始至终贯彻着一个基本标准,这就是儒学的标准。比如,程颐认为,孔儒之教是以所“贵”者引导人,佛陀之教相反,是以所“贱”者引导人。他说:“圣人之教,以所贵率人,释氏以所贱率人。”⑦《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第一册,第37~38页。胡宏人为,儒学探求真理,以直接接触事物、研究事物为途径,而佛教所谈论的“真理”,则是脱离事物的“空幻”之说。他说:“即物而真者,圣人之道也;谈真离物者,释氏之幻也。”①《知言·往来》,《胡宏集》,第13页。朱熹认为,儒家所言“性”是仁、义、礼、智之实理,而佛教所言“性”是“空”。他说:“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②《性理一》,《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全书》(拾肆),第192页。可见,宋代儒家学者对佛教的认识和评论,都是以儒学为标准而展开的,以儒学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学之真伪为真伪,这就是所谓“故凡道理不经圣人所定,皆粗浅而狭陋者也,非精深闳博也。”③《唐书·志》,《习学记言序目》(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589页。既然认识佛教、评价佛教都以儒学为坐标,那么在佛教中不符合儒学的思想观念自然或被改造、或被否定,从而直接导致对佛教的误读。
(二)认识和判断价值的实用化。所谓“认识和判断价值的实用化”,是指宋儒在认识和评价佛教的实践中,处处表现出“经世致用”之要求,以实用的标准要求于佛教。比如,张载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气”,“气”有聚有散,佛教由于不了解“太虚”是“气”之散,所以视“太虚”为“空”,由于不知道生、灭、变、化是“气”之变,所以认世界为“幻”。张载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和判断呢?因为“气”即“实”、即“事”,它符合儒学实用精神的。胡宏指出,佛教“道体”尚寂灭、言死生,于修身有功,但不能“开物成务”,没有实际的作为。他说:“夫释氏之道,上焉者以寂灭为宗,以明死生为大,行之足以洁其身,不足以开物成务”④《书·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97~98页。朱熹认为,佛教所言“心”是没有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的“心”,所以不能“事天”,不能“事天”则为“空”。他说:“释氏虽自谓惟明一心,然实不识心体;虽云心生万法,而实心外有法;故无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备。……若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⑤《与张钦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朱子全书》(贰拾壹),第1327页。因此,与儒家“见得无一物不具此理、无一理可违于物”相比,佛教是不折不扣的“空幻”观:“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⑥可见,宋儒对佛教的认识和评价中具有鲜明的“实用”倾向,而由于佛教属于精神学科,这种“实用”要求必然会导致对佛教认知与评价的失真。
(三)认识和判断取向的常识化。所谓“认识和判断取向常识化”,就是指宋儒把佛教教义降低为日常生活知识,再以日常生活知识的标准理解、判断佛教。比如,佛教有“不染一尘,不舍一法”之说。这句话完整表述是“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那么,宋儒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呢?朱熹说:“他云‘不染一尘,不舍一法’。既‘不染一尘’,却如何‘不舍一法’?到了是说那空处,又无归着。且如人心,须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他做得彻到底,便与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都不相亲;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⑦《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35页。在朱熹看来,既然“不染一尘”,就不能“不舍一法”,如果这边“不染一尘”,那边又“不舍一法”,就是“空”。为什么这样说呢?朱熹认为,本来,人心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但佛教做得彻底,所以心中虽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而不相亲,实际上是“无”;儒学则有分寸,所以心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故是“有”。可见,朱熹实际上是用日常知识来衡估“不受一尘,不舍一法”的,“不受一尘”就是数量上的绝去一切,“不舍一法”就是数量上的包含万有,因而要么“不受一尘”,要么“不舍一法”,二者只居其一。这种理解显然没有触及佛教“性法一如”本体观内蕴。再如,宋儒也常识化理解佛经中的某些观念。朱熹说:“试将《法华经》看,便见其诞。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几万几千几劫,更无近底年代。又如佛授记某甲几劫后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以待阙许久?又如住世罗汉犹未成佛,何故许多时修行都无长进?今被它撰成一藏说话,遍满天下,惑了多少人。势须用退之尽焚去乃可绝。今其徒若闻此说,必曰,此正是为佛教者。然实缪为此说,其心岂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应处。”⑧《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63页。所谓“恒河沙数几万几千几劫”,《法华经》云:“诸比丘,是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抹为沙,一尘一劫,比佛灭度以来,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祗劫。”⑨林世田等编:《佛教经典精华》(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恒河沙数”就是无数无量之意,“劫”在佛教中亦是指“其年无数”,所以“恒河沙数几万几千几劫”就是指时间很久远很久远。朱熹质疑“为何不讲近的年代”,这种质疑显然毫无道理。《法华经》云:“同号曰普明,转此而授记。我灭度后,某甲当作佛。”⑩“授记”就是“佛对发心之众生,授与当来必当作佛之记别也”,就是说,“授记”就是指佛陀为弟子们预告,亲证菩提的时间,佛法的授记思想,在于证明人人都能成佛,不论何人,如能修行佛道,便可依据各人的根性和修行的法门以及勤惰的态度而判定成弗的迟早。而朱熹质疑说,佛有神通,度人成佛应是举手之劳,何需花千年万年甚至亿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能尽快让人成佛,而要历经无数
⑩《佛教经典精华》(上),第209页劫之后?可见,朱熹的质疑只是要求佛法符合日常知识而已。事实上,宋儒对佛教本体论、伦理观、轮回说、道体的理解,无不具有常识化取向,所以不想误读也不可能。
(四)认识和判断方式的片面化。所谓“认识和判断方式的片面化”,是指宋儒对佛教的理解和评论存在方法论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以践行代替思想。就是所说宋儒对佛教的理解与判断,偏向以实践为标准,而且主要是以“出家”为标准。比如,二程说:“所谓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则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愿学也。如其合于先王,则求之《六经》足矣,奚必佛?”①《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二程集》第一册,第9页。再如胡宏说:“释氏狭隘偏小,无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身为事,绝灭天伦,屏弃人理,然后以为道,亦大有适莫矣,非邪说暴行之大者乎?”②《书·与原仲兄书二首》,《胡宏集》,第121页。可见,宋儒对佛教的理解,不是从佛教教义去理解佛教,而“出家”因为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的消极影响而为他们所反对,但这种理解方式显然是不利于全面、准确理解佛教的。正如道衍所批评的:“程夫子不知释氏之道而攻其迹。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③《道余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二册,第31页。其二是以排斥代替分析。宋儒对佛教缺乏耐心,不能理性地学习和理解,而是动则批判,取一种非理性的排斥态度。比如,张载指佛教不知“穷理尽性”,所以其法不可行——“浮图不知穷理而自谓之性,故其说不可推而行。”④《正蒙·中正》,《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1页。张栻认为佛教根本不值得学习:“盖圣门实学,循循有序,有始有终者,其唯圣人乎!非若异端警夸笼罩,自谓一超径诣,而卒为穷大,而无所据也。”⑤《答周允升》,《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909页。朱熹则声称“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备具,不必它求。”⑥《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37页。可见,宋儒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拒绝的、排斥的。如果一种思想或学说被拒绝学习,怎么可能对它有准确、完整的理解呢?第三,以危害代替不足。也就是所谓“夸大危害的方式”,即指将佛教的局限“合理地”夸大成危害,然后再将这种被夸大的危害附在佛教身上,以理解和评价佛教。比如,李觏指出的“佛教十害”,⑦《富国策第五》,《李觏集》,第141页。胡宏批评的佛教“灭义忘亲,三纲弛绝”,⑧《皇王大纪论·西方佛教》,《胡宏集》,第224页。叶适揭露的佛教“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⑨《唐书六·列传》,《习学记言序目》(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630页。朱熹批判的佛教“绝类止善”,⑩等等,都是将他们所认为的佛教“局限”放大为危害,甚至是灭族亡国。试想,宋儒动不动就紧盯着佛教的局限,又将这种局限随意放大成严重的危害,他们怎么可能对佛教有客观、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呢?
综上所述,宋儒对佛教的误读是客观存在的,其所以误读的原因大致有四:认识和判断坐标的儒学化、认识和判断价值的实用化、认识和判断取向的常识化、认识和判断方式的片面化。因为坐标的儒学化,认识和判断佛教就必然远离佛教本身而以儒学为是非;因为价值的实用化,认识和判断佛教就必然否定佛教的超越性而以功利为旨趣;因为教义的常识化,认识和判断佛教就必然轻视佛教义理而下落为日常知识;因为方法的片面化,认识和判断佛教就必然支离佛教教义而难以欣赏佛教的优长。因此,宋儒对佛教的误读是难以避免的。而这四大原因中,有些是属于认识论的,如常识化、片面化,由认识上造成的误读,我们称之为“非自觉性误读”;有些属于价值论的,如儒学化、实用化,由价值上造成的误读,我们称之为“自觉性误读”。最后值得提醒的是,检讨宋儒对佛教的误读,并不意味着这种误读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诠释实践中的误读是思想得以发展与完善的途径之一。⑪李承贵:《宋儒重构儒学利用佛教的诸种方式》,《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