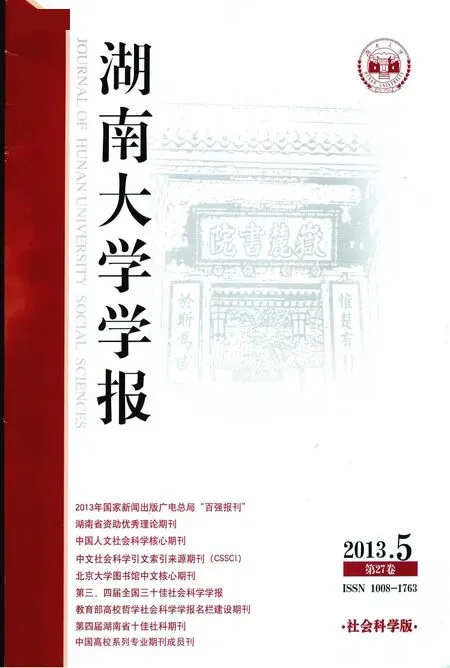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吴劲雄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有这样的一句话:“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学者已指出:其文字与《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基本相同。①裘锡圭按语,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语丛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218页。然而学界对于这两段极为相似的句子解说甚多,纷纭各别,虽不至于争论不休,然至今仍未有定论。为求得当中情实,今对诸家议论及先秦相关典籍再作如下的考察。
一 各家之意见
计今所见诸家议论,大概有三种:
(一)《语丛四》抄自《庄子》
李学勤先生认为:“《语丛四》所录引的,正是《庄子·胠箧》。”②李学勤《从郭店简<语丛四>看<庄子·胠箧>》,《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74页。陈伟先生《郭店竹书别释》则稍有不同:“《庄子·盗跖》也有大致相当的记载,写作:‘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简文前一句同于《胠箧》,后一句则同于《盗跖》。”③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234-235页。
(二)《庄子》借用《语丛四》
高正指出《语丛四》此语与《墨子·鲁问》的思想观点很相近:“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并认为“《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明显受其影响。”④高正《诸子百家研究》(增订第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341页。
(三)两书可能有同一来源
饶宗颐先生认为:“由《语丛》所记,知此数句乃战国以来楚人流行之重言,庄子作《胠箧》时借用之,并不是他自己所写的东西。”①饶宗颐《从新资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派试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61页。郭永秉指出:“即使我们忽略《语丛四》和《胠箧》存在的不同,仅据《胠箧》逻辑严密、‘窃钩者诛’一段在文中不可分割等事实,也不能必然得出其他古书与此有关的内容一定就抄自《胠箧》的结论,也不能必然得出《胠箧》之文并非从他处引来的结论。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各书的相关内容完全有可能皆有同一来源,而不是简单的谁抄谁的关系。”②郭永秉《再谈郭店简<语丛四>8、9号简与<庄子·胠箧>之关系及相关问题》,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03
综而观之,上述第二、三种情况的论点虽有不同,然而各家所要表达的想法,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语丛四》这段话很有可能是先秦流行语,而为包括《庄子》《墨子》在内的各家所共见。然而还是停留在推测阶段,各位学者皆未质言之。
二 与《庄子·胠箧》、《盗跖》及《墨子·鲁问》之异同
诸位时贤已经指出《庄子·胠箧》与《语丛四》的相似性,然他们的引文并不完整,今再征引之如下: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③(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三,《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60页。下文所引诸子文,皆为《诸子集成》本。
此文前两句的意思,与《语丛四》第八、九简的内容几乎相同。然而《庄子》的本旨,乃在最后一句:窃仁义圣知(知读作智)。即大盗所窃不限于邦国,而且连同仁义圣智也一同窃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胠箧》的前文就说:“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④同上,58-59页。在庄子看来,智者和圣人竟成了替大盗聚敛和守护的人,田成子盗取了姜齐的整个国家,而且也得到了姜齐用以治国的圣智之法。所以说《庄子》这段话的着眼点在“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一语,论者引述《庄子》之言而省略此语,反失《庄子》精义。
《庄子·盗跖》也说:
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⑤(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199页。
这段话所举的例子,有与《胠箧》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而《盗跖》的用意所在,是要证明“义士”的言行相悖,言不顾行。什么叫做义士?这里指的是管仲和孔子。《盗跖》要批评的是,他们虽然仁义礼智不离于口,但是仍然事弒君之主、受篡君之礼。所以说他们言行相悖,不辨是非。可以看出,《胠箧》的“仁义”与这里的“义士”虽然只是一字之别,但是立意已有所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至于学者所引关于《墨子·鲁问》的文字亦有缺省,今录其可反映《墨子》全意之文如下:
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⑥(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三,284页。
《语丛四》第八、九简的意思,大概与《鲁问》这里所引的前半段内容相同。但是《墨子》此文的用意却是在“是故”之后:“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因为《鲁问》前面是这么说的:
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锺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⑦同上。
“小物”是指贱人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即所谓“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大物”是指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即所谓“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所以,可以看出《墨子》的论证方式跟《庄子》的两篇文章一样,先举出若干事例然后得出结论,并不是简单地讨论一犬一彘、一国一都的问题,而是要对“世俗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这种行为作出批评。《胠箧》所说的“钩”、“国”,《盗跖》所说的“小盗”、“大盗”,其实也就是《墨子》这里说的小物、大物;《盗跖》所说的义士,跟这里所说的世俗君子也很相似。
可见,学者们指出的《庄子·胠箧》、《盗跖》及《墨子·鲁问》与郭店楚简《语丛四》相似的地方,其实有同有不同,相同的是推导的前提,就是都看出了为一般人所忽略的互相矛盾的社会现象,并且作出精辟的分析;不同的是他们所举的例证,以及他们所要阐述的道理和批评的对象,各有立足,各有所指。如前所述,道、墨两家是用了近似的理论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目前所看到的《语丛四》这句话,恰恰没有了后面可以反映作者态度取向的文字,看不出作者的立足所在。从《语丛四》第九简的图版可知,这句话后面是空白,而且明显划上了中止符,所以不存在错简或者断简的问题。究竟是作者据以摘抄的典籍本身没有后面半段话,还是摘抄者没有把它跟前面的句子一同抄写下来,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语丛四》后面还存在跟《庄》《墨》相类似的可以表达作者意向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可以据以判断《语丛四》这句话究竟是抄自道、墨,还是道、墨之外的哪一家典籍了。而从当前材料来判断,《语丛四》这句话的意思明显与《庄子·盗跖》更为贴近,因为他们所批判的都是“义士”,而不是“仁义”。
三 与之相似的其他先秦文献
在《庄子·胠箧》、《盗跖》及《墨子·鲁问》之外,先秦文献中还有跟这种议论相似的内容。《吕氏春秋·听言》就说:
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膌,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辠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
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①(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十三,130页。
第一段之意谓:当时的诸侯国君,生活奢靡,不管人民的死活,遇到灾害不赈救,还攻打没有过错的国家,诛杀无辜的群众,却想用这种悖逆的行为,祈求国家的兴旺、宗庙社稷的安稳,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第二段“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指的是以挖穴通地道的方式盗取他家的货财,也就是《墨子·鲁问》所谓“贱人之攻其邻家”的意思。这是显而易见的小事,大家看到了都会批评这是不对的。“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指的是趁其他国家遭受荒灾,守备又残破未能及时修理的时候偷袭;也就是《墨子·鲁问》所谓“攻其邻国”的意思。这是大事件,但是也显而易见,然而人们看到之后并没有对这种行为作出批评。
但是,《吕览》第一段的批评奢靡误国,与第二段劫家虏货之“小”、袭而篡国之“大”有什么关连呢?且看《墨子·尚贤中》: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②(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二,31-32页。“已此故也”之“已”读作“以”。
意谓:王公大人想实行人才兴国的政策,却又背其道而去之,有其名无其实,授爵不授禄,以致贤人不至,小人秉国,造成国家破败、社稷倾覆。最后总结所以失国的原因:“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赏禄易见易为,其物为小;治乱难见难为,其物为大。然小、大虽别,道理则一,故有此论。可见这种论述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基础之一,也是《吕氏春秋·听言》想要表达的思想。
而最后《吕氏春秋·听言》将这种情况归结为“不知类”。“不知类”正是《听言》要批评的地方。什么是“类”呢?《墨子·公输》说:“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③同上卷十三,294页。“类”即事理,对于同类的事,应该有相同的判断标准,否则就是“不知类”;根据《公输》的意思,知道杀害一小部分人也是不对的,却认为杀害很多人是对的,叫做“不知类”。少、众亦即《鲁问》《尚贤中》的小、大,《听言》的家、国。知道劫家夺货的不对,却认为篡权夺国是对的,这是《听言》要批评的“不知类”。可见《听言》这里所说的类,方法上参照了《鲁问》《尚贤中》,概念上则参照了《公输》。而《听言》与《墨子》各篇不同的地方,更在于《墨子》是正叙其事,《听言》则换了种表达说“今人曰”,假设成是听话的人在考察别人的议论,进而判断说话者说话内容的善与不善。
此外,《吕氏春秋·达郁》还说:
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④(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二十,266页。
所要表达的意思,与《鲁问》《尚贤中》《公输》《听言》一样,是要对知细不知大的现象进行批评,并且也使用了“不知类”的概念。这里所讲的细功是镜子可以照出人的美丑,大功是士人可以照出君王的得失。但是立足点又与前四篇文章不同:“士可明己而人恶之”。要表达的是:豪士与忠臣的忠谏敢言,对于君主及其国政有疏通郁塞的作用。
四 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以上所论《语丛四》《庄子·胠箧》之钩、国,《盗跖》之小、大;《吕氏春秋·听言》之家、国,《达郁》之细、大,以及不知类,与《墨子·鲁问》、《尚贤中》、《公输》的“知小物不知大物”均有密切关联,而且《吕氏春秋》借用《墨子》而不借用《庄子》的痕迹清晰可见。而以今所见《墨子》材料,不独《鲁问》《尚贤中》《公输》有此论述,《非攻上》也是全篇用“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作非攻思想的推导:
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①(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81-82页。
攘人犬豕鸡豚虽然是小事,不过人们知道批评这是不道义的行为,亦即《鲁问》所谓的“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庄子》所谓的“窃钩诛”、“小盗拘”;攻打别的国家,侵占他国的土地,这是大事件,却不知道这是错的,反而赞誉战胜国的威武义举,亦即《鲁问》所谓的“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庄子》所谓的“窃国诸侯,仁义所存”。《非攻上》又接着说:“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正是墨子多篇文章一贯的推论方法:知小物不知大物。且由“今有人于此”起首的句子,论白、黑之辩,《鲁问》也是如此。不过这里的表达又不同:天下君子不知义与不义之辩。根据《非攻上》的表述,义为攻打他国的大事件,不义则是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实际上与大物、小物的辨析是一样的。
尚不止于此,《墨子·天志》上、中、下三篇,也是用“知小而不知大”的方法,来论证天志思想的存在。《天志上》是这样说的:
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②(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118-119页。
居家得罪了家长,居国得罪了国君,犹有邻居、邻国可以避难,而且亲戚、兄弟、朋友一定会告诫他不可以这样做。这是小而可以逃避之处,大家都知道不对。至于昊天之下,如有犯错,则明必见之,无可躲藏。这是大而无可逃避之处,比得罪家长、国君的事情更为严重,然而天下之君子却不知道互相儆戒,不可妄为。按照墨子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知小而不知大。此文与《天志下》首段的意思一样,而文字表达则详略有异。
《天志中》又说:
今有人于此,欢若爱其子,竭力单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③同上卷七,126页。
又见《鲁问》《非攻上》“今有人于此”、“君子明细不明大”的表达,而论证的例子却又不限于前几篇的窃犬彘、桃李、货财。细的方面是爱子没有报答慈父的恩惠,天下之君子会说他不仁不祥;大的方面是天兼爱天下,长养万物,受到惠泽的百姓唯独没有报答昊天的举动,天下君子却不知道批评这种行为是不仁不祥的。可见,墨子天志思想,也是以这种方法作为推导原理之一。而《吕氏春秋·达郁》所谓“细”、“大”,亦见于此。
《天志下》则又有不同的表达:
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
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自杀一不辜人者;逾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蚤累者;与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累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
……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有人于此,能少尝之甘谓甘,多尝谓苦,必曰吾口乱,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杀人,其国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因以为文义,此岂有异蕡黑白、甘苦之别者哉?①(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129-137页。“此蚤越”三字或有脱误。
杀一不辜之人、格人之子女,窃人之金玉蚤累、牛马、桃李瓜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王公大人知道这是不道义的,肯定会施予惩罚,就像《庄子》说的“窃钩诛”、“小盗者拘”。侵凌、攻伐、兼并,数千万倍于以上诸事,这是大事件,王公大人却自以为是合乎道义的事情,就像《庄子》说的“窃国诸侯,仁义所存”。这是因为他们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缘故。而且本文又有“今有人于此”、“明于小而不明于大”的用语,见于《鲁问》《非攻上》的黑白、甘苦之辩。可见《墨子》诸篇的表述虽然不同,所举的例子也不一样,但是,用来论证的方法还是一以贯之的。
由上所见,“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论,贯穿于《墨子》重要篇章《尚贤中》《非攻上》《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鲁问》《公输》之间,为墨子主要思想体系中关于尚贤、非攻、天志诸论的主要推导基础;据《天志中》“天兼天下而爱之”而言,应该还与“兼爱”思想存在某种关联。
而且各篇用于推导的例证多样,变化多端:《尚贤中》批评了治国不尚贤又想国家兴旺的谬误;《非攻上》指出知道惩罚偷窃桃李、犬豕鸡豚、马牛、衣裘、戈剑的人,却不知道侵略他国的不对;《天志上》表达了知道处家、处国不可得罪家长、国君,而不知道活在世上不可违逆天意;《天志中》论述了知道报答慈父而不知道报答昊天的不合理;《天志下》知道惩罚杀一不辜之人、格人之子女,窃人之金玉蚤累、牛马、桃李瓜姜的行为,却对侵凌、攻伐、兼并表示赞誉;《鲁问》也指出了君子知道窃一犬一彘的不义,却不知道窃一国一都的不义;《公输》也批评了义不杀少而杀众这种不知类的行为。此外又辅以黑白、甘苦之辩,使“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论,融贯于各篇之中,论证了非攻的合理,也使天志的存在得到了证明,从而为墨子思想体系的建构铸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 结 论
(1)计今所见“窃钩诛、窃邦侯”之论,流传于《墨子》之七篇、《庄子》之两篇、《吕氏春秋》之两篇、又出土文献《语丛四》一篇之中,共有十二篇先秦文献,故本文认为:“窃钩诛、窃邦侯”为先秦流行语。而饶先生谓“战国以来楚人流行之重言”,单表楚地,稍有偏差。
从今材料所见,郭店简《语丛四》第八、九简和《庄子·胠箧》、《盗跖》的表述,与《墨子·鲁问》诸篇的表述异曲同工,而《墨子》的时代更早、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已将《语》《庄》涵括在内;再就思想体系的连贯性、例证的多样性而言,《墨子》亦在《庄子》之上。《吕氏春秋·听言》、《达郁》两篇实际上杂糅了《墨子·鲁问》、《尚贤中》、《公输》、《天志中》的思想而成。学者说古书的相关内容很可能存在同一来源,本文认为:“窃钩诛、窃邦侯”的共同来源是《墨子》。
先秦显学首推孔墨,“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贯穿于《墨子》的七篇文章之中,融通有尚贤、非攻、天志等重要思想,这种论调应该是经过墨子大力宣扬后,为天下学者所共闻熟知,因此成为先秦流行语。而以后各家的著述,受到墨子的影响,化用墨子文章作为自己的论证方法的情况渐多,所以在多种文献中都有所表现(《庄子》的表述则为“窃钩诛、窃国侯”)。
(2)《庄子》的用语,与最相近的《鲁问》相比较,或者是与其它墨子各篇作比较,都显得更精警、更有穿透力。所以自从《庄子》的文章出来之后,更受其它诸子所喜用,欢迎度反在墨子之上。以致后人论及此语,都说是庄子的首创。而墨子当时艰辛开创与大力呼吁的功劳,反淹没而无闻于千古之后,岂不哀哉!幸好还可以通过《吕氏春秋·听言》、《达郁》追寻其话语来源。
(3)《语丛四》与《庄子》的关系,以今材料所见,未足以定是非。如不得已一定要做一些比较的话,窃以为前者抄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首先,《语丛四》的用语与《庄子》为近,而与《墨子·鲁问》为远;而且通观《墨子》各篇的用语,所窃者多,独未见“钩”;“不义”、“罚之”者多,独未见“诛”。而极有可能如陈伟先生所说的那样,前句抄自《胠箧》,后句抄自《盗跖》,而檃括之。再者,《语丛四》为格言性文字类编,若论精警与便于传诵,则《墨》《庄》二者首推《庄子》。而且,虽然《庄》《吕》有借用《墨子》思路的痕迹,却没有任何一处简单重复的地方;《庄》《吕》分别四次出现了这种表述,但都各有不同的倾向,就像《墨子》有七个地方出现过一样,表述也不尽相同。可见《庄》《吕》著述的用心,并不是随便借用那么简单。